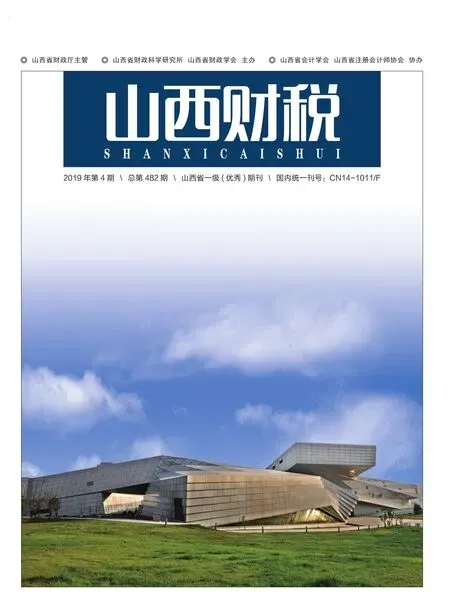偉大的作家也是偉大的思想家
□王 彬
我愛好文學,特別愛看小說,年輕時曾做過文學夢,后因忙于生計就很少看了,近幾年業余時間多了,又看了一些小說,如:卜伽丘的《十日談》、柳青的《創業史》、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張平新出的《重新生活》,同時也關注一些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但只知道它反映生活、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田等,并不大懂為什么這么吸引人,后來讀了一位名人的書后才明白,“世界上許多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思想家”。
由此我想到,文學史和文學理論闡述的,文學的思想性表現在多方面,有的表現在鮮明的政治性上。如《國際歌》是由作者歐仁·鮑狄埃1871年作詞,皮埃爾狄蓋特于1888年譜曲而成,歌曲熱情謳歌了巴黎公社戰士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英勇不屈的革命氣概,反映了自由與和平這個全人類共同向往的思想。從1923年6月20日在廣州東山恤孤院路后街31號中共三大會址響起,每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閉幕時和黨的重大活動結束時,都會演奏這首歌曲。這首深入我們心靈的歌曲,每每唱起都會讓我們熱血沸騰。再如,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時期,戰士們看到歌劇《白毛女》之后,在槍桿子上刻上了“為喜兒報仇”的誓言,英勇地投入了戰斗。土地改革中,廣大的貧雇農看到了《白毛女》,激起了對舊的社會制度的刻骨仇恨,提高了階級覺悟,有力地推動了土地革命運動的開展。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近年來紅色影視劇熱映,成為影視市場上的新風尚。電視劇《亮劍》自2005上映后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李云龍是該劇塑造出的經典形象,其政治可靠、敢想敢干、能打勝仗的“闖勁”和“干勁”,有魄力、有熱情、直來直去、敢于“亮劍”的個性為人們所喜歡,并希望現實生活中多一些“李云龍式的干部”。今年3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有一部《血戰湘江》放映后,學生們自發起立、默哀、鞠躬;戰士們激動地跑到臺上去,說“如果祖國有需要,馬上就去上戰場”,感人至深。
文學的思想性還表現在強烈的人民性上。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激勵了我們一代又一代青年,有的青年讀了該書后,以保爾·柯察金對照自己,從而激發起自我改造的愿望和決心。在工作和學習中碰到困難時,想起保爾·柯察金,就增添了勇氣和力量。再如,2017年電視劇《情滿四合院》講述了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間,北京四合院里的故事,傳遞了關于“孝”的文化和美德,罕見地引發了“全家追劇”。劇中的何雨柱是鋼鐵廠的廚師,為人善良仗義、熱情耿直卻口無遮攔,人稱“傻柱”,但看似不著調的“傻柱”,不僅在生活上資助他人,而且為孤寡老人送終,改革開放后還辦起了飯店,把四合院改建成了養老院,和鄰里家人幸福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我也曾感嘆“傻柱”的路為什么越走越寬,就在于他用真情踐行了我們主流價值觀,收獲的不只是精神道德,還有物質財富。
今年3月首播的電視劇《都挺好》引發全民熱議,該劇反映了表面上無限風光的蘇家,隨著蘇母的突然離世,瞬間分崩離析。意想不到的隱患層層顯露,圍繞毫無主見卻又自私、小氣的蘇父的安置和后續生活問題,打破了三家的平靜生活,最終蘇家人明白雖有血脈相連,但一家人彼此間的溝通也不能忽視,終于實現了親情回歸。該劇引發了我對正確處理家庭關系的思考,培養了我的家庭是非觀念,反映了我希望“家和萬事興”,同心創造屬于自己的家庭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文學作品并不是都能表現鮮明的思想性的。一些山水詩、風景畫,往往不直接體現思想傾向,但歌頌了祖國的壯麗河山、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同樣引人入勝、令人神往,為廣大讀者觀眾所喜愛,同樣具有人民性。比如,今年3月“兩會”期間央視新聞聯播播出的《大美中國》42秒各地短視頻,伴隨著《我愛你中國》的音樂,視頻以空中視角俯瞰了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立體化展示我國各地歷史人文景觀、自然地理風貌及經濟社會發展,全景式俯瞰一個觀眾既熟悉又新鮮的美麗中國、生態中國、文明中國,讓我不時產生無限向往。
再如,還有的文學作品的思想性不僅表現在文學價值上,而且表現出寶貴的史料價值。《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距今已有2500年,它反映了西周和東周奴隸制500年間社會各個方面,描述了復雜的社會生活,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揭露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同時還反映出我國奴隸時期西周和東周的歷史面貌和財政狀況,如《小雅·谷風·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描述了那時國家財政收支與國王私人的收支不分的社會現象。
文學作品的思想性是文學作品的“招牌”,無論哪種類型的思想性都是打動人、感染人的關鍵和靈魂,如今我們已進入新時代,更希望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創作出更多優秀作品,以啟迪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