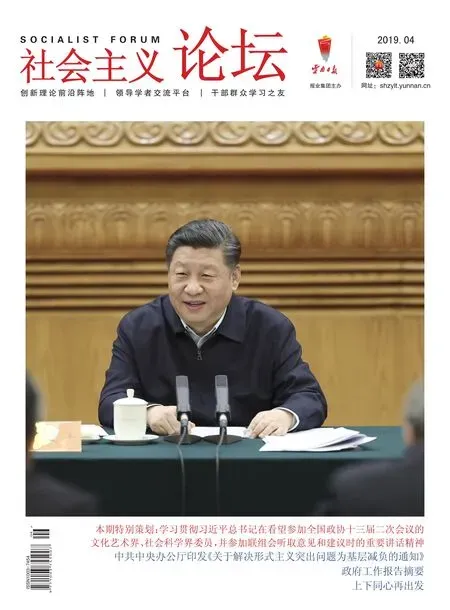深化云南少數民族藝術體系學術研究
文 毛祥麟 云南大學《思想戰線》編輯部
云南少數民族藝術體系的學術研究是云南學術領域的空白,同時也是世界藝術體系學術研究陌生且空白的領域。這一領域的研究是云南大學民族學學科的責任,需要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并把學術成果介紹到世界,形成影響廣泛的云南學術話語。
關于對民族藝術體系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民族藝術研究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闡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方式在社會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等方面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研究民族藝術體系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指引。
近代以來云南的學者,尤其是云南大學的歷史學家,以“巢乾”之精神,在民族學研究方面的貢獻已經記錄于史冊。相當一個時期,云南在民族學的研究,基本是在以政治史為主線的基礎上開展,其他領域則是在此基礎上把事件和經濟、文化的發展貫徹其間,似乎形成研究模式。但我們在研究中應該充分認識到,藝術體系是一個民族進化歷史中文化集中表現的類型,這是研究民族歷史文化建構的“存在”意識,這種“存在”和“人的本質”的關系,就是研究藝術的歷史唯物觀。因為藝術表現的核心就是民族個體的共同意識的反映。如,民族的舞蹈共同的特點就是反映他們的民族精神和審美特征;民族的音樂則是頑強地表現他們的語言語音特征和多彩的生活,并伴隨著自然形成的舞蹈形式;民族的戲劇則是伴隨著他們在舞蹈、歌謠的發展中“概括了社會歷史演進的基本形態”的表現,同時,也揭示了這個民族在綜合舞蹈、歌謠的基礎上的創造力;民族的美術(包括繪畫藝術、雕塑、工藝美術和建筑藝術)則是形象地反映了民族的不同情趣的美學的形象集成,也是該民族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的歷史記錄。這就是民族藝術的現實主義表現方式。正如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這封信中寫到:“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關于現實主義的“典型”理論,如果我們以民族的戲劇為例,把近代的戲劇體系和民族戲劇作比較,那么會在研究中找到“體驗”和“體現”的表演元素。綜合民族的藝術體系的表現,我們可以在研究中“論證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一些民族的舞蹈源于民族的祭祀傳統,是這個民族的生活氣息和風情的集中表現,這是他們美學觀的立體展現;民族的音樂是生活的詠嘆調,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融合其他民族的元素豐富本民族的旋律,不斷追求盡善盡美的表現;美術包括繪畫、雕塑、工藝美術和建筑藝術,這些藝術形式都具有本民族的美學意趣、內容和形式,是本民族地區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的反映,為本民族人民所喜聞樂見。民族的藝術體系是在本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的“典型”學說的反映,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至于在學術方面的研究還需要在“解釋”的前提下對整個學術體系作科學的探索。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學說,成為20世紀文化發展最有指導性的創作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文藝流派。今天,這一學說對我們探討藝術體系的學科建設仍有啟示意義。我們以“典型”學說來研究民族藝術,就要聯系民族的歷史、經濟和社會形態的發展軌跡,這樣才能全面地反映他們生活的生動性和豐富性,只有這樣才具有研究民族藝術的思想深度,這也是讓云南少數民族藝術體系學術研究走向世界舞臺的前提,也是我們的學術任務。
云南少數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性的文化精神和美學理想藝術元素:戲劇、舞蹈、音樂、美術等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就是已經形成并反映民族性格的藝術形式。云南民族藝術是世界文化陌生的角落,而這個角落閃耀的是這個民族的歷史演變智慧和力量:因為他們在頑強地表現本民族歲月風塵刻下的烙印,顯示自己在這個地球上存在的藝術魅力。
同時也要認識到,在云南少數民族藝術體系學術研究方面,對其價值的認識有時是不充分不全面的,甚至僅僅當作文化部門的“項目”,而沒有進入“學術”的范疇,在歷史學、民族學的研究強勢面前,它有被邊緣化的趨勢,這一現狀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否則對云南民族藝術的研究與建設,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就此論題,通過民族學的理念,進入建立“藝術體系”的學術規則,并再次強調:這是民族學的責任,我們沒有拒絕的理由,通過民族學的規則形成相應的制度和文化的責任,使“藝術體系”進人科研、教學一體化的學術視野。
回溯19世紀英國作家蘭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認識,就是學術研究的認識,他認為其戲劇僅有閱讀價值,與其姐姐一起編寫《莎士比亞故事集》,名聲大振。之后蘭姆又在研究戲劇與詩的學術思想的同時,著《莎士比亞同時代戲劇詩人之范作及注》,影響了英國詩壇。這是他在學術思想上擺脫理性主義、古典主義的創作約束,抒發個性和追求感情的另類學術觀的成就,這是當年在英國文壇的傳奇。又如,云南民歌《小河淌水》走向世界,是因為這支歌曲的音樂旋律有彝族、白族、漢族民歌的元素,是彌渡居住民族長期文化交融的音樂反映。著名的作曲家時樂蒙通過對彌渡各民族山歌和民族的學術研究,將其改編成美和浪漫相結合的管弦樂,登上世界音樂舞臺,轟動了西方——被譽為“東方小夜曲”;俄國芭蕾舞劇團曾經以《小河淌水》的旋律,編排過芭蕾舞劇演出。云南大山的《小河淌水》成為世界音樂傳奇,這是我們今天的民族學藝術研究領域值得思考的問題。這首歌曲是1947年由云南大學的學生尹宜公記錄、改編,并在云南大學不定期的音樂刊物《教學唱》刊登而傳唱,自此以后,這首歌曲多年以來被音樂理論家作為學術研究的課題而走向世界。
民族藝術體系研究的學術態度
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建立在這一民族共同生活習俗與文明規則的基礎上,也就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這種民族藝術的形成是他們的信仰確立的共同的記憶,在他們生活的社會中是共同倫理的表現形式。
云南多民族以不同的文化共同存在,這是形成云南各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各民族的文化呈現“同質化”,就不能稱之為云南民族文化,這是重要的定位和核心要素。云南民族文化的定義在對各民族文獻、歷史、語言以及田野調查(不能把田野調查理解為“口述”的記錄,那才是“跨出的一步”。“調查”包括研究學術的因素,那是能量的積蓄)的研究,是不能回避對民族藝術體系的學術研究。
在此不妨回顧云南大學戲劇學研究的一段歷史:20世紀四五十年代,云南大學的戲劇學研究在全國高校位居翹楚。20世40年代云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徐嘉瑞先生,于1948從湖南大學聘來的趙景深的得意門生葉德均先生,奠定了云南大學戲劇學的“霸主”地位。徐嘉瑞先生的《云南農村戲曲史》《金元戲曲方言考》等著作,葉德均先生的《曲品考》《曲目鉤沉錄》《元代曲家同姓名考》《宋元明講唱文學》等戲曲史研究,都位于當時中國高校戲劇研究的前沿,名震教壇,享譽中國學術界。他們在課堂以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的“在實踐中學習”和“在戲劇實踐中學習”兩個教育理念,通過戲劇的教育魅力,運用戲劇體系的文學元素滲透在戲劇文學的課堂,讓學生認識人生“大舞臺”,從戲劇文學的情境中感悟生活、人生和文學的關系,在生活的“大舞臺”中找到人生的角色定位,從而面對將來人生的挑戰。《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推進素質教育是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題,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時代要求。”其中提出“開放特色課程”,而戲劇教學就被認為是培養學生全面素質的最好的教學手段之一。這也是徐、葉兩位先生早就實踐的教學手段。
在云南民族學研究領域,如果回避或放棄云南少數民族藝術體系學術研究的空間領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解釋云南研究民族學的深度。云南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藝術有不同的概念,研究必須遵照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研究規律,要從“人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的歷史觀切入。“只要知道某一民族使用什么金屬——金、銅、銀或鐵——制造自己的武器、用具或鐵——制造自己的武器,就可以臆斷地確定它的文化水平。”這一理論對民族藝術研究也是對的。我們進入民族的藝術領域,一定會在民族藝術的寶庫發掘民族學的“文化”研究課題的深層次思想,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性,并從這個“經典”發現民族學在民族藝術體系的研究中去解讀“文化”的概念,會再一次找到研究的空間,這就是直覺和理性的相通。建立民族藝術體系的課題的前提,我們必須認識馬克思在探索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的學術態度,繼承馬克思“做學問”的科學精神,發揚獨立思考的精神。
云南民族藝術體系的研究基礎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并以不斷研究、不斷完善、不斷追求的科學態度在研究過程中不拘于傳統而有所創造,有所發展。云南少數民族藝術體系學術研究不僅是云南大學民族學的責任,而且是我們不可推卸、必須承擔的沉甸甸的擔子。民族藝術是在本民族生存的共同體過程中形成,這就需要聯系本民族的歷史中首先書寫藝術的分類(指戲劇、舞蹈、音樂、美術等)歷史,從歷史中研究藝術體系的個性(指不同藝術類型的藝術性),從而在此基礎上涉及表演學、舞臺學、化妝學、美術流派等的藝術特性,從而在美學、哲學的領域進行學術闡述。與此同時,對研究的學術成果必須做好對外翻譯工作,把學術論文推向世界的學術期刊,這是民族藝術體系的學術研究必不可少的過程,從而讓世界了解云南民族藝術體系研究這塊在世界學術舞臺尚未開墾的處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