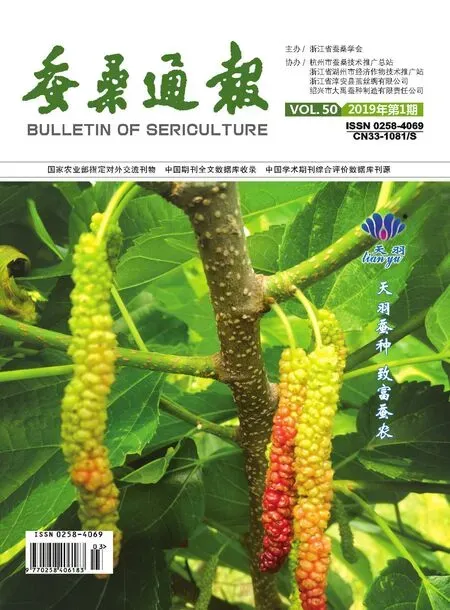隋、唐、五代時期的蠶業
蔣猷龍
第一節 隋代的蠶業
隋自公元581年代北周以后,至公元589年中定南朝的陳,南北對峙的局面遂以結束,中國又取得了統一。
隋文帝在統一全國后,實行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使連續三百年的戰爭得以停止,民眾得以休息,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在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間(581~604),“平徭賦,倉稟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人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間宴如也”,與隋朝以前的漫長歲月戰亂紛呈的情景相比,形成鮮明對照。
隋代重視發展農業,其中包括蠶桑,統治者每年行“祭先農蠶、親耕桑之禮”,從農民種桑養蠶繅絲中所得的勞動果實,以“調”的形式征為己用。
對農民征調農產品,包括糧、綿、絲、麻,建立在均田的基礎上。為了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保證農產品的征收。文帝在奪取了北周政權以后,首先就頒布了新令實行均田,“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①《隋書》“高祖紀下”。受田的辦法是:“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后齊之制,并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田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②《隋書》“食貨志”對一般農民授予永業田和露田。按北齊的辦法,即一個丁男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另每丁又給永業田二十畝,所以一夫一婦之家共可受用一百四十畝。永業田為桑田或麻田,露田以外的田可以買賣。雖是推行均田,絕不是將所有的土地都拿來進行還受分配,也不是所有的農民都可以得到土地或得到應分的土地,受田不足的情況很普遍。
農民所要負責的租、調、力役標準是:“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仆隸各半之”③《隨書》“食貨志”。這個賦役標準,較北齊、北周的“絹一匹,綿八兩”有所減輕,且隋時有時對租調力役也作出適當的改變或減免,如開皇三年(583)“減調絹一匹為二丈”,這樣的租調標準,并不是很高的,頗得農民的擁護,不少荒地得以墾辟,人民生活安定,對恢復和發展業起到一定的作用,蠶業也有所發展。故在開皇年間(581-600),“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國家積累大量的物資,文帝在滅陳以前,“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及至滅陳(589)以后,每年賞功賜臣所用的綢絹達“數百萬段”,而還是“庫藏皆滿”,不得不建造左藏院來堆放,還是無處存放,就在公元592年下詔說:“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隋煬帝即位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④《隋書》“食貨志”。當時蠶絲生產極為興盛,河北的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襄國一帶的農民,“其俗務在農桑”,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山東的一帶農民也“多務農桑”,梁部則更以綾錦聞名⑤《隋書》“地理志”。江浙贛一帶(揚部)“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其俗頗同豫章”,而“豫章之俗頗同吳中,……一年蠶四、五熟,勤于紡績”⑥《隋書》“地理志;《資治通鑒》卷177“隋記”
隋代曾是一個富饒的朝代,這種富饒的根源,就是黃河和長河兩大流域的統一,經濟和文化比起秦漢以至南北朝來,有很大的發展,但文帝傳到煬帝——歷史上少有的奢移皇帝,民眾辛勤地積累起來的財富迫不及待地消耗盡了,加以連年出兵遠征,死者十之八九“桑農咸廢”,百姓“始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以至于亡。
第二節 唐代的蠶業
唐代前期,社會得以保持較長時間的安寧狀態,勞動民眾得以逐漸恢復和發展生產,補救前代破壞的創傷,并主要表現農業生產上,這就為唐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至唐代中期,藩鎮叛亂,戰爭連年不息,黃河流域遭受戰禍;而長江流域則保持相對的穩定,工商業業發達,為朝廷支付巨大的財政費用;提供了經濟來源。國際問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為祖國贏得崇高的聲望。國內經濟、文化也在發展。正由于統治階級的大量消費,在商業興盛的同時,農民遭受的剝削日趨嚴重,農業不斷衰落,待至唐代末年,朝廷內部分裂愈烈,長江流域發生割據戰爭,統治力量大為削弱,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死亡。
隋末戰亂之后,“百姓離殘,弊于兵甲,田畝荒廢、饉飢薦臻”⑦《全唐文》卷2“高祖勸農詔”,唐初人口,“比于隋時,才十分之一”⑧《舊唐書》“高昌傳”。唐高祖(618-626)在“申禁差抖詔”中說“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修產業”,使百姓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在勸課農桑,招徠難民號召下,武德七年(624)頒布了均田令,一部分農民獲得了土地,并為政府收取賦稅固定了來源。
均田的一般標準是:“丁男、中男以一頃,老男、篤疾、廢疾以四十畝、寡妻妾以三十畝,若為戶者,則減丁之半。凡田分為二等:一曰永業、二曰口吩。丁之田二分永業,八分為口分。”⑨《唐大典》卷3“戶部尚書”人無,永業田得由繼承人接受,口分田歸官另行分配。按照北朝以來的制度,永業田種桑或麻,解決衣的總是,口分田種糧食,解決吃的問題。
勞動民眾經營了這些土地以后,負擔的賦役“有四:一日租、二日調、三日役、四日雜徭。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一作二匹),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凡丁歲役二旬,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
由于唐代可以繳納絹布等實物來代替力役,這叫做庸,所以通稱唐朝的賦役辦法為“租庸調法”。當時江南的辦法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綢綾絹供春綵”⑩《新唐書》“食貨志”,這種租庸調法,并按年成的好壞規定減免的辦法,“凡水旱蟲霜為災害,則有分數。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若已役、已輸者,聽免其來年年”?《新唐書》“食貨志”。
唐代以人口為收稅的單位,對蠶絲來說,每個“丁”(21歲以上至59歲)負擔的稅額是:
調:蠶鄉輸絹二匹,綾、絁各二丈,外加絲綿三兩;
庸:每年勞役二十日,不勞役時,統治者收取代價每天絹三尺,共六丈。但也可以因國家多事要延長勞役時間,如超過十五日,則免收調絹。
在天寶年間(741~756),統治階級的收入統計,每年“課丁八百二十余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余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余萬匹(每丁計兩匹,按此均將力役交絹布計算),綿則百八十五余萬屯(六兩為屯)……,大凡都計租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得五千二百二十余萬端、匹、屯、貫、石”?杜佑《通典》卷6“賦和丁”,絹綿在國家財政總收入中占六分之一強。
根據《唐六典》、《元和郡縣志》、《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唐代各地貢獻絲織品的情況如表1。
農民交納的絹綿是靠自己養蠶織綢而來的,養蠶靠桑田,桑田就是每丁所受的二十畝永業田(非蠶區,這二十畝永業田種麻,統治者則收布)。這桑田可以子孫繼承,也可買賣,并不因年老而分出,這對多年生的桑樹管理是有利的,對促進蠶業的發展有作用,“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630)斗米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陸龜蒙《甫里先生集》卷9,表現出國泰民安,繁榮富強的景象。農村忙著蠶事,正是“四鄰多是老農家,百樹維桑半頃麻,盡趁晴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繅車”?《唐書》“食貨志”的情景。
本來,均田制是統治者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保證征收賦稅的一種手段,唐初時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僅在不觸動地主利益的情況下,把一些熟地或荒地給民眾墾種,得不到土地的人,仍只好自己覓地,統治者對這些人說淡不上均田,但他們也要負擔租庸調,更在官僚、豪商、地主三位一體的強行霸占侵奪下,土地兼并,以致“制度弛紊,疆理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陸贄《墮宣公奏議》卷四“均節賦稅恤百姓”。所以到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均田制的作用已經消失。農民既然失去田地,不得不大批逃亡,轉成為私人地主的莊客佃戶,因此,到唐高宗時“一夫之耕才兼數口,一婦之織不瞻一家;賦調所資,軍國之息,煩徭細役,并出其中”?《唐會要》卷83“租稅上”。官家逼租、索絲的慘景歷歷寸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tiao)新谷”?聶夷中詩《傷田家》;“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柳宗元詩《田家詩》,都是當時蠶絲生產的現實寫照。武后時,逃戶問題嚴重起來,雖然他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到要“勸農桑,薄賦徭”,但農民已失去了立足之地,民眾根本無法負擔租庸調的苛刻剝削,生產不能發展,統治階級的賦稅收入也頓形枯竭,特別是“安史之亂”?公元755-763年,唐朝大軍閥安祿山和史思明為爭奪政權而發動的一次叛亂以后,均田制破壞,與之相適應的租庸調法根本不可能執行,“農桑廢于征呼,膏血竭于笞捶”。就在建中元年(780)由揚炎的建議改行兩稅法,即以戶為納稅的單位,全年交夏稅和秋稅(一說為戶稅和地稅)。兩稅的弊端是“定稅之初,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折價不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陸贄《陸宣公全集》卷2政府這種給錢少而輸絹多的辦法,比商人納剝削更苛重。農產品剛剛收獲,“絲不容織,粟不容舂”,通過高利貸商人立即轉入官府,農民困景到達頂點,“典桑賣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白居易詩《杜陵叟詩》,真實地描寫了當時杜陵叟老實一家的情景。
兩稅法非但不能促進蠶絲業的發展,僅是中飽豪富,引起朝野人的反對。當時統治階級對農民栽桑不限于永業田,而要求每畝田種桑兩株?《唐書》“憲宗本紀”,以便征收絹綿,并限令不得砍桑作柴薪?《舊唐書》“武帝本紀”,可見到唐末,農村的蠶業基礎已破壞殆盡了。
唐代的蠶業地區,以各地的貢賦中可以了解到約有一百多州郡,幾乎遍及全國的十道,西部的陜西,甘肅和黃河東的山西,只有個別的州郡略有蠶桑生產,但據天寶十二年(753)記載“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似乎西北的蠶桑也已可觀了,又把桑和蠶種傳播到新疆,從近代發掘新疆的地下文物證明新疆在唐代生產蠶絲已有一定比重。
蠶絲生產較普遍的是華北大平原和河南一帶,四川也相當發達,南方的江南道產絲絹己占全國的五分之一,但都密集在江蘇、浙江和福建,其余還只是另星生產,浙江在唐初有意識地迎娶北方繅絲婦女成家,傳授技術,在開元至貞觀的一百年間,絲織技術進步很快,越州(包括會稽、山陰、諸暨、蕭山、剡縣、上虞)相當于現代錢唐江南岸紹興地區一帶,已成為南方的絲織中心?《新唐書》“地理志”,“安史之亂”以后杭州也開始繁榮起來,除臺州外、湖州、杭州、睦州、婺州、衢州、處州、溫州和明州都有絲和綿的生產,德宗時(780-805)“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賴焉”?《舊唐書》卷129“韓晃傳”,南方絲織乃開始超駕北方;淮南地區在唐的后期也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的一部分。總之,在唐代,江南蠶絲業發展很快,“曠土盡辟,桑柘滿野”,“絲綿布帛之繞,覆被天下”(沈約語)。
在西南地區,云南自古飼養一種拓蠶并利用其絲繭,技藝則另一體系,“蠻地無桑,悉養柘蠶,繞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干數丈。三月初蠶已生,三月中蠶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為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為常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為衣服;其絹極粗,原細入色,制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樊綽《蠻書》卷7。,同上書中記載著:“(鳥蠻)婦人以黑繒為衣,其長曳地”,“(施蠻)男以繒布為縵襠褲”,“(粟栗兩姓蠻)丈夫、婦人以黑繒為衣,其長曳(ye)地,又東有白蠻,丈夫、婦女,以白繒為衣,下不過膝”,”南詔以紅綾,其余向下皆以皂綾絹”,“貴緋紫兩色。得紫后,有大功,則得錦”。“婦人一切不施粉黛,貴者以綾錦為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為飾”,可見當地產絲甚多民眾在唐代就以絲綢為常服了。
唐代后期與當時的南詔交往很頻繁,許多工巧將絲織技術轉入云南,大和三年(829)南詔人至成都掠去當地子女工技數萬,所詔“驅盡江頭濯錦娘”?徐凝蠻詩:《入酬后詩》。,這也是使云南絲織技術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西藏地區也因文成公主出嫁時(641)帶去蠶種和工匠,借以發展蠶絲業,并從此更加強了漢藏兩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
唐代,絲綢和綿不僅作服飾的主要原料之一,且由于絲綢等可以代替勞役,在兩稅制實行后又可代替錢幣,因此,在市場上流通甚多,勞動民眾除把應繳的絲綢部分上繳外,還把多余的在市場上換取生活用品。農村除生產普通的織物外,還在發展傳統技術的基礎上,生產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品。統治階段為了特種需要,限令農民或招收官奴生產高貴的織物以供揮霍。織工技藝在這一時期中,有了出色的造詣,絲綢紋樣講究造型的完美、寫實和精神的刻劃,并能正確地掌握形象,達到雍容美麗的程度,其價值真要“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杜甫詩:《白絲行》。。
政府對各地絲織品按傳統貨量嚴格地分成等級。“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絹分八等”?《唐六典》卷2”少府寺”。。產絹地區和等級為:
一等:宋、毫;
二等:鄭、汴、曹、懷;
三等:滑、衛、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兗、貝、博;
四等:滄、瀛、齊、許、豫、仙、埭、鄆、深、莫、洛、邢、恒、定、趙:
五等:穎、淄、青、沂、密、壽、幽、易、申、光、安、唐、隨、黃;
六等:益、彭、蜀、梓、漢、劍、遂、簡、綿、襄、褒、鄧;
七等:資、眉、邛、雅、嘉、陵、閬、普、壁、集、龍、果、涇、渠;
八等:通、巴、蓬、金、均、開、合、興、利、泉、閩。
中唐開元以來,國內商業已蓬勃向前發展。商業性質,從偶然交換或特產品的販賣發展到固定的城市商業,有常設的市肆和店鋪,有專門從事商業供應的行幫如絹行和織經錦行,甚至農村中還有定期的集市如蠶市(《茅亭客話》春9)。
貿易的媒介,從銅錢和布帛雜用向金屬貨幣過渡,主要通行東羅馬金幣、波斯銀幣和日本銀幣。
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和兩稅法的建立,絲綢商人乘機興起,“自初定兩稅,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俞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后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新唐書》“會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