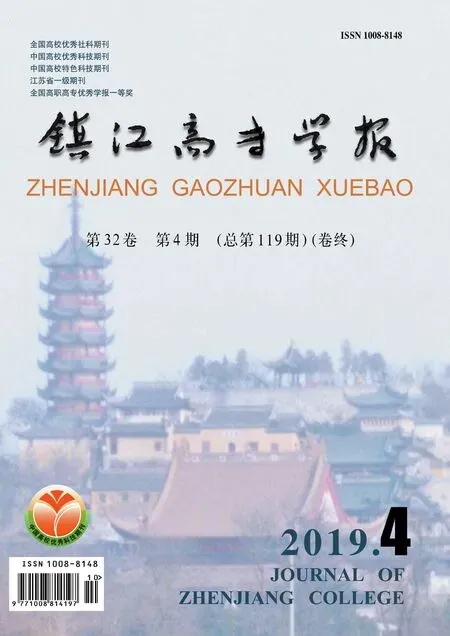方玉潤《詩經原始》原型闡釋研究
方 新
(安徽黃梅戲藝術職業學院 基礎部,安徽 安慶 246000)
《詩經》闡釋史呈現經學和文學兩條路徑。受封建時代整體話語環境的影響,經學式的闡釋成為主流,尤其是漢代以降,宣揚“溫柔敦厚”的詩教觀,闡釋者們往往著重宣揚《詩經》所蘊含的政治美刺功用。清代盛行考據之風,以乾嘉諸子為代表的學者在解讀《詩經》時極盡訓詁考證之能事,過度闡釋文本,讓詩美無存。方玉潤(1811—1883年)立足文本,以審美的眼光觀照,以詩性的視野求索,發掘《詩經》的深刻意蘊,揭示其在文學史上的原型意義,具有革新價值。
《詩經原始》的品評文字新見疊出。方玉潤跳出前人繩墨規矩進行闡釋,開一代詩經闡釋的新風氣。方玉潤重回詩美的解讀路徑,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品讀章法煉字”[1]、“重塑詩情意境”[2]和揭示原型意義。筆者已撰文論述前兩個方面,這里專以原型揭示為題,指出其對詩意的發明創見之處和垂范后世的價值。
對《詩經》原型意義的揭示,姚際恒之前已有一定論述。姚際恒評價《鄘風·君子偕老》篇:“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感嘆作品充滿神韻風采,好像是天神仙女降臨人間。他認為這篇作品能很好地傳神達意,意境天成,“遂為《神女》《感甄》之濫觴”[3]100。姚際恒明確指出《詩經》作品的示范意義,也初步闡釋了《詩經》的原型價值。其后,方玉潤從題材意象、藝術技法、詩體風格三方面分析《詩經》原型價值,得出“三百所以為詩家鼻祖”[4]421的結論,進一步拓展了《詩經》文學解讀的領域。
1 題材意象的原型揭示
《詩經》在漢初被尊為“經”,對中國詩歌的影響深遠。方玉潤注意到詩經的題材意象對后世詩歌創作的影響,并結合具體作品進行了分析。方玉潤評論《衛風·伯兮》“宛然閨閣中語,漢魏詩多襲此調”[4]186,意即詩作以女性口吻的筆法創作香奩題材作品。漢魏時期樂府詩頗多此類綺艷題材。方玉潤評《周南·桃夭》“艷絕,開千古辭賦香奩之祖”[4]324,認為開啟后世女性青春情愛寫作之先河。確乎以桃花和美人作比,便有崔護無限悵惘之“人面桃花”,有李香君千古一嘆之《桃花扇》,有曹植明艷清麗之“容華若桃李”。
再看其解《秦風·渭陽》。《毛詩正義》《詩集傳》等對此僅進行字句梳理,鮮有論及作品藝術風貌。姚際恒關注到詩蘊情感,褒獎其“悱惻動人”[3]99。方玉潤視野更顯開闊,其解讀集中于三點: 1) 詩筆干凈凝練,詩風簡樸動人,方玉潤評曰“詩格老當”,認為反復涵泳,可體味詩體“情致纏綿”的藝術成就。2) 詩中深情皆觸景而生,相離之時,無以排解,唯以河水寄托,以物品相贈,“令人想見攜手河梁時也”。3) 這首詩作體例成熟,方玉潤定位其“為后世送別之祖”[4]333。這三點確立了《渭陽》“送別詩”題材的原型意義,展現了方氏的詩性眼光和豐厚學養。且看后世送別,有白居易《南浦別》之“南浦凄凄別,西風裊裊秋”,有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之“荊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有嚴維《丹陽送韋參軍》之“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等。“悠悠”之意從未缺席,由悠悠水流引出迢迢前路、搖搖舟楫、招招樓簾、漂漂浮萍、澆澆酒水、裊裊西風等諸多意象。以流水喻別意,至太白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可謂一總結矣。至于離別以物品相贈,后世詩中有折柳、聞笛、賦月、寄梅,抒發別情不一而足。
方玉潤《詩經原始》對《詩經》題材原型的揭示,還表現在題材的分類分析方面。方玉潤指出,《鄭風·溱洧》詩風樸素,濃厚的抒情筆法寫出了青年男女互表愛慕的場面。古代所稱“情詩”往往以游子、思婦為主人公,這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艷詩”,在成篇于東周之前的《鄭風·溱洧》后,“艷詩”寫作出現了很長時間的空白。直到唐宋(如元稹、陸游等)才出現“艷情詩”創作的高峰。可見,在向來重視“詩言志”的中國詩歌史中,《鄭風·溱洧》詩體開拓“別為一種”,稱為“冶游艷詩之祖”頗為恰當。不僅如此,《詩經原始》中已分田園、冶游、送別等題材類別進行闡釋,并結合后世題材來揭示原型的意義。如對于《魯頌·閟宮》的解讀,朱晦庵評為“千乘、大國之賦也”[5]241,注意到宏大鋪陳的結構、夸張熾烈的語言共同產生的詩作氣勢。姚際恒評為“序事近冗,而辭亦趨美熟一路”[3]214,指出詩篇冗長,稍顯繁瑣,用筆“美熟”,即美艷老到。方玉潤評為“開后世辭賦家虛夸之漸”[4]639,認為既為辭賦的先聲,又是虛夸文風的前導,“早開西漢揚、馬先聲”[4]639-640。此評突出其賦化特征,認為此詩開啟了楊雄、枚乘、司馬相如在題材上以宮廷臺榭、羽獵四方、祭祀封禪、樂舞相和的書寫,并引領了以極盡炫耀、鋪張揚厲為能事的賦化方式。
2 藝術技法的原型揭示
藝術技法是在不斷繼承發展中形成。《詩經原始》要揭示題材層面的原型意義,需分析不同題材的創作技法,在這方面,方玉潤創獲頗多。如其論《鄭風·大叔于田》:“描摹工艷,鋪張亦復淋漓,便為《長楊》《羽獵》之祖。”[4]207認為后來的漢大賦在“描摹”與“鋪張”這些創作技法方面對此進行了繼承。
方玉潤揭示《鄘風·桑中》一詩在藝術技法上的原型意義尤為精彩。歷代評述此“濮上之音”,皆認為是譏刺當時衛國宮闈淫亂,在位世族公卿“相竊妻妾”,指出《鄘風·桑中》意在“刺奔戒淫”。方玉潤解法獨到。方玉潤從文意指出,詩中所采谷物不同(唐、麥、葑),所會之地不同(鄉、北、東),所約之人不同(孟姜、孟弋、孟庸),然而卻都“期”之于桑中,“要”(邀)之于上宮,“送”之于淇上,若依據前人解此詩為“自詠其事”,那么言下之意,“豈一人一時所期,而三地三人同會于此乎?”[4]161方玉潤認為太過于“巧且奇”,顯然于理不通。方玉潤的解讀可歸納為四點: 1) 賦詩者并非“詩中之人”,詩中事也并非“賦詩人之事”,只是“代為之辭耳”;后世所謂“代言體”詩作由此萌芽,越秦漢魏晉,至“三曹七子”時,已有大量“代言”詩作出現,如曹丕的《猛虎行》與《代劉勛妻王氏雜詩》、曹植的《浮萍篇》與《棄婦詩》等,再至《古詩十九首》已呈成熟態勢。2) 詩中人并非“真有其人”,詩中事并非“真有其事”,而是出于詩人“虛想”,延展而言。以這兩點附評三國曹植之《洛神賦》,若合一契矣。3) 結合這種“猜疑莫定、若遠若近”的詩作技法,方玉潤解讀李商隱“無題詩”,挖掘出詩中交織的迷惘、幻滅、希望、絕望、茫然等情緒,明確其幽微深邃、百回千轉、細膩深思的藝術特色。4) 基于歷史的眼光,勾畫出原型意義,文本的藝術價值被有效放大,進而方玉潤提出“音由心生,詩隨時變”[4]161,前人的詩旨爭論便沒必要了。上述四點層層推進,表現出方玉潤寬闊的歷史視野和敏銳的審美感覺。
再如解《陳風·月出》。受到姚際恒的啟發,方玉潤注意到此詩在技法上的特色,他指出詩中“皎、皓、照、僚、懰、燎、窈、憂、夭、糾、受、紹、悄、慅、慘”等韻腳用字以險,似“方言之聱牙”,認為此詩“尤妙在三章一韻”[4]289。結合此評,我們看到,作為“風詩”,它本應具有民歌意味,朗朗上口,清新自然,這里險韻之多,顯然出于刻意改造。結合此處一韻到底、不惜運用險韻的特點來進行分析,后世詩作如《洛神賦》《李憑箜篌引》《高軒過》《神弦》《野歌》等,在意境和用韻上確有源出《月出》的意味。應當看到,險韻詩作的初步形成是在南北朝,并經由唐宋杜甫、韓愈、孟郊、元稹、白居易、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王安石等人臻于成熟,表現出“因難見巧”[6]197的藝術手法。
3 詩體風格的原型揭示
《陳風·月出》是首男女歌辭,其“對筆”寫法讓詩意頓生活潑,中間轉換若干字詞,讓懷人幽思之情逐步深入。方玉潤提出:“至其用字聱牙,句句用韻,已開晉唐幽峭一派。”[4]290方玉潤注意到《月出》一韻到底、運用險字的手法,并總結其在風格上引領了晉唐以來幽峭奇艷的詩風。
再如《邶風·谷風》一詩,歷來解讀者眾多,但都是圍繞詩歌主題進行分析,探討“婦人為夫所棄”背后的道德警示意義。方玉潤卻指出其與漢魏詩風的淵源。他說詩中所寫棄婦“必有一番怨抑難于顯訴”[4]136,但作者并不是單純地描寫棄婦,而是借此抒發“忠臣義士”在遭到貶斥或讒譏后的“無罪見逐之狀”。方玉潤認為,此詩細節較多,用語頗顯繁瑣,在看似平和淺露的行文中,表現出憤憤不平和良多屈辱的情感。他總結此詩風格:“雖卑詞絮語中,時露忠貞郁勃氣。”[4]136方玉潤認為“漢魏以降,此種尤多”[4]136。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漢末魏晉以來,諸多文學作品風格上表現出驚人的神似,如曹植之《浮萍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漢樂府之《孔雀東南飛》“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古詩十九首》之《冉冉孤生竹》“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這些作品起句皆出以“興筆”,主題表達“棄婦之怨”,行文之中蘊藏憂郁傷懷與忿怨之氣。由此可見方玉潤眼光獨特深邃,解讀作品視野開闊。
在詩歌風格評論方面,方玉潤常以“調”代指詩歌風格。方玉潤稱《邶風·谷風》具有“忠貞郁勃氣”之“調”。在梁代蕭子顯所著《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忠貞郁勃氣”的風格即所謂“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魄……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7]90(明朝王世貞著《藝苑卮言》中亦引用蕭子顯此論)。方玉潤此處的“調”是指《邶風·谷風》呈現出一種突兀硬直的風格,體現出方玉潤對于作品風格的思考和詩歌風格史的把握。方玉潤認為《衛風·伯兮》詩歌風格與《邶風·谷風》相類:“宛然閨閣中語,漢魏詩多襲此調。”《衛風·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從題材方面而言,此詩出以閨閣思婦語;從技法言,此詩出以白描筆法。對題材技法的學習和延伸,漢魏作品有常見詩句。“膏沐誰為容,明鏡暗不治”;“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相去日已遠,衣帶漸已緩”等。從詩歌風格角度考察可以看到,《邶風·谷風》質地簡樸,情感真摯,抒情直露,有所興寄。可以說,此詩成為“思婦詩”的原型,奠定了該類詩在意象塑造、抒情方式、藝術風貌上的基調。
要之,方玉潤《詩經原始》從文本審美出發,有意排除“經學式”注解詩歌的干擾,避免過度解讀“碎義難逃”[4]414的缺憾,用寬廣的歷史眼光和卓越的審美眼光,從題材意象、藝術技法、詩體風格三個方面,揭示出《詩經》對后世詩歌的原型意義和價值。方玉潤吸收了孔穎達、朱熹、姚際恒等人的學術觀點,從藝術角度開拓了《詩經》的批評,使《詩經原始》成為立足文學立場解詩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