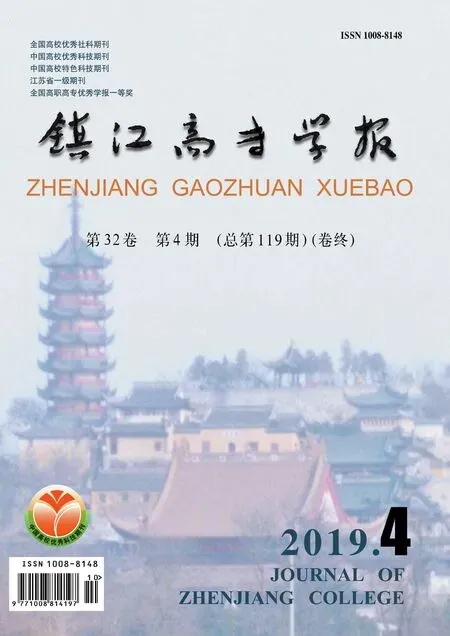失望與希望的輪回
——賽珍珠《母親》中強迫性反復心理意象探究
雷喻婷,周衛京
(揚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揚州 225100)
賽珍珠(Pearl S. Buck)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女性作家[1]53。她在中國生活了近40年,對中國農民的苦難充滿同情,也深深敬佩中國人民堅韌不屈的品質。作為一名女性作家,賽珍珠對父權文化下的婦女命運始終保持敏感[2]135。《母親》一書雖然并非是賽珍珠最為出名的作品,但卻是公認的一部出色的小說。朱磊指出《母親》反映了舊中國婦女的命運[3]。《母親》中的主人公一直遭遇苦難,卻從未被苦難打倒。強迫性反復心理在“母親”一生中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
1920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首次提出“強迫性反復”這一概念。在弗洛伊德的臨床研究中,他的病人會重復敘述一件曾經令自己痛苦的事情,特別是病人在幼年時曾經歷過的一些痛苦或遺憾,病人在成人后會將其投射到類似的其他人或事物之上,以期彌補曾經的痛苦或戰勝曾經的失敗。徐其萍指出,創傷事件在重復中才有被創傷主體“同化”的可能,“同化”蘊含著治愈創傷的希望,但也可能等同于再創傷的過程[4]。
《母親》一書通過多種意象(如“子嗣”“眼藥”“首飾”“藍色”“大紅袍”等)表現主人公的強迫性反復心理。該心理不斷給人以希望,又讓人失去希望,失去希望激發個體下一次戰勝失敗的信心,從而推動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
1 子嗣:母性與社會認同的體現
無論是傳統西方價值觀還是傳統東方價值觀中,對子嗣傳承的重視與重男輕女的觀念都有著驚人的相似。生育子嗣不僅是女性的本能,而且是女性獲得社會認可的重要途徑。小說中的“母親”是一個有著“強烈母性的女人”[5]104,“凡是天真、親情而感性的事物,都能牽動‘母親’的心”[5]76。以多子為榮的傳統家庭觀以及對孩子的渴望與遺憾,使“母親”產生了與之相關的強迫性反復心理。
婚后的“母親”有一位孩子氣十足的丈夫,有一位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的婆婆,有3個孩子,這些人都需要她的照顧,甚至稻場拴著的水牛、家里的狗和床底下的雞都需要她一一照應。生活的辛勞沒有讓“母親”對貧窮的命運低頭,相反,村里人對她的贊美和擁有許多“孩子”的幸福使得“母親”對生活充滿了希望。“母親”在農作時失去過一個孩子,她常想“那一個如果不是因小產死了,現在也一定會是一個可愛的、快學會走路的男孩了”[5]7。這一次創傷加強了母親修復“失去孩子的遺憾”的愿望,她對子嗣的強迫性反復心理、自身具有的健壯身體以及繁忙的農作使得她很快振作起來,并從來年就懷上的小兒子身上找回了希望。
然而,男人的出走,使得“母親”陷入了無盡的痛苦與悲傷。這個事件,不僅使得“母親”失去了一個“孩子”(文中的丈夫生得年輕漂亮,卻像小孩子般任性,文中多處以“孩子氣”“任性”“賭氣”描寫這位不負責任的男人),更讓“母親”失去了再生育的資格。至此之后,常年的壓抑與痛苦,使得“母親”不得不通過其他途徑來重現“丈夫尚在的情景”以及修復“失去孕育子嗣權利”的創傷。在這種強迫性反復心理影響下,“母親”明知與管事私通是有違天道之事,但仍舊做了。“母親”為了能與管事重組家庭,恢復自己孕育子嗣的權利,不惜謊稱丈夫死在了異鄉。然而管事最終無情地拋棄了她,“母親”只得偷偷打掉懷上的孩子。
自此之后,“母親”轉而將修復創傷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小兒子像他父親一樣漂亮,健壯得像小公雞一樣,“母親”非常疼愛他,她通過各種理由企圖將小兒子留在身邊,來彌補丈夫出走帶給她的傷害與遺憾。然而,悲劇命運再一次重演,小兒子最后一次連夜將一包東西藏在家中后,便再也沒能回過家,母親內心中最恐懼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母親”一生都在追求子嗣繁榮,她失去又得到,又再次失去。無論是瞎子女兒嫁進荒山,還是小兒子被人當成土匪殺了,“母親”都將他們不幸的命運歸結為自己造成的罪孽,沉浸在巨大的悲傷之中。直到孫子問世后,老人才從這半生的辛酸與死亡中看到新的希望。
2 眼藥:母親對女兒愛莫能助的悲哀
在封建時代,因為認為女孩不能傳宗接代,很多家庭一旦遭遇經濟困窘,女嬰都首當其沖成為犧牲品[6]。“母親”的小女兒生來患有眼病,這使其痛苦不已。“下次她的父親從城里回來,我要叫他到一家藥店里買點眼藥回來”,“眼藥”這一意象在《母親》一文中反復被提及。“買眼藥”的行為原本是父母對女兒的一種關愛行為,然而卻被一拖再拖,這恰恰反映了女性在當時社會中家庭地位的卑微和話語權的缺乏。“母親”一方面心疼女兒,另一方面繁重的農活以及捉襟見肘的窮苦生活又使得她不得不放下帶女兒看病的念頭,這種有心無力的困苦、煎熬與遺憾使得“母親”只得通過不斷重復著一句話來安慰自己愧疚的內心,“下次她的父親從城里回來,我要叫他到一家藥店里買點眼藥回來”,“母親”寄希望于丈夫能在下一次返鄉時帶回一盒眼藥。在男權主宰的社會,父親對女兒表現出漠不關心的姿態,而“母親”不能獨立去實施自己的意愿,只能通過強迫性反復話語的方式來安慰自己給女兒買藥又不能實現的痛苦。隨著時間的推移,女兒的病情不斷惡化,當最后“母親”不再寄希望于男人時,女兒已經近乎瞎了。自此之后,瞎子女兒便是“母親”的一塊心病。“母親”在女兒出嫁時反復強調:“我的女兒是不能燒火的,老頭兒,她絕不能燒火!煙!會弄傷她的眼睛”[5]162。
3 首飾:女性在男性心目中的價值體現
“首飾”這一意象在《母親》中表現的不僅是“母親”內心愛美的天性,更是母親渴望得到男性尊重與認可的強烈愿望。然而迫于生活和撫養孩子的壓力,她始終將這份屬于女孩子的渴望藏在心里。男人漠視她,從不為她購置金銀首飾,這是母親心底的傷痛。她羨慕客店老板娘的銀戒指和耳環[5]7;她氣憤男人用家里所剩無幾的錢去買金戒指,但更讓她傷心的是男人說“不是為你買的”。母親雖嘴上說首飾不實用,但她內心其實是期望男人能為她買一副。為彌補內心對首飾強烈的渴望,當長舌寡婦問她可曾想到為自己花過一點錢時,“母親”撒謊稱“我已經叫銀匠給我定制一副耳環、一對戒指,這是我男人應許我的”[5]69;在城中遇見管事時,也謊稱“我想去買銀簪子”。對于自己渴望而又得不到的首飾,“母親”的強迫性反復心理促使她不斷對別人也對自己撒謊,她企圖制造出自己即將擁有金銀首飾和受到男性尊重與認可的假象,以期修復丈夫對自己從不用心的創傷。當管事滿足了她內心多年的渴望,送了一副銀首飾給她時,她以為自身作為女性的美的價值得到珍視,便將管事看作是改變悲慘命運、提升自我價值的希望。可即使母親得到了男人贈送的銀首飾,依然沒有得到男性的尊重,并因此造成其后半生的悲哀和痛苦。
4 藍色:厄運的承載與矛盾的激化
藍色,就賽珍珠的本族文化——美國文化而言,具有憂郁的含義。在中國近代革命前夕,藍色一直是中國社會最底層人們常使用的顏色。在《母親》中,窮困農民大多身穿藍色的衣衫褂子[5]83,母親新婚的被子、母親遞給丈夫吃飯的碗(白底藍花)、丈夫出走那日母親遮頭用的手巾、母親去首飾店時穿的布衫、女兒出嫁的嫁妝(褂子)等都是藍色的。小說中,藍色這一意象超出了貧窮的意味,而具有遭遇厄運與矛盾激化的含義。作者反復運用這一意象,使它的每一次出現,都會引起矛盾、罪惡、希望破滅、至親分離與死亡。丈夫從城里買回假金戒指并與“母親”大吵一架時,天空是灰藍色的[5]28——矛盾激化;布販子誘導丈夫買寶藍色布料時,天空是蔚藍色的[5]33——矛盾激化;丈夫穿上新做好的藍長衫離家出走[5]45——至親分離;“母親”與管事發生關系那日,“母親”身穿藍布薄衫褲在炎熱的陽光下勞作[5]96——罪惡;在炎熱的天氣下農作時,“母親”會不自覺地看向遠方,去尋找那渺茫的藍色影子[5]83——希望破滅;女兒帶著兄嫂做的嫁妝(深藍色褂子和褲子)離開自己從小生活的村莊[5]163——至親分離;女兒死亡的前一天,天空藍得讓“母親”突然想起丈夫走的那一日,一點陰云也沒有[5]170——死亡;小兒子被殺頭時,正處天空將亮之時[5]213——死亡。
通讀整篇小說,藍色的抑郁氛圍在“母親”人生的各個階段不斷重現,它的每一次出現都使得“母親”內心的創傷不斷擴大,“母親”如同陷入一個循環往復的離別與死亡的詛咒。在這種矛盾與沖突、死亡與分離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母親”忙碌一生得到又失去的寂寞悲涼。
5 紅壽袍:人類對死亡的恐懼與反抗
在《母親》中,除了“母親”外還有一位具有強迫性反復心理的人物,即“老太婆”。在傳統的中國農村,老人去世后穿壽袍進棺材,因此,壽袍是死亡的象征[5]17,但對于“老太婆”而言,它卻有著新的意義——穿破它,如同戰勝了死亡。老太婆年事已高,也知道自己終歸是要死的,她常說“老了,一個沒用的老太婆,早就該死啦”[5]1。但她有著如斗士般戰勝死亡的強迫性反復心理,這種心理使得她在死亡面前展現出強烈的生存欲望與斗志。她將穿壞一件又一件壽袍看作是她對死亡的正面回擊,她樂得聽別人夸耀她長壽。她常常對著媳婦說:“我還能穿破這件紅壽袍嗎?”[5]57她對布販子說:“這是我的第二件壽袍,又快要穿破了,布料真一天比一天不耐穿。”[5]34她對著村里人說:“我一直穿著這件應該到棺材里的壽袍,真不敢說我還會穿壞幾件呢!”[5]17臨死的時候,“老太婆”仍強撐著瀕死的身體等著穿上兒子為她置辦的新壽袍。
父親的性別歧視和厭女癥使賽珍珠遭受許多折磨與痛苦。[2]128。作者將童年時遭受父親漠視的心理創傷帶入小說創作中,刻畫了男權統治社會中女性在強迫性反復心理影響下的命運,同時也表現了中國勞動婦女的執著。主人公一次次重現不幸的過往,企圖修復過去所帶來的創傷,如同一次又一次的輪回,一次又一次的涅槃,主人公不斷向悲慘的命運發起挑戰,直至獲得最終的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