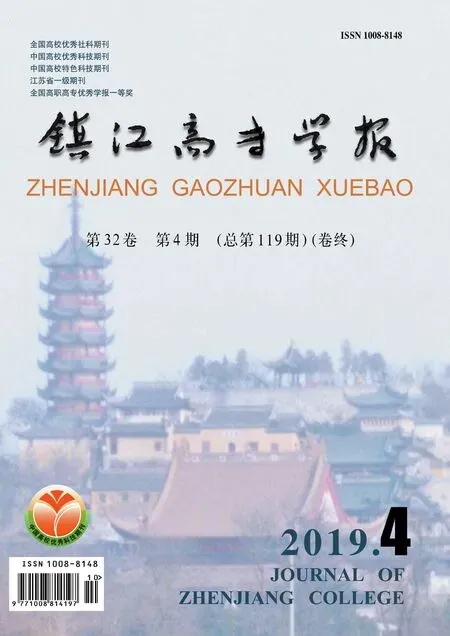論賽珍珠作品中的文化相對主義
——以《生命與愛》和《結發妻》為例
李曉華,張 雅
(重慶三峽學院 文學院,重慶 404020)
賽珍珠81年豐富的人生經歷具有中西結合的特點,這也決定了其文學創作的獨特性。賽珍珠的前半生在中國度過,《結發妻》是她早年以中國人為題材寫成的著名短篇小說,《生命與愛》是她回美國后,于晚年寫就的以美國人為題材的經典短篇小說。就目前國內賽珍珠的文化相對主義思想研究而言,大多從其中國題材作品角度進行探究,將其外國題材作品與中國題材作品進行對比研究的論文為數甚少。異質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在國與國之間已成為常態,深入研究賽珍珠的文化相對主義思想不僅具有學術理論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文化相對主義思想最早于1725年由意大利哲學家維柯闡發。楊須愛將這一思想理論進行了歸納,肯定了其積極性的一面,如“文化是由特定社會的所有行為模式構成,是人類心理的產物,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和價值標準”“民族是文化的實體,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獨立的”“每一個民族的文化或每一種文化都有自身獨特的價值”[1]。姚君偉分析了賽珍珠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作品,認為賽珍珠是“積極意義上的文化相對主義者”[2]。筆者在姚君偉的論證基礎上,將賽珍珠早年和晚年的兩個代表短篇進行對比,探究文化相對主義思想在文中的體現,明晰兩個故事的主人公行為背后的文化差異性和賽珍珠傳達的存異求和、天下一家的理想。
1 理性堅定、保守固執的“舊”人與激進開放、盲目樂觀的“新”人
《結發妻》中,淵的父親是個篤信孔子儒家文化的商人,從唐朝以來“重冠冕”的傳統觀念使得其“對于自己的兒子并無奢望,只想他出去做一個大官”[3]28。他不贊同淵的全盤西化,告誡淵“最好一面還是熟讀四書,一面到洋學堂去求學”[3]29。此言表現出賽珍珠具有建立在中西文化基礎上的辯證思維。
淵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雖說在家里有一定的話語權,卻不敢違背家庭的最高權威——淵的父親。淵的母親親自為兒子挑選門當戶對的妻子,以兒子自選的妻子為異類,否定兒子的西學成果,由此可看出她既看不起處在社會最底層的、無法獲取知識的貧苦大眾,同樣也無視和否定積極向西方學習新知識的現代知識分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婦道思想已內化成其人格的一部分。
結發妻自從父母死后,便“埋葬在婆家”[3]23,她在老宅守了7年活寡,數載光陰在侍奉公婆、管教子女、操持家務等忙碌中如夢般挨過,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來,竟等來一紙休書。無奈與痛苦中,她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從而能保證靈位進入婆家祠堂。結發妻自盡的橫梁在風水上是形煞。賽珍珠在這里借“橫梁”象征淵與結發妻注定的悲劇婚姻,同時,也象征了橫亙在他們之間的“新”“舊”文化的阻隔。辜鴻銘在談到中國婦女的婚姻生活時曾說過,“在中國,一個真正的婦人,不僅要愛著,而且要絕對無我地為她丈夫活著。事實上,這種‘無我教’就是中國的婦女尤其是淑女或賢妻之道”[4]65。結發妻的形象令人聯想到賽珍珠的《東風·西風》中的桂蘭。與之相比,結發妻這個形象在當時更為普遍,所以結發妻只有一個代稱。桂蘭在青少年時代的命運雖與結發妻相似,但所幸的是,她的丈夫在國外習得的家庭文化更為人性化,其丈夫的態度與淵對待結發妻的態度完全不同。結發妻與《生命與愛》中的葛萊辛也存在某種相似性。結發妻在婚后10年間,思想如葛萊辛一般固執而守舊,兩人對新文化都有著本能的排斥,在舊文化中尋找出路方面都表現得異常堅定。結發妻離開學校時冷靜而執著,決定以死了結時又是異常決絕。葛萊辛在毀掉玩偶屋前也表現得異常平靜。這些特質,若從固守舊文化方面來看,是難以改變的人性缺點;若從與新文化存異求和方面來看,它們又都會變為盲目求新者所不具備的優點。
《生命與愛》里的葛萊辛和《結發妻》里的淵的父母、結發妻都是各自所處時代的“舊”人的典型,因文化差異而各有不同表現。淵的父親雖保守,在文化上亦有包容的一面;葛萊辛則表現出更專制的一面。葛萊辛擅于積累財富,終身未婚,是個虔誠的清教徒。在偶得玩偶屋后,他曾短暫享受過作為玩偶們的天父所帶來的權力上的滿足感,但在發現圣母的存在后,內心產生激烈的思想斗爭,最終一神論思想促使他毀滅了玩偶屋,但終究他也沒能得到上帝的任何啟示,剩下的只有無盡的孤獨與絕望。
作為被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淵和他自選的未婚妻顯然并非絕對正面的人物。兩人是積極學習西方文化的留學生的典型,然而他們在摒棄傳統舊文化后,卻為新文化所束縛而不自知。淵堅決地對父親說“四書今已無用”[3]21。淵接觸了“新”文化,就擯棄了“舊”文化:丟掉毛筆,改用外國金筆,拒絕再讀四書,拒絕與結發妻溝通和同房,單方面對她發出指令,單方面提出離婚等。科學知識、西方宗教文化、軍國主義等等一系列思想在他脆弱的心靈里混雜。我們在淵的身上也能看到葛萊辛的影子。葛萊辛在玩偶屋里對玩偶們發號施令,稍有不從,非打即罵。淵留學歸家后對結發妻的冷漠與疏離也是一種冷暴力的表現。淵受了7年新文化的熏陶,全盤接受了西方文化,徹底拋棄了中國傳統文化。很顯然,淵表現出的這種“新”并不被賽珍珠所認可。
真正的“新”體現在玩偶屋里的玩偶們身上,體現在淵的兒女身上,尤其是淵的女兒秀蘭身上。《結發妻》中的一雙兒女形象有著明顯的象征意味,他們象征著賽珍珠所期待的中國民主與科學的光明未來。未被纏足的女兒,強烈渴望進新學堂,“若不讓我去,我就去死”[3]46。兒子雖恃寵而驕,活潑頑劣,卻對新興科技表現出極大興趣,當父親告訴他可以帶他去坐火車、輪船、飛機時,他開心得忘乎所以。玩偶屋里的老夫人領著大小不一的孩子們住在一起。大家互相依靠,互為獨立,過著賽珍珠理想化的中美文化完美融合的家庭生活。玩偶們在偽善的“慈父”葛萊辛統治下,喪失了民主和自由,偶爾違抗就會招來葛萊辛一頓打罵。但搖籃里的嬰兒是新生命和希望的象征,如同《東風·西風》中桂蘭哥哥和美國嫂子的愛情結晶一般,融合了中西文化特征,體現了賽珍珠存異求和的文化相對主義思想。
賽珍珠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溝通。她以比較客觀的創作態度塑造了眾多不同年齡、性別和國籍的人物,又在主觀情感上以中國為母國,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報以極大的熱情和好感,表現出在文化思想上、在秉持情感上更傾向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相對主義思想。
2 在舊文化中尋求出路的“舊”愛與在新文化中迷失自我的“新”愛
《結發妻》中的淵并未愛過結發妻,在他看來,結發妻不過是為他的家族延續后代的“我兒的媽”[3]8罷了。結發妻性格內斂,對淵沉默而順從。因為封建禮法的限制,她竭力克制情感。賽珍珠通過刻畫結發妻的眉毛和耳根的微妙變化表現出她的心路歷程,令人印象深刻。結發妻想到淵是她的主,“忽然感到羞澀,耳根漸漸地緋紅”[3]9,聽到賓客預祝淵連生貴子,“耳根下面的血流又加高熱度了”[3]12,當她放棄了接受新知的機會,試圖在她所認可和熟悉的舊文化和舊體制內尋求躲避新文化的猛烈沖擊的避風港時,她用著近乎絕望的語氣抽噎著說“我再也不能離開這里了”,聽說淵要休妻另娶,且要趕走她、帶走她的兒女之后,“她兩次竭力想說話,卻只有雙眉在眼上聳動”[3]68。面對這一切變故,她無計可施,只能被迫以死抗爭。
淵的“新”愛是跟他一起留過洋的女同學。他愛她,也迫切希望父母能接納她;淵的女同學勇敢地沖破了傳統包辦婚姻的牢籠,憧憬于自主選擇的新的婚姻生活。然而淵徹底拋棄舊傳統,全盤西化,最終能否與“新”愛有個圓滿結局不得可知,淵的女同學自主選擇的在封建原生家庭成長起來的淵能否給她完美的婚姻生活,這是個當時激進而盲目的熱血青年們來不及深思的時代問題。
淵在給父親的信中提及希望得一“智識之妻”陪伴他,為他料理家務與教育孩子,他認為這就是新時代妻與丈夫的“并立平等”。淵所憧憬的完美婚姻不過是賽珍珠父母、賽珍珠與第一任丈夫婚姻的翻版,與民主和平等相悖的婚姻顯然并不為賽珍珠所推崇,她理想的大家庭是《生命與愛》里的玩偶屋。自從有了玩偶屋,葛萊辛很快拋棄了其他收藏品,葛萊辛“發覺這就是他一生中所尋求的東西。這兒——一個真正的家和家屬,還有聽從他的孩子們”[5]56。但頑固的“一神論”思想還是使他追隨了他的上帝,也使他親手毀滅了精神樂園。郭清香曾引用《圣經》中耶穌的一段話,“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愛父母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于愛我,不配作我的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掉生命;為我喪失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6]153。玩偶屋里的女性形象是基督的受害者,耶穌不僅以神的權威占據她們的心靈,還以男性的優越控制了她們的個性。我們從文本后面圣母“臉上顯著溫和的表情”可以讀出,玩偶屋里的女性的覺醒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在婦女身上產生了一種不可壓抑的獨立感和表達自我的欲望”[7]。但漫長的中世紀宗教獨裁者的統治導致了宗教信仰的固化,玩偶屋中女性的女性意識不可能成為一種能真正對抗男性權勢的力量。
《結發妻》從淵被動擇“舊”愛到主動尋“新”愛再到“舊”愛自毀結束。淵有權自主選擇新的妻子,賽珍珠借淵的父親之口提出了較折中的解決方法,淵的父親曾寄給淵一封信,“今且允吾愛女隨余等而居,為汝撫育子女,切勿令知其已遭離異為要。余絕不以此言告伊,居此世外桃源中,伊亦無庸知矣”[3]65。《生命與愛》中的葛萊辛是從主動擇“新”愛到無意發現宿敵再到主動毀“新”愛終結,只因為葛萊辛無法理性地面對異文化,做不到存異求和,無法容忍文化共存。兩部小說共同說明了最適合愛存活的是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環境。
3 源遠流長的“舊”思想與繼往開來的“新”思想的激烈碰撞至理性融合
賽珍珠的父親是保守的基督教徒,母親是虔誠的清教徒,“每天上午,賽珍珠會在母親的安排下閱讀美國的教科書,而一到下午,父母又給她請了一位中國老秀才做家庭教師”[8]24。終其一生,賽珍珠都習慣從中西方兩種思想文化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賽珍珠接受的并非只是儒家思想,對中國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也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她晚年仍清楚地記得:“孔先生細心地講授了道家學說……他擁護兩者的結合。他說:‘讓你的行為是儒家的,讓你的情感和思想是道家的。’”[9]60賽珍珠的一生的確遵循了先生的教誨,“學會以自己的方式去隨我所愿,自由而又創造性地感受”[9]61。
淵拋下父母妻兒,離開祖宅外出留學,也徹底拋棄了中國傳統“舊”思想。淵重新找了一個跟他有相同“新”思想的良伴,并回到祖宅欲與結發妻離婚。結發妻面對突如其來的新思想的迅猛沖擊,無勇氣和能力拋棄固有的“舊”思想。賽珍珠對于淵這種非舊即新做法的態度,通過淵的父親給淵的信表達了出來,“設汝必如汝意,則任此可憐弱息隨余等終其余年,即不為汝婦,亦為余輩女也。余等愛之不稍變”[3]64。淵的舊式父親尚能體恤兒媳娘家父母雙亡、家宅錢財也被娘家兄弟們悉數瓜分,而淵卻變得如此冷血和不近人情。淵只談民主平等自由,拋棄孝悌忠信,失去了本性。在《生命與愛》中,葛萊辛的冷血和不近人情則體現在禁止約翰和瑪麗夫妻倆親吻,讓老祖母外出工作來謀生活,打翻搖籃,對躺在地上兩天的嬰兒不聞不問。賽珍珠深刻揭露了中國和美國兩個家庭體現出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自私,對已婚女性的尷尬境地給予深切同情。
葛萊辛也是一個喪失自然性的人。起初,玩偶屋看似在慢慢治愈他的異化、病態的人性,賽珍珠借玩偶們傳遞了“新思想”,諸如“人性中有神性的光輝,人的生命有著神的高貴”[6]153,248、建立中美文化融合的大家庭等。但頑固的“一神論”思想又使葛萊辛自我否定,直至作出喪失理性的舉動。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士稱葛萊辛有一個太窄的心靈,只可容納他的上帝,威廉·詹姆士把它稱作“奉神病狀態”。確乎,只有在遵循自然純真本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人類的聰明才智,人類社會才會走向真正的幸福與和諧;反之,如果人類迷失了本性,那么無論社會多么文明、科技多么發達,人類社會依然會長期處于一種無謂的爭斗狀態,永遠不得安寧。
賽珍珠曾深入調查研究中國的家庭,她認為中國傳統大家庭原本的、未染上摩登味的生活是怡情宜居和自然的,是純粹中國的。美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不如中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聯系得那樣緊密,這是賽珍珠推崇中國式家庭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賽珍珠的父親是一個一心追求‘上帝事業’、不顧家庭的典型傳教士,這給賽珍珠造成了一生永遠無法彌補的父愛的缺失”[7]54。從《結發妻》與《生命與愛》中,我們可看出,賽珍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和理性有著由衷的贊美和推崇。賽珍珠在《生命與愛》中對玩偶屋進行了理想化的建構。她舍棄了《結發妻》里的老父親首位制,取而代之的是老夫人為一家之尊。中國封建傳統家庭強調長幼尊卑、強調夫權,美國家庭更注重平等、自由和個性獨立。玩偶們組成的家庭是賽珍珠心目中中西合璧的理想家庭的代表,一家子黃頭發藍眼睛的老老少少以老夫人為中心,既和諧地居住在一起,又相對獨立地分隔于不同的房間,充分體現出賽珍珠是一位積極意義上的文化相對主義者。
4 東方“舊”信仰的和諧包容與西方“新”宗教的專一難容
《結發妻》中,淵的父親是孔子的信徒,淵的母親是終身吃素、從不殺生的虔誠佛教徒。面對淵母親的信仰,父親只是平和地對待,“信你的神罷,不過你在怎樣的季候里去求怎樣的東西,我相信你是容易辦到的”[3]11。這句話充滿了先秦的實踐理性精神。自南北朝以后,儒佛道互相攻訐辯論,在唐代三者逐漸協調共生。賽珍珠接受了普通中國民眾的宗教立場,認為“每一種宗教都是混雜在迷信和虛假中的真實和善良,宗教只不過是人們根據他們自己的信念和行為而創造的”[10]152。
淵有不同于父母的另一種信仰,他“信仰那新奇的戰艦、犀利的炮火、精銳的陸軍……”[3]30。淵留洋7年,長期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在基督教文化中,教會提倡“禁欲”,對于男女關系強調“要節制”,認為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夫妻生活應是為了傳宗接代,婚姻中夫妻關系以男人為主、女人為輔。所以淵才會在回家第一晚即對結發妻說“現在我們免了這種形式罷,不但今晚”[3]14。淵所期待的不過是能為他料理新家、替他教育子女的伴侶,這與賽珍珠父親對賽珍珠母親的態度何其相似。
相比于淵,淵的父親對待異國文化的態度要更加理性,他勸告淵既要學習他國文化也需熟讀本國經典。淵的父親深感憂慮,“我的孫兒將來大了會不懂得孝悌忠信”[3]32。淵的父親的勸告體現了賽珍珠一直堅持的多元文化觀,賽珍珠認為多元文化觀是中國文化中最可貴的精神。
《生命與愛》中的宗教文化沖突更加明顯和激烈。異質宗教互不相容,同源異派間的沖突也一樣激烈。當葛萊辛意識到自己握有絕對的權力時,他就從“父親變成了天父,醉心于他自己全能的力量”[5]61,野蠻而殘忍地濫用“神權”。葛萊辛形象的塑造體現了賽珍珠對輕視妻子和患有“厭女癥”的父親的控訴與不滿。葛萊辛效仿上帝對“新”人進行最后的審判。做完這一切后,“葛萊辛卻先走到窗外去,他看著天空,已是黎明時模糊的淡藍色。在他不停地盯視著的時候,什么也沒有”[5]64。作者暗示葛萊辛試圖找到上帝的啟示,卻徒勞無獲。通過描寫葛萊辛對異教徒的敵視和仇恨,賽珍珠表達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怨憤與惋惜。新舊文化的沖突和不相容使得葛萊辛始終無法真正融入玩偶屋那個理想家庭。
《結發妻》里淵的父親對淵的母親代表的佛家文化體現出一種包容的態度,這與葛萊辛的狹隘形成了鮮明對照。賽珍珠曾說過:“……我既不屬于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或許是它們兩者,有時也不完全只是它們兩者,我不是一名無神論者。”[11]257賽珍珠的基本宗教立場是基督教的立場,但是,因為受到儒家、道家等中國宗教思想的影響,她的宗教思想更加圓融、開放,特別是更強調回歸人性。賽珍珠的生活經歷“使她逐漸領悟到對待不同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堅持平等態度的重要性,以及反對以一種文化的價值標準要求另一種文化這一行事方式的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賽珍珠的跨文化、跨國界的實際生活促使她逐步確立了文化相對主義的思想,這是她的文化精神之源”[12]25。
5 結束語
淵全盤舍棄中國傳統文化,老父親對西方文化既覺新奇又畏縮不前,葛萊辛對圣母仇恨難容,玩偶屋式的理想大家庭制難以在美國立足,究其根源,這些都是新舊文化沖突所導致的悲劇。賽珍珠認為不同的文化之間應該彼此尊重、彼此融合,“愛”便是實現這一理想的途徑,“恨是要付出代價的,相比之下,愛的代價要低得多”[13]116。賽珍珠善于以敏銳的眼光考察不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相互碰撞或相互沖突的,從而探討人們如何通過“愛”進行溝通。讀者從作者筆下的人物看到了持不同文化觀的人對待文化差異所持的迥異態度。更為難得的是,兩部小說展現了中美兩種文化在家庭婚姻方面的獨特性,也讓人們看到了賽珍珠的價值判斷和傾向性。朱希祥說過:“全球意識一方面要求注意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接軌,即各民族加強文化之間的聯系,實行互補互滲;另一方面,又要求文化的多樣化,要求各民族保護自己的文化特色,以求全球文化豐富多彩、五光十色。”[14]43《生命與愛》最后一句頗具意味,“從這廣大的空間,那遮住了天空的半邊的,是一只巨大的、敏捷的、有力量的、復仇的手狠狠地擊向著他”[5]64。在《結發妻》中,作者以結發妻自殺的代價啟示讀者,死是“舊”的終點,亦是“新”的起點。作者借這些藝術處理表達了自身觀點:與其互相敵視,互相攻擊,最后兩敗俱傷,不如采取存異求和的相處方式。賽珍珠推崇天下一家的理念,通過敘述兩個家庭的文化沖突悲劇,探討了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空間和平共處的問題。作為一名“積極意義上的文化相對主義者”[2],賽珍珠主張不論“新”與“舊”,在不同時空都只是相對概念,每種文化都有其長處和短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應該互相寬容理解,共同為天下一家的理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