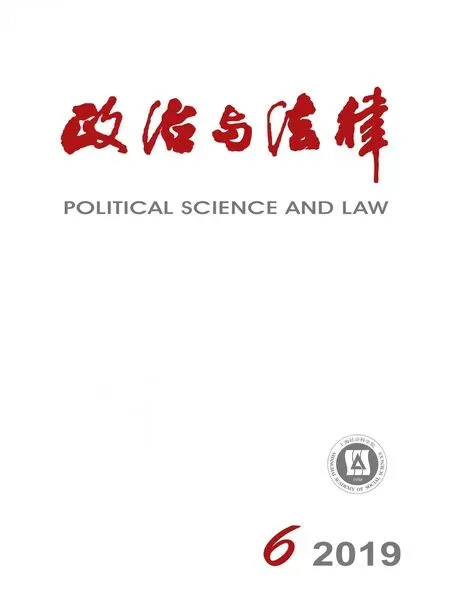真正不作為犯:義務困境與解釋出路*
(湖南大學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82)
一、問題意識與研究對象的界定
(一)問題意識
從2006年至2016年,我國《刑法》一共增修了12個不作為犯,不作為犯的數量整體上增加了三分之一。這一變化,體現了立法者在風險防控需求下對不作為犯的青睞,同時也對解釋者提出了艱巨的任務。由于義務的內容和主體這兩個關鍵要素無法在具體條文中詳細闡明,導致真正不作為犯的義務邊界相當模糊。如何開展義務解釋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議題。[注]義務問題已經上升到“當今刑法的五個基本問題”之一。參見約亨·本克:《當今刑法的五個基本問題》,樊文譯,載陳澤憲主編:《刑事法前沿(第十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頁以下。
在義務內容上,學界存在從其他法律、法規出發解釋義務的路徑與從條文所保護的法益來確定義務的路徑之對立。例如在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中,法院堅持從我國《公司法》的規定來理解“忠實義務”,[注]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07)浦刑初字第1521號刑事判決書。這種解釋得到顧肖榮的認同,[注]參見顧肖榮:《論我國刑法中的背信類犯罪及其立法完善》,《社會科學》2008年第10期。但李軍指出,這會不當地限制該罪的實踐效力。[注]參見李軍:《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中“違背對公司忠實義務”的認定》,《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7期。在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中,王文華主張,該罪義務內容應由相應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確定,[注]參見王文華:《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適用分析》,《人民檢察》2016年第6期。但劉憲權反對這一觀點,認為需要根據該罪的法益確定值得刑法處罰的義務違反內容。[注]參見劉憲權:《論信息網絡技術濫用行為的刑事責任》,《政法論壇》2015年第6期。兩種解釋路徑的對立,大體上是解釋方法的不同選擇。前者以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和歷史解釋為支撐,后者認為目的解釋才是最優方法。當不同解釋方法得出不同結論時,如何在各種解釋方法之間進行選擇呢?這涉及方法論中解釋方法的抽象順位與具體順位問題,有必要根據真正不作為犯的特點,確定解釋立場、建構類解釋規則來縷析義務內容。
與義務內容相比,義務主體在條文中的明確程度要高一些,但模糊性仍然存在。有的真正不作為犯的刑法條款對主體的規定并不清楚,像“負有報告職責的人”或者“負有扶養義務的人”這類表述的范圍就亟待澄清。為此,羅克辛(Roxin)提出了“回溯保證人理論”的主張,[注]Vgl. Claus Roxin , StrafrechtAT Band 2 , Besondere Erscheinungsformen der Straftat , Beck , 2003 , S . 636.需要注意的是,羅克辛以主體是否適用保證人理論作為標準,認為該罪是不真正不作為犯;在我國的分類標準下,遺棄罪顯然是真正不作為犯。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贊同。德國主流觀點就認為,德國刑法中的“違反義務型”背信罪,[注]《德國刑法典》第266條(背信罪)規定:“行為人濫用其依據法律、官方委托或法律行為所取得的處分他人財產或使他人負有義務的權限,或者違反其依據法律、官方委托、法律行為及因信托關系而負有的管理他人財產利益的義務,致委托人財產的利益遭受損失的,處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主體應當是負有財產照管義務的保證人,并且,這種保證人并非根據一般的保證人理論即可篩選而出,即僅僅是對財產負有保管職責(如工廠的保安)還不夠,還必須是對委托人負有財富增值義務的升格的保證人。[注]Vgl. Schoenke/Schroeder/Perron , Strafgesetzbuch 29 Auflage 2014, §266, Rn 23b.在我國,張明楷教授提到了遺棄罪中保證人理論的運用,[注]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頁。敬力嘉認為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主體也屬于保證人。[注]參見敬力嘉:《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的刑法教義學展開》,《東方法學》2017年第5期。將保證人理論運用于真正不作為犯的做法,開辟了義務主體實質解釋的新方向。然而,目前學界仍停留在個罪探討階段,尚未就這種做法從整體上進行理論說明和規則提煉。將屬于不真正不作為犯領域的保證人理論運用到真正不作為犯,其合理性及根據何在、其適用范圍多大、應當適用什么樣的保證人理論、如何通過保證人理論來確定主體范圍等問題都應當逐一解決。
(二)真正不作為犯的范圍
探討真正不作為犯的義務,必須先界定清楚該類犯罪的范圍。學界對真正不作為犯有兩種定義。一種觀點認為,真正不作為犯是刑法明文規定“只能”由不作為構成的犯罪。[注]參見黎宏:《刑法學總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頁;周光權:《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頁。此為我國通說。另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對不作為成立犯罪的條件在條文上有明確規定”,就是真正不作為犯。[注]參見山口厚:《刑法總論》,付立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頁。兩種觀點對于構成行為中既規定了作為又規定了不作為的犯罪如何歸屬存在爭議,包括罪狀中的不作為與作為之間呈“或者”關系的類型(如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罪狀中的不作為與作為之間互為必要條件的類型(如侵占罪、非法集會游行示威罪),以及兩種形態混合的類型(如挪用公款罪)。[注]白建軍教授認為這類犯罪屬于真正不作為犯和不真正不作為犯之外的第三類不作為犯,是學界沒有揭示的新類型。參見白建軍:《論不作為犯的法定性與相似性》,《中國法學》2012年第2期。根據通說,上述犯罪都不屬于真正不作為犯,根據后一觀點則需要具體分析。
筆者認為,通說欠缺妥當性。首先,通說強調構成行為只能是不作為的做法,造成了分類上的不周延。對于罪狀中既包含作為又包含不作為的犯罪,如果一概否定其成立真正不作為犯,只能將其全部歸類為純粹的作為犯或者不真正不作為犯,這恐怕并不合適。其次,通說易使不作為犯背離自由主義刑法立場。由于真正不作為犯與自由主義刑法存在某種程度的抵牾,以自由主義刑法為立場制定和解釋真正不作為犯時,相關的審查和解釋規則往往要嚴于一般犯罪。[注]See Joshua Dressler, Some Brief Thoughts (Mostly Negative) about Bad Samaritan Laws, 40 Santa Clara L. Rev. 971 (2000). P986-989.若認為構成行為中既包含作為又包含不作為的犯罪不屬于真正不作為犯,就意味著這些犯罪無需堅持嚴格的立法和解釋規則。最后,通說與其結論有相違背之處。例如,遺棄罪沒有爭議地被認為是真正不作為犯,但遺棄罪既可以由作為構成,也可以由不作為構成。
自由主義刑法將真正不作為犯與不真正不作為犯分而視之,認為不真正不作為犯因缺乏明文規定,對其進行解釋屬于探討應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則下確定法益保護范圍的“法解釋極限領域的問題”,而真正不作為犯考慮的是那些對法益保護和罪刑法定原則進行權衡后,無法回避后者的質疑、必須立法的不作為。[注]參見日高義博:《刑法解釋論與不真正不作為犯》,張光云譯,《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是“對不作為成立犯罪的條件在條文上明確規定”,就不屬于“法解釋的極限領域”,那么就是真正不作為犯。由此出發考察既包含作為又包含不作為的犯罪,可得如下結論。
第一,在不作為和作為呈現“或者”關系的類型中,根據行為人的具體行為來判斷,以作為實施該罪的就是作為犯,以不作為實施該罪時就是不作為犯。[注]參見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頁。如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就既是作為犯也是不作為犯。刑法中那些明示了職責、義務的犯罪,如玩忽職守罪、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也屬于這一類型,“嚴重不負責任”既包括不履行職責也包括恣意履行職責,[注]參見前注,張明楷書,第150頁;李國慶等:《環境監管失職罪歸責的規范分析》,《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違背忠實義務”既能通過積極行動也能通過消極不作為來實現。[注]Vgl. Claus Roxin, StrafrechtAT Band 2, Besondere Erscheinungsformen der Straftat, Beck, 2003, S.633.當行為人以不作為的方式實施該類犯罪時,應認定為真正不作為犯。這類真正不作為犯和不真正不作為犯表面相似,實質并不相同,后者始終難以逃脫類推的質疑,[注]例如,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中,“殺人”原本只能由作為構成,只是學者們根據禁止規范包含命令規范,將“不救人”勉強解釋進“殺人”中。參見松宮孝明:《刑法總論講義》,錢葉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頁。而前者從文義解釋來看就能夠認為其明確包含了不作為。[注]有學者指出,這會導致同一個犯罪性質認定上自相矛盾。參見陳興良:《本體刑法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59頁。然而,筆者認為一個犯罪有多重屬性并不罕見,不應當作為反對的理由。
第二,對于作為和不作為互為必要條件的類型,應實質性地考察條文譴責的重點。若法益侵害實際上由作為造成,條文譴責的重點在“作為”,則該犯罪應系作為犯,反之則為不作為犯。例如,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中,處罰的是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的作為,并非處罰“行政機關通知改正后‘拒不執行’”的行為,后者只是一個限制處罰范圍的客觀處罰條件,而非引起法益侵害的行為。又如,非法持有國家秘密、機密文件、資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說明其來源與用途的,對法益的侵害來自“非法持有”,而非“拒不說明來源與用途”,這說明了其中的“拒不說明”其來源和用途的成立其他犯罪。侵占罪的爭議更大,不少學者根據“拒不退還”這一規定認定其為不作為犯,但不作為犯的成立必須具有“作為可能性”,在侵占罪中,沒有作為可能性即“退還可能性”的情況比比皆是,卻不影響行為人成立侵占罪,說明該罪并不強調“作為可能性”,因此該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不作為犯。
第三,對于條文中既包含必要關系,又包含選擇關系的類型,視情形采取前述兩種判斷即可。以挪用公款罪為例。行為人挪用公款,用于營利活動或者非法活動的,該構成行為系作為,與其呈“或者”關系的構成行為是“歸個人使用,超過三個月不還”,該構成行為屬于作為和不作為互為必要條件的類型。據此,“挪用公款超過三個月不還”這一類型的挪用公款罪是否屬于真正不作為犯,應當考察該罪構成行為的譴責重點。由于該罪的譴責重點在于“挪用”,“超過三個月不還”只是表明該行為達到了可罰性,其本質是限制處罰范圍,因此,挪用公款罪并非不作為犯,而是作為犯罪。
綜上所述,凡是刑法條文中包含不作為、條文譴責的重點在不作為的,都屬于刑法明文規定的不作為犯。真正不作為犯的范圍應以這一標準來框定。
二、義務內容的解釋
(一)解釋方法的抽象順位與具體順位
認為真正不作為犯的義務內容應當從其他法律法規來確定的,主要采取的是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和歷史解釋方法。例如,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就明確規定了義務應當來源于其他法律法規;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中的“忠實義務”和遺棄罪中的“扶養義務”雖未如此明確規定,但使用了和其他法律法規相同的表述,刑事立法者不可能脫離這些“前見”來制定刑法。相反,認為真正不作為犯的義務內容應當根據刑法條文的保護法益來確定的,其根據在于刑事違法和其他違法畢竟存在區別,目的解釋應當優先于其他解釋方法,條文中的語詞解釋必然要服務于本條最終欲達到的目的。既然如此,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也好,忠實義務、遺棄義務也罷,都需要以各罪保護的法益作為解釋終點。可見,解釋路徑之間的對立實際上是解釋方法的選擇問題。
是否能夠通過比較解釋方法本身的優劣來決定其適用順位呢?長久以來,方法論一直在努力對各種解釋方法的優先順位進行排列,但是至今也沒有成功。即使不少學者將目的解釋視為是最高位階的方法,但那是從其“對法律人最重要、要求最高”以及“最具創造力”的角度來說的,而不是指其效力的絕對優先性。也就是說,解釋方法之間具有“抽象順位的不可決定性”。然而,當具體到個案時,法律適用者“根據他的前理解和可信度衡量”決定了大致的方向后,能夠在個案中實現解釋方法“具體順位的可決定性”。[注]英格博格·普珀:《法學思維小學堂》,蔡圣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頁。關于前理解和方法選擇,更詳細的論述參見Josef Esser. Vorverstaendnis und Methodenwahl. 1970。“法官在做出裁決時,不能僅僅把實在法的‘內容’看作基于實用的調整目標而被實證地給予的”,也不能簡單地根據各種學術性的解釋方法,而是必須“回溯公正秩序的前實證標準”,“將前理解程序納入解釋過程之中”。[注]舒國瀅:《戰后德國評價法學的理論面貌》,《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4期。只有這樣,文本視域和解釋者視域才能交匯,對象與目的之間的相互關系才得以建構。[注]參見德沃金:《法律帝國》,李常青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頁以下。
那么,什么是“前理解”呢?在刑法解釋中,最為基本的“前理解”,是作為刑法適用基礎的罪刑法定原則。這決定了解釋條文的根本目標是含義清晰,且該含義不能超出制定法范圍。普珀(Puppe)認為,根據這一前理解,可以得出解釋方法的基本順位:第一,解釋方法是為了澄清條文意思服務的,在具體個案中,能夠給出清晰結論的解釋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第二,在幾種解釋結論都清晰但互相沖突的情況下就面臨所謂的“選擇問題”,此時應以文義解釋為基礎,即使是目的解釋也不能超出文義解釋的范圍。[注]參見前注,英格博格·普珀書,第79~ 81頁。不過,普珀也承認,上述規則僅是一個基礎,遠遠不夠完整和清晰。對于真正不作為犯的義務解釋來說,還應當從該類犯罪的特點出發,繼續深挖“前見”,澄清解釋立場。
在筆者看來,解釋立場的選取與立法狀況緊密相關。在社會發生變化而立法沒有變動的情況下,應當從解釋論的角度將刑事政策導入教義學中,彌補立法的遲緩。然而,在立法頻繁變動的情況下,解釋論毋寧將重點放在對立法的審視上,防止因為立法的急速擴張,甚至是情緒性立法、象征性立法對自由主義根基的破壞。真正不作為犯的立法,從法益二分的角度來看,恰好呈現出上述兩種情況。一方面,立法者增設的真正不作為犯中,絕大多數是集合法益類犯罪。這說明,立法正在順應社會需求向安全保障價值傾斜。風險社會下不斷強調社會整體的保護,大量創制集合法益,有立法者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如何對集合法益進行教義學上的限定,避免立法者通過刑事政策信馬由韁,是學者應當作出的應對。集合法益類犯罪的設定固然大大補充了刑罰漏洞,但其和不作為的結合所蘊含的侵犯人權的風險,必須通過解釋規則的設定加以最大的限定。另一方面,立法很少設置以個人法益保護為目標的真正不作為犯。這主要是因為,以不作為侵犯個人法益的,一直依賴不真正不作為犯處罰。由于不真正不作為犯只能借助現行刑法中的作為犯條文來保護法益,這使得其保護范圍必然受限于現行刑法的規定。然而,風險社會中人的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受到的威脅在不斷上升,侵害的形式也在不斷翻新。以前或可容忍的侵害程度,現在難以接受;以前沒有出現的侵害類型,現在不斷困擾著個體。要彌補個人法益保護的不足,解釋者在對這類真正不作為犯進行解釋時,應當采取擴張的立場,力求對個人法益進行全方位的、深入的保護。
基于上述解釋立場,筆者以下將真正不作為犯按照超個人法益和個人法益兩種類型來區分建構義務解釋規則。
(二)超個人法益類真正不作為犯的解釋規則
在該類真正不作為犯中,宜首先通過其他法律法規來限定義務范圍,或者說劃定“底線”,在此基礎上再以目的解釋進行限縮,不能以法益為根據突破前者的范圍。
首先,超個人法益的真正不作為犯以行政違法的加重處罰形式出現,對應的行政法律法規一般都對義務內容做出了清晰規定,能夠為義務內容劃定基本的邊界。然而,超個人法益抽象、模糊的特點使得目的解釋難以得出明確的解釋結論,若優先選擇目的解釋,將違反“含義清晰”這一根本的解釋目標,而且,超個人法益放大了目的解釋方法與自由主義刑法中嚴格解釋的要求相違背的嫌疑,[注]參見勞東燕:《刑法中目的解釋的方法論反思》,《政法論壇》2014年第3期。其與“義務”這一輪廓模糊的概念結合,更容易在指導解釋條文、框定條文射程時“過界”。[注]許多學者已經指出了集合法益的這一特質。參見黃國瑞:《法益論之解構》,《輔仁法學》(臺北)2012年第12期;馬春曉:《使用他人許可證經營煙草的法教義學分析———以集體法益為進路》,《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9期。
其次,通過行政法確定的義務和超個人法益并不存在“目的沖突”,兩者在秩序維護這一內核上具有親和性,[注]參見孫國祥:《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及其邊界》,《法學研究》2018年第6期。不存在“超驗的價值差別”,“僅存在著不法程度的區別,即量的區別”。[注]Vgl. Erik, Wolf. Die Stellung der Verwaltungsdelikte im Strafrechtssystem, in Festgabe fuer Reihard von Frank Bd.2, Tuebingen, 1930, S.521ff;Roxin, AT4,§ 2 Rn. 132.轉引自王瑩:《論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對我國行政處罰法與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河北法學》2008年第10期。很多國家將一些超個人法益類犯罪放在附屬刑法中就是例證。只不過,超個人法益指涉的“秩序利益”更窄,限定在維護個人自由和發展所必須的社會秩序方面,在由其他法律法規確定了義務之后,應當以法益在此基礎上進行目的性限縮,排除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給當事人擬定的義務,或者是一些宣示性的義務。
最后,以是否滿足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作為認定犯罪的前期關卡,能夠在刑法解釋上彌補立法偏差,是最為有效地防止犯罪邊界不當擴張的做法。刑法是社會治理的手段之一,但絕非最優手段。在以秩序維護為目標的領域,社會治理的著重點往往在于風險控制。對于風險控制來說,更迫切的需求毋寧通過各種法律法規對義務內容進行完善,建立完美的風險控制系統。刑法在這一領域中實際上只能起到一個擔保或者助攻的作用,[注]參見科納里爾斯·普瑞特韋茲(Cornelius Prittwitz):《刑法作為適切手段》,陳俊偉譯,載《世新法學》(臺北)第十卷第三號(2017年6月),第23頁。忽視其他法律法規而直接采用刑法手段,將刑法放在社會治理的最前線,在立法思路上一開始就已經錯了,更不應在解釋刑法時延續這個錯誤。
基于上述分析,具體適用超個人法益類真正不作為犯的解釋規則時應遵循以下判斷。
第一,在其他法律、法規未規定義務內容時,應嚴格否定義務的存在,而不宜以法益包攬義務的認定。例如,在朱某某、王某某等妨害傳染病防治案中,[注]在該案中,法院依法判處被告人朱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判處被告人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判處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判處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參見《河北四村民干涉非典醫院設立被判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05/id/59965.shtml,2018年11月4日訪問。數被告人得知樂亭縣人民政府已確定閆各莊分院為防治非典疑似病例定點醫院,便利用村廣播煽動群眾阻止定點醫院工作的實施,造成閆各莊分院外南北路口聚集村民200余人,機動車10余輛,將道路堵塞,使運送防治非典的醫務人員、藥品、設備等不能及時到位,延誤達50小時,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此,法院錯誤地將“利用村廣播煽動群眾到閆各莊分院阻止定點醫院工作”的行為解釋為“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的”這一構成行為,并將數被告人認定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這很可能是從該罪法益“公共衛生管理秩序”出發,對構成行為進行恣意解讀的結果。倘若能夠考慮到“拒絕執行預防控制措施的”行為內容必須以傳染病防治法中的明確規定為基礎,就很難將本案中的行為認定為該罪。
第二,應當以其他法律法規中明確的義務內容作為定罪根據,而不宜從籠統的義務規定出發。[注]美國司法判例亦要求,只有對行為人規定了明確的職責,而行為人沒有履行時,才可能成立瀆職犯罪。參見白潔:《美國瀆職犯罪實體問題》,《中國刑事法雜志》2018年第3期。在余某某玩忽職守一案中,被告人在企業第一次改制時已經就國有資產的評估問題進行了匯報,但沒有收到上級領導的指示,因而在第二次改制時沒有就國有資產的處置問題提出反對,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法院認為,“被告人余某某作為國有資產的產權代表,依其職責對國有資產的流失的發生負有特定的避免義務,竟沒有履行自己法定的義務,未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結果的發生”,構成玩忽職守罪。[注]廣東省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江中法刑二終字第35號刑事判決書。然而,所謂的“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的義務”缺乏具體明確的內容,這也是被告人一再認為自己已經履行了義務的原因。筆者認為,被告人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應以其是否確實違反了《關于企業改制領導小組和職能部門分工》中對被告人所要求的“企業的審計、評估及確認;協助改制企業制定改制方案、章程等有關資料、報告”,以及“企業方案正式上報后交領導班子集體討論通過,并報請審批;協助改制企業召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監事會、通過公司章程等工作”等具體的義務內容來判斷,判決對此沒有予以充分論證,不具有說服力。[注]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必要把“明文規定”作為職責認定的必要條件,根據國情、政策或者根據工作便宜口頭要求,某工作人員承擔某項職責的,只要該職責足夠清晰、具體,就應當認定其效力。參見周光權:《瀆職犯罪疑難問題研究》,《人民檢察》2011年第19期;賈健等:《玩忽職守罪中的職責界分應予明確》,《人民檢察》2016年第14期。
第三,在其他法律法規不完善的情況下,應當盡力加以完善,而不宜在激進立法后再寄希望于刑法理論或者特殊的立法規定來控制入刑。例如,對于我國《刑法》第286條之一規定的“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各種不同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義務的范圍、內容應當是不同的,但我國相關行政法律法規沒有預先詳細做出規定,而是設定“積極的、一般性的監管義務”。[注]參見楊彩霞:《網絡服務提供者刑事責任的類型化思考》,《法學》2018年第8期。這種虛化其他法律法規的義務規定的做法,使得刑法學者不得不祭出諸如中立幫助行為等理論來限定犯罪。[注]如劉艷紅認為應當通過“全面性考察”標準對網絡中立行為的可罰性進行判斷。參見劉艷紅:《網絡中立幫助行為可罰性的流變及批判》,《法學評論》2016年第5期。然而這些理論都還沒有達致統一的認識,在實踐中運用的效果可想而知。立法機關在刑事立法中也注意到了本罪的范圍可能會無限度擴張,因此規定了一個前置程序來控制犯罪的成立范圍,即“經監管部門責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這一程序在入罪控制上走到了極端,以至于本罪的判決已經到了難覓蹤影的地步。然而,該規定帶來了更大的隱患:即使行政法律規定對于義務的范圍、內容、主體都無清楚規定,只要監管部門認為是違法的,從業者就必須為了避免頭頂懸著的“刑罰”這把劍隨時落下而放棄行動。這無異于通過刑事威脅來迫使網絡服務提供者無限度地“自我監督”,極大限縮了從業者的行動范圍。若能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中各種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義務內容,就能在構成行為的審查階段將大量不宜處罰的行為排除在外。這相對于刑法理論和刑事立法來說,是一個更為高效、順暢、合理的出罪機制。
(三)個人法益類真正不作為犯的解釋規則
在分析了超個人法益類真正不作為犯之后,個人法益類真正不作為犯應當遵循的解釋路徑及其理由就呼之欲出了。沒有必要以其他法律的規定來劃定這類犯罪的解釋界限,應從其保護的具體法益出發來填充義務內容。一方面,個人法益的解釋力足夠強、能夠對義務內容具體化,以其指導個罪解釋,并不會出現不當擴大處罰范圍、犯罪界限不明的問題。也就是說,個人法益類犯罪從其他法律法規處獲取幫助的需求沒有那么大。另一方面,與超個人法益不同,個人法益和其他法律、法規的保護目的存在較大的區別。若以其他法律法規的內容去框定該類犯罪的義務,所得結論會與個人法益的保護相去甚遠。因此,在對這類犯罪進行義務解釋的過程中,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可以用作參考,但決定義務內容的核心因素還在于個人法益本身。兩者相沖突時應以后者為準。基于上述分析,要解釋此類不作為犯中的義務內容,首先應確定個罪法益,不能僅以犯罪所在章節作為確定法益屬性的標準,一些犯罪表面上看是對超個人法益的保護,其實屬于個人法益類犯罪;[注]Vgl., Luis Greco, Gibt es Kriterien zur Postulierung eines Kollektiven Rechtsguts? Scientia Universalis, Festschrift fur Roxin, 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KG, 2011, ss210~ 213.其次,應結合個案闡釋如何將個人法益運用于對個罪義務的解釋,即將法益具體化為義務內容。
以我國《刑法》第169條之一規定的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為例。該罪中“忠實義務”如何確定,頗值得探討。一種觀點認為,該罪規定在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一節,保護的重點法益是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因此,該罪中的“忠實義務”必須根據我國《公司法》中第147條、第148條規定的“忠實義務”來理解。[注]參見前注③,顧肖榮文。這種觀點錯誤理解了本罪保護的法益,且極大地限制了本條的適用范圍。若以超個人法益和我國《公司法》的規定來判斷忠實義務,由于第148條多處以“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為前置條件,[注]我國《公司法》第148條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一)挪用公司資金;(二)將公司資金以其個人名義或者以其他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三)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將公司資金借貸給他人或者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四)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同意,與本公司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五)未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同意,利用職務便利為自己或者他人謀取屬于公司的商業機會,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所任職公司同類的業務;(六)接受他人與公司交易的傭金歸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違反對公司忠實義務的其他行為。”會導致只要行為人采取各種方式“遵守”了上述前置條件,即使其實施了無償向他人提供資金、放棄債權、無正當理由提供擔保等行為,也無法構成該罪。[注]參見前注④,李軍文。
該罪雖然被規定在“秩序類”犯罪中,但實際上強調的是“損害上市公司利益”。背信類犯罪是人類發展到后工業社會后,財產和管理分離現象的必然需求,[注]參見謝焱:《背信罪的法益研究》,《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1期。旨在彌補現有財產犯罪對財產管理者損害財產的處罰漏洞。考慮到公司是以資產不斷發展作為目標價值的,因此,該罪中的“忠實義務”應當既包括對現有財產的保管義務,又包括積極使公司資產增值的義務。不僅僅是掏空實體資產的行為、公司管理層所有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甚至包括確定的可期待利益,[注]如在德國,行為人違反財產照管義務故意放棄被害人可以獲得的獲利機會,以及行為人能夠為公司簽訂商業合同謀取利益但故意不這樣做的,也屬于造成被害人的財產損失。Vgl. OLG Bremen NStZ 1989, 228; Vgl. BGH NStZ-RR 1997, 357.轉引自王鋼:《德國判例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頁以下。只要能夠進行衡量和評估,都應當屬于“違背忠實義務”的行為。在余蒂妮等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案中,法院認為,被告人掩蓋沒有完成股改業績承諾款的事實,指使他人偽造財務報表,致使公司被終止上市的行為,由于并非通過與關聯公司不正當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的行為,不構成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注]李某甲伙同被告人余蒂妮等人為達到實現股票上市流通的目的,掩蓋沒有完成3.84億元股改業績承諾款繳納的事實,以博元公司實際控制人、高級管理人員的身份,指使財務人員偽造財務報表,實際操縱公司,致使公司被證監部門稽查并被終止上市,客觀上損害了博元公司利益,致使博元公司遭受重大損失。法院認為,我國《刑法》第169條(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1款列舉的前五項均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通過與關聯公司不正當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的行為,因此第六項兜底條款的解釋應當采用相當性解釋。參見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4刑初131號刑事判決書。但這種將該罪限于掏空實體資產并且強調“與關聯公司不正當交易”的做法,實質是將該罪視為特定類型的毀壞財產行為,限縮了義務內容,也大大消解了該罪本應發揮的作用。在筆者看來,被告人的行為違背了管理者照管公司利益的義務,也給公司帶來了利益損害,公司不僅會受到證監會的處罰,而且會承擔商譽上的損失、投資者訴訟要求賠償的損失、因喪失上市地位可能承擔的違約責任等有形和無形的財產損失。因此,被告人應構成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注]在對該案審理后,法院沒有認定行為人構成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另一個理由是,本案只有一個行為,該行為已構成了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不能成立本罪。然而,這是罪數問題,不應妨礙本罪的成立。
在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中,有必要理解何謂“報告職責”。若認為本罪中的報告職責來源于我國《安全生產法》,[注]我國 《安全生產法》第70條規定:“生產經營單位發生生產安全事故后,事故現場有關人員應當立即報告本單位負責人。”第71條規定:“負有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接到事故報告后,應當立即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上報事故情況。負有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和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對事故情況不得隱瞞不報、謊報或者拖延不報。”則易將本罪理解為行政違反加重犯,將重點落在“故意”違反“報告職責”上,將本罪所要求的嚴重后果理解為限制處罰范圍的客觀超過要素。這種對“報告職責”的來源及本罪罪質的認定并不恰當。更重要的是,我國《安全生產法》并沒有規定“報告職責”的具體內容。因此,從行政法來導出本罪義務的做法并不可取。筆者認為,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雖然規定在我國《刑法》危害公共安全一章,但其在侵犯到“公共安全”的同時,總是以侵犯個體安全為前提的,因此本罪的法益應當解讀為可能處于公共空間中的個人安全。本罪中的“報告職責”,并不是像瀆職類犯罪那樣強調職務本身的履行,而是強調對法益的保護。生產經營企業作為社會組織體,其造成的侵害遠遠大于一般的個體侵害型犯罪,隨時需要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回避結果發生。企業領導人對于這樣的一個“危險源”可能造成的損害,既有積極救助的義務,也必然包括向更有能力者求助的義務。總之,應從本罪的法益出發,將“報告職責”理解為保護公共安全法益、避免損害結果發生的義務之一部分。這樣的認定,一是能夠準確界定本罪的過失犯性質。行為人以為可以控制險情而“故意”沒有報告或者錯誤報告,貽誤了救援,但行為人對“險情擴大”并非存在故意的,應當以本罪論處。[注]明知會發生貽誤搶救的結果而不報告的,視情形成立不作為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殺人罪等。二是能夠細化報告職責的具體內容。行為人應當及時報告事故起因、損害現狀、目前的施救情況以及對所需救援的預估等與避免損害擴大相關的事項。因過失而沒有完全報告上述內容,導致險情擴大的,也成立本罪。
三、義務主體的解釋
關于義務主體的解釋,涉及什么樣的真正不作為犯應適用保證人理論以及如何適用該理論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主體為“任何人”的犯罪,不必適用保證人理論,[注]我國《刑法》規定的真正不作為犯中,有5個屬于主體為“任何人”的犯罪,包括拒絕提供間諜犯罪、恐怖主義犯罪、極端主義犯罪證據罪,戰時拒絕、逃避征召、軍事訓練罪,戰時拒絕服役罪,戰時拒絕軍事征收、征用罪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這類犯罪要求全體公民履行某種義務,其主體不需要再判斷,顯然不是“保證人”。但是除此之外都不清楚。
(一)保證人理論的適用基礎
保證人理論是不真正不作為犯領域的核心理論,以保證人理論“跨領域”適用于真正不作為犯,必須論證其適當性。在通常由作為構成的犯罪中,不是每一個人的不作為造成的結果都與作為造成的結果相當,只有那些應當履行義務者的不作為才能適用作為犯的構成要件。因此,如何確定義務主體,是該類犯罪的關鍵。從各種保證人理論來看,都是從不真正不作為犯中“等置”的要求出發,通過強調保證人和法益侵害結果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來保證以不作為實施犯罪的違法和責任程度和作為犯罪相當,進而適用同一刑法條文。[注]Vgl. Kristian Kuehl,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3 neubearbeitete Auflage, Muenchen: Verlag Franz Vahlen GmbH, 2000, S.658.申言之,“不作為”本質上是通過“義務違反”來侵害法益,保證人理論的功能是提供一種與作為產生侵害結果的違法相當的義務違法性。其所強調的主體和法益之間的高度關聯,實質承擔了部分結果歸責功能,[注]參見 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815頁。只有具備這種程度的關聯才能達到與作為相當的違法程度。基于保證人理論的內涵考察真正不作為犯,當某個真正不作為犯的主體和法益之間需要達到高度歸責關聯時,該犯罪主體之解釋就應當適用保證人理論。
(二)保證人理論的適用規則
哪些真正不作為犯應當適用保證人理論?如何確定某個真正不作為犯主體與法益之間應達到高度歸責關聯?筆者認為,可將該真正不作為犯放在刑法分則犯罪整體中進行比較,借助與該真正不作為犯的構成行為相當的不真正不作為犯來對前者進行體系定位。這里的構成行為相當,是指兩罪都通過不作為達到同樣的侵害結果。這里的“比較”,是比較兩罪的法定刑。由于兩罪在行為(不作為)和侵害結果上相同,根據該真正不作為犯與不真正不作為犯的法定刑比較,就可以判斷前者的主體是否應當達到保證人的程度。
第一,如果某個真正不作為犯存在與其構成行為相當的不真正不作為犯,且后者的法定刑明顯高于前者,則說明該真正不作為犯不需要適用保證人理論。在此,筆者以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為例加以說明。以牟利為目的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導致淫穢圖片、視頻傳播的,表面上也可以評價為不作為地“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行為,但后者的法定刑要高得多。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釋是,(不作為地)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要求主體具有保證人地位,而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的主體并非保證人,造成了兩罪在違法和責任程度上的差別。若認為兩罪主體都是保證人,就會導致兩罪重合,進而架空刑罰更低的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產生體系上的不協調。換言之,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的主體與犯罪結果之間無需存在高度歸責關聯,該罪的“結果”如違法信息大量傳播等,并不屬于本罪法益,只是對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類型的指引,[注]參見李永升、袁漢興:《正確把握刑法中的信息網絡管理義務》,《人民法院報》2017年4月26日,第6版。以及從可罰性的程度上對該罪范圍的限縮。
第二,如果某個真正不作為犯存在與其構成行為相當的不真正不作為犯,且兩者的法定刑相當,則該真正不作為犯應當適用保證人理論。例如,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是過失犯罪,保障的是公共空間中的個人安全,這與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性質相當,法定刑也相當。行為人以不作為的方式致人死亡,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時,需要具備保證人地位,[注]從新過失論的立場出發,重視監督、管理過失的認定,將過失實行行為解讀為“沒有履行結果回避義務”,消弭了作為和不作為的區別,這種觀點不為筆者認同。為了確保刑罰上的公平協調,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的主體也應當為保證人。又如,玩忽職守罪致人死亡的情況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罰相當,[注]玩忽職守罪的構成要件結果是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根據司法解釋,玩忽職守致人死亡的與公共財產重大損失等其他損失等同視之。前者也必須和后者一樣,在不作為地造成侵害后果時其主體適用保證人理論。
第三,如果某個真正不作為犯不存在與其構成行為相當的不真正不作為犯,則該真正不作為犯主體宜以保證人理論來認定。遺棄罪是其適例。遺棄罪保護的法益是被害人生命、身體的安全,[注]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65頁。處罰的是制造了生命、身體危險的行為。與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相比,遺棄罪是刑法對生命、身體法益的提前保護。由于刑法中只有遺棄罪保護該法益,不存在其他相應的不真正不作為犯,因此,倘若只要求遺棄罪主體與扶養對象之間具備形式上的關聯,就會導致“刑法處罰違法和責任輕的行為(主體并非保證人)而不處罰更重的行為(主體是保證人)”的不合理局面。換言之,那些更應當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即與受侵害法益之間具有高度關聯的人實施的遺棄行為,將無罪可構成,造成不應有的處罰漏洞。從保證人的角度來認定遺棄罪的主體,已為多個司法判決所采用。例如在王浩等遺棄案中,[注]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07)浦刑初字第134號刑事判決書。法官認為,被告人雖然和被害人素不相識,但其駕駛出租車將被害人遺棄至偏僻地方的行為已經構成了遺棄罪。在王益民、劉晉新等遺棄案中,[注]參見陳興良:《判例刑法學(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1頁。法官也無視律師提出的被告人不符合遺棄罪主體的辯護,主張福利院相關負責人不再扶養“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無生活來源”的公費病人的行為成立遺棄罪。在這些案件中,倘若仍然堅持從婚姻法、親屬繼承法等出發,形式地理解遺棄罪中的扶養義務,是不可能得出上述結論的。
(三)如何適用保證人理論
在確定了需要適用保證人理論的真正不作為犯后,就面臨適用什么樣的保證人理論以及如何適用的問題。
不同的保證人理論對于主體和法益之間關聯程度的要求不同,導致對義務主體的確定范圍存在差別。目前在我國,爭議集中在因果經過排他支配說和結果原因支配說之間。[注]支持排他支配說的觀點,參見馮軍:《刑事責任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8頁;李曉龍:《論不純正不作為犯作為義務之來源》,載高銘暄、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黎宏:《排他支配設定:不真正不作為犯的困境與出路》,《中外法學》2014年第6期;陳興良:《作為義務:從形式的義務論到實質的義務論》,《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支持結果原因支配說的觀點,參見張明楷:《不作為犯中的先前行為》,《法學研究》2011年第6期;歐陽本祺:《論不作為正犯與共犯的區分》,《中外法學》2015年第3期。前者要求主體和法益之間的關聯性極高,犯罪主體必須對危險發生、擴大和實現的整個因果流程都有排他支配才能夠認定為保證人。[注]參見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劉明祥、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然而,“排他支配”這一核心概念在內在邏輯和所得結論上都值得商榷。既然保證人的作用是使不作為等置于作為,在作為犯的場合都只需要行為人對因果流程的開始有支配,那么在不作為犯的場合,也不應當要求對整個因果流程有支配。[注]參見前注,山口厚書,第89頁。與此同時,“排他性”的界定模糊,排他究竟是事實上的概念還是規范的概念,存在疑問,[注]如黎宏教授在其原先撰寫的教科書中,強調在交通肇事的場合必須有“將被害人抬入車內”這種事實上的排他,卻又在父親帶小孩去公園的場合主張“社會一般觀念下,只有父親對該小孩有支配”這種規范的排他。黎宏教授在其后(2016年出版)的教科書中對什么是“排他支配”避而不談,但這一問題顯然還是存在的。參見黎宏:《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頁;黎宏:《刑法學總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3~ 91頁。甚至連強調排他性的日本司法實踐也不能貫徹“排他”這樣的要求。[注]從日本判例來看,不作為的放火罪,多數以“自己的住宅失火”,因而處在自己的支配下這一理由來認定作為義務,但在小偷侵入了事務所后,過失起火卻不救火這類場合,就完全沒有考慮行為人是否具有排他的支配。參見廣島高岡山支判昭和48年(1973年)9月6日判時743號,第112頁。此外,“排他支配”始終無法合理解決親子、場所管理等社會持續性保護關系下的保證人認定問題。[注]有的學者直接對社會持續性關系直接予以承認,而有的則是通過將其轉化為先行行為來認定。參見前注,西田典之書,第94頁;前注,黎宏文。兩種觀點都存在缺陷,前者未加篩選地認可社會持續性關系下的保證人,而后者則限定得過窄。在筆者看來,結果原因支配說能夠克服排他支配說的上述問題,合理地為義務來源提供理論支撐。其對主體和侵害法益之間的關聯性要求不需要達到排他支配說的高度,主張應考察行為人和被監督的危險源或者面臨危險的法益之間是否存在事先的常態的支配。支配的對象是法益侵害的重要原因,即被害法益與危險源,而不是整個因果流程;支配的程度應當達到像作為犯中行為人對自己的手那樣的支配程度,擁有與此相當的支配力度和支配意志,而并非強調“排他”。[注]參見班德·許乃曼:《德國不作為犯法理的現況》,載許玉秀、陳志輝合編:《不疑不惑獻身法與正義》,春風煦日學術基金(臺北)2006年版,第667頁;前注,張明楷文;前注,山口厚書,第89頁。總的來看,無論從理論自洽性還是實踐合理性上來說,結果原因支配說都更勝一籌,宜以該說來劃定真正不作為犯義務主體的范圍。[注]參見姚詩:《不真正不作為犯的邊界》,《法學研究》2018年第4期。例如,在謊報安全事故罪中,司法解釋將該罪主體理解為“負有組織、指揮或者管理職責的負責人、管理人員、實際控制人、投資人,以及其他負有報告職責的人”,[注]參見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這種廣泛而模糊地規定義務主體的做法既不科學合理,也違反比例原則,[注]例如,投資人是否一律應當作為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的主體,值得商榷。司法解釋以“其他”作為兜底項,導致不當擴張處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更不符合自由主義的刑法立場。既然報告義務本質上是結果回避義務的一部分,則根據結果原因支配說可得出的結論是:事故現場對危險源有監督義務者,包括直接操作人員及其組織管理者,以及對安全事項有垂直領導關系的上層管理者是該罪的保證人。
在玩忽職守罪中,目前司法實踐直接適用監督管理過失理論而不去討論主體應否為保證人,[注]日本學者井田良也曾批評新過失論導致了過失犯認定上的不當擴張,提出應對不作為的過失犯以保證人理論進行限縮。參見井田良:《大規模火災事故に お け る管理·監督責任と刑事過失論》,《法學研究》(日本)第66卷第11號,第7頁注〔10〕。轉引自呂英杰:《監督過失的客觀歸責》,《清華法學》2008年第4期。堵截了出罪路徑,導致了不合理的現象:一方面該罪處罰范圍不當地擴張,很多不應入罪的行為都被論以玩忽職守罪;[注]例如,在某案中,被告人未有效制止某村民無證在宅基地上聯戶開發建房的行為,后因有關單位缺乏監管,該村民又一房二賣,騙取316戶居民巨額購房款,致“兩會”期間購房者集體上訪。法院就以被告人沒有履行職責,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由,認定其成立玩忽職守罪。然而,這樣的案件中,被告人顯然不應承擔刑事責任。于是法院又以“多因一果”、村民實施了詐騙行為為由,對被告人免除刑事處罰。參見河南省魯山縣人民法院(2013)魯刑初字第125號刑事判決書。另一方面法院不得不對那些不宜入罪的行為人免除處罰,造成了該罪免除處罰率畸高。[注]筆者在無訟網以“玩忽職守”為關鍵詞,共搜索到9595份刑事判決,其中5396份免予刑事處罰,免除處罰率也達到了56%(2018年12月22日訪問)。這遠遠高于平均值。根據曾文科統計,我國2009年至2013年刑事生效判決的免除處罰率在1.6-1.8%之間變動。參見曾文科:《免除刑罰制度的比較考察》,《法學研究》2017年第6期。考察判決理由,“多因一果”是法官做出免除處罰判決的最為重要的根據。然而,“多因一果”并不是一個法律用語,不能以此作為免除處罰的根據。必須對“多因一果”的情形進行具體分析。根據結果原因支配說,只要行為人與脆弱法益或者危險源之間達到高度關聯,即使行為人的不作為只是“多因”中的一因,也應當認定為犯罪,但是如果沒有達到高度關聯,就必須排除犯罪成立。[注]英美法系也有類似的情況。以英國的毒井案(poisoned wells)(Sutradhar v. 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為例,在該案中,一個研究機構受地方政府的委托為某一口井的井水出具研究報告,地方政府合理地和可預見地用這份報告作為水供應安全的根據,但該研究機構忘記進行砷的檢測。該地區699人飲用了井里的水后受到了身體健康受到了損害。對此,法院承認了研究機構有過錯地導致了結果發生,并且對結果可預見,但認為無需就此承擔責任,理由是該機構對地方政府和居民都沒有所謂的控制支配(control),對于該地居民的安全也沒有承擔責任(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See David Howarth, Poisoned Wells: "Proximity" and "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Negligence, 64 Cambridge L. J. 23 2005, P. 24.
在遺棄罪中,從婚姻法、親屬繼承法等出發來理解遺棄罪的義務主體,不當限定了扶養義務的主體范圍,不少司法判決已經意識到傳統觀點在遺棄罪主體認定上的不妥。前述王浩等遺棄案就是如此。美中不足的是,法官尚未找到對遺棄罪的主體進行合理解釋的根據,在判決說理上難以服眾。實際上,以結果原因支配說對遺棄罪的主體進行實質解釋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上述兩個案件中被害人事實上依賴于被告人生存、救助,被告人處于對脆弱法益的支配狀態,毫無疑問屬于遺棄罪中“負有扶養義務的人”。[注]從遺棄罪和故意殺人罪的關系來看,也可以輔助說明這一結論。兩罪一起共同構成對廣義的生命法益的保護,兩者的法益具有同質性,只是程度不同。與此同時,遺棄罪的構成行為包括不救助被害人的不作為,以及使被害人陷入生命危險境地的作為兩種方式,其能夠被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行為所包容。行為人有義務避免被害人的生命遭受侵害時,自然也有義務避免被害人生命、身體的危險。因此,既然在故意殺人罪中需要適用保證人理論來確定其不作為的主體,則在遺棄罪中也當如此。
四、結 論
可以預見,隨著法網的嚴密,立法還將不斷增加真正不作為犯。這一趨勢將使得義務邊界的模糊性問題不斷凸顯,與自由主義刑法的矛盾日益加劇。[注]See Andrew Ashworth, Positive Obligations in Criminal Law, Oxford and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Ltd. 2013. P30.理論界針對個罪進行零星研究已不能滿足實踐需要。筆者于本文嘗試從整體視角出發澄清義務內容和義務主體,以便厘定真正不作為犯的義務邊界。在義務內容的解釋上,對于集體法益類真正不作為犯,依循先考慮行政法再考慮刑法保護的法益的解釋路徑有利于限縮這類犯罪的范圍,矯正立法擴張可能帶來的危險。對于個人法益類真正不作為犯,以行政法作為對義務內容的提示,以犯罪所需要保護的法益作為確立義務核心的根據,有利于充實對個人法益的保護。筆者于文中對個罪的解釋結論,無論是將遺棄罪、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貫通起來形成對生命、身體法益的階梯保護,還是將事故報告職責還原為救助義務的一部分,或是將背信類犯罪的保護法益從現有財產延伸到可期待利益,都凸顯了筆者于本文采取的基本解釋立場。對于部分真正不作為犯的義務主體,應當運用保證人理論進行實質解釋,通過將真正不作為犯和構成行為與其相當的不真正不作為犯進行比較,來確定前者的義務違反程度是否應當達到后者的要求,以便從體系協調的角度決定該真正不作為犯的主體應否為保證人。根據筆者于本文提出的具體判斷規則,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無需適用保證人理論,但遺棄罪、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玩忽職守罪等則需要借助保證人理論來確定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