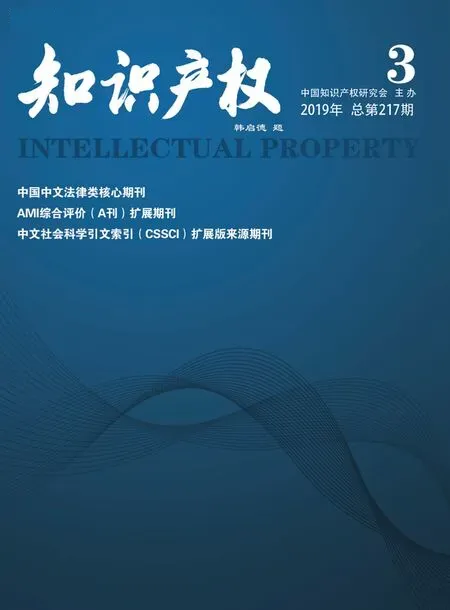《電子商務法》對知識產權法的影響
徐卓斌
內容提要:《電子商務法》是一部綜合性法律,其中散見于該法第一章、第二章及第四章的諸多條款,賦予平臺經營者保護知識產權的積極義務、核驗保存提供交易信息的義務,明確了標記自營業務的責任,亦明確了競價排名的性質,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避風港”規則,基本達成了各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平衡,將對當前涉及電子商務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產生重大影響。《電子商務法》的相關法律規則,對當前知識產權特別法未予明確的問題進行了具體規定,并與其他法律互相配合,成為知識產權權利人發起侵權訴訟的請求權基礎,也成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
引 言
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法》),該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電子商務法》于2016年12月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初審,歷經三次審議修改,充分吸收了各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和建議,達成了最大社會共識。生效施行的《電子商務法》,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指導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規制電子商務行業秩序的綱領性法律文件。有統計顯示,61.54%的電子商務企業曾遇到知識產權侵權糾紛,①冀瑜、邢雁發等:《電子商務市場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缺失及其對策》,載《知識產權》2014 年第6 期,第58 頁。法院受理涉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糾紛案件自2008年以來呈逐年上升趨勢。②陳文煊:《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綜述》,載《電子知識產權》2012 年第4 期,第72 頁。知識產權保護是電子商務行業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電子商務產業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不解決好網絡交易中的侵害知識產權問題,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將永遠蒙著一層“陰影”。也正由于此,構建完備、合理、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電子商務法》的最大關切。值得欣慰的是,《電子商務法》通過建立較為完善的“避風港”規則(亦可稱“通知—刪除”規則),基本上構筑起了為電子商務產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的“避風港”,同時也構筑了保護權利人知識產權和消費者利益的“護城河”,基本達成了各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平衡。
《電子商務法》是一部綜合性的法律,其中關于電子商務合同訂立與履行的法律規則,是合同法相應法律規則的特別法,可歸入狹義民商法的范疇;關于電子商務爭議解決的內容,特別是關于舉證責任分配的內容,屬于民事訴訟法的范疇;關于電子商務經營者辦理主體登記、依法納稅,以及對其違法行為進行處罰的內容,則屬于行政法范疇。而散見于《電子商務法》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的諸多條款,將對當前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產生重大影響,無疑可歸入知識產權法的范疇。本文旨在探究《電子商務法》對知識產權法產生的具體影響,即從實證法的角度、采法解釋學的方法,基于解釋論而非立法論,考察《電子商務法》相關條文如何解決電子商務交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中如何適用《電子商務法》。
一、《電子商務法》的適用范圍
(一)涉及各類知識產權
電子商務已經成為21世紀主流的經濟貿易方式。③賀寧馨、肖尤丹:《促進電子商務知識產權保護的戰略思考》,載《中國科學院院刊》2014 年第6 期,第77 頁。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定義,電子商務是指通過電子方式生產、分銷、營銷、銷售、交付商品和服務。④參見世界貿易組織網站,載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ecom_e/ecom_e.htm,最后訪問日期:2018 年10 月6 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電子商務是指通過計算機網絡進行的商品或服務的銷售或購買,但貨款的支付和貨物(服務)的交付不一定在線進行。⑤參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網站,載https://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D=4721,最后訪問日期:2018 年10 月6 日。有學者認為電子商務是指通過互聯網或其他網絡購買、銷售、流通、交易數據、商品或服務。⑥Efraim Turban et al., 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ial and Social Networks Perspective, 9th edition, Springer, 2018, P.7.根據《電子商務法》第2條規定,電子商務是指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該規定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于電子商務的定義較為接近,將交易途徑限定為互聯網或其他信息網絡,將交易對象限定為商品和服務。對于學術上將數據作為交易對象的觀點,數據是否為合法商業交易的對象,目前尚存爭議,因此立法沒有將其明確納入,這有其合理性,即使商業實踐中部分數據成為交易對象,將其解釋為商品或服務,亦不存在根本障礙。
《電子商務法》第2條將交易途徑限定為互聯網或其他信息網絡,將交易對象限定為商品和服務,有其實踐上的意義。首先,其交易途徑為互聯網等信息網絡,意味著并不限于互聯網。當前,互聯網已經成為各經濟體的重要基礎設施,對于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福祉均具有極重要之價值。互聯網具有無限的開放性,凡接入互聯網的信息設施本身即成為互聯網之一部分,自然人、法人及其他主體可借由國際互聯網溝通信息、達成契約、展開商業活動。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移動通信終端(典型如手機)上的應用程序(如微信)仍需依托互聯網開展信息通信,所有基于互聯網開展的關于商品和服務的商業交易,均屬于電子商務活動。在互聯網之外還存在局域網,雖然局域網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網絡系統,但其規模也可以非常龐大,在其上開展的交易活動同樣具有互聯網商業活動的特點,因此亦應納入電子商務法律制度的規制范圍。“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這一措辭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即使未來由于技術發展而演變出更高更新形式的可用于商業交易的技術網絡,仍不能逸出這一范圍。
其次,《電子商務法》第2條將交易對象限定為商品和服務,囊括了現實中商業交易的全部客體,從知識產權相關性看,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乃至經營者競爭優勢等諸方面。當代經濟環境中,用于商業交易的商品或服務,無不凝結著大量的知識產權。以一部手機為例,其生產中涉及數以千計的技術發明和外觀設計,手機正常運行需要大量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計算機軟件,而不同手機廠商亦需借助商標權展開市場競爭。有統計表明,近年來,知識產權犯罪現象呈現出明顯的從線下向線上轉移的趨勢,⑦胡曉景:《電子商務領域知識產權保護的調查與思考——以義烏市為例》,載《公安學刊》2017 年第6 期,第34 頁。知識產權侵權亦同此理。在電子商務環境中,各類知識產權均成為商業主體交易的對象,也容易成為侵權對象。
(二)信息網絡傳播權例外
《電子商務法》第2條第3款規定,金融類產品和服務,利用信息網絡提供新聞信息、音視頻節目、出版以及文化產品等內容方面的服務,不適用該法。利用信息網絡提供內容服務涉及著作權中的信息網絡傳播權,這一規定可理解為信息網絡傳播權不在《電子商務法》調整范圍之內,但不能寬泛理解為著作權被排除在外。凡交易合同通過計算機網絡達成者,皆可歸入電子商務范疇,但商品或服務的交付方式,因交易對象的區別而有所不同,據此又可將電子商務區分為直接電子商務與間接電子商務。前者指可直接在線交付的無形商品,比如付費下載的音樂、書籍;后者指有形商品的交易達成,但其交付并不能直接在線進行。⑧See Faye Fangfei Wang, Law of Electronic Commercial Transactions,2nd edition, Routledge, 2014, P.8.就著作權而言,其交付形式較為特殊,兩種形式皆而有之,既可以在線直接交付,比如通過互聯網直接下載,亦可以有形商品的形式交付,比如網購印刷書籍。對于消費者而言,不同的交付形式可能僅出于其不同的消費偏好,但就法律規制而言,卻存在很大不同。
數字化的作品天然是互聯網交易的標的物,因此著作權包括信息網絡傳播權從邏輯上講并不能置身于電子商務之外。⑨See Alan Davidson, The Law of Electronic Commer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9.根據《電子商務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不受該法規制,原因可能有三。其一,電子商務法的制度設計系圍繞有形商品展開,服務的提供或商品的交付,均需在線下進行,而涉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交易行為可全部在線上完成,兩種不同的交易形式,宜采取不同的規制手段;其二,信息網絡傳播權已有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法規《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予以保護,特別是其首次采納了“避風港”規則,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已進行明確,實踐表明該條例基本適應產業發展需求,且其“避風港”規則與《電子商務法》之“避風港”規則存在一定差異,為避免法律上之沖突,宜將信息網絡權排除在外;其三,互聯網內容服務涉及國家意識形態及文化安全,有諸多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等進行特別規定,而電子商務本身一般無涉文化安全問題。綜合上述因素,將信息網絡傳播權相關交易排除在《電子商務法》之外,有其合理之處,亦具有實際操作上的可行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權相關有形商品如書籍、唱片、影視光盤、玩具等的網絡交易,仍屬電子商務范疇,應受《電子商務法》一系列法律規則的制約。
二、經營者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
(一)保護知識產權成為法律上的積極義務
《電子商務法》第5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從事經營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遵守法律和商業道德,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履行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等方面的義務,承擔產品和服務質量責任,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該法第41條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與知識產權權利人加強合作,依法保護知識產權。上述規定直接向電子商務經營者施加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義務,這在立法上尚屬首次,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
私法體系圍繞權利而建,權利意味著主體享有某種利益或行動自由,可以為或不為某種行為而不受法律之外的制約。私法亦是基于責任而建,⑩Ernest Weinrib, The Idea of Privat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權利的對面便是義務,凡義務者,其主體必須為或不為某種行為,或必須承受某種不利負擔。但法律上的義務,仍可分為積極義務與消極義務,積極義務須主動作為,消極義務則僅須不作為。根據《電子商務法》第5條及第41條之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為一種積極義務,即經營者不僅須尊重權利人之知識產權、負有不侵權之消極義務,還負有積極作為、主動保護知識產權之責,若其未盡此義務,則需承擔法律責任。這一義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等專門知識產權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所未進行規定,而由《電子商務法》作出的特別制度設計。在將保護知識產權規定為積極義務之前,電子商務經營者當然亦具有不侵權之消極義務,但將其規定為積極義務,將推動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民事責任從補充責任往連帶責任甚至單獨責任方向發展,在侵權訴訟中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將可能從共同被控侵害行為人轉變為單獨被控侵害行為人,侵權責任潛在分擔方的減少,意味著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民事責任形勢。
如果說《電子商務法》第5條尚是一種籠統的、概括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該法第41條則對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據該條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并與知識產權權利人進行合作。首先,這是一種法律上的積極義務,所謂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是指平臺經營者根據其經營業務的特點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電子商務法》第9條將電子商務經營者分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平臺內經營者以及通過自建網站、其他網絡服務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電子商務經營者,實際上有兩種經營者身份:平臺經營者和直接經營者。平臺經營者僅提供信息發布等中介服務,平臺本身只是真實交易雙方的交易場所,平臺經營者并非合同之一方。而所謂的平臺內經營者以及通過自建網站、其他網絡服務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電子商務經營者,實質上均是直接經營者,即直接與消費者簽訂買賣合同并負有交付義務的一方。平臺經營者與直接經營者無疑是相對的概念,如果平臺經營者不僅僅提供中介服務,而是自身直接向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則其此時已不是平臺經營者,而是直接經營者,換言之,平臺經營者或直接經營者,并非一成不變的法律身份,而是通過其實際行為予以定性,僅提供交易中介服務的為平臺經營者,與買方訂立合同、向買方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為直接經營者。以中國市場較為典型的電子商務經營者為例,京東集團借助京東網站、亞馬遜公司借助亞馬遜網站開展自營業務時,其為直接經營者;而相對其平臺內網絡店鋪而言,京東集團、亞馬遜公司為平臺經營者;淘寶網、天貓網均為阿里巴巴集團的購物平臺網站,但其自身并不直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而僅提供交易中介服務,則其為典型的平臺經營者。
有觀點認為,法律賦予平臺經營者注意義務,實際上賦予了其公共管理權力。?劉斌、陶麗琴、洪積慶:《電子商務領域知識產權保障機制研究》,載《知識產權》2015 年第2 期,第66 頁。本文認為,平臺經營者所建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可視為其與平臺內直接經營者之間的合同條款,該合同義務作為平臺內直接經營者面向消費者開展業務的前提,違約則需承擔相應責任,即平臺經營者將知識產權保護義務間接轉移至平臺內直接經營者,平臺經營者通過設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并將其作為合同義務予以履行,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商業上的自我治理。從法律上觀之,則體現平臺經營者的注意義務,即電子商務平臺由于網絡交易泛在性、匿名性的特點導致其平臺上可能產生海量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平臺經營者通過建立并運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以此遏制、減少侵權行為的發生,若平臺經營者未履行此注意義務、疏于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則基于對注意義務的違反而可能承擔侵權責任。
(二)交易信息核驗保存提供義務
《電子商務法》第27條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要求申請進入平臺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聯系方式、行政許可等真實信息,進行核驗、登記,建立登記檔案,并定期核驗更新。該法第31條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記錄、保存平臺上發布的商品和服務信息、交易信息,并確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商品和服務信息、交易信息保存時間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此兩條規定給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設定了交易信息的核驗、保存義務。平臺內經營者的身份信息以及交易信息,對于此后可能出現的侵權糾紛,具有重要的意義。凡侵權訴訟,首先應確定被告即侵權行為人,其次應當查清侵害行為之事實過程,對于電子商務領域的訴訟而言,最關鍵的即為平臺內經營者身份信息及交易信息,據此方可確定訴訟對象及訴訟客體。當前面臨的現實是,權利人難以獲得被控侵權人的身份信息、所在地信息等,由此導致取證困難、維權成本高、時間長等問題,而這正是侵權人逃避法律責任的有利因素。?張為安:《電子商務立法中知識產權保護相關問題探討》,載《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17 年第3 期,第61 頁。由于網絡交易的表面匿名性特點,知識產權權利人一般難以直接通過購買公證的方式確定被控侵權行為人,此時往往須借助電子商務平臺的信息,如果平臺經營者沒有或不愿提供平臺內經營者的身份信息,則侵權訴訟根本難以發起,維權也就成了無本之木。因此,電子商務法將登記、核驗平臺內經營者信息的義務加之于平臺經營者,既沒有過分加重平臺經營者的負擔,又可起追溯責任人之效。
《電子商務法》要求平臺經營者將交易信息保存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系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關于普通民事訴訟時效三年的規定,因如有侵害知識產權行為發生,其交易完成之日可視為侵權行為日,自該時起滿三年而權利人不發起維權訴訟的,將依法喪失勝訴權,即該獲得賠償的權利將失去國家強制力的保護。平臺經營者如違反上述核驗、保存信息的法律義務,即構成對其注意義務的違反,需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并且,由于平臺經營者違反上述義務,可能導致實際侵權行為人難以確定,平臺經營者自身可能單獨承擔侵權責任。
《電子商務法》第62條規定,在電子商務爭議處理中,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記錄。因電子商務經營者丟失、偽造、篡改、銷毀、隱匿或者拒絕提供前述資料,致使人民法院、仲裁機構或者有關機關無法查明事實的,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對電子商務經營者未盡到交易信息保存提供義務的,設定了法律責任。這一規定的價值首先在于解決舉證難問題。該條規定系針對電子商務經營者,即既針對平臺經營者、亦針對直接經營者,平臺經營者在侵權糾紛發生后應有關機關要求而未能提供交易信息的,系對其注意義務的違反,應承擔連帶責任或補充責任。直接經營者在侵權糾紛發生后應有關機關要求而未能提供交易信息的,該條規定的適用效果相當于設定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商標侵權訴訟中權利人亦可援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63條第2款之規定,法院可參考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判定賠償數額。
除非信息披露的成本或不利后果不合比例地過分高于權利人損失,平臺作為信息占有者應當披露相關交易信息。?Jaani Riordan, The Liability of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II.4.65.電子商務經營者具有獲取、保存交易信息的技術優勢和成本優勢,交易信息的核驗、保存法律義務由電子商務經營者承擔,實際上是由其承擔信息核驗與保存的成本,而電子商務經營者相比較于監管者、消費者以及知識產權權利人而言,是這一成本的最低承擔者,無疑有利于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因此這一制度設計具有正當性。
(三)標記自營業務的責任
《電子商務法》第17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全面、真實、準確、及時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務信息,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該條所謂商品或者服務的信息,當然包括商品或服務本身的來源信息,比如生產者、產地、生產時間等,也包括銷售者信息,即所交易商品或服務的直接提供者信息,電子商務經營者若系直接經營者,應當予以明確,若其僅提供平臺中介服務,則應披露平臺內的直接經營者。該法第37條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在其平臺上開展自營業務的,應當以顯著方式區分標記自營業務和平臺內經營者開展的業務,不得誤導消費者。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對其標記為自營的業務依法承擔商品銷售者或者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平臺經營者直接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時,其在法律上應認定為直接經營者,若存在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則其為侵權行為人,自然應當直接承擔民事責任。上述條文的意義在于,首先是向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施加了標記商品或服務來源的義務,當平臺經營者開展自營業務時,其已不再是單純的平臺經營者,而是已具有直接經營者身份,此時應標明其真實身份以保障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其次,平臺經營者對標記為自營業務的商品或服務直接承擔民事責任,而不論該業務客觀上是自營還是平臺內經營者所營業務。
對于電子商務平臺標記為自營的業務,客觀上存在兩種可能:一是確實為平臺經營者自營,此時平臺經營者實際上是直接經營者,其直接承擔民事責任,應無疑義;二是實際并非平臺經營者自營而是平臺內經營者所營業務,但表象上標記為平臺自營,對此電子商務法明確由平臺經營者直接承擔民事責任。對于第二種情形,由于平臺經營者對于是否標記為自營以及對所銷售商品或服務如何標記來源事實上具有或應當具有控制能力,一旦出現錯誤標記的情形,均可認定平臺經營者存在主觀過錯。或者說,電子商務法認為錯誤標記的自營構成了平臺經營者不可反悔的自認。但平臺經營者是否承擔責任,實際上取決于作為原告的權利人的選擇。在侵權訴訟中,作為被告的平臺經營者可能抗辯稱其并非真實的經營者,并披露實際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的平臺內經營者,但根據《電子商務法》第37條第2款的規定,平臺經營者并不能據此免責,權利人此時具有選擇權,即既可以單獨起訴平臺經營者,亦可將平臺經營者和實際經營者作為共同被告,主張由兩者承擔共同侵權責任,且此時平臺經營者須承擔連帶責任。當然,權利人也可僅主張由實際經營者承擔侵權責任,因亦存在平臺經營者誤標且實際經營者基于在平臺內繼續經營的考量而愿意自行承擔侵權責任的情況,權利人此時放棄追究平臺經營者的責任,無疑是以其自行承擔判決執行風險為代價的。
由平臺經營者對標記自營業務承擔責任,也符合權責一致原則,因為標記為自營業務將明顯影響消費者的購買選擇,從而影響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情況,而平臺經營者與實際經營者存在實質上的利潤分成關系,即平臺經營者會因其錯誤的自營標記而獲取不當得利,因此《電子商務法》第37條第2款的制度設計具有正當性。
(四)競價排名的廣告屬性
競價排名以及由此導致的商標侵權問題由來已久。早在2008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即首次在大眾交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訴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等商標侵權案中,認定競價排名服務侵害了原告的商標權。?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7)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47 號民事判決書。但對于競價排名服務的性質,一直存在較多爭議,比如有觀點認為競價排名服務屬于廣告,因存在競價收費并且內容可控,搜索結果受到了付費者及搜索服務商的干預,并非中立的技術搜索;?參見蘭蓉:《對一起搜索引擎競價排名廣告的認定》,載《工商行政管理》2011 年第5 期,第52 頁。也有觀點認為競價排名系基于網絡搜索技術,仍可適用技術中立原則,由于立法對其定性不明確,司法判決中實際認定競價排名為廣告的僅占極少數。?參見肖江平、杜曉:《對百度競價排名的法治思考》,載《法制日報》2016 年5 月11 日第007 版。從立法上看,對競價排名是否屬于廣告,一直并不明確。2015年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以下簡稱《廣告法》)第2條將廣告定義為:商品經營者或者服務提供者通過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間接地介紹自己所推銷的商品或者服務。該法第44條規定,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活動,適用本法的各項規定。雖然競價排名屬于互聯網領域,但仍不能據此得出競價排名屬于廣告的結論。2016年9月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出臺了部門規章性質的《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第3條規定互聯網廣告包括推銷商品或者服務的付費搜索廣告,但仍未直接明確規定競價排名屬于廣告。
《電子商務法》直面該問題,其第40條明確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根據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銷量、信用等以多種方式向消費者顯示商品或者服務的搜索結果;對于競價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務,應當顯著標明“廣告”。此系立法首次對競價排名的法律性質作出明確規定。雖然此條系針對平臺經營者而言,范圍局限于電子商務領域,但平臺經營者提供的搜索服務,與一般網絡搜索服務并無本質區別,因此對競價排名的法律定性也可在其他互聯網搜索服務領域類推適用。
競價排名明確定性為廣告后,將給平臺經營者帶來明顯影響,因為這意味著平臺經營者具有了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布者的法律地位并承擔相應的法律義務。根據《廣告法》第2條的規定,廣告經營者是指接受委托提供廣告設計、制作、代理服務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廣告發布者是指為廣告主或者廣告主委托的廣告經營者發布廣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競價排名這一商業模式中,平臺內經營者(廣告主)向平臺經營者付費,平臺經營者繼而根據付費情況給出相應的搜索排名,實際上同時扮演了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布者的角色。根據《廣告法》第34條的規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應查驗有關證明文件,核對廣告內容,對內容不符或者證明文件不全的廣告,不得提供設計、制作、代理服務,亦不得發布。《廣告法》第56條規定?《廣告法》第56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發布虛假廣告,欺騙、誤導消費者,使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由廣告主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不能提供廣告主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的,消費者可以要求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先行賠償。 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廣告代言人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前款規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廣告代言人,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制作、代理、發布或者作推薦、證明的,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雖是從保護消費者角度對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的法律責任進行明確,但其精神卻完全可以應用到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利益的侵權訴訟中。
雖然有調查表明95%的受眾并不信任廣告,廣告仍會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向產生重大影響,并進而對商品生產者、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狀況產生影響,廣告只有在內容真實的前提下才可能產生正面效應,?Barton Beebe, Thomas Cotter, Mark Lemley, Peter Menell, Robert Merges, Trademarks, Unfair Competition, and Business Torts, Wolters Kluwer, 2011, §1.A.1.內容不真實的廣告將對市場競爭產生扭曲效應,侵權的競價排名關鍵詞廣告,無疑屬于內容不真實的廣告。當競價排名關鍵詞廣告并非真正的權利人所發布時,將導致消費者對相應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混淆。?Mary LaFrance, 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 3rd editio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6, P.193.從侵權責任法的角度看,作為廣告經營者和發布者的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由于其具有保護知識產權的義務,其在制作和發布進行競價排名的關鍵詞廣告的過程中,應當審查付費的廣告主是否具有相應的商標權、字號、域名等知識產權權益,并審核、保留廣告主的真實身份信息,這屬于廣告經營者及發布者應盡的注意義務。一旦認定廣告主構成知識產權侵權,如平臺經營者已盡到審核的注意義務并向權利人披露侵權行為人的真實身份,則其可以免責,否則其亦成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承擔連帶責任。
三、《電子商務法》的“避風港”規則
“避風港”規則對于發展電子商務至為重要,?Graeme Dinwoodie(ed.), Secondary Liability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Springer, 2017, P.31.各國多對此作出規定。《電子商務法》立法最大的亮點在于構建了針對電子商務平臺比較完整的“避風港”規則。該法第42條至第45條對通知—刪除規則、平臺經營者的權利義務及責任、權利人的權利義務及責任作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
(一)“避風港”規則的改進
“避風港”規則最初出現在信息網絡傳播權相關立法中,其他領域的涉網糾紛亦多參考借鑒,《電子商務法》規定的“避風港”規則與《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的“避風港”規則相比較,兩者既有相同、亦有區別。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同樣是關于平臺經營者(網絡服務提供者)及權利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兩者的異同見表1。
通過對比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的“避風港”規則與《電子商務法》“避風港”規則,可以發現兩者具有很多共同點,但亦具有明顯差異,比如:(1)《電子商務法》規定惡意錯誤通知的,承擔加倍責任,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避風港”規則無此規定;(2)《電子商務法》規定權利人收到不侵權聲明15日內須向平臺經營者送達已投訴、起訴的反通知,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避風港”規則無此規定;(3)《電子商務法》規定平臺經營者須及時公示通知、聲明及處理結果,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避風港”規則僅規定通知無法轉達的予以公告;(4)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避風港”規則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未主動審查的不認定具有過錯,已采取合理、有效技術措施的認定無過錯,而《電子商務法》規定平臺經營者應當履行知識產權保護義務、應當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實質上認為平臺經營者具有主動審查的義務。(5)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避風港”規則列舉了網絡服務提供者措施是否及時、“應知”如何認定的判斷因素,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具體例外情形,而《電子商務法》并無此類細化的具體規則,當然,細化規則可留待司法解釋、行政法規等予以處理。
總體看,《電子商務法》強化了平臺經營者(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注意義務和責任,其“避風港”規則設計更為科學,此系因應互聯網產業發展壯大現實、順應加大知識產權及消費者利益保護趨勢之舉。當然,由于《電子商務法》目前并不適用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相關糾紛,相應“避風港”規則并不會產生直接的沖突。并且,《電子商務法》“避風港”規則的設計亦非完美周延,在司法適用中仍會出現諸多問題。
(二)及時采取必要措施
根據《電子商務法》第42條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接到通知后,應當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并將該通知轉送平臺內經營者;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平臺內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對此規則,實際法院早有相關判決。①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0)浦民三(知)初字第426 號民事判決書。雖然本條并未規定平臺經營者應當對權利人的初步證據進行審查,但從“避風港”規則的運行效果和保障市場交易秩序角度考慮,應認為平臺經營者接到通知后應對初步侵權證據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對于明顯不構成侵權的,不應采取所謂的必要措施,相當于賦予平臺經營者“裁判者”角色。必要措施包括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終止交易和服務等,其核心在于終止涉嫌侵權的網絡交易、避免損失進一步擴大。信息網絡傳播權“避風港”規則中,同時使用“立即”“及時”的措辭,可以認為所謂“及時”即“立即”之意,鑒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業務流程復雜性等因素,該所謂的“立即”應含有“不得拖延”之意,即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自身及網絡交易規模等具體情況,其應調配適當的資源用于應對權利人侵權投訴并保障其內部處理流程的有效和暢通,在此基礎上應給予網絡服務提供者合理的處理時間,而不應理解為網絡服務提供者一接到通知即同時采取刪除、斷鏈等措施。并且,必要措施應當與技術發展相吻合,②陶鈞:《知識產權保護中電子商務平臺責任的界定——以“微觀經濟學”為視角》,載《中國市場監管研究》2017 年第2 期,第30 頁。不應賦予平臺經營者過高的義務。《電子商務法》第42條規定的“及時采取必要措施”,亦應作如是解讀,即平臺經營者在其合理處理時間內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具體案件中對此產生爭議的,平臺經營者應就其合理處理時間承擔舉證責任。
(三)通知錯誤的責任
《電子商務法》第42條第3款對通知錯誤規定了相應責任,這一條款一般系針對發出通知的知識產權權利人,但也適用于轉達通知的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如平臺經營者在轉達通知過程中發生錯誤,亦承擔相應責任。因根據該條第1款、第2款的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接到知識產權權利人的適格通知后,應在合理時間內立即采取刪除、斷鏈等終止網絡交易的必要措施,該措施將對被涉及的平臺內直接經營者產生重大影響,可能被經營者作為相互之間的競爭手段而濫用,進而嚴重干擾交易秩序。③董篤篤:《電子商務領域知識產權權利警告的規制》,載《知識產權》2016 年第4 期,第77 頁。因此,該條第3款的制度設計,目的是通過對錯誤通知的實施者施加民事責任,對錯誤通知行為進行事先法律威懾。
但該條款在實施過程中仍存在如何界定損失及責任的范圍之問題。凡后續處理過程中平臺內直接經營者未被認定構成侵權的,應認為權利人發出之通知為錯誤通知,并推定該權利人具有過錯。通知錯誤屬于侵權行為,根據侵權責任法的損失填平規則,發出錯誤通知的權利人應當賠償平臺內經營者全部實際損失。所謂“惡意發出錯誤通知”,應指權利人并非出于正當維權需要,而是借由維權進行欺詐牟利、敲詐勒索或干擾競爭對手的正常經營,甚至可能其據以發出通知的知識產權權利系虛構或權利證書系虛假制作,④杜穎:《網絡交易平臺上的知識產權惡意投訴及其應對》,載《知識產權》2017 年第9 期,第38 頁。這顯然屬于故意侵權行為,讓其加倍承擔賠償責任具有懲罰性賠償之性質。暫且不論實際損失如何計算,對于損失的范圍是否僅限于交易終止期內的直接損失,還是及于商譽損失、未來交易機會損失,仍存在探討的空間,未來發生實際案件時,損失及賠償數額的計算將成為難點。
(四)及時終止所采取的措施
根據《電子商務法》第43條第2款規定,平臺經營者接到不侵權聲明后,應將該聲明轉送權利人,轉達后15日內未收到權利人已向主管行政機關投訴或向法院起訴之通知的,應及時終止針對平臺內直接經營者所采取的措施,即應恢復受影響的網絡交易。對此作進一步解讀,意味著如權利人及時投訴或起訴的,平臺經營者應當繼續維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如果權利人系正常維權,當然不會產生負面效應。但如權利人或競爭對手之間濫用該“通知—刪除”規則發出錯誤通知,由于存在損失計算規則不明的問題,可能導致受通知的平臺內經營者之權益嚴重受損。該款“15日內”之限定,并非指平臺經營者必須等待滿15日。商場如戰場,商業機會稍縱即逝,在一些重大營銷節點更是如此。對此,為消除雙方權利義務不對等之局面,建議平臺經營者建立侵權保證金制度,即當平臺經營者收到權利人侵權通知并轉達平臺內直接經營者后,除不侵權聲明及初步證據除外,如直接經營者愿意根據權利人之侵權主張情況繳納相應數額的保證金,平臺經營者在收到該保證金后應及時終止所采取的措施,恢復該直接經營者之網絡交易,如后續程序中該直接經營者被認定構成侵權,則其應付賠償金從中扣除。該侵權保證金制度與《電子商務法》不相違背,處于行商主體之間的自治范疇,有利于維護電子商務平臺的經營秩序,亦不影響后續的行政投訴或侵權訴訟,各方權利義務尚能平衡,應屬可行。
(五)主動審查義務
《電子商務法》第5條規定平臺經營者應當履行知識產權保護義務,該法第41條要求平臺經營者應當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再結合該法第45條之規定,實質上該法設定平臺經營者具有主動審查平臺內直接經營者是否侵犯知識產權的義務。該義務在“避風港”規則之外,給平臺經營者施加了主動采取刪除、斷開鏈接等終止交易措施的法律責任。這意味著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通過技術或人工手段對其交易平臺內的商品和服務進行知識產權相關的審核、巡查、監督,對于明顯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如價格畸低的名牌商品)應進行主動處理而無需等待權利人之通知,否則即可能違背其注意義務而承擔相應侵權責任。當然,主動審查義務并非無限的法律義務,平臺經營者提供的是網絡服務,其所承擔的審查義務應該考慮公平、效率的原則,而不應讓其承擔過高的預防成本。?? 石必勝:《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知識產權審查義務的標準》,載《法律適用》2013 年第2 期,第104 頁。
結 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電子商務法》的相關法律規則對知識產權法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當前知識產權法領域諸多未予明確的問題進行了具體規定,并與其他法律互相配合,成為知識產權權利人發起侵權訴訟的請求權基礎,而非僅為倡導性的軟法,我們將在法院的法律文書中越來越多地看到《電子商務法》條文成為案件判決依據。可以預見,《電子商務法》通過聚焦和規范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行為和責任,將在凈化市場環境、明晰商業規則、推進公平競爭、改善營商環境、構建市場秩序、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和發揮其獨特并且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