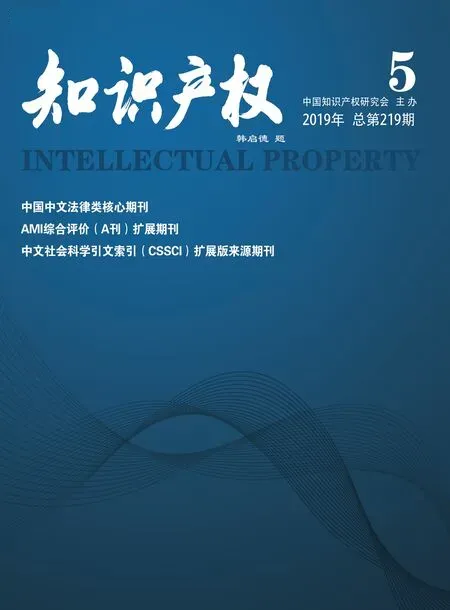知識產權轉讓不破許可之證偽
張 軼
內容提要:知識產權被轉讓后,新知識產權人是否可以禁止訂立在先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繼續使用知識產權客體,是知識產權利用制度中的焦點問題。遺憾的是,相關法律中用語較為模糊,并在追求效果的穩定性方面呈現明顯欠缺。對這些規范的內容及其引發的諸多困境進行分析后,進一步對相關租賃合同規范的類推適用可能性予以考察。隨后對許可關系自身的特殊性進行了立法論層面的分析。在解釋論和立法論均不能貢獻支撐轉讓不破許可的正當理由之后,在權利變動層面對許可的法律本質進行初步探討,最終得出知識產權轉讓不破許可在中國法下未被確立的結論。
一、問題的提出
知識產權被轉讓后,在先訂立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在合同約定范圍內繼續使用知識產權客體,是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學術界的普遍共識。①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頁;黃暉著:《商標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頁;陶鑫良主編:《專利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頁;董美根著:《專利許可合同的構造:判例,規則及中國的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頁。從現有判決來看,司法界的態度與學術界保持高度一致。②代表性判決,如南京希科集團有限公司與珠海匯賢企業有限公司專利侵權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2)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53號民事判決書;黑龍江沃德科技開發集團有限公司與蓬萊市海達石油有限公司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糾紛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魯民三終字第144號民事判決書。這一規則似乎并沒有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與我國略有不同的是,在同樣踐行物債二元財產體系的大陸法系的德國,知識產權轉讓不破許可的規則雖然在立法層面予以確立,③通過強制性法律條款實現對被許可人的法定保護,參見§15 (3)PatG, §30 Abs. 5 MarkenG, §33 UrhG, § 22 Abs. 3 GebrMG;Art.23 III SortSchVO .在學界贏得了眾多德國學者的支持,④較早文獻如Breuer, GRUR 1912, 44, 55;Ullmann in Benkard, 7. Au fl. 1981, § 15 PatG Rdn. 60; Klauer/M?hring, 3. Au fl. 1971, § 9 PatG Rdn. 39; Krausse/Kathlun/Lindenmaier, 5. Au fl. 1970, § 9 PatG Rdn. 57; Tetzner, 2. Au fl. 1951, § 9 PatG Rdn. 39; Hubmann,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4. Au fl. 1981, S. 160; Patentgesetz 1929, § 6 Anmerkung 18.但是反對之聲的理性依然難以被忽視。⑤See Bock/Bruchhausen in Benkard,6. Au fl. 1973, § 9 PatG Rdn. 49; Schramm in Grundlagenforschung 1954, S. 85.尤其是在立法最終接受轉讓不破許可規則之前,換言之,在司法判決尚有自由權衡空間的條件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甚至帝國法院(RG)均在相關判決中清楚闡明過相反觀點,⑥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82年3月23日的判決中對轉讓擊破許可的堅持,詳見 Urteil vom 23. M?rz 1982 durch Kartellsenat des Bundesgerichtshofs (KZR 5/81 = GRUR 1982, 411 Verankerungsteil);“2. Eine von dem Ver?u?erer eines Patents erteilte einfache Nutzungserlaubnis mit schuldrechtlicher Wirkung verp fl ichtet den Erwerber des Patents nicht“ (Amtliche Leits?tze) ”;較早的還有德國帝國法院(Reichsgericht)在1911年5月5日的一份判決中 (RGZ 76, 235f.)支持轉讓擊破許可。以防范既定民事財產權利結構被動搖。
被許可人為使用知識產權客體的前期資金投入是否必然會因為權利的在后轉讓而付諸東流?未曾簽訂許可合同的新權利人,在受讓知識產權之時甚至完全有可能并不知悉許可合同的存在,其履行他人為自己設定義務的法理基礎是否具有充分說服力?在利益平衡層面,規則向每個在先被許可人傾斜,均是以加重新在后權利人的負擔為代價(法定禁用權受限)。轉讓不破許可法律規則能否真實回應交易實踐中被許可人、新權利人和許可人的三方利益格局?對被許可人的特別保護,能否在維護公平和保障效率這兩個基本法律價值的前提下增進知識產權交易在我國的繁榮?直觀性的答案似乎并不可靠。
在我國既有民事法律框架和民法權利理論體系之下,知識產權轉讓不破許可的理由,共存在以下五種可能。其中任何一項理由的成立均能夠充分支撐知識產權轉讓不破許可規則的正當性。第一,出于交易主體之間利益格局特殊性的內在要求,強制性法律將轉讓不破許可作為法定例外予以直接規定。第二,鑒于被許可人、新權利人和許可人的三方利益關系與法律既有規制情形的高度相似性,類推適用其他合同類型相關規則得出知識產權轉讓不破許可的必然結果。第三,雖然缺少法律直接規定和類推適用條件,但利益格局的特殊性迫使司法機關以法官造法的途徑確立轉讓不破許可。第四,在知識產權領域突破絕對權權利類型法定原則,將各類許可證的法律屬性一律視為設定在知識產權之上的對世性負擔。第五,同樣拋棄潘德克吞體系,但是,基于許可合同授權,知識產權權利人的部分絕對權為獨占、排他甚至普通被許可人所擁有,以致于在后轉讓僅構成了知識產權的部分轉讓。因為除手護手規則(Hand muss Hand wahren)之外,任何人都沒有可能轉讓他沒有的權利,⑦羅馬法原則“nemo plus iuris ad alium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t”,參見Ulpian, D,50,17,54,轉引自 Max Kaser/Rolf Knütel,R?misches Privatrecht,20Au fl., München, 2014, p.139.后來的(部分權利的)權利人無法禁止被許可人繼續使用知識產權客體。
基于前述可能性和理由,本文對“轉讓不破許可”規則進行遞進式逐層論證。首先,法律既有直接規定的分析和解讀。其次,近似合同類型的類推適用性考察。這兩個階段從純粹法教義學視角共同構成了對現有規定及其相互銜接中內在邏輯的解釋論考察。再次,在解釋現行法無果后,從立法論層面考察三方關系的特殊性,驗證確立新規則的必要性。最后,解釋論和立法論均不足以驗證轉讓不破許可的正當性之后,在知識產權制度下重新審視潘德克吞財產性民事權利體系的合理性,在更為基礎的知識產權權利變動層面探尋許可證的法律本質。
二、知識產權規范中的立法者意志
(一)文義模糊性
新權利人不得對在先被許可人行使禁止權被普遍認為是現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然而,轉讓不破許可是否真實存在于我國現行法律之中,并未經過任何嚴密論證的檢驗。換言之,當前司法中顯現的實然狀態僅能以(并不正確的)學界認知作為根基,卻并不能當然體現立法者的意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第二句規定,……讓與人與受讓人訂立的專利權轉讓合同,不影響在合同成立前讓與人與他人訂立的相關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效力。就商標權轉讓對在先商標許可的影響,最高人民法院在其《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作出了與技術合同司法解釋具有相似表述的規定。⑧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規定,注冊商標的轉讓不影響轉讓前已經生效的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的效力,但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的理解,載http://www.npc.gov.cn/huiyi/lfzt/qqzrfca/2008-12/18/content_1462612.htm,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2月2日。關于著作權轉讓對在先許可的影響,著作權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沒有作出相應規定。但對于法律規定的由作者享有著作權的職務作品,《著作權法》第16條明確賦予法人在其業務范圍內享有優先使用權。而且作品完成兩年之內,未經單位同意,作者不得許可第三人以與單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該作品。如果該條款尚未完全剝離作者所享著作權中的處分權能部分,即轉讓著作權財產性權利,則作為受讓方的新著作權人無法以相同方式自己使用,或許可第三人以相同方式使用該作品。簡言之,為期兩年的優先使用權,作為作者發放給其“單位”⑨此處僅為對法條術語的沿用,指法人;單位在民法中并不構成一個確切的概念。的一種許可類別,足以依據法律明文規定對抗新的著作權人。即該條款構成轉讓不破職務作品獨占許可的法定情形。
在作為法律規則基礎要素的透明性(Transparentsgebot)方面,前述涉及專利和商標許可證效力的條款帶有無法忽視的缺陷。專利權或商標權轉讓之后,許可合同的許可人成為無權處分人,并因此無權繼續許可他人實施專利或者使用商標。該類情形在從傳統民法視角構成繼續性合同履行的主觀不能。鑒于法條自身沒有增設生效附加條件,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所指的許可合同,早在專利權或商標權轉讓發生之前就已成立、生效,甚至可能已經進入履行階段。通過在后的轉讓行為動搖業已生效的合同效力的可能性,難以被任何既有債法理論所接納。⑩《合同法》第51條是針對合同訂立時無權處分的情形以及出賣他人之物的規定,所以無法適用。此外,對物權變動規則和《合同法》第51條錯誤根源,已經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3條規定的出臺為契機,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討論,此處不贅。縱然以專利、商標轉讓為時間點,純粹從分析技術角度將訂立在先的許可合同拆分為兩個組成部分,而在后部分,即使其被視為一個獨立合同,則該合同也不會因為轉讓行為的發生而無效。縱然忽視許可人發放許可的意思表示是早在“無權狀態”出現之前做出的事實,規定出租無權處分物不影響租賃合同效力的《合同法》第229條,也具備類推適用的可能性。由此可見,適用上述條款所得到的結論與民法總則、合同法總論的指向并無二致,11詳細規定合同效力問題的《合同法》第52條、《民法通則》第58條(《民法總則》第145條到第156條)中所列舉無效情形并未包含在后合同的訂立。僅僅構成一項純粹的注意規定。在推斷起草司法解釋的法官確立上述條款的意圖的努力中,作為首當其沖的解釋路徑,文義解釋路徑顯然無法通向買賣不破許可的確定結論。1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的解讀同樣沒有是被許可人和新權利人的法律關系更為明朗,載http://www.npc.gov.cn/huiyi/lfzt/qqzrfca/2008-12/18/content_1462612.htm,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2月2日。對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的規范解讀,會令任何一個希望繼續使用專利或商標的被許可人在面對新權利人時,無所適從。
(二)條款內在沖突
更深層次的矛盾與困惑來自于具有基本相同內容的《商標法》第43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依照其規定,未在商標局備案的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無法對抗善意第三人。13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規定,……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未在商標局備案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商標法》第43條內容與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相同:商標使用許可未經備案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當商標受讓人構成該條款意義上的善意第三人時,則轉讓擊破未在商標局備案的許可。假設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第二句和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要求轉讓不破許可,則《商標法》第43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將轉讓是否擊破許可的問題與許可合同備案以及新權利人的善意掛鉤,即善意新商標權人可以擊破沒有備案的許可。同時,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最高人民法院將善意第三人理解為許可合同外的與商標權人就該商標進行交易的人。在先訂立未經備案的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的效力,不能抵抗善意第三人與注冊商標人之間就該商標在后所訂立合同的效力。14就條文關于合同效力表述問題的糾正,參見上文。未備案的獨占商標許可不會影響普通許可的發放。在堅持許可債權性的前提下,無論是否備案的獨占商標許可,均不會影響普通許可的發放。不言而喻,該解釋路徑僅體現該條款解讀的可能性之一。另一毋庸置疑的解讀方式是,第三人是商標受讓人。雖然從體系上解釋,在考察轉讓是否擊破許可時——鑒于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的存在——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并非首選。但是從更具優先級別的文義解釋角度,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完全適用于商標受讓人構成第三人的情形。且《商標法》第43條也作出了與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內容一致的規定。當商標受讓人構成該條款意義上的第三人時,并且在商標轉讓合同訂立之時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在先許可的存在,從而滿足善意要件,則被許可人依據此條在許可合同未經備案的情況下無法在商標轉讓后繼續使用商標。這種視野下,該條文背后的立法者意志可能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走向。第一,由于在先許可(包括普通許可)被視為絕對權,在后轉讓構成商標權人的無權處分。如果該用益權未經備案,則新商標權人可能會善意取得完整的,沒有負擔的商標權。本文不傾向這種解讀,因為下文即將進行的分析結論與許可的絕對權性質形成抵觸。第二,債權性的(未經備案的)許可當然不得對抗在后的(善意)受讓人。現有文獻的梳理無法使我們確定,該條的反向解釋是否成立。換言之,立法者是否認為經過備案的許可必然能夠對抗——因為備案的存在而缺乏所謂“善意”的商標受讓人,從而使在先被許可人得以繼續使用商標,不得而知。如果反向解釋成立,暫且不論備案是否應該具有等同登記的功能,則商標權轉讓不破許可的制度在合同備案的情形下業已確立。那么,《商標法》第43條、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與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第二句之間的實質性沖突便了然于目。事實上,在被許可人與新權利人之間利益權衡的實證研究或者更有力的論據在立法論層面被得出之前,無論新權利人是否知道在先許可的存在,立法者對其禁用權予以限制的做法有失慎重。單純是否備案的考量在三方關系權衡中尚不足以成為唯一決定因素。框架整體得以變動之前,立法者應當重審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19條及《商標法》第43條的表述,考慮是否徹底消除反向解釋的可能性。
三、租賃合同規則的有限借鑒價值
許可和租賃均屬于通過訂立合同使用他人財產的法律行為的兩類具體形態。當該財產構成物權法上的物時,此類合同受到租賃合同規范調整;當該類財產構成各知識產權單行法規制的客體時,此類合同則被稱為許可合同。合同法中不同有名合同之間的分工劃分,甚至不同部門法的作用和約束,并不能減弱規范所服務的核心法律關系的近似性。比對表明,我國《合同法》第229條關于租賃合同的表述,與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高度相似: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生所有權變動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民法學界通行觀點認為《合同法》第229條確立了我國民法制度中“買賣不破租賃”的基本規則。1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第135條第2款(原119條)規定,私有房屋在租賃期內,因買賣、贈與或者繼承發生房屋產權轉移的,原租賃合同對承租人和新房主繼續有效。知識產權學術界也有觀點借此反對新權利人禁止在先被許可人使用知識產權客體。16參見黃暉著:《商標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頁。
(一)《合同法》第229條的檢討
我國《合同法》第229條已經受到了民法學界的廣泛批評。17關于《合同法》第229條的缺陷,代表性觀點見張雙根:《談“買賣不破租賃”規則的客體適用范圍問題》,載《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1卷,第3-6頁。縱然大膽地信賴通說的認知,特別是鑒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119條第2款的存在,將《合同法》第229條立法者的目的推測為買賣不破租賃原則(Kauf bricht nicht Miete)的確立,18朱慶育:《“買賣不破租賃”的正當性》,載《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1卷,第31頁、第32頁;本文此處論述以《合同法》第229條規定了買賣不破租賃原則的假設為前提。該條款依然不能成為支持轉讓不破許可的類推對象。首先,買賣擊破租賃是羅馬法的悠久傳統和基本原則,19Brox/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4 Au fl. 2010, p. 190.而非買賣不破租賃。大陸法系德國支系的發端德國,在對羅馬法的繼受和發展中并沒有顛覆該原則,更沒有簡單地將承租人的債權上升為用益物權。20Brox/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4 Au fl. 2010, p. 190f.買賣不破租賃作為法律原則的例外規定,僅適用于房屋和土地的轉讓。21Brox/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4 Au fl. 2010,p. 190f;§ 566, H?ublein,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BGB) 6. Au fl. 2012, Rn 1ボ.該例外旨在加強保護被立法者認定為弱勢群體一方的承租人,從而在整體效果上達到法律所追求的社會平衡和公正。其次,同樣奉行物債二元民事財產權利體系的中國法,在對羅馬法繼受的過程中同樣沒有顯現出改變買賣擊破租賃原則的內在需求。22因為不僅物債對立分離的原則在中國民法中得到不斷鞏固,而且租賃法明確抵制債權轉化為用益物權。債權物權化僅僅指特定相對性的突破,而非變為物權。在沒有特殊理由的情況下,立法者通過《合同法》第229條不區分動產和不動產,對所有租賃物一概實行買賣不破租賃的做法,23張雙根:《談“買賣不破租賃”規則的客體適用范圍問題》,載《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1卷,第4頁。值得慶幸的是,由于第229條錯誤的概念運用,這個問題在中國法下并不真正存在。實質上將買賣不破租賃上升為法律原則。這種做法嚴重背離了潘德克吞體系物債二元區分對立的理論基礎,在租賃法體系內已經難圓其說,更加難以成為專利、商標許可制度的借鑒依據。最后,在現行中國租賃法律框架內,《合同法》第229條對于房屋租賃關系的適用,對于承租人而言沒有實際幫助。因為在法律對于出租人解除房屋租賃合同的自由沒有作出更嚴格的限制之前,作為出租房屋的新舊所有權人均可以微小代價輕易擺脫租賃合同義務的約束。該條提供的保護與關懷毋寧說呈現了更多的宣示意義。
(二)租賃關系類推適用的批判
與出售租賃房屋中各方利益格局的比較顯示,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和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的“立法目的”(司法解釋目的)不應指向轉讓不破許可。首先,《民通意見》第119條第2款承認房屋承租人需要法律的特別保護,使得買賣不破房屋租賃成為法律明確規定的例外情形。而被許可人顯然不構成該規范意義上的經濟或社會弱勢階層。其次,從各知識產權客體交易類型中,尚不足以提取出被許可人在知識產權許可關系中處于類似程度的弱勢地位,以至于突破原則作出例外規定成為立法者不二的選擇。被許可人總是構成弱勢一方當事人的假設很難成立:鑒于技術需求方的研發能力和市場地位,處于弱勢地位的專利被許可方似乎構成常態情形。然而,由于缺乏實施專利的條件,個人作為專利權人向企業發放許可證的情況在實踐中也屢見不鮮。專門的研發機構和大專院校作為權利人發放許可的情況也在增加。在商標許可中,雖然被許可人常為弱勢一方,但是弱勢的許可人也并不少見。24諸如蘋果公司與深圳唯冠公司“iPad”商標權屬糾紛案中的許可關系。在著作權許可中,作為雇主的職務作品被許可人無論如何不為弱勢一方。同樣,相對于出版社,作為許可方的作者才是差距懸殊的弱勢當事人。我們無法確定被許可人總是構成許可合同的弱勢一方,甚至無須衡量被許可人是否達到與不動產承租人旗鼓相當的弱勢程度。最后,由于專利技術無法被占有或者實際控制,新專利權人可能難以獲悉在先許可的存在。25對比適用《德國民法典》第566條對于“überlassung”租賃物的要求,參見§ 566, H?ublein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GB) (6. Au fl.) 2012, Rn 14.與動產或不動產的買賣不破租賃制度相比,新專利權人在轉讓人有意隱瞞的情形下,其利益所受威脅較新所有權人程度更為顯著。基于權利外觀程度的差異,以及被許可人、承租人分別在與新權利人利益平衡的對比下,無法得出許可領域可以簡單沿襲買賣不破租賃的結論。
四、法政策的導向價值
租賃規范中“買賣不破租賃”類推適用的失敗,標志著既有法律所確定的交易秩序在公平和安全兩方面的價值取向上,并沒有對“買賣不破許可”作出特定的要求。如果許可合同當事人以及新知識產權人三方關系的分析,能夠證明許可的特殊性決定了對被許可人的特別保護不可或缺,則應該設立新的強制性規范來阻止轉讓擊破許可。甚至,在我國缺少發達的法律和法學雙重精密性所制約的現階段,盡管略顯簡單粗暴,將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和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強行解釋為轉讓不破許可。在激勵機制色彩異常濃厚的知識產權領域,尊重促進交易繁榮的價值導向,與法律體系內的邏輯推理正確具有至少近似程度的重要性。
(一)許可數量與轉讓頻率之間的選擇
《合同法》第323條揭示我國現有法律體系內技術合同類型的存在價值,并準確反映立法者意志。法律要求技術合同應當“有利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加速科學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和推廣。”專利轉讓不破在先許可的制度安排,在客觀上可以促進更多數量許可證的發放,26否則使得“投資者望而卻步”,參見林廣海、邱永清:《專利權、專利許可使用權與專利許可合同——以物權法原理借鑒為視點》,載《法律適用》2008年06期,第18頁。從而使技術在同一時期得以被更多的市場主體所使用。當然,許可人嚴格履行合同義務的獨占許可除外。然而以此推斷轉讓不破在先許可的制度安排必然促進技術在市場中更好應用和推廣,甚至更有利于科技進步,該結論并不總是顯得可靠。因為不破許可雖然可能會擴展同一時期內使用者的數量和范圍,但同時會降低專利權在市場上的流通速度。而擊破許可的制度安排恰恰可以刺激專利權的買賣交易。換言之,更多的被許可人僅能代表更龐大的使用者數量,而這些使用人共同構成的技術應用范圍,并不必然大于一個新專利權人對技術的應用范圍。實踐中,絕大多數專利并沒有被權利人親自使用或者授權他人使用,制造企業申請專利的戰略目的首先是借助禁用權劃分技術領域,進而達到劃分市場份額和提高利潤的目的。“技術更好的應用和推廣”和轉讓是否擊破許可似乎沒有必然內在關聯。何種模式可以使技術在禁用權整個有效期內的使用更為廣泛和高效,從而更好實現《合同法》第323條所確立的追求科技應用、推廣和進步的目的,似乎只能在做出具體情形的分析后得出定論。到底是追求同一時期內更多的使用者數量,還是追求專利技術在整個專利有效期內更為流暢和頻繁的交易,僅僅是一個并未包含價值評判的政策取向。傾斜新權利人,或者傾斜被許可人的政策取向并不關乎技術合同法確立的技術交易原則。至于商標和著作權權利的客體的交易,則更加無法推斷出法律應該更加傾向于許可合同被許可人,還是潛在的權利繼受人。一個確定的理由似乎并不存在。
(二)帝王條款誠信原則下的信賴利益保護
為了使用知識產權客體,被許可人通常會投入高額資金。27同注釋?。基于對許可合同內容的信賴而投入的資金應當受到法律保護。28同注釋?。基于此,法律不應該籠統規定轉讓不破許可。立法者必須區分被許可人是否已經開始為生產著手準備工作。如果僅僅是單純地簽訂了許可合同,而被許可人還沒有開始著手準備生產,則立法者完全沒有理由以信賴利益的保護為由來加重新權利人的負擔。29對比適用《德國民法典》第566條對于“überlassung”的要求,參見§566, H?ublein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GB) (6. Aufl.) 2012, Rn 14;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II Besonderer Teil, 2014,17 Aufl. Rn.497;Brox/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4 Au fl. 2010, p. 191.換言之,轉讓不破剛剛簽署的、尚未來得及著手開始準備履行的許可合同是極為荒謬的。如果被許可人已經開始著手制造準備,那么對這種信賴利益的保護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實現。第一,禁止新權利人行使禁用權。第二,由許可人承擔因轉讓而無法繼續履行合同義務的違約賠償責任。被許可人為了準備生產而進行的投資(至少部分)會落空,甚至包括與新專利權人的談判也會產生額外的交易成本,以及可以期待的收益,均為被許可人的損失。該類損害應該通過實現違約責任的方式得到填補,因為很難想象的是,由無法繼續使用專利而引發的損失會比專利本身的價值(轉讓專利的收益作為責任財產)還大。30德國法下重要擔憂為支付能力,如Fromut V?lp,Weitergeltung der Lizenz bei Ver?u?erung des Schutzrechts GRUR 1983, 45 .只有在許可人處于破產程序,破產管理人轉讓知識產權的情形下,被許可人的處境將會極度困難。因此,立法者可以考慮是否有必要單獨規定許可方企業破產程序中的知識產權轉讓不破許可,賦予被許可人繼續使用的權利。以轉讓不破許可籠統平衡三方利益,并不可取。
綜上可見,轉讓是否擊破許可并沒有由現行法律明確作出規定,是否應當作出取決于實證研究的結果。現有文獻的梳理未能發現實證考察,其也不是本文的初步研究的對象或是本文篇幅所能涵蓋的內容。結論會因個案的不同而呈現較為顯著的差異。
五、在先許可絕對權屬性之排除
在維持現有財產權利構造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在先許可無法被立法者重新賦予絕對權屬性。詳言之,許可證的發放既不能被視為具有對世效力用益權的設定,也不能被視為部分權利轉讓。
(一)在先許可用益權屬性的缺失
被許可人依據許可合同所獲得的權利,由于在時間、地域以及權利內容方面均可任意由當事人雙方約定,而具有(無限)高度任意性。如果該權利被上升為可以面向任意第三人產生法律約束力的用益權,則相對權和絕對權的界限在知識產權領域內將不復存在。此類基于當事人私人設定的用益權的出現,將顛覆潘德克吞體系賴以存在的根基。盡管如此,仍然有眾多學者和法官支持用益權說。
第一,獨占許可不是知識產權用益權。有學者視獨占許可為知識產權用益權。31溫世楊:《財產支配權論要》,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5期,第66-67頁;邱永清著:《專利許可合同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頁。有學者的表達沒有如此明確,但認為商標權人轉讓商標甚至需要被許可人的同意,參見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頁;李明德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頁; 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頁。其用于支持用益權性質的理由,即關于被許可人權利是與權利人相當的支配權的論述,32例如邱永清著:《專利許可合同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頁。有待商榷。因為現有法律規定并沒有賦予獨占被許可人直接對抗許可人和在后的被許可人的力量。首先,獨占被許可人沒有禁止許可人使用的權利。獨占許可人為其使用行為僅承擔違約責任。侵權責任并不存在,即獨占被許可權作為合同債權無法被(無論第三人抑或債務人)侵害。其次,如果在后被許可人基于有效的許可協議使用知識產權,獨占被許可人不能起訴,因為不存在侵權行為的時候,商標法司法解釋第4條無法適用。商標法司法解釋第4條僅允許被許可人起訴實施商標權侵權行為第三人。暫不討論該條款賦予被許可人訴權的正當性,33詳見張軼:《論專利獨占被許可人的訴權》,載《知識產權》2018年第1期,第19-26頁。基于權利人授權使用知識產權客體的在后被許可人,其行為不會觸及任何現行知識產權規范的侵權行為條款,從而當然能夠繼續其使用行為。最后,獨占被許可人權利的消極內涵,很難使其權利主體直接支配權利客體。34參見張軼:《中國專利消極許可的構建》,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第1-8頁。甚至真正的權利人,也只是借助法律禁止他人使用來實現間接控制其客體的效果。
第二,普通許可不是支配權。有法官基于轉讓不破租賃的規則,甚至認為普通許可也是支配權。35邱永清著:《專利許可合同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頁、第55頁。然而上文分析清楚表明,關于中國法律直接確立了轉讓不破許可的認知,除權利人為作者的獨占職務作品外,原則上并不符合既有法律規定的實然狀態。立法論層面是否應該作出轉讓不破許可的規定,還取決于(結論尚不確定的)新權利人與被許可人的利益權衡,減少被許可人的投資損失等考量。直接誤讀法律沒有的、關于普通許可不為轉讓所破的規定,得出普通許可為絕對權的結論,有因果關系倒置之嫌。
第三,域外法律不具有證明功能。有我國法官以德國的Klauer/M?hring專利法評論為佐證,36同注釋32。試圖得出獨占許可為物權或準物權的結論。37這里物權以及準物權概念的使用不妥,對于“物權”(Dingliches Recht)或“絕對權”(Absolutes Recht)的表述,見Zhang Yi,Der Lizenzvertrag im chinesischen Schutz- und Schuldrecht, Herbert Utz Verlag, 5.2014,P35. 關于準物權概念的規范使用,參見崔建遠著:《物權:規范與學說——以中國物權法的解釋論為中心》,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656頁。該觀點有待商榷。首先,德國法下專利轉讓合同的登記功能與中國法所持基本態度不同。由于德國法下專利權轉讓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所以在挑戰立法者權利生成原則基本態度之前,從權利生產可能性角度判斷以內容私人意定的獨占許可是否可以具有對世效力(所謂的物權性或準物權性)的法律基礎截然不同。38由于在學界主流觀念中沒有絕對權種類限制(Numerus Clausus)的約束,各種類型的分割及轉讓在德國法下被普遍認可,如Kra?er, Verpf l ichtung und Verfügung im Immaterialgüterrecht, GRUR Int. 1973, 230 f.; Die Wirkung der einfachen Patentlizenz, GRUR Int. 1983,537ボ;但也存在個別反對觀點,如 Rosenberger, Zur Frage des Fortbestandes der einfachen Lizenz bei übertragung des Patents, GRUR 1983,203ボ.絕對權權利類型法定不適用于知識產權領域基本成為德國通說觀點,Forkel, Zur dinglichen Wirkung einfacher Lizenzen, NJW 1983,1764ボ.; Gebundene Rechtsübertragung [Habil.], 67 ボ.; Kra?er, Die Wirkung der einfachen Patentlizenz, GRUR Int. 1983, 537ボ.; Verpflichtung und Verfügung im Immaterialgüterrecht, GRUR Int. 1973, 230 ボ.; Der Schutz vertraglicher Rechte gegen Eingriボe Dritter [Habil.], 113f.; Krieger,Die gemeinschaftliche Benutzung von Warenzeichen durch mehrere Unternehmen nach deutschem Recht in Beier/ Deutsch/Fikentscher, Die Warenzeichenlizenz, 46.其次,Klauer/M?hring就獨占許可為物權或準物權的觀點在德國本土并非沒有遭到有力質疑。39持反對意見的代表性文獻,例如R. M Hilty, Lizenzvertragsrecht: Systematisierung und Typisierung aus schutz- und schuldrechtlicher Sicht, Bern 2001, S.147f.對以概念為鮮明法學研究背景下許可和轉讓概念邊界的模糊,甚至混同,應當予以修正。40See R. M Hilty, Lizenzvertragsrecht: Systematisierung und Typisierung aus schutz- und schuldrechtlicher Sicht, Bern 2001, S.147ボ.所以,該觀點在德國法下的自洽性以及正確性,依然需要深入探討。再次,至于普通許可是準物權觀點,41轉引自邱永清著:《專利許可合同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頁;該文引用Schriker與Ulmer兩位德國學者關于著作權的著作來說明普通專利許可的絕對權效力問題,但并未解釋德國學界在專利領域和著作權領域的不同認知。德國法中的確有過普通專利許可為絕對權性質的觀點,該觀點主要存在于較為久遠的文章,頗具代表性的有如Forkel Hans,Zur dinglichen Wirkung einfacher Lizenzen,NJW 1983, 1764-1768;持相反意見的代表性文獻主要為Stumpf/Gro?, Der Lizenzvertrag, 8 Au fl. Heidelberg, 2005,Rz39;See Kra?er, Patentrecht,Ein Lehr- und Handbuch zum deutschen Patent- und Gebrauchsmusterrecht, europ?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Patentrecht,6Au fl. München, §40,更多相似文獻此處不再羅列。在德國不僅并非主流,事實上更是早已飽受非議。42Stumpf/Gro?, Der Lizenzvertrag, 8 Au fl. Heidelberg, 2005,Rz39;See Kra?er, Patentrecht,Ein Lehr- und Handbuch zum deutschen Patentund Gebrauchsmusterrecht, europ?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Patentrecht, 6Au fl. München, §40.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對我國某一具體法律制度的描述、分析以及合理性論證,有別于對客觀存在事物或普遍自然規律的發現。即使該制度與外國法高度近似、甚至重合,但無論是德國立法中的某項具體規定,還是德國學者對于德國法下許可證性質的論斷,都無法成為我們推斷中國知識產權制度下許可債權屬性抑或物權屬性的理由,更無法作為中國法律作出某一具體規定的基礎或依據。
(二)在先許可權利部分轉讓屬性的缺失
暫且放緩對潘德克吞民法體系這一宏觀背景的關注,或者突破絕對權類型法定和物債二元的約束,知識產權體系內部分具體條文也間接排斥了時間或地域受限的專利轉讓或者商標轉讓。由于法律規定專利權、商標權的轉讓從登記、公告開始生效,43《專利法》第10條;《商標法》第42條。與之相對,轉讓合同的登記在德國法下僅具有宣示功能,對于權利轉讓的效力則不產生任何影響,Kra?er, Patentrecht, 5. Au fl. 2004, § 23 Va 2;中國立法者對于登記效力的基本態度是諸多域外制度能否被借鑒的前置條件;這也這是直接借鑒德國法具體規則產生錯誤的根源所在。僅對權利的產生。而帶有期限或地域限制的專利權和商標權無法被登記,所以當事人就無法對該區域或期限內的專利權或商標權進行轉讓。如果獨占許可構成部分權利的轉讓,則法律為專利和商標轉讓設定的強制性規定,以及由此彰顯的立法者就權利變動中登記簿功能及權利公示的作用的基本態度,就必然會被規避和改變。而該認知恰恰與一國市場主體誠信水平和普遍交易習慣密切相關,而難以從學理角度自上而下在知識產權單獨一個部門法內部予以改造。這顯然構成立法者難以接受的法律內部邏輯沖突。沒有期限或地域限制的專利商標許可構成權利整體轉讓,同樣會涉及法律規避問題,比如,《專利法》第10條要求中國人向外國人轉讓專利權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手續。因此,將在先許可的本質視為部分知識產權權利的轉讓,從而支持轉讓不破許可的正當性,也無法取得期待效果。
結 語
綜上所述,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以及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尚未確立轉讓不破許可制度。即便立法者希望以法定例外的方式確立該制度,那么現行技術合同司法解釋第24條和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20條充滿歧義的表達也難當此任。確立轉讓不破許可的表述似乎應該是:“……讓與人與受讓人訂立的專利權轉讓合同,新的專利權人不得禁止合同成立前讓與人與他人訂立的相關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在許可合同范圍內繼續實施專利”,以及“注冊商標的轉讓后,新的商標權人不得禁止轉讓前已經生效的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在許可合同范圍內繼續使用商標……”44《合同法》第229條應當區分動產和不動產。然而,這種變動并不必要,因為,在現有法律體系看來,“轉讓不破許可”的制度建立基礎只能是平衡特定利益考量的結果。而這種考量,或者說知識產權許可和轉讓關系的特殊性,似乎——在更充分的實證考察被做出之前——并不足以突破既有民法理論基石層面的原則而制定例外。換言之,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以增設法條或者修訂現有法條的方式確立“轉讓不破許可”規則,來改變當下法律的現實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