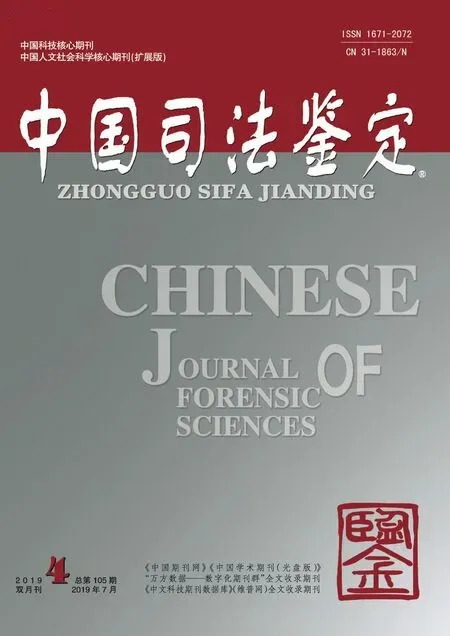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被告身份及民事責任的反思與省察
郭華
(中央財經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1)
目前,理論界對法院將司法鑒定機構作為被告以及裁判其鑒定過錯承擔賠償問題的討論甚囂塵上,特別是“法院親子鑒定出錯,女子錯養兒子23年!狀告河南高院索賠295萬案件”以及因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鑒定中心的醫療過失參與度鑒定意見,法院判決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的案件,不僅引發司法鑒定界的熱烈討論與激烈爭論,也引起法學界對此問題的再度思考與重新審視。本文對司法鑒定機構及其鑒定人在鑒定意見作為證據的案件能否作為被告以及應否承當民事責任問題略加探討,希冀引起學界與實務界對此問題的特別關注與深入探討。
1 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因鑒定問題應否作為被告
當事人對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提供的鑒定意見有異議或認為存在錯誤,或者認為鑒定行為或提供的鑒定意見給其造成損害能否提起訴訟,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均曾給出否定性的答案和回應。因為“鑒定機構受法院委托出具鑒定意見書是一項輔助證明活動,是法院司法行為的延伸。在訴訟活動過程中,鑒定意見的合法性、真實性是由人民法院通過審查、質證及重新鑒定、補充鑒定等程序設置來實現的。當事人如持有異議,單獨就鑒定意見或鑒定行為提起效力確認之訴的,應裁定不予受理。[1]”而現實案件的裁判卻又呈現出“圍剿”司法鑒定的另外一番場景。
案例11995年12月,河南蘭考縣公安局在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中解救了一批被拐賣兒童,其中被取名為許某某的男孩疑似為朱某某的兒子。為慎重起見,朱某某夫妻倆決定做DNA鑒定,蘭考縣公安局遂委托河南省高院做親子鑒定,朱某某夫妻繳納了1 500元鑒定費。1996年1月15日,河南省高院出具了(1995)豫法醫鑒字第19號《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親子關系鑒定》,結論為許某某與朱某某夫妻具有生物學親子關系。2018年1月,有媒體報道稱四川南充一名叫何某某的女子曾到當地警方主動投案,稱她早在1992年從重慶渝中區解放碑抱走一名小男孩,后取名劉某某,對方如今已長大成人,多年來一直跟隨她生活在南充順慶區,自稱想贖罪要替他尋找親生父母。2018年3月,朱某某收到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的《DNA檢驗報告》,確定她與許某某的親權關系不成立,與劉某某的親權關系成立。隨后,朱某某向重慶渝中區法院提起訴訟,索賠各類損失共計295萬余元。2018年3月25日,渝中區法院經審查認為,她的起訴符合法定受理條件,決定立案審理。河南高院對此予以答辯,并表示,他們對此高度重視,通過咨詢有關專家,積極查找鑒定意見出現錯誤的原因。他們了解到,DNA指紋檢測技術于上世紀90年代初引入我國,由于實驗環節復雜、技術要求嚴格,特別是實驗方法難以標準化等原因,該項技術存在局限性。自9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PCR-STR分型技術的推廣與應用,DNA指紋檢測技術逐步被更加成熟的技術取代。由此認為,由于技術條件所限,他們1996年出具的案涉親子關系鑒定結論錯誤,為此向朱某某深表歉意,秉持最大的誠意在訴訟全過程繼續與朱某某女士協商、和解;尊重、接受合法公正的判決結果,愿意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①參見李興罡:《重慶一母親狀告河南高院 索賠295萬》,《華西都市報》2019年6月10日第A3版;《法院親子鑒定出錯致錯養兒子23年 母親狀告法院索賠295萬》,《云南法制報》2019年6月12日.。
對于此案的探討,我們撇開河南高院作為提供鑒定意見特殊主體的身份不作分析,僅就其出具鑒定意見的機構作為被告進行探討,可以發現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作出鑒定意見的鑒定機構能否作為被告?這一問題涉及到鑒定意見是否可以作為訴訟標的?又進一步延伸到鑒定機構及鑒定人作出鑒定意見的行為屬于何種行為?也就是說,對此問題的探討應基于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作出鑒定意見的行為來分析以及其提供鑒定意見是否具有可訴性來論證。
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做出鑒定意見的行為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取決于我國的訴訟制度和鑒定制度。我國訴訟模式在改革前屬于超職權主義,改革后為職權主義并攜帶了當事人主義的色彩,然而依附于原超職權主義的鑒定制度并未隨之變動。在訴訟中,司法鑒定的啟動權依然由職權機關獨享,盡管在民事訴訟之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允許當事人自行委托鑒定②參見200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八條規定:“一方當事人自行委托有關部門作出的鑒定結論,另一方當事人有證據足以反駁并申請重新鑒定,法院應予準許”。。但是,對這種訴前鑒定是否屬于司法鑒定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存在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當事人訴前委托進行的鑒定不屬于司法鑒定。只有在訴訟活動中進行的鑒定才符合司法鑒定的定義,而對訴訟活動的開始較為普遍的理解是以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開始。即法院的訴訟活動尚未啟動,因此不屬于司法鑒定。另一種觀點認為,對于司法鑒定不應機械地理解為在訴訟過程中進行的鑒定,還應當包括為了解決舉證中的專門性問題,而在立案前進行的鑒定。在訴前委托進行鑒定的結論在司法活動中可能會作為證據使用,其鑒定屬于司法鑒定[2]。上述不同觀點是因不同的判斷依據造成的,與鑒定本身無關。依據上述觀點還無法解決司法鑒定機構能否作為被告的問題。基于此,司法鑒定行為的性質界定需從以下二方面進行分析。
1.1 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與司法鑒定機構的被告地位
無論是我國《刑事訴訟法》還是《民事訴訟法》均未賦予當事人啟動鑒定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請,可以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實的專門性問題向人民法院申請鑒定。當事人申請鑒定的,由雙方當事人協商確定具備資格的鑒定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當事人未申請鑒定,人民法院對專門性問題認為需要鑒定的,應當委托具備資格的鑒定人進行鑒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當事人申請鑒定,可以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申請鑒定的事項與待證事實無關聯,或者對證明待證事實無意義的,人民法院不予準許。”在民事訴訟中,無論是法院基于當事人協商一致委托的鑒定還是協商不一致或者法院依職權指定的鑒定,其鑒定的實質啟動權均歸屬于法院,其鑒定的委托人均為法院。那么,對于法院委托或者指定的鑒定機構或者鑒定人進行的鑒定行為,必然與法院產生相應的法律關系。由于法院委托或者指定的司法鑒定需要當事人繳納鑒定費用,當事人這種繳納鑒定費用的行為是否也與鑒定機構及鑒定人產生法律關系呢?有觀點認為,鑒定機構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技術、設備獨立鑒定系受法院委托,鑒定意見本身并不能直接確定當事人具體的權利義務,也不是對當事人的人身權、財產權進行直接處理,鑒定意見是否發揮作用、是否被采信、對當事人的利益能否產生影響,均取決于委托的法院,如果鑒定意見沒有被法院采信,當然不會對當事人產生法律上的影響。盡管鑒定意見與當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但鑒定機構依法履行職責,只對委托法院負責,與當事人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情況下當事人不能起訴鑒定機構[1]。在原告魏某某訴北京盛唐司法鑒定所侵權責任糾紛一案中③參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20524號民事裁定書。,法院認為,在該案件審理過程中,魏某某向西城法院申請司法鑒定,經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隨機確定鑒定機構,西城法院委托盛唐司法所就北京積水潭醫院對魏某某治療行為有無過錯、過錯程度及與魏某某肩膀骨折有無因果關系進行鑒定。在西城法院向盛唐司法所的委托鑒定函上寫明鑒定費由原告方即魏某某先行負擔。雖魏某某向盛唐司法所交納了鑒定費用一萬元,但該行為系其在西城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為查明案件事實所進行的訴訟行為,并非其直接委托盛唐司法所進行的鑒定行為,故該案中,魏某某與盛唐司法所之間并非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不屬于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故本院依法予以駁回。再如,再審請人謝某某與被申請人東南司法鑒定中心侵權糾紛一案,法院認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鑒定機構作出司法鑒定僅是民事訴訟證據形成之一,其并不具有可訴性,一、二審駁回起訴并無不當④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蘇民申2566號民事裁定書。。司法實踐的態度是明確的,厘清了司法鑒定行為性質、鑒定作為證據與委托的職權機關以及當事人的關系。
鑒定意見作為法定證據的種類,是因職權機關在訴訟中就專門性問題委托鑒定機構進行鑒定而得出的意見,當事人委托的鑒定并不必然作為證據,即使當事人委托專家就專門性問題作出的解釋,僅僅作為當事人的陳述,也不是獨立的證據種類之一。作為證據的鑒定意見不是證明對象,僅僅是鑒定人對專門性問題或者其他證據的判斷與解讀,在一定意義上與其他證據類型不同。基于此,職權機關委托或者聘請的鑒定,不應是人民法院審理和裁判的對象,也不屬于訴訟標的范圍,因此,當事人不得針對鑒定意見提起訴訟。如果該證據在程序上或實體上存在的問題,當事人應當請求審理法院依法委托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但其申請能否得到批準,還應由審理法院決定[3]。基于當事人并不是司法鑒定的委托人,其與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之間不存在直接的法律關系,盡管民事訴訟中的鑒定費用由當事人承擔,但因當事人不繳納鑒定費用而不啟動鑒定,這種不啟動源于法院,因為司法鑒定機構承擔著不得拒絕法院委托的職責。即使鑒定機構及鑒定人提供鑒定意見,其意見是否作為證據依然取決于職權機關,對當事人權益影響是職權機關的權力而非鑒定行為。鑒定是“對有關專門性問題作出判斷,而不是對有關事實問題作出法律評價”,因鑒定意見是鑒定人基于專門性問題提供的判斷性意見,是對專門性問題的認識,僅僅涉及事實問題,不是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也不是法律判斷,其本身是法庭需要查證屬實的對象,不直接影響對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進行調整[4]。因此,當事人以鑒定過錯或者鑒定意見錯誤為由起訴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就會因缺失訴訟標的而無法成為真正的訴,鑒定機構和鑒定人不屬于適格的被告,法院對此應當不予受理。
1.2 司法鑒定行政管理制度影響了鑒定機構的被告身份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一條規定:“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從我國司法鑒定管理制度來看,《決定》強調訴訟活動中對案件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的活動,那么,鑒定是否在訴訟中啟動便成為衡量是否受《決定》調整的關鍵。因此,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做出的鑒定意見能否作為證據不完全受《決定》的調整,也不在司法鑒定行政管理的范圍。無論是鑒定行為還是鑒定意見均受制于職權機關,其影響也取決于職權機關的職權,如果當事人以對自己權益無影響的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作為被告,因行政管理部門的責任追究也就失去了可能,否則,出現責任的重復追究問題。如果鑒定是當事人直接委托的,沒有法院或者其他職權機關任何意志參與,當事人直接與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必然存在民事上法律關系,對此,不應排除當事人起訴鑒定機構或者鑒定人的權利。
司法鑒定行為既不是行政行為⑤在貨幣真偽鑒定中存在不同意見,但法院毅然選擇了不是行政行為的認定。參見宋剛,寇秉輝.貨幣真偽鑒定行為不具有可訴性[J] .人民司法,2013(22):103-105。,也不是司法行為,因為司法權不得委托,也不宜簡單稱為法律服務行為,其旨在補充職權機關在認識上的困難和能力的不足,是協助職權機關解決專門性問題的司法保障行為。但司法實踐也存在將此認定為司法行為的裁判。例如,湖北省上訴人程某某不服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人民法院(2015)鄂洪山民三初字第00756號民事裁定與被上訴人武漢平安法醫司法鑒定所侵權責任糾紛一案的一審判決認為:“平安鑒定所根據武漢市公安局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分局的委托,對案外人鄭某的損傷進行鑒定后所出具的武平安法(2015)臨鑒字第389號法醫鑒定書,屬于證據的一種形式,和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其他證據一樣,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被告在鑒定過程中是否存在過錯,法醫鑒定書是否應該采信,應由委托鑒定的辦案機關進行審查,屬于司法行為。⑥參見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6)鄂01民終4024號。”這種通過司法行為的界定來繞開鑒定機構及鑒定人作為被告的困境雖然具有意義,但其性質認定卻值得商榷,因為辦案機關審查行為的性質與其審查對象的性質不應混同。但其觀點背后折射出的司法鑒定行為具有不可訴性依然不失其實踐價值。
2 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承擔何種民事責任
《決定》作為司法鑒定管理的法律文件在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的法律責任上僅僅規定了其行政責任以及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問題,即“鑒定人故意作虛假鑒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罰。”對其是否承擔民事責任沒有作出相應規定。對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規定民事責任源于司法部的行政規章。《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司法鑒定機構在開展司法鑒定活動中因違法和過錯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按照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執行。”《司法鑒定人登記管理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司法鑒定人違法執業或因過錯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司法鑒定機構承擔賠償責任。司法鑒定機構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的司法鑒定人追償。”那么,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因鑒定存在過錯是承擔民事責任以及應當承擔何種責任,是需要討論的問題。然而,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7)豫01民終3964號】認定為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鑒定中心的鑒定行為有過錯,判決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案件⑦參見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7)豫01民終3964號。,再次引發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案例2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認定事實:原告因醫療損害賠償糾紛訴至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被告經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委托對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對原告的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在醫療行為與萬謙的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及過錯參與度,以及萬謙現在是否適宜評定傷殘及傷殘等級進行鑒定。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鑒定中心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鑒定中心法醫臨床司法鑒定意見書》(豫司警院司法鑒定中心【2012】臨鑒字第340號)鑒定意見為: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對被鑒定人萬謙的醫療行為存在過錯,其過錯和被鑒定人萬謙目前的智能障礙有因果關系,過錯參與度為25%。被鑒定人萬謙目前構成二級傷殘。原告對《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鑒定中心法醫臨床司法鑒定意見書》中的第一項鑒定意見不服,并多次要求進行重新鑒定,期間單方委托北京京城明鑒醫學科技有限公司進行司法鑒定論證,北京京城明鑒醫學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作出了《法醫鑒定論證意見書》(京法【2013】醫鑒論字第029號)論證意見為: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對患兒萬某的診療行為存在醫療過失,該醫療過失與被鑒定人損害后果(去皮層狀態)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醫療過失參與度建議擬80%~90%。患兒萬某目前腦部呈彌漫性、不可逆損害,已構成一級傷殘。被告認為《法醫鑒定論證意見書》程序違法,且京城明鑒醫學科技有限公司不具有鑒定資質,不予認可。后雙方同意重新鑒定。鄭州市二七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依法委托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進行司法鑒定。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了《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鑒定意見書》(司鑒中心[2015] 臨鑒字第1529號)鑒定意見為: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對被鑒定人萬某的診療行為存在過錯,醫療過錯與萬某的損害后果(缺氧缺血性腦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醫療過錯系主要因素,參與度擬為60%~80%)。被鑒定人萬某屬于完全護理依賴(護理人數建議為2人)。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中采用75%的醫療過失參與度。庭審時原告方稱,原告因重新鑒定造成的損失包括:北京鑒定費4000元,北京鑒定人員出庭質證費5000元,車票(以原告舉證為準),在上海開的聽證會花費15 779元+1 277元,共計29826.5元;2012年至2014年原告因訴訟借款產生的利息20 000元、耕地無人看管雇人看管土地種植產生的費用2 8000元、將40畝的麥苗以40000元的價格賣給別人,別人轉賣61 000元,直接損失21 000元、雇人干活10000元。以上共計108826.5元。一審法院判決如下:一、被告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鑒定中心于本案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支付原告萬謙賠償款10萬元;二、駁回原告萬某的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2300元,由被告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鑒定中心負擔。
基于以上判決的說理與引用的依據以及司法鑒定管理部門規章對民事責任的規定,我們認為需要討論以下問題:
2.1 行政管理規章應否需要規定民事責任問題
根據《立法法》第八十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權限范圍內,制定規章。”“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于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而《決定》沒有對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在司法鑒定過程中的民事責任作出規定,司法部《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作為“執行性”的立法而非補充性立法,有無必要規定民事責任呢?對此需要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是按照《決定》的規定和精神對司法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實行行政上登記管理,對于違反法律或者規章的,司法行政部門有權讓其承擔行政責任。民事責任也不是違反行政管理的責任,司法鑒定機構“按照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執行”不屬于行政管理權限范圍內的事項。“凡不屬于本部門管理的事項,不要在本部門規章中規定,[5]”法律法規可以設定訴權⑧不可否認,目前存在一些“涉民性”和“民事性”的行政規章,即使如此,其行政權僅僅作為嵌入式的調整,也不直接調整民事法律關系。。基于司法鑒定不屬于涉民性規章且無創新性立法的空間,無需創設《決定》沒有涉及的民事權利、義務或者責任的規則,僅僅對違反登記管理的行政責任以及涉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移送職責作出規定即可。況且,與之相應的《公安機關鑒定人登記管理辦法》也未規定。
二是司法實踐對規章的規定存在不支持的觀點。例如,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1242號的民事裁定認為:再審申請人安徽同聚祥實業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安徽梅龍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梅龍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中因鑒定機構違反原建設部辦公廳《關于對工程造價司法鑒定有關問題的復函》(建辦標函【2005】155號)規定的“從事工程造價司法鑒定,必須取得工程造價咨詢資質,并在其資質許可范圍內從事工程造價咨詢活動。工程造價成果文件,應當由造價工程師簽字,加蓋執業專用章和單位公章后有效”的資質等級規定,最高法院認為:(1)部門規章的規定不能直接導致鑒定無效;(2)鑒定時雙方對鑒定機構的乙級資質是明知的,但并未提出異議,而且當時也并不知道鑒定工程造價會超過5 000萬元,也就是當時選擇乙級資質鑒定機構并不存在過錯;(3)在鑒定過程中鑒定機構作出的鑒定意見經過質詢、復核等系列環節,程序到位,如果再重新鑒定,顯然浪費司法資源。
基于此,有必要在修改《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和《司法鑒定人登記管理辦法》時刪除有關民事責任的規定,僅僅依據《決定》規定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的行政責任以及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2.2 基于鑒定意見存在錯誤是否承擔民事責任問題
在上述河南的案例中,其判決書將司法鑒定委托確認為“有償的委托合同”,并依照我國《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條“有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過錯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的規定作出裁判。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鑒定人出具錯誤鑒定所謂給當事人造成損失而承擔責任的依據何在?承擔的是何種責任?責任主體是鑒定機構還是鑒定人本身?針對上述裁判,澄清這些疑問,需要追問司法鑒定的委托是有償合同嗎?如果不是,應當屬于何種類型的合同?
一是從國外的考察來看,專家證人和普通證人的法律地位相同。為了消除專家證人作證的顧慮,如果專家證人出具虛假證詞損害了對方當事人的利益,英美法系國家認為,專家證人應享有證人的作證豁免權。在這種情況下,對于鑒定人出于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作出錯誤鑒定導致對當事人的損害,大陸法系國家一般追究鑒定人的侵權責任[6]。我國的司法鑒定與英美法系國家的專家證人不同,也不完全同于大陸法系,不僅鑒定意見作為獨立的法定證據種類,而且還存在一個專司司法鑒定登記管理的行政部門,這些制度使得鑒定出現錯誤或者制裁錯誤鑒定的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的責任主要限于行政處罰,通過當事人投訴以及管理過程中發現和其他職能機關建議等方式予以行政處理,而非是通過民事責任的方式解決。《決定》規定“司法鑒定實行鑒定人負責制”,況且司法鑒定機構還承擔不得拒絕接受職權機關委托的行政責任。為了“保證鑒定人的內部獨立性,這應使得他能在不存在可能的賠償壓力的情況下出具鑒定書”[7],因此,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鑒定過錯可以通過行政責任解決,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相比,前者更能發揮防范鑒定錯誤的功能,可以剝奪其鑒定資格或者終身不授予鑒定資格,民事責任也就必然被放逐管理的范圍。
二是從我國訴訟原理來分析,我國的司法鑒定除了訴前的當事人的特殊委托外,訴訟中的委托均屬職權機關的職權行為,當事人沒有直接委托鑒定的權利。這種職權機關基于職權的委托不同于一般民事委托。一般的民事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處理委托人事務,并在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務后,委托方支付費用的合同。職權機關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鑒定,司法鑒定機構與職權機構之間形成了非平等性的委托和受委托關系,但因費用由當事人承擔,形成了不同于民事委托的訴訟法律關系,而非民事法律關系,法律關系的性質不同。如果因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給當事人造成損害,因當事人與鑒定機構及鑒定人不具有委托和受委托的合同關系,當事人要求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承擔的法律責任也就失去依據。理論上講,鑒定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不會直接給當事人造成損害,其損害是職權機關委托錯誤或者采用了錯誤的鑒定意見造成的,在一定意義上是職權機關未能履行職責造成的。如果當事人自己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鑒定,就相當于民間委托,即當事人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鑒定,其鑒定啟動屬于當事人與鑒定機構的合意(有些鑒定機構不接受當事人委托,這種不接受委托不負任何責任),由委托的當事人支付司法鑒定費用,可以按照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依法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然而,有觀點認為,法院委托的鑒定,不論鑒定機構的行為如何(如不接受鑒定委托、接受鑒定委托進行鑒定或鑒定結果如何),都不會給法院作為委托人造成損失,只有可能給沒有參加委托的當事人一方造成損失。所以,在法院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鑒定的情況下,當事人要求司法鑒定機構承擔的不應是違約責任而只能是侵權責任。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三條、第六條第一款的規定:“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如果法院對原告提起的訴訟不予受理,那么,在法院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進行司法鑒定時,由于另一方當事人與司法鑒定人惡意串通或者是在鑒定人因過錯而損害了一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一方當事人要通過什么途徑才能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呢?我們認為,在當事人自行或者訴前委托鑒定機構進行鑒定時,鑒定機構作出的鑒定意見一般都對委托鑒定的當事人有利。如果鑒定機構故意作出了對委托鑒定的人有利的鑒定意見,正常情況下不會給另一方當事人的民事權益帶來損害,另一方當事人完全可以不認可該鑒定意見。如果當事人委托鑒定,鑒定機構作出的鑒定意見存在錯誤,導致委托鑒定人重新申請鑒定而損害了委托鑒定人的利益,可以認為受委托的鑒定機構未認真履行委托合同,鑒定機構的行為可以認定為一種違約行為,要求鑒定機構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因鑒定錯誤給委托鑒定當事人一方造成的損失。
基于以上的討論,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因自己的過錯是否需要承擔責任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承擔的這種責任不僅存在自行鑒定的違約責任,還存在鑒定過程中導致被鑒定直接損害的侵權責任。對于鑒定意見而言,盡管司法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存在過錯,其過錯導致裁判錯誤,卻是因職權機關的意志參與所導致的,將其納入國家賠償更為適宜。如果鑒定是當事人訴前自行鑒定導致的損害,或者鑒定人在進行鑒定時直接損害被鑒定人的人身或財產權利,鑒定人與被鑒定人之間產生了侵權的法律關系,此時,受到損害的被鑒定人可以依照侵權法的規定要求鑒定人承擔賠償責任,法院對此類案件應當受理,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可以作為被告并承擔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導致的民事責任,對于一般的過錯責任,則需要豁免,以保持鑒定人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