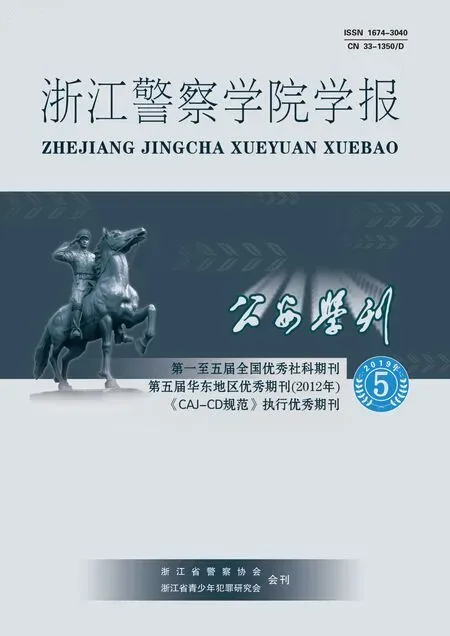不是“切除”而是“治愈”
——“楓橋經(jīng)驗”的隱喻學(xué)闡釋進(jìn)路及對中國法治的啟示
余韻潔
(重慶大學(xué),重慶400044)
一、引 言
“楓橋經(jīng)驗”是中國農(nóng)村地區(qū)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產(chǎn)物。20世紀(jì)50年代,土地改革運動的興起,將地主分子、富農(nóng)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劃分組成集合的敵對階級,作為無產(chǎn)階級的敵人來予以打擊、管制、監(jiān)督和改造,而對“四類分子”進(jìn)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便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①毛澤東主席曾在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一場面向7000人的大會上指出:“對于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并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的分子統(tǒng)統(tǒng)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dāng)?shù)姆椒ǜ脑焖麄儯顾麄兂蔀樾氯恕!雹诘聦嵣希鐣髁x教育運動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和平運動,尤其在初期,斗打、亂捕甚至亂殺的過激方式占據(jù)了主流,充斥著血腥和暴力,從斗打個別“表現(xiàn)不好”的“四類分子”擴(kuò)展為斗打一般的“四類分子”,再到斗打“四類分子”的直系親屬,③斗打的范圍、斗打的程度都無異于一場“趕盡殺絕”的激進(jìn)政治運動,嚴(yán)重背離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本質(zhì)與初衷。兩年后的1963年,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qū)以“一個不殺、大部不捉、說理斗爭”的方式在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嶄露頭角,④與武力制服階級敵人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楓橋群眾利用感化、說理的溫和方式順利改造了“四類分子”,成為不流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新標(biāo)桿。此后,諸暨縣楓橋區(qū)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實踐上升成為聞名遐邇的“楓橋經(jīng)驗”,其主要精神被總結(jié)為“發(fā)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xiàn)捕人少、治安好”。⑤
“楓橋經(jīng)驗”誕生于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斗爭大背景下,其卓越品質(zhì)體現(xiàn)為,以階級之內(nèi)的方式解決階級之間的矛盾,即用對待“人民”的方式對待“敵人”,孕育了否定階級斗爭的萌芽,具有了平等對待所有人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chǔ)。本文試圖通過隱喻學(xué)的方法,對“楓橋經(jīng)驗”的核心與本質(zhì)作出闡釋,以把握和進(jìn)一步理解“楓橋經(jīng)驗”中的創(chuàng)新之所在,為實現(xiàn)社會的長治久安、和諧穩(wěn)定提供啟發(fā)、賦予靈感,并給未來法治的深入推進(jìn)提供建設(shè)性的意見。
二、身體政治學(xué)隱喻坐標(biāo)構(gòu)建
隱喻,作為一種與明喻相對應(yīng)的修辭方式,是人們認(rèn)識、理解、解釋復(fù)雜社會現(xiàn)象與事物并進(jìn)行運用的思維方式。⑥同時,與明喻中本體——喻體之間具有表面相似性的特征不同,隱喻中本體——喻體之間是一種隱晦實質(zhì)性的映射關(guān)系,質(zhì)言之,“隱喻就是一種類比”,⑦在理論和學(xué)術(shù)研究范圍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楓橋經(jīng)驗”的核心內(nèi)容——和平解決階級斗爭——可以通過隱喻學(xué)的理論獲得一種新的認(rèn)知進(jìn)路。同時,由于階級斗爭的起源主要來自于身體政治學(xué)隱喻,本文將以此建立坐標(biāo)中心(鑒于篇幅受限,只選擇西方的這一國家機(jī)體論作為討論背景),闡釋“楓橋經(jīng)驗”核心內(nèi)容對此隱喻基點的暗合與突破。
(一)身體政治學(xué)隱喻的西方源起
在基督教浸入西方的整個歷史中,教會與國家之間相互滲透、彼此影響,無論是禮儀、法學(xué)、哲學(xué)還是人文主義領(lǐng)域,都制造出了各種混合狀態(tài)的事物。例如,世俗世界的領(lǐng)導(dǎo)者(國王)在加冕的時候,要像基督教世界的領(lǐng)導(dǎo)者(教宗)一樣被授予一枚戒指,“到最后,神職人員有了一副皇帝的樣貌,而國王則帶上了一種教士的調(diào)子”。⑧又如,基督教徒出于福音性的圣愛而殉道的做法,通過人文主義者的手,轉(zhuǎn)換成了領(lǐng)土性君主國家的人為了“祖國的愛”而獻(xiàn)身的愛國主義行動。⑨政治體的構(gòu)成也毫不例外,從西方中世紀(jì)至18世紀(jì),神學(xué)家、法學(xué)家、政治家借用基督教神學(xué)中的“基督奧秘身體”發(fā)展出了世俗對應(yīng)物——“國家神秘身體”(即國體),⑩以此鞏固世俗主權(quán)的統(tǒng)一性、延續(xù)性、永久性,就好像永恒的基督圣體一般。
“基督身體”的隱喻來源于新約圣經(jīng)中圣保羅的機(jī)體論概念,“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體”,“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哥林多前書》12∶12,12∶27,6∶15)。“身體只有一個,圣靈只有一個”,“全身都靠他聯(lián)絡(luò)得合式,百節(jié)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以弗所書》4∶4,4∶16,4∶25,5∶30)。按照圣經(jīng)中所說,基督乃“基督身體”的頭部,各個器官、肢節(jié)都在頭部的主導(dǎo)下發(fā)揮作用,以維持整個身體的穩(wěn)固存在。
到了中世紀(jì)中后期,教會以“基督身體”為模板,發(fā)展出了“基督奧秘之體”的政治體涵義用語,在這里,由基督教社會所有過去、現(xiàn)在以及未來的信徒所構(gòu)成的教會成為了“基督奧秘”這個集體性的、社會性的、法人性的有機(jī)體的身體,“基督奧秘”的頭仍是基督,其可見的頭則是基督在世俗間的代理人——羅馬教宗。阿奎那認(rèn)為:“正如整個教會被認(rèn)為是一個奧秘之體,因為她與人的自然身體類似,也因為其活動的多樣性符合肢體的多樣性,因此基督被稱為教會的‘頭’……。”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認(rèn)為:“羅馬教會的合眾政治體‘體現(xiàn)為一個奧秘的身體,基督是她的頭,而基督以上帝為頭’。”
教會將“基督奧秘之體”政治化的過程深刻影響了世俗政治體的構(gòu)建。毋庸諱言,這種“基督教政體”機(jī)體性結(jié)構(gòu)原理正為新興的領(lǐng)土世俗性國家所需,并在極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現(xiàn)代國家政治形態(tài)。13世紀(jì)開始,機(jī)體論的概念便從教會轉(zhuǎn)移至了世俗國家,并賦予了其與教會相似的某種超自然性的價值屬性,“國家奧秘之體”得以產(chǎn)生。一方面,“國家奧秘之體”是由頭和許多肢體構(gòu)成的無形的、合眾性的、與各個有形自然體相區(qū)分的擬制體,君主是“國家奧秘之體”的頭,“國家奧秘之體”是君主的身體。1536年,由英格蘭高等民事法院(Common Bench)審理的Willion v. Berkley一案中,索斯科特法官在論辯中寫道:“國王有兩個職能,因為他有兩個身體,其一是自然之體,由自然的肢體構(gòu)成……另一個是政治之體,其肢體就是他的臣民,他和他的臣民一同構(gòu)成了這個合眾體。”13世紀(jì)晚期的比利時哲學(xué)家戈弗雷認(rèn)為:“依照自然本性,每個人都是社會共同體的一部分,也是神秘身體的一個器官。”英國的約翰·福蒂斯鳩爵士寫道:“正如人的身體由胚胎發(fā)育而來,受一個頭的管治,王國也是從人中生長而出的,作為一個奧秘之體而存在,由一個人來做頭來統(tǒng)治。”另一方面,“國家奧秘之體”比擬“基督奧秘之體”(即教會)屬靈的超自然基礎(chǔ),創(chuàng)設(shè)了世俗政治體得以存在并且永恒存在的神秘性基礎(chǔ)——正義性、道德性與政治性,人們依照這樣的德性和倫理性組合構(gòu)成國家政治體。正如盧卡斯·德·佩納在論述合眾體原理時所說:“人們在屬靈上加入屬靈的身體,有基督為其頭……人們也是在道德與政治上加入國家,即一個以君主為其頭的身體。”
至此,以基督為頭部的“基督身體”和以教會為頭部的“基督奧秘之體”為摹本,世俗領(lǐng)土君主國最終發(fā)展出了以君主為頭部的“國家奧秘之體”(又稱“國家身體”“國體”),這種國家機(jī)體論概念不但促成了政治性國家的生成,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還極大地影響了關(guān)乎世俗政治體存續(xù)的“國家身體”中頭部與身體的關(guān)系(主權(quán)者與國家的關(guān)系)、肢體與身體的關(guān)系(臣民與國家的關(guān)系)以及神經(jīng)脈絡(luò)與身體的作用關(guān)系(法律的作用),而正是這些關(guān)系從理論上深刻影響了階級斗爭的形成、走向以及實質(zhì)意義。
(二)以身體政治學(xué)隱喻為基點的階級斗爭
1.頭部的地位與作用
以機(jī)體論概念建立起來的國家身體中,作為身體的一部分,肢體是為身體服務(wù)的,支持身體、服從身體是其題中之義。不但如此,與同作為身體一部分的頭部相比,肢體的重要性也要位居其下,不但要依照自然理性聽從頭部指揮、侍奉頭部,必要的時候還要為了頭部做出犧牲。因為頭部是身體的大腦、中樞神經(jīng)、靈魂之所在,斬去作為國家身體的頭,無異于斬去統(tǒng)一于身體的靈魂,靈魂破裂或者消失,整個身體也將不復(fù)存在。1628年英國主教勞德對國家身體的闡釋足以說明靈魂對身體的重要性:“正如在一個人身體中,靈將所有器官聯(lián)系在一起,但是,如果靈魂破裂,成員則四分五裂。教會亦然,國家亦然。”因此,頭部毀滅,作為其結(jié)果,各個肢體也將毀滅自身,相當(dāng)于整個身體毀滅。
在“國家身體”中,作為頭部的是君主或國王,而社會各個階層遍布頭部以外,成為身體的各個肢體或器官。一方面,這些肢體或器官的任務(wù)是執(zhí)行頭部大腦發(fā)出的行動指令,同時也要對抗一切攻擊頭部的行為,阻擋一切有害物或無用物。薩爾茲伯利的約翰在《論政府原理》中寫道:“國家的頭部是君主……心臟是議會……法官和地方主政官是耳朵、眼睛和嘴;官員和士兵是手……兩足對應(yīng)的是農(nóng)民。”兩個多世紀(jì)以后,法國人比贊繼續(xù)論道:“貴族和騎士是政治體的手臂,普通臣民為胃腹、腿和足。”“王國的頭就是國王……王國的任何一部分攻擊國王,就是攻擊頭,并威脅整個身體,最后也是毀滅他自己。”另一方面,肢體、器官對于身體的作用也在于服從、支持以及保護(hù),任何背反身體的行為都無異于自我毀滅,亦即肢體器官的任何自我攻擊也等同于冒犯國家,比如,自殺也構(gòu)成叛國。第一,公民為了保衛(wèi)“國家身體”而貢獻(xiàn)個人的財產(chǎn)(納稅)、外出征戰(zhàn)、甚至犧牲生命都是國家機(jī)體論的自然延伸。1214年,自布汶戰(zhàn)役開始,法國的王家軍隊的一部分便來自于普通公民集合,由這些法蘭西政治體上的“肢體”來捍衛(wèi)祖國安危,同時,另一些“肢體”——教會的教士——也要以其他一些方式如負(fù)擔(dān)戰(zhàn)爭的經(jīng)濟(jì)開銷來完成保衛(wèi)法國奧秘之體的任務(wù)。事實上,每一個居住于法蘭西這個以所謂“道德和倫理”之永恒價值建立起來的國家身體之中的人——無論是貴族還是下等人——都有奮力保衛(wèi)身體的責(zé)任。第二,在國家機(jī)體論觀點下,自殺者會因為這個最為私人的行為而觸犯重罪,因為其作為身體的一部分,傷害了國家的安危,使得國家損失了健康。來自英國的法學(xué)家埃德蒙·普洛登在其編纂的《判例報告》中記錄一個衡量自殺行為法律性質(zhì)的經(jīng)典案例——Hales v. Petit案,首席法官戴爾勛爵認(rèn)為自殺是三重犯罪:“自殺者犯了重罪,不僅因為他的行為有悖自然、冒犯了上帝,而且也冒犯了國王,導(dǎo)致國王喪失了一名臣民,他作為頭就喪失了他的一個奧秘的肢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機(jī)體合眾體概論下,不支持、服從身體的任何肢體器官都被視為腐化、墮落、丑陋的一部分,是與整個身體格格不入、不相協(xié)調(diào)的,必須要被“切除”。1296年,一位法國王室的法學(xué)家在一本匿名小冊子中宣稱:“那些拒絕服從整體,拒絕支持自己身體的無用、半癱瘓的肢體,乃是腐化墮落的器官,無論他是教士還是俗眾、貴族亦或是平民,如果他拒絕為他的頭或身體——即我主君王和王國——提供幫助,他們就證明他們自己是不順服的器官,是無用、半癱瘓的肢體。”而對于這種如同斷肢、有害于身體健康的部位,身體政治學(xué)論者皆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切除”,“如果為了全身的健康(整個身體的利益),我們說一個手或一只腳——就像國家的公民,必須要被切除。”
2.階級斗爭的隱喻:誰是頭部
以身體政治學(xué)為坐標(biāo)原點,階級斗爭的隱喻是決定誰為“國家身體”的頭部,誰控制“國家身體”的靈魂和理性,誰主導(dǎo)“國家身體”的行為方式。頭部雖然只是“國家身體”的一部分,但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沒有了頭部,只剩下軀干和沒有生命的四肢,這哪是身體?并且,身體政治學(xué)中,頭部必須是唯一的,排斥多個頭部的存在,因為那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身體,而是一個怪物。無論是霍布斯還是博丹的國家主權(quán)理論,都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機(jī)體論構(gòu)造。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寫道:“在一個有主權(quán)者存在的王國中如果又另有一個最高權(quán)力者存在,這本身就是個分裂的王國……每個臣民不可能要服從兩個統(tǒng)治主……。”博丹在《主權(quán)論》中指出,主權(quán)(頭部)不可分割,君主或是貴族或是民主只能占據(jù)其一,不存在兩個或多個頭部并存的混合政體。
在“國家身體”中,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被喻為身體各個部位的器官,各司其職。但由于頭部的重要性和唯一性,誕生了爭奪“國家身體”頭部的階級斗爭,即誰成為頭部,誰就是主權(quán)者,誰就是“國家身體”的靈魂之所在。
3.敵人的隱喻:腐化墮落的肢體
國家政治體由“一個身體、一個頭部、一個靈魂”三位一體的身體理論打造而成,并對外表現(xiàn)為一個健康、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的整體。就如自然身體的手、足、器官、關(guān)節(jié)等都只能聽從于頭部的大腦而統(tǒng)一運動一樣,國家整體、各個階層、每個人也只能聽從于主權(quán)者的命令而進(jìn)行行動,在國家中,主權(quán)者的思想即為大眾人的行動指南,違背其思想就會導(dǎo)致如身體紊亂一般的社會動蕩。當(dāng)國家的主權(quán)者確立之后,“國家身體”便擁有了唯一的頭部,身體的思想、身體的理性、身體的良心都由頭部所主宰。質(zhì)言之,頭部大腦的思想統(tǒng)轄軀干肢體的思想,這是身體政治學(xué)中“身體靈魂只有一個”的理論延伸。主權(quán)者,在現(xiàn)代國家中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貴族、還可以是民主(議會),成為了一個國家的精神、思想、信仰的源泉。正如薩爾茲伯利的約翰所言:“如果國王安然無恙,所有人都是一個頭腦;如果國王死去,信仰則破裂。”
因此,不聽從主權(quán)者指揮、不服從主權(quán)者思想、不支持主權(quán)者理性的敵人便成為了“國家身體”中腐化墮落的肢體,其存在危害了統(tǒng)一的身體機(jī)能,為了保全整體,無能為力,只能切除掉。“切除”意味著,那些不服從國家政權(quán)的敵人只能被消滅。
三、“楓橋經(jīng)驗”的隱喻學(xué)闡釋進(jìn)路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推行進(jìn)程中,楓橋地區(qū)的干部群眾獨樹一幟的地方便是脫離了傳統(tǒng)的對敵斗爭方式。即使在中央制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大方針前提下,當(dāng)時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區(qū)分?jǐn)澄摇^(qū)分?jǐn)澄颐芎腿嗣駜?nèi)部矛盾的基礎(chǔ)上。這直接導(dǎo)致的結(jié)果便是捕、判、殺等激烈的運動方式盛行,因為敵人的歸宿應(yīng)當(dāng)是滅亡。而楓橋地區(qū)的廣大干部群眾在浙江省委工作隊發(fā)動的“武斗好還是文斗好”的大討論中,一致同意后者,并且在之后的社教運動中也積極貫徹了這一“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文斗理念。本部分內(nèi)容將從身體隱喻學(xué)理論出發(fā),揭示“楓橋經(jīng)驗”在對敵斗爭實踐中精華之所在。
(一)拋棄階級斗爭:身體大于頭部
在“國家身體”的構(gòu)造理論中,主權(quán)者是國家的頭部,國家是主權(quán)者的身體。這隨之帶來了一個問題,到底是頭部重要還是身體重要?歷史上,頭部重要的觀點直接映射為“君主主權(quán)”的政治形態(tài),而身體重要的觀點后來演變?yōu)椤白h會主權(quán)”的政治形態(tài)。事實上,頭部重要的觀點有可能導(dǎo)出頭部可以吞沒整個“國家身體”的結(jié)論,就好像中世紀(jì)教會政治中的教皇派所言的:“基督的奧秘之體,就在頭所在的地方,那就是,教皇所在之處。”這種實質(zhì)將肢體與頭部完全等同的理論會導(dǎo)致不受限制的君主絕對主義,明顯不符合國家機(jī)體論中身體應(yīng)當(dāng)大于器官的概念,因為頭部也只不過是身體的一部分,屬于身體的一個器官而已。16世紀(jì),亨利八世對咨議會所說的話中明顯表達(dá)了這個含義:“……當(dāng)朕處在議會中的時候,王家等次是最高的,在其中,朕是頭,而你們是肢體,聯(lián)合并交織在一起,構(gòu)成一個政治之體。”上文提到的Willion v. Berkley一案中,也表達(dá)了同樣的含義:“另一個身體是一個政治體,其上的肢體就是他的臣民,他和他的臣民一同構(gòu)成了這個合眾體……他與他們連結(jié)在一起,他們也與他連結(jié),他是頭。他們是肢體……。”其實,機(jī)體論的“國家身體”概念中并沒有發(fā)展出國王與基督一樣具有“兩個身體”的觀念。也就是說,世俗君主作為“國家身體”的頭部并不構(gòu)成一個擬制的“獨立身體”,他的身體只有一個——那就是他的自然之身。鑒于機(jī)體論中強(qiáng)大的頭部與肢體之間的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理論,頭部與肢體之間必須相互區(qū)別而又彼此牽連,頭部根本不能吞并身體,因而,“君主大于個別的公民,但小于其全體”的區(qū)分肢體與頭部、身體大于頭部、整體大于部分的機(jī)體概念得以勝出。這標(biāo)志著頭部和身體是相互依賴的,正如君主在一些方面是至高無上的,作為政治體的“國家身體”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同樣如此。
而階級斗爭在身體政治隱喻中的實質(zhì)意義即為爭奪并確立“國家身體”的頭部。沒有了頭部,成何身體?但同樣,沒有了肢體、軀干,又成何身體?頭部統(tǒng)領(lǐng)肢體在內(nèi)的整個身體,但并不意味著頭部能夠替代或者吞并其他身體部位,因為每個部位對于身體來說都具有不同的價值。實質(zhì)上,在身體政治學(xué)中,雖然強(qiáng)調(diào)“國家身體”的統(tǒng)一性,同時也強(qiáng)調(diào)“國家身體”的機(jī)能協(xié)調(diào)性,包括頭部在內(nèi)的任何肢體器官都只是身體的一部分,都只能在相應(yīng)的位置發(fā)揮作用,共同為身體的健康運轉(zhuǎn)發(fā)揮合力。階級斗爭將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劃分為主權(quán)者(人民)和被主權(quán)者(敵人),對于敵人要打擊殆盡,這實質(zhì)是將頭部的地位置于身體之上——為了頭部的利益要舍棄身體的某些機(jī)能,是將“國家身體”肢解的另一種方式。“楓橋經(jīng)驗”在階級斗爭的大背景下,破除了階級斗爭的思維定勢,用所謂階級之內(nèi)的方式解決階級之間的矛盾,即用對待“人民”的方式對待“敵人”,孕育了拋棄階級斗爭的萌芽,是將整個“國家身體”的機(jī)能利益置于“各個身體部位”局部利益之上的考量和突破。因而,無論是在國家政權(quán)奪取、鞏固的改革開放前的時代中,還是在國家政權(quán)已經(jīng)穩(wěn)固的今天,“楓橋經(jīng)驗”彌足珍貴的核心意義都無異于在昭示國家政治體中的每一個人:無論是作為頭部,還是身體四肢,亦或是其他器官,你們都與整個共同體一脈相承,同呼吸、共命運。
(二)以人為本:不是“切除”而是“治愈”
國家猶如身體的政治理念中,那些拒絕支持國家和主權(quán)者的人就好像自然身體中一個半癱瘓的肢體或不順服的器官,是被認(rèn)為與整個身體機(jī)能相排斥、格格不入的無用的一部分,必須要被“切除”。這一身體政治傳統(tǒng)深刻地造就了近代“整體大于部分”“主權(quán)高于人權(quán)”的國家主義理論以及現(xiàn)代國家中對司法機(jī)關(guān)的性質(zhì)與職能定位。
“保全整體,犧牲個體”是機(jī)體論中“身體大于部分”理念在近現(xiàn)代國家中的極度濫用,其構(gòu)成了一種膨脹的國家主義或國家理性。這意味著,國家在緊急狀態(tài)下甚至任何必要的時候可以為了國家利益剝奪公民權(quán)利。更為重要的是,被喻為連接自然身體各器官、各肢體于一身的“神經(jīng)和肌腱”的世俗化結(jié)果——國家法律——同時也變成了低于國家理性的存在。質(zhì)言之,在國家理性的主導(dǎo)下,法律的最高目的是維護(hù)國家整體、增進(jìn)公共福祉,而不是維護(hù)整體中的每一個個體。基于此,西方歷史上的英國就曾經(jīng)引發(fā)了一系列的悲劇。從14世紀(jì)開始,英國的國家理性開始膨脹,直至17世紀(jì)到達(dá)頂峰,由此爆發(fā)了議會與國家之間的爭戰(zhàn)。在此期間還誕生了臭名昭著的“剝奪公民權(quán)利法案”(Bill of Attainder)。這項法案于1542年1月29日由亨利八世在國會通過,導(dǎo)致了諸多著名的歷史人物被處決。剝奪公權(quán)(Attainder)這個詞最早在英國歷史中的隱喻是“污血”,起源于身體政治學(xué)中的“腐朽潰爛的身體一部分”,在國家政治體中演變?yōu)榉赣兄刈锘蚺褔锏淖锓副救耍瑫r,與身體中腐化有毒的部分應(yīng)當(dāng)被“切除”一樣,重罪者、叛國者也必須被處死。并且,這些罪犯不享有任何公民權(quán)利,不享有正常的司法審判程序,將由對應(yīng)的司法外程序進(jìn)行處置,即議會通過即時立法、事后立法和審判繞過了專門的司法程序來剝奪掉這些罪犯的公民權(quán)利(以生命權(quán)為首,還包括財產(chǎn)權(quán)、世襲貴族頭銜的權(quán)利等)。在英國這段時期的歷史中,有一個很著名的案例——斯特拉福德伯爵案(Strafford trial)——生動地揭示了身體政治學(xué)對“剝奪公民權(quán)利法案”的影響。在對托馬斯·溫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即第一任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審判中,圣約翰先生在論證應(yīng)當(dāng)剝奪公民權(quán)利所發(fā)表的法律意見中這樣說道,“議會是一個偉大的政治身體,她囊括了從國王到乞丐的一切”,因此,“為了維護(hù)整體,(議會這一政治身體)對其本身以及身體上下每個部分都享有任意的權(quán)力。(議會)既是醫(yī)生也是病人:一方面,如果身體有恙,為了自我治愈,她有權(quán)切開靜脈,讓污血排出;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分感染病毒并腐爛了,為了保全其余部分,她有權(quán)將其切除掉”。其實,在自然身體中,腐化有毒的一部分實質(zhì)上也確保了機(jī)體免受進(jìn)一步被入侵的危險,從這一程度上講,其并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也應(yīng)當(dāng)是增強(qiáng)機(jī)體免疫性的有益的一部分。在處理這一有益的感染腐爛部分時,作為身體機(jī)體首先應(yīng)當(dāng)是治療她,盡力使她痊愈,而不是一味地切除,因為這一部分在被切除掉的同時,身體本身也失去了對自己有益的一部分。政治身體如果可以類推自然身體的話,不是“切除”而是“治愈”才是對整體實質(zhì)有益的進(jìn)路,更何況,自然機(jī)體論真的可以一成不變地套用到國家身體論中嗎?在國家身體論中,我們更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到,國家中的每一個人都具有同國家一樣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
同樣是在身體政治理念的影響下,以審判機(jī)關(guān)為首的國家機(jī)器被喻為“刀把子”。以我國為例,從新中國成立起到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刀把子”一直都是人民法院的隱喻,常見于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講話以及諸多司法文件之中,具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司法工作的主要鋒芒是對著反革命,這不是說把什么案件都看作是反革命案件,但只要有敵人,我們同敵人的斗爭就是尖銳的。司法干部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這一點。死刑要不要?我們是從來不說廢除,但要少用。死刑好比是刀子,我們武器庫里保存這把刀子,必要時才拿出來用它。”而彭真在1979年《實現(xiàn)四化一定要有一個生動活潑、安定團(tuán)結(jié)的政治局面》的講話中也指出:“公、檢、法機(jī)關(guān)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武器,是黨和人民的刀把子,根本任務(wù)是打擊敵人,保護(hù)人民。”有論者認(rèn)為,“刀把子”對人民法院的隱喻來源于其本身的原始含義與司法權(quán)的屬性與功能的契合,例如:“‘刀把子’原是把握道具的部分,可引申為對司法權(quán)的掌控”、“‘刀把子’為人人可用的器物,由此聯(lián)想到司法的大眾化特征”、“‘刀把子’系不祥之器,容易衍生出厭訟的社會心理”,但這種論點實際上只停留在了對“刀把子”的表層理解,其產(chǎn)生的根源還是在于國家機(jī)體論構(gòu)造。按照身體政治理論,國家的其他部位不順服頭部、不支持頭部甚至還要對頭部發(fā)起攻擊,性質(zhì)完全等同于不聽從國家靈魂的指揮、破壞統(tǒng)一的身體機(jī)能,是傾向于毀滅整個身體的最終意圖,而這些部位便是“國家身體”中腐化墮落的肢體部位(國家的敵人),應(yīng)當(dāng)予以“切除”(消滅)。切除自然身體的腐爛部位需要相應(yīng)的刀具,而消滅“國家身體”的敵人需要國家機(jī)器,刀具對應(yīng)于國家機(jī)器。在中國的相關(guān)語境中,刀具具體對應(yīng)為“刀把子”,國家機(jī)器具體對應(yīng)為人民法院,這同時具有兩層含義,一方面,“刀把子”的“把子”即握持部位由國家頭部(人民)所掌握,另一方面,“刀把子”的“刀鋒”部位是指向敵人、砍向敵人、消滅敵人的。我國從20世紀(jì)50年代中期開始,就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標(biāo)語口號下進(jìn)行治國,這種過分區(qū)分?jǐn)澄摇O度強(qiáng)調(diào)階級矛盾的階級斗爭范式,使得法律完全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司法機(jī)關(guān)也純粹淪為貫徹“切除”思維的“刀把子”。殊不知,“刀把子”的運用也是有利有弊的,運用得好,可以消除“國家身體”中無可醫(yī)治的腐爛部位,運用不好,便是傷害“國家身體”的統(tǒng)一機(jī)能,使得其損失了原生于身體的一部分。事實上,極端階級斗爭的有害之處在于,將“國家身體”割裂為“頭部”與“頭部以外”的部分,消滅“頭部以外”的原屬于身體的部分其實是以“頭部”取代整個身體的體現(xiàn),這從國家機(jī)體論中“身體應(yīng)當(dāng)大于頭部或器官”的概念來看,也是不可取的。
如前所述,傳統(tǒng)的“打、捕、殺”對敵斗爭、階級斗爭方式在國家機(jī)體論隱喻中代表著一種被“國家身體”全面否認(rèn)的“切除”模式,而楓橋地區(qū)干部群眾以“一個不殺、大部不捉、說理斗爭”溫和方式和平化解階級矛盾的經(jīng)驗,則是一種全力拯救身體各個部位的“治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舊式機(jī)體論照搬運用于國家政體中的癥結(jié),具有了更為現(xiàn)代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所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基礎(chǔ)。一方面,“楓橋經(jīng)驗”中的“治愈”手段意味著階級之間的矛盾等同于階級之內(nèi)的糾紛,都被視為整個國家機(jī)體的疾病,要想國家機(jī)體得到最為完全的康復(fù),這些疾病都需要對癥下藥,進(jìn)行及時、有效、全面的治療,或清除膿液或矯正畸形,如果每次都揮舞著“刀把子”切除這些病灶,“國家身體”上勢必留下一個又一個的創(chuàng)傷,長此以往,對國家整體的機(jī)能性、協(xié)調(diào)性、健康性都是不可挽回的打擊;另一方面,“楓橋經(jīng)驗”中的“治愈”手段超越了舊式的機(jī)體論,表現(xiàn)為清楚地區(qū)分了政治身體與自然身體的本質(zhì)不同,即肢體、器官不但體現(xiàn)為“國家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也體現(xiàn)為每一個鮮活、獨立、與眾不同的生命個體,代表了法治基石的以人為本、保護(hù)人權(quán)的意義呼之欲出。
四、余論:對中國法治的啟示
從身體政治隱喻學(xué)的闡釋進(jìn)路中,本文揭示了“楓橋經(jīng)驗”創(chuàng)新精神的基礎(chǔ)性價值,這種價值體現(xiàn)為對身體隱喻基點的的暗合與突破。一方面,國家機(jī)體論構(gòu)造中,頭部、軀干、肢體、器官都是“國家身體”的一部分,彼此分離而又相互依賴,誰都不能吞并誰,并且,“國家身體”作為整體比任何身體部位都要重要,因而身體比頭部重要;“楓橋經(jīng)驗”在階級斗爭的大背景下,用對待“人民”的方式對待“敵人”,孕育了拋棄階級斗爭的萌芽,破除了階級斗爭——頭部最重要與爭奪頭部——的思維定勢,將整個“國家身體”的機(jī)能利益置于“各個身體部位”局部利益之上,是對“身體大于頭部”機(jī)體論的暗合。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國家機(jī)體論構(gòu)造中,“身體大于頭部”“身體大于肢體”“整體大于部分”是基本原則,但極度濫用也會造成絕對的“國家身體主義”,就像不受限制的君主(頭部)絕對主義在現(xiàn)代國家會導(dǎo)致君主的專制,從而導(dǎo)致大部分人的權(quán)利無法得到保障,而不受限制的國家(身體)絕對主義在民主國家中也會導(dǎo)致多數(shù)人的暴政,進(jìn)而少數(shù)人、個別人的權(quán)利同樣無法得到保障。“楓橋經(jīng)驗”將階級之間的矛盾等同于階級之內(nèi)的糾紛,一視同仁進(jìn)行解決,不但具有反對以人的身份劃分行為性質(zhì)(反對區(qū)分?jǐn)澄?的平等自由的思想,同時還具有反對以暴力、血腥的激烈手段消滅敵人(反對“切除”手段)而以感化、說理的溫和方式改造敵人(提倡“治愈”手段)的以人為本、保護(hù)人權(quán)的思想,區(qū)分了政治身體與自然身體的本質(zhì)不同,杜絕了國家機(jī)體論的濫用,是對舊式機(jī)體論原則的超越以及突破。
迄今,中國的法治建設(shè)一直偏向于“整體大于部分”的國家主義,這固然有出于對特定國家歷史、文化、倫理等情況的特殊考量,但“楓橋經(jīng)驗”告訴我們,即使是在國家處于比較混亂、不穩(wěn)定的時期,體現(xiàn)了個人自由主義的溫和有理的“治愈”手段也遠(yuǎn)比激烈殘暴的“切除”手段在社會治理方面付出的成本更小、取得的效果更好。轉(zhuǎn)向如今和平穩(wěn)定倡導(dǎo)和諧社會的新時期,中國的法治建設(shè)更應(yīng)當(dāng)回歸至個人權(quán)利本身,在既有的國家主義法治元素的思維中更多地融入個人主義的元素,更多地維護(hù)和保障作為社會共同體而不只是國家政治體的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尊嚴(yán)、財產(chǎn)以及自由,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緊迫的。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全面建設(shè)小康社會,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中首次將“社會更加和諧”作為重要目標(biāo)提出;之后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guān)于加強(qiáng)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shè)的決定》進(jìn)一步提出了“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具體任務(wù);直至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仍然將“建成富強(qiáng)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qiáng)國”作為當(dāng)下以及未來需要實現(xiàn)的“中國夢”。和諧為何屢屢被提及,重要性何在?和諧,意味著徹底否定了區(qū)分?jǐn)澄业碾A級斗爭,意味著反對以保全整體為由犧牲個體,這同時也代表了中國法治的理想維度,即法律不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法律的最高目的從保護(hù)人民轉(zhuǎn)向為保護(hù)所有人。事實上,和諧社會所要求的理想法治不僅是立法形式層面的“去階級性”,更是訴訟程序、司法制度層面實質(zhì)性的“去階級性”,而理想法治的實現(xiàn)程度又集中體現(xiàn)于國家對于罪犯(無論是輕罪還是重罪、政治性罪或非政治性罪)所秉持的理念和所采取的措施。因為,侵害了法益(國家利益)的罪犯是給“國家身體”造成損害的一部分,其形式上等同于“階級性”國家政治體中的敵人,而按照身體政治論所言,敵人屬于腐化墮落的肢體是必須要被“切除”的。如果在“去階級性”的國家政治體中,罪犯與敵人的最終結(jié)局相同或相似,那么兩者實質(zhì)相同,即這些罪犯在“去階級性”的國家政治體中替代“階級性”國家政治體中的敵人“復(fù)活”了,“去階級性”成為一紙空言。如前所述,“楓橋經(jīng)驗”的寶貴價值在于拋棄階級斗爭,堅持以人為本,現(xiàn)代法治的核心同樣在此,即實質(zhì)是“去階級性”、保護(hù)人權(quán)。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都要體現(xiàn)每個人皆平等,都要尊重和保護(hù)人權(quán)。
進(jìn)而,秉持著“楓橋經(jīng)驗”所示的法治價值,刑事訴訟法的真正目的也彰顯出來,其并不是為了控訴犯罪、追求事實真相的制度構(gòu)造,而是保護(hù)人權(quán)、預(yù)防犯罪的制度構(gòu)造。現(xiàn)代社會中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區(qū)分和自然科學(xué)與社會科學(xué)的區(qū)分也能夠簡單論證前述觀點。一方面,如果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hù)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免遭損害,從而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加強(qiáng)社會秩序,刑事訴訟法的目的恰恰是保護(hù)少數(shù)人的利益免遭侵害,從而維護(hù)人類的基本尊嚴(yán)與自由。質(zhì)言之,刑法所保護(hù)的損害是個人可能對國家造成的,而刑事訴訟法所保護(hù)的侵害則是國家可能對個人造成的,可以說,刑事訴訟法與刑法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刑事訴訟法絕不是貫徹執(zhí)行刑法的程序法。另一方面,與自然科學(xué)相比,作為社會科學(xué)的法律對于追求事實真相是毫無優(yōu)勢可言的,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真實的目的,那么社會科學(xué)是沒有必要存在的。換言之,社會科學(xué)的優(yōu)勢并不是“求真”而是“求善”,在面對善惡的價值判斷面前,甚至可以過濾或拋棄真實。美國學(xué)者赫伯特·帕克在刑事訴訟的正當(dāng)程序模式中,將刑事訴訟程序比喻為一場障礙賽,這意味著在以人文本、保護(hù)人權(quán)的理念下,刑事訴訟是一場遍布一個又一個障礙阻止被告人被判有罪的單向跨欄賽,當(dāng)國家無法通過自身力量跨越法律設(shè)置的障礙時,那么比賽就終止,絕不能再回頭重新賽跑。
綜上,“楓橋經(jīng)驗”的隱喻學(xué)闡釋進(jìn)路表明,對于“國家身體”中腐朽墮落的肢體、器官(不聽從主權(quán)者指揮、不服從主權(quán)者思想、不支持主權(quán)者理性的敵人),應(yīng)當(dāng)竭力“治愈”而不是一味“切除”(和平說服而不是打擊消滅)。相應(yīng),中國當(dāng)下的法治建設(shè)應(yīng)當(dāng)吸取“楓橋經(jīng)驗”這一精華之所在,真正消除法律以及司法中的“階級性”,回歸個人權(quán)利本身,在既有的國家主義法治元素的思維中更多地融入個人主義的元素,更多地維護(hù)和保障作為社會共同體而不只是國家政治體的每一成員的生命、尊嚴(yán)、財產(chǎn)以及自由。罪犯享有人權(quán)、受到法律的特別保護(hù),同時,刑罰的功能也轉(zhuǎn)向為矯正、預(yù)防以及規(guī)范犯罪。
注釋:
①金伯中:《論“楓橋經(jīng)驗”的時代特征和人本思想》,《公安學(xué)刊》(浙江公安高等專科學(xué)校學(xué)報)2004年第5期,第12頁。
②趙義:《楓橋經(jīng)驗——中國農(nóng)村治理樣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頁。
③吳錦良:《“楓橋經(jīng)驗”演進(jìn)與基層治理創(chuàng)新》,《浙江社會科學(xué)》2010年第7期。
④1963年,時任公安部領(lǐng)導(dǎo)的謝富治在一個偶然的時機(jī)下,將浙江農(nóng)村楓橋區(qū)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實踐口頭匯報給毛主席,毛主席對楓橋“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采取說理斗爭的方式“教服”“四類分子”的做法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并當(dāng)即表態(tài):“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
⑤參見前引③,吳錦良文,第43頁。
⑥劉風(fēng)景:《法律隱喻的原理與方法》,《山東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1年第5期,第124-125頁。
⑦[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理學(xué)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頁。
⑧[德]恩內(nèi)斯特·康托洛維茨:《國王的兩個身體》,徐震宇譯,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第305頁。
⑨參見前引⑧,康托洛維茨書,第348-366頁。
⑩佀化強(qiáng):《國體的起源、構(gòu)造和選擇:中西暗合與差異》,《法學(xué)研究》2016年第5期,第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