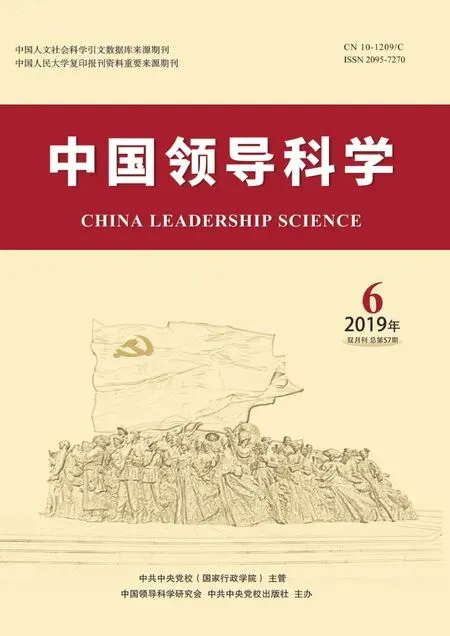信馬由韁的甩手掌柜和罕見的管控者
——里根總統的領導風格
◎ 樊 超
領導人的領導風格本質上反映的是他們的決策模式以及基于此所產生的特征。在當今時代的政治制度設計中,無論各國政體如何設計,無論影響公共政策的因素如何多元、政策產生的過程如何復雜曲折、各類行為主體的互動如何迂回,最終都需要由領導人及其領導下的職能部門直接完成從政策藍本到政策成型的最后環節。簡而言之,行政機關中最頂層的政治精英才是制定公共政策的直接載體。[1]因而,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策界,都承認領導人在決策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和關鍵性作用。以美國領導人的領導風格而言,領導人與職能部門合作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既存在領導人絕對控制領導職能部門的風格,也存在領導人信馬由韁,放任職能部門自動運作的風格。盡管后者在領導人風格和決策案例中占據的比率較低,但鑒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巨大影響力,仍然需要研究和應對美國總統放任式的領導風格。
一、誰在做決策?
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行政權屬于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經咨詢并取得參議院同意,總統有權任命行政部門首長、大使、公使、領事、最高法院法官和任命手續未由本憲法另行規定而應由法律規定的合眾國所有其他官員。但國會認為適當時,應依法將這類低級官員的任命授予總統一人、法院或各部部長。[2]憲法賦予了總統對行政官員的任命權,也就賦予了總統在行政系統內的最高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是總統在各個行政首長及其職能部門的襄助下,完成憲法賦予的行政職責。從理論上講,在總統與職能部門合作制定政策的工作框架內,總統處于領導地位,在決策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但從現實情境來考慮,總統及其所任命的行政首長們大多是職業政客,并不具備在各行各業的專業知識,甚至作為平常人的一分子,總統不僅專業知識有限,而且精力體能有限,決策興趣有限。在這樣的條件下,總統實際上只能依賴行政職能部門形成的龐大文官系統來幫助自己,以此擴展自己的工作量,彌補自己在專業知識和精力體能上的不足。與此相應,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可以要求每個行政部門長官就他們各自職責有關的任何事項提出書面意見”[3]。這種情形實際上決定了總統領導行政系統的兩個基本內容和特點。
第一,總統親自參與的行政系統運作是極其有限的。換言之,總統對行政系統的領導是對各個職能部門的工作做出指令回應和綜合性處理。總統在決策中參與度最高的環節,就是開啟決策、設置決策議程的環節,以及從政策備選方案中抉擇最終政策的政策制定環節。除此之外,無論是激發決策的情報和信息,還是醞釀政策備選項的專業準備,抑或是政策的執行過程,都是依賴甚至是徹底由行政職能部門來完成的。
在政策研究中,如何界定和描述政策是研究的起點。而研究者總是面臨究竟是采集政策文本還是政策實施結果的選擇。如果以政策最終執行實施的結果作為定義政策的標準,那么職能部門在制定政策上則發揮著更為強大的作用。因為“法律和政策總是比較原則的,在運用于具體事例時,必須考慮到千差萬別的具體情況而決定應如何執行。行政官員對法律和政策的解釋,事實上起到制定政策的作用,即使最低一級的行政官員也在某種程度上起著這種作用”[4]。也就是說,職能部門在執行政策過程中所享有的自由裁量空間與權力,實際上決定了政策的最終面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總統的工作不過是在行政職能部門所提供的素材和選項框架內進行工作或創造。當總統對行政職能部門的領導強度減弱乃至缺失時,政策實際上就變成了各個職能部門自行運作、折中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對政策施加影響的行為體,都應該將工作的重心從總統挪向行政職能部門。
第二,總統對行政系統的領導還包括協調、整合各個職能部門的運作。現代國家制度的成功之處在于,政府機構按照業務范圍劃分為不同的職能部門,每個部門負責一個領域的事務,各部門之間有序合作,才能保證龐大的政府可以順利運作、落實政府的職能。[5]在通常情況下,總統不具備過問職能部門具體工作的條件。根據以往的業務經驗而制定的預案和早已形成的日常標準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職能部門會自行運作。[6]其過程并不直接體現總統的領導能力與智力水準,而是更多地反映了職能部門各自獨有的業務標準,以及基于此而產生的相對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基于官僚政治斗爭的本能,各個部門出現權力爭斗,[7]還是出于各個職能部門在業務標準、職業操守上的鴻溝與隔膜,都會使各職能部門在協作問題上存在某種天然的缺陷。所以,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組織或社會共同體都必須有某種形式的“權威”或“支配”作為基礎。否則,任何組織都無法達成自己的目標。[8]
為了保證行政系統的正常運作,總統要憑借自己在行政系統的至高權威,組織和協調各個職能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美國并不存在一項關于職能部門之間關系或協作關系的成文法或規章,因此,總統的協調行為需要是動態的和常態化的。一旦總統作為最終協調者、仲裁者的身份或功能缺失,無論是職能部門之間潛在的爭斗,還是等待總統裁決的時間間隔,都會拖慢決策的節奏。無論客體是本國受眾,還是外國政府,這都會極大地改變政策客體的應對美國行政系統方式,并最終改變它們之間的互動方式。
總體而言,美國總統基于其在行政體系內的最高權力與權威,掌握有最終決策的權力。但總統的這種領導權或決策權也是相對的。在現代政府治理方式下,各個職能部門具備成熟的社會管理方法和相對獨立的運作模式。總統的領導作用在于如何啟動決策程序和分配任務,一旦總統對職能部門的把控力度降低,政策將更多地反映職能部門的專業標準、方案與利益訴求。在美國的歷史上,里根總統就是一個以放任風格領導職能部門的極端案例。他對領導職責的刻意逃避,導致了兩類嚴重的行政困境:一是大量政策議題無法啟動,只能在職能部門的日常標準操作程序的框架內推進;二是總統的幕僚團隊、行政部門首長之間出現意見分歧乃至內斗之時,總統的協調仲裁功能缺位,導致政策久拖不決。這都給美國的內政外交留下了重大的影響。
二、放任式領導風格
根據里根對決策議題的領導和介入程度,政府在決策上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即最常見的放任模式和罕見的管控模式。放任模式是里根執政生涯中最常見的領導模式。當里根遇到政策議題時,“并不會對其花費多少精力,因為他根本就不想做決策”。他在內閣會議上會走神、涂鴉、打瞌睡。[9]所以,里根喜歡將具體事務交給下屬去做。他自己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是演講和準備演講,最熱衷的事情就是度假和睡懶覺。[10]
在此模式下,由于總統領導的嚴重缺位,大多數政策要么在啟動后就被委派給行政職能部門處理和抉擇,要么就長期處于未激活、未啟動的狀態,而是由行政職能部門按照以往的政策慣性或日常標準操作程序,對問題做出被動式的回應。里根上任第二年,美國輿論就注意到里根獨特的領導風格,并做了如下評論:“里根先生經常做的只不過是批準顧問們的決定罷了。”[11]毫不夸張地說,里根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消極的人……真正的決策者與其說是里根,不如說是為其理念而戰的工作人員。[12]
里根政府剛剛上任,中美關系立即就成為里根領導風格的受害者。在競選階段大放親臺言論的里根,引起中國政府的警惕。為徹底解決美國對臺軍售問題,里根政府甫一上任,中國政府就開始向美方施壓,希望能開啟談判進程解決對臺軍售問題。但很少過問政事的里根,既不在意中方的訴求,也未認真對待這一議題,只是將此事交予國務卿黑格處理。被迫無奈的中國政府只好利用坎昆會議的首腦外交機會,通過政府總理向里根提出中美談判解決對臺軍售問題。甚至外長黃華罕見地動用了最后通牒,才迫使里根同意開啟談判。[13]
更為罕見的是,中美圍繞對臺軍售問題的談判,明明已經構成了中美外交關系的危機,卻未能讓中美關系納入里根的決策議程。甚至直到1984年初,中美兩國領導人即將展開互訪之際,美國政府才發覺,里根上任三年以來,尚未制定對華政策。與中國的互動要么是遵循慣例,要么是按照國務院的專業程序做出回應。因而在兩國領導人互訪之前,匆忙通令各個職能部門合作,制定出了正式的對華政策。[14]
訪華結束之后,里根再次將對華政策與事務交由國務卿舒爾茨操持。里根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鮑威爾也曾回憶:“總統的消極管理風格讓我們身負重擔。直到我們適應了這一風格后,仍覺得很難在沒有明確決策的情況下執行建議。……弗蘭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曾抱怨:‘我的天,我們不是雇來領導國家的!’”[15]回顧里根執政時期,放任的領導風格幾乎占據著主導地位并貫穿始終。但此類領導風格并非成熟的領導模式,在處理日常決策議題時,放手讓職能部門和專業意見駕馭決策可以收到奇效。但面對復雜的決策議題時,任何內政或國際環境的干擾因素,都可能將政策引向不確定的前景,因而需要全面的情報與方案備選項,而這恰恰是放任式領導風格無法完成的。里根執政期間面臨的最大危機——伊朗門事件就詮釋了這一原理。[16]
三、罕見的管控式領導風格
在管控模式下,里根即便因為罕見的興趣或危機而專心駕馭行政系統,也會因為專業知識的欠缺而使決策帶有極強的主觀情感特征。在管控式領導風格下,里根決策的原則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依賴樸素的意識形態等感情、感性因素作為取舍備用方案的標準;一種是按照自己最鐘愛的人際關系標準打造和維系自己的內閣班底。法國總統密特朗曾經對施密特評價過里根:“這是一個沒有想法、沒有文化的人,他肯定算是那類自由主義分子,但透過表象你會發現他并不笨,他有很強的感知力,有極其良好的意圖,遇到用智力無法理解的事情,他就用本能去感知。”[17]因而當里根介入和管控決策進程的時候,他對決策備選方案進行抉擇時,主要依賴的是意識形態、從生活中積累的樸素的感情、幕僚團隊和第一夫人給他的建議。
里根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自身的感情和樸素的生活閱歷,而非依賴專業知識的支撐。演員出身的里根沒有任何外交經驗和外交專業培訓的經歷,他不喜歡出國旅行,也沒怎么出過國。距離他任職最近的出國旅行還是1978年的時候,他為準備總統競選而進行的出訪,而臺灣島則是他到訪的目的地之一。此次訪問進一步密切了里根及其幕僚與臺灣當局的關系。[18]因而,對臺灣當局形成的親臺姿態成為他對華政策當中最頑固也是最穩定的底色。在里根所有涉及臺灣問題的言談中,尤其是在中美圍繞對臺軍售問題而展開激烈談判的過程中,他都堅持對臺灣的責任和義務。[19]這些親臺理念并非源自任何的國際關系原理或外交原則。
按理說,一個對蘇聯發起新冷戰的強硬總統,本應急切拉攏中國政府,利用當時的中蘇對抗,強化自身的外交資源。但里根的現實選擇卻暴露出他在決策中對直覺的倚重。需要指出的是,里根的幕僚對他的這種樸素的直覺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不少幕僚都與臺灣當局有著長久的利益聯系,并持親臺立場。他們包括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白宮辦公廳副主任迪弗、財政部長里甘、總統法律顧問米斯等。[20]當然,對里根影響最大的要數他的夫人南希。她“是里根的白宮里一支強大得驚人的力量”。她清除過所有位高權重的里根幕僚,最后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白宮辦公廳主任”[21]。甚至連美國政要也提醒中國駐美外交官,“不要低估里根夫人的作用”。[22]
除去危機情形,里根還會在內閣班底秩序失控時開啟管控式領導風格。里根有著極強的人際交往能力,喜歡與人為善。在總統任期內,他一直希望“他的屬下之間一團和氣,洋溢在一團和氣的氛圍中”。[23]但他經常性的放任式領導風格,卻容易放大行政部門間的協調困難,極端時甚至會出現屬下爭權內斗的情形。這又逼迫里根不得不開啟管控式領導風格,理順下屬之間的關系。
黑格與里根團隊的其他成員存在著政策和權力的矛盾,其易怒的性格又使這種矛盾逐漸變得尖銳而不可收拾。最后,黑格幾乎與里根的每一位高級顧問都矛盾頻發。對華政策一度就成為黑格與艾倫、溫伯格、李潔明等人爭斗的戰場。[24]里根認為黑格只想在內閣中大權獨攬,在外交政策上排擠所有閣員甚至里根自己。這既導致政府運作的不暢,也破壞了里根對祥和的人際關系的堅守,因而解除了黑格的職務。[25]
越來越多的政策研究成果表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決策才是決策過程中的常見模式。[26]這實際上對領導人的領導風格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過于放任的領導風格可以充分激勵職能部門的專業建議,但也存在部門爭權導致的決策拖沓,貽誤時機;過于嚴緊的管控領導風格可以防止混亂的決策過程,但卻又把精力和知識能力有限的領導人逼入親力親為的決策全過程,把政策陷入和專業知識隔絕的險境。明確區隔領導人的協調、抉擇功能與職能部門的情報及方案規劃功能,可能是克服領導風格這種兩難境地的出路。隨著西方一批政治素人裹挾著民族主義情緒上臺,可能將領導風格的這種兩難境地推向極端甚至是極端之間的搖擺。
[注 釋]
[1]Thomas R. Dye and Harmon Zeigler, The Irony of Democracy: A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14th Edition [M].Boston, MA: Wadsworth, 2009: 1-2.
[2][3]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About Americ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 World Book, Inc,2004: 25, 26-27.
[4] 李道揆. 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下冊[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61.
[5]張清敏. 對外政策分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91.
[6][7]格雷厄姆·艾莉森、菲利普·澤利科. 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M]. 王偉光,王云萍 , 譯 .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5:163-164,285-288.
[8]馬克斯·韋伯. 支配社會學[M]. 康樂、簡惠美,譯.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
[9]How Reagan Decides, Time, December 13,1982, p. 15. Laurence Leamer. Make-Believe: The story of Nancy & Ronald Reagan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344.
[10]Time, February 6, 1984: 23. Lou Cannon.Reagan [M]. New York: Putnam's, 1982:398.
[11]Howell Raines. “With Haig Leaving, Reagan Closes a Compatible Inner Circle,”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82.
[12]Mark Hertsgaard. On Bended Knee: 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 [M]. 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 1988: 26.
[13]Donald Reagan. The Reagan Diaries [M]. New York: Harper, 2007: 10, 23, 45, 46. 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M].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261-262.
[14]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Premier Zhao Ziyang, January 9, 1984: 1-3.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 PR01513. The President's Visit t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1,1984: 2-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 PR01529.
[15]Col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334.
[16]David Mervin. Ronald Reagan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M]. UK: Longman Group, 1990: 159.
[17]埃德蒙·莫里斯. 荷蘭人:里根傳(下冊)[M].李小平等,譯. 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591.
[18]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M].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99: 115.
[19]Donald Reagan. The Reagan Diaries [M]. New York: Harper, 2007: 10, 46, 61-62, 75,76, 83, 84, 98.
[20]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78.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115.
[21]Mark Hertsgaard. On Bended Knee: 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 [M]. 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 1988: 24. Jane Mayer and Doyle McManus. Landslide: The Un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84-1988 [M].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8: 380.
[22]張穎. 外交風云親歷記[M].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 2008: 60.
[23]Lou Cannon. Reagan [M]. New York:Putnam's, 1982: 376.
[24]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M].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99: 120.
[25]Donald Reagan. An American Life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361-362.“The Phrase is Howell Raines”,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82.
[26]Gustavo Barros. Herbert A. Simon and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Boundaries and procedures.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 3 (119),July-September/2010: 457-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