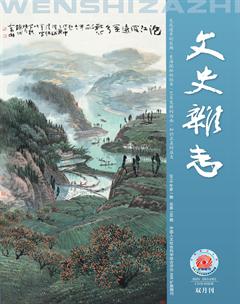左拉實驗小說第一部的意義
謝桃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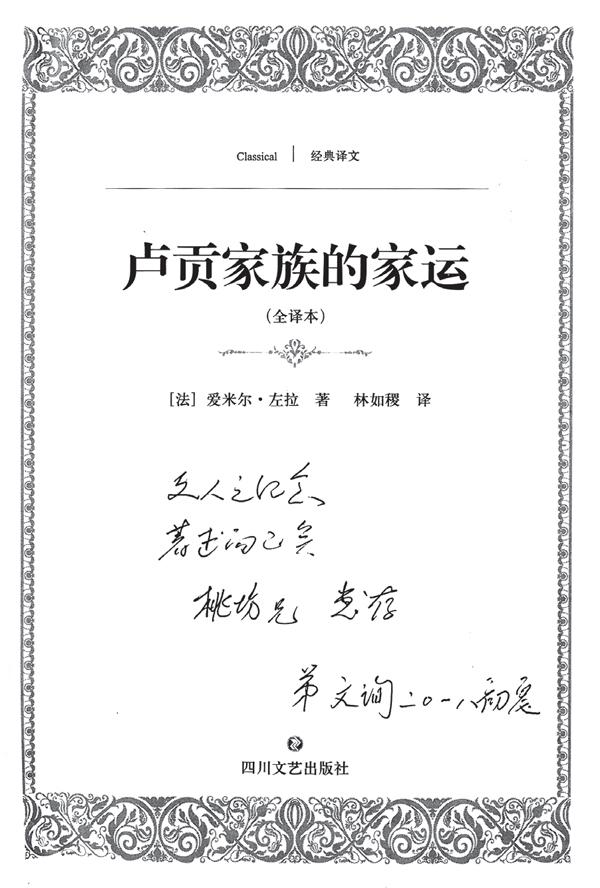

關鍵詞:左拉;林如稷;遺傳;帝政;共和;實驗小說
法國19世紀文學史上,愛米爾·左拉(Emile Zola)是繼巴爾扎克之后的偉大作家。他的《盧貢·馬加爾家傳》的總題名為《第二帝政時代一個家族之自然史及社會史》,由20部小說組成,共用了25年的時間。它是堪與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相媲美的巨著。在這部巨著中實踐了左拉提倡的實驗小說的理論,其中第一部小說《盧貢家族的家運》尤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它采用遺傳學的理論追溯了盧貢·馬加爾家族的血統淵源及家族的遺傳特點與演變發展,成為理解整部巨著家族遺傳的關鍵;其次它以法國南方一個縣城發生的政變,反映了法蘭西第二帝政時代的社會現實生活,預示了整部巨著的歷史背景;尤其是只有在這部小說中才通過一對年輕人參加反抗義軍的悲壯故事表達了作者光輝的共和思想。因此我們若要理解或研究左拉的巨著《盧貢·馬加爾家傳》,則此《盧貢家族的家運》是一部必讀的作品。此著的中譯者林如稷先生是中國新文學史上淺草社和沉鐘社的重要作家。他在法國留學時即喜愛左拉的作品,準備翻譯《盧貢·馬加爾家傳》的系列小說。他譯的左拉實驗小說的第一部《盧貢家族的家運》于193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今修訂本由四川文藝出版社于2018年5月出版,經林如稷先生之哲嗣林文詢先生據原稿校理。林如稷先生是小說家、詩人兼文藝理論家。他從法文原版將此著精心譯出,文筆流暢優美,特具法文特色,尤能體現左拉的創作風格,因而這是我國經典譯文中的精品。
一
左拉(1840—1902)是法國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家,他主張以科學的實驗方法從事文學創作。1880年他發表《實驗小說論》闡明了其新的創作理論。19世紀是自然科學輝煌發展的時代,各種自然科學取得巨大的成就;促使人類的智慧在不同的科學領域中得以充分和精湛的表現,體現人類尋求真知而向客觀真理的境界前進的崇高精神。然而文學創作是否可以采用科學的實驗方法,使它客觀、精細、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呢?左拉認為是完全可以的,因而他說:“根據我的理解,對實驗小說的含義予以明確闡述,在我看來是十分需要的。”[1]這要求小說家要像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研究非生物那樣,要像生物學家研究生物那樣,去研究人類的社會現象和人物的性格與情感。作家必須像科學家去揭示自然的秘密那樣去反映社會的現象,反對主觀想象的虛構杜撰,而且要找出社會中起決定的因素,盡可能地用觀察和實驗來檢驗所要表達的作家的先驗思想。當作家寫一部小說時,應力求達到對真理的完全認識;當計劃確定后,思想是自由的,但時時僅接受現象與決定因素相符的客觀事實。左拉實施其實驗小說計劃采取的方法是以研究一個家族,解剖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作為創作對象。他說:
在研究一個家族、一群人時,我認為社會環境同樣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將來有一天,生理學無疑會給我們解釋形成的思想與情感的道理。我們將會明瞭人這架單機器如何運轉,他如何思想,如何熱愛,怎樣從理智發展到激情和瘋狂。然而,這些現象生理器官機制的這些事實,是在內部環境影響下發生作用的,決不會孤立地在身體外部和真空中產生。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會中,社會環境中,因而對我們小說家來說,這種社會環境在不斷改變上述現象。[2]
這試圖說明個人的生理特征及思想情感與家族和社會環境存在著某種關系,每個人物決非孤立的現象。左拉的實驗小說理論的產生的契機,是他于1864年讀了克萊蒙恩·魯瓦耶譯的達爾文著作,繼讀了勒圖爾諾醫生的《情感生理學》,次年讀了克洛德·貝爾納的《實驗醫學導論》,特別是于1868-1869年關于魯加醫師的《自然遺傳論》作了許多札記。左拉認真研究了這些著作,于1868年開始創作《盧貢家族的家運》,于1871年出版。法國傳記作家阿爾芒·拉努以為在這部小說里,“不僅遺傳學為他的小說里人物提供了必要的聯系,而且科學也為他提供了嶄新的表現手法。是時,在《盧貢·馬加爾家族》的創作中,他一直堅持運用這種創作方法。他大膽地將醫學理論運用于文學。這樣一來,小說家不再是觀察家了,而是一個實驗家。這些思想的總和構成了他的自然主義理論,而實驗小說也隨之誕生了。”[3]左拉在這第一部實驗小說中是按照他理解的遺傳公律來考察盧貢·馬加爾家族的。他在序言里表明:“我想解說一個家族——一群人——如何在一個社會里面立身處世,這家族在發展之時,產生了十個、二十個分子,他們在頭一眼看來,好像極不相似,但經過分析之后,卻指示出他們是彼此深切地關聯著的。遺傳有它的公律,正如同萬有引力有它的公律一樣。我一方面解決環境與氣質的雙重問題,一方面努力尋求和追隨從一個人必然通到另一個人的嚴密線索。”[4]因此由二十部小說組成的《盧貢·馬加爾家傳》的巨著,雖然各部小說獨立完整,它們皆演繹著一個家族的遺傳公律,而這公律又受時代與社會環境的影響表現為極為復雜的現象和關系。左拉描寫這個龐大的家族所受遺傳公律的制約與變化,在這部《盧貢家族的家運》中作了探源析流的分析和敘述,成為我們理解整個巨著的家族遺傳變化的基本線索,展現了這個家族生理遺傳的譜系。
盧貢·馬加爾家族興起于法國南部樸若昂司省區的古城樸拉桑。這個縣城有1萬左右的居民,形成三個區:貴族區即圣馬可區,居住著貴族和官員;老城區居住著工人、商人和貧民,有一個墳場被改造為圣密特廣場;新城區居住著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為縣公署所在地,有一個索威爾公共廣場。在老城區圣密特廣場后面有一大片菜地為胡格家族經營。胡格家族在當地是頗為富有的,但只留下了一個女孩阿得拉伊德。她生于1768年,在18歲時,因父親由瘋狂病死去,她遂成為孤女。她身材高大細長,面色青白,眼光總是帶著驚惶的神情,其狂亂的精神是受了父親的遺傳。阿得拉伊德雖然有很大一筆財產,但無能力管理,不久她與園丁盧貢結婚了。盧貢是一位憨厚老實的青年農民,粗笨、魯鈍、庸俗。阿得拉伊德本來可以選擇社會條件較好的男子結婚,她卻選擇了盧貢,這在當地人們是難以理解的。婚后12月她生了一個男孩,不久盧貢突然死去。這位年輕寡婦,過了一年,便與情人馬加爾同居了。馬加爾居住在圣密特廣場鄰近胡格菜園的破屋內,他的父親是硝皮廠的工人。他30歲,高大精瘦,有著密雜的胡須,蓬頭亂發,棕褐色的眼睛閃閃發光,具有流浪漢的本性。他孤獨一人,大多數時間在外販賣私貨,或者偷獵。阿得拉伊德偏偏熱烈地喜愛他,只要他回到圣密特廣場邊的破屋,她便去與他同居,根本不顧市民們的議論。她與馬加爾生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在她分娩后經常二三月發作神經病,全身痙攣;只要她的情人回來,便丟下孩子們去了。在她42歲時,馬加爾在邊界被稅關的保安兵用槍打死了。她后來又被兒子奪去了財產,晚年孤獨地住在馬加爾留給她的破屋里,壁上掛著一支馬加爾的重型步槍。

林如稷譯《盧貢家族的家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阿得拉伊德與盧貢的合法生的兒子彼得·盧貢,受其父的遺傳,中等肥胖的身材,富于理性和計謀,處事謹慎,卻又矯偽、懦弱、陰險。他吞沒了母親的全部家產,懷著政治野心,與當地油商的女兒、黑皮膚、小個子而性格剛強的菲麗西德結婚。他們成為小說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他們改變了盧貢家族的家運。盧貢家族的遺傳,由菲麗西德而改良了。他們生了三子兩女。長子雨瑟,遺傳了父母的優點,身材肥胖,富有智慧和野心,做事專擅,有幾滴貴族的血統,后在巴黎成為律師并角逐權力。次子巴士加,身材高大,性情溫和莊嚴,具有正直的精神,熱愛科學,鄙薄財富,是杰出的醫師。他好像未受到盧貢家族的遺傳,令人懷疑遺傳公律出了錯誤。幼子阿里斯底德,身材瘦小,充滿貧欲,渴求財富和享樂,生情懶惰;妻子昂琪兒是軟弱的金發女子。盧貢家的大女兒馬爾塔在馬賽,二女兒西都妮在巴黎。
阿得拉伊德與馬加爾的私生子,一男一女。兒子昂多萬遺傳了父母的缺點,愛好流浪,有酗酒傾向,脾氣粗暴,懦弱而又陰險,自私自利,貪圖享樂,反復無常,混入共和黨而進行政治投機。他與芬娜結婚,有兩女一子。長女莉莎為郵務局長婢女,次女薏爾維絲,跛腳,下流,虛弱,嫁與工人;幼子若望勤勞健康,在盧貢家當學徒。阿得拉伊德與馬加爾生的女兒玉爾蘇有慢性肺癆,嫁與帽商莫瑞,生了一女兩子。女兒海倫嫁與雇員;大兒子弗朗奈阿與盧貢的二女瑪爾塔結婚,成為盧貢商店的幫手;小兒子西魏爾是工人,成為狂熱的共和黨人,為其崇高的理想而參加了反抗義軍。
《盧貢家族的家運》的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851年12月上旬的數日,左拉以追述的方式簡略地敘述了盧貢·馬加爾家族的形成,而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分析了這個家族登場人物所受之遺傳及其在時代與環境作用下所發生的變異,呈現出極為復雜的情況。他在這第一部實驗小說中所繪制的盧貢·馬加爾家族的譜系在此后的系列小說里分別演繹了這個家族所受生物遺傳公律的支配。這主要表現為盧貢一系的人物為政治家、律師、資本家、醫生,進入了社會的上層;馬加爾一系的人物則為小商、工人、貧民、妓女,淪落為社會的底層。因此這部小說是理解和研究《盧貢·馬加爾家傳》巨著時必讀的,尤其是這部小說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皆是系列小說中最為優秀和杰出的。
當1851年故事發生之時,家族中的阿德拉伊德已經70多歲,人們稱她為第德太婆,她是孤苦的老婦人,居住在破屋里,早已被兒女和人們遺忘了。彼得·盧貢已50歲,肚子大得挺出,面孔呆滯灰白,外表頗為得意和莊嚴,掩藏著他的不得志的憤怒和強烈的貪婪。他等待著社會政治的變化以實現掠奪財富和竊取政權的野心。在這個樸拉桑小城發生的陰謀政變使盧貢·馬加爾家族的成員紛紛登場,盧貢家族的家運由此有了轉機。
二
法蘭西的大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光輝的一頁。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進攻丟伊勒宮,王權中止;9月2日至5日處死大批貴族及反革命分子;9月21日國民大會開幕,宣布法蘭西為共和國。1793年1月21日共和國處死國王路易十六,5月31日巴黎人民包圍國民大會,革命派雅各賓黨專政。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共和國的社會理想。此后拿破侖建立了第一帝政,1848年又再建共和政制,而政權落到拿破侖一世之侄路易·拿破侖·朋拿巴德親王之手。1851年12月1日路易·拿破侖發動政變,3萬名兵士部署巴黎,宣布戒嚴,政變者建議由親王——總統起草新憲法。共和派議員組織反抗力量,巴黎及外省的工業區和紅色農業區組成反抗義軍。新建立的第二帝政在各省成立特別委員會,逮捕了26000名反對分子,徹底消滅了共和派。自1851年至1870年為法國第二帝政專制的時代。1871年《盧貢家族的家運》出版時,第二帝政剛剛結束,左拉的巨著《盧貢·馬加爾家傳》實是第二帝政的自然史和社會史。他對這時代是極為憤恨的:
第二帝國激起了人們的貪欲與野心,貪欲與野心大放縱。渴望享樂,而且享樂得精神與肉體都疲憊不堪。對于肉體來說,是商業的大繁榮,投機倒把的狂熱;對精神來說,是思想的高度緊張,與近乎瘋狂的行為。疲勞過度,然后是墜毀。[5]
他的巨著即是以第二帝政時代為歷史背景。左拉自述創作的意圖是:“我把它置于現代的真實性上寫種種野心與貪欲的擁擠沖突。我考察一個投身于現代社會的家族的野心與貪欲,它以超人的努力進行奮斗,卻由于自己的遺傳性與環境的影響,剛接近成功又掉落下來,結果產生出一些真正道德上的怪物(教士、殺人犯、藝術家)。時代是混亂的,我所寫的正是時代的混亂。”[6]這部家族史系列小說的第一部正是發生在1851年12月的政變時期。它對南方的樸拉桑小城也有突出的反映,或者我們可以由此見到一個巴黎陰謀政變的縮影。
法國政變時,樸拉桑由自由黨人、正統王黨、峨爾良旁系王黨、朋拿巴德黨以及教士的混合而形成強大的反動勢力,它們準備著去撲滅共和制。這個反動勢力的結合有加拉爾網侯爵、市議員格魯納、地主儒第葉、大隊長西加多、書店老板魏業為代表的人物。他們時常在彼得·盧貢客廳里聚會,向共和制發出攻擊的吠叫。1851年11月醞釀政變。路易·拿破侖稱帝的消息于12月3日午后傳到了樸拉桑,第5日鄰近的反抗義軍武裝起來了,第7日傳來有3000人的義軍將到達樸拉桑。“這些大事變成了盧貢家族的家運。他們投身混雜在這個變動的階段之中,他們在自由的廢址上長大了。這些待機而起的強盜所搶劫的便是共和,在別人扼住它咽喉的時候,他們幫助來攔路打劫它。”左拉對小縣城政變的描寫是帶著強烈的主觀情感的,表達了他的憎恨與鄙視,因此我們絕不要以為自然主義的作品是純客觀的照相似的反映現實生活。
反抗義軍于晚上暫時駐扎在樸拉桑,這僅是路過,而非目的地,所以次日早上便開發了。義軍俘去了市長及一些官員,地方的反動分子都藏匿起來了。義軍撤走后,盧貢從母親阿得拉伊德的破屋里出來,他躲在此處是最安全的。他感到共和黨人把樸拉桑給他留下了,等待他來收拾殘局。他糾結一群反動勢力,串通黨徒共40余人聚集在廠棚(藏槍支的地方)進行分工。市政廳尚有留守的20多個共和黨人,而政治投機分子——盧貢的同母異父弟弟昂多萬正坐在市長的位子上,想當政府的領袖。晚上盧貢作了周密的計劃。拂曉時,他帶著一群黨徒單線行至市政廳。守衛大門的兵士抱著槍坐在門口睡著了,盧貢上前奪下槍并制服了兵士。他們悄悄進入市長辦公室。昂多萬在與四人起草告示,盧貢等人與他們發生沖突。在爭斗的過程中,盧貢手上的長槍機柄滑動,發生一聲巨響,子彈飛出去打碎辦公室內的一面大鏡子;又有三人由儒第葉指揮向天空開槍。昂多萬被俘,其余的共和黨人逃散,盧貢等人勝利了。鏡子的打碎有如荷馬史詩式的偉大結局,它迅即被盧貢夸張講演,于是樸拉桑市民中傳說著41個小紳士掃蕩了3000反抗軍的神話。次日晚上,傳說一小群反抗義軍將從樸拉桑經過,但天亮了,未見一個反抗軍。不久又傳說巴黎政變失敗,路易·拿破侖親王被囚,馬賽及南方各省均被反抗軍占領,反抗軍快到樸拉桑來了。全城立即陷入恐懼之中,而盧貢等人更加驚惶失措。盧貢的妻子菲麗西德從郵局獲得大兒子雨瑟來自巴黎的密信,告知政變完全成功,巴黎被壓服,各省無舉動。他還希望父母對局部反抗軍的叛亂采取堅決鎮壓的態度。盧貢夫婦得知消息后,制定了一個陰謀的計劃,即讓恐怖的氣氛更厲害地鬧下去,而盧貢保持英雄的姿態,制造一場政變。由菲麗西德去市政廳說服被關押的昂多萬,把他放出去,由他組織同伙把市長辦公所奪取回來,然后給他1000佛郎逃出國界。次日盧貢獨自一人威風凜凜占據著市長辦公室,中午去巡視各城門,命令國防軍嚴守。晚上盧貢組織國防軍分若干小隊秘密到市政廳埋伏,告知共和黨人暴亂,熄滅了燈光,準備消滅來犯的共和黨人。半夜昂多萬與狂熱的共和黨徒50人,宣稱反抗軍快到城門,他們先奪取市政廳。這伙人沖進市政廳后被埋伏的國防軍包圍。一個國防兵被打死,三個共和黨人死了,另有一個死在廣場,共和黨人逃散,教堂警鐘轟鳴,城內保安軍和國防軍奔跑,似乎有數萬人在進行著偉大的戰爭。然而這場槍戰的真相卻從來沒有人知道。官兵到了,市長回來了,聯隊長也來了,宣布逮捕和處死共和黨人。省長接見了盧貢等城市的保衛者。很快雨瑟來信告知,父親盧貢將被委任為樸拉桑的特別收稅員。盧貢家族將飛黃騰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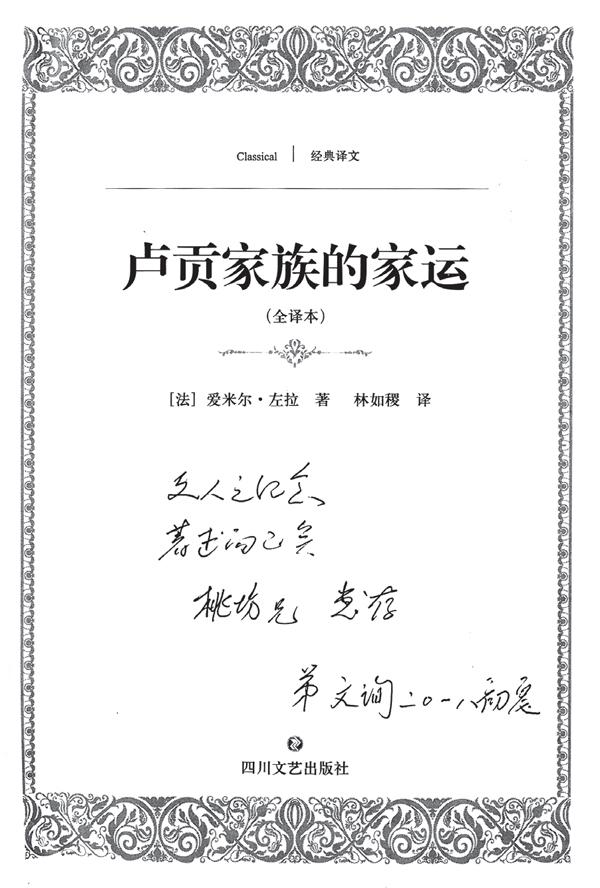
無論巴黎的政變還是樸拉桑的政變,它們有某些共同之處。政變者們對陰謀計劃是否能成功,實際并無信心。他們如果失敗便立即成為階下囚,被加以叛國或盜匪的罪名;如僥幸成功,則將卑劣自私的打算變成愛國的大義,陰謀變成義舉,他們也成為英雄而彪炳史冊了。歷史上的政變的成功與否,都具有偶然性,而歷史的必然又總是以偶然性出現的。樸拉桑的政變是巴黎政變的局部反映,左拉通過它反映了路易·拿破侖政變的本質。這次政變的成功開始了法國第二帝國的歷史,它是盧貢·馬加爾家族系列故事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左拉細致而真實地揭露了政變者的自私心理和可恥的陰謀,將一場滑稽丑惡的鬧劇的真相細加描繪,體現了批判的深度和藝術的力量。作者不僅在寫一個家族在政變中依附反動勢力的發家史,更重要的是由此展開“一個充滿瘋狂和恥辱的奇異時代的畫圖”。

馬奈繪左拉肖像(1868年)
三
法國在第二帝政時期雖然實施專制,但共和反對派仍然通過報刊進行活動。1869年共和派報紙的總數為十萬份,這是一個巨大的數目。此年在選舉之前,共和派制定了著名的《貝爾維爾綱領》,要求個人自由,出版完全自由,真正的普選,集會集社權,義務教育,教會與國家分離,按社會等級納稅等等。[7]左拉是共和的擁護者,他的朋友多為共和黨人。1870年8月5日第二帝國覆亡的前夕,左拉發表了一篇《法蘭西萬歲》的文章,呼吁和平:
在此時刻,在萊因河兩岸,集結著反帝國的五萬名將士。他們不要戰爭,不要常備軍隊,更不要把整個民族的生命和命運交給一個獨裁者的可惡政府。[8]
左拉因此被指控為“煽動對政府的不滿和仇恨,蠱惑人們違逆法律”。幸好帝國很快倒臺,否則左拉會被受到審判的。由此我們可見左拉對共和擁護和對帝國的憎恨。當我們縱觀《盧貢·馬加爾家傳》的系列小說時,顯而易見除了最后一部《巴士加醫師》而外,沒有一個主要人物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而都是被否定的被批判的。左拉的共和理想,在第一部實驗小說《盧貢家族的家運》中通過一對年輕人——西魏爾和蜜埃特參加反抗義軍的英雄的悲壯故事得以唯一的充分表達。它成為整部巨著中最為鮮明的理想之光。
西魏爾是阿得拉伊德與馬加爾的私生女玉爾蘇的幼子。這孩子6歲時父母死了,由外祖母阿得拉伊德(第德太婆)撫養,在嚴重的愁郁貧苦中成長;12歲時學習制車技藝,由學徒成為工人。他身上承襲的外祖母的精神昏亂已轉變為慢性的狂熱,轉變為對一切偉大的不可能的事物向往的激情。他有著固執的求知欲望,愛深思,具有雄偉的壯志,努力追求偉大的思想,是極高尚而天真的——共和國的思想自然地激發起來。他17歲時,已是一位健美的青年,面龐瘦而狹長,厚嘴鼻,黑灰色的眼睛,中等的粗壯身材,有著堅強的面相,著綠色綿絨短上衣褲,戴軟呢帽。他與附近農莊的女子蜜埃特相愛。蜜埃特的父親是農民,因一次偷獵而用步槍打死一名保安隊兵士,遂囚在監獄做苦工。她9歲時曾跟祖父乞討生活,后到樸拉桑姑母家莊園做農活。這位南方姑娘發育很快,加上長期的農莊勞動,在13歲時已強壯如同成年的女子,充滿熱烈的生命活力,有著豐腴的奇異的動人之美。1851年12月7日反抗義軍將到樸拉桑時,西魏爾準備參加義軍,晚上在圣密特廣場與蜜埃特約會。他對蜜埃特說:“反抗義軍已經出動了,他們昨晚是在阿波瓦日過夜的。我們要去加在他們一起,這是已經決定的了。”他堅信:“斗爭是不能避免的了,不過正義是在我們這邊,我們會勝利的。”他將對共和國的愛和對蜜埃特的愛連結在一起,他說:“我把整個的心給了你。我愛共和國,你看,因為是我愛你。”他們的愛情與共和理想都是純潔的。他們離開廣場前去迎接義軍。夜10點鐘妮司大道的山坡后的大道轉彎處,傳來共和國歌《馬賽曲》,帶著復仇的憤怒情緒,歌聲激蕩,產生可怕的震響。左拉以熱烈的情感描述說:“隊伍帶著一種卓絕的不可抵抗的激情走下來,再沒有比這幾千人在天地的死寂和冰凍的和平里的出現更非常的偉大了……《馬賽曲》充滿了天際,如同一些巨大的嘴在吹奏神圣的軍號,用鋼鐵一般的冷酷態度把顫響《馬賽曲》向山谷的一切角隅投去。”義軍有3000余人,參軍的沿途增加,隊伍8人一排,浩蕩地前進。西魏爾和蜜埃特加入義軍。蜜埃特在銀色的月光中,身著朱紅色外衣,紅色的風帽像1793年大革命時共和黨人戴的赤色軟帽。她從義軍中拿過大旗,把旗桿緊緊挨在胸膛,挺起身子,血紅的大旗飄飛;這時她有如自由女神一樣。在西魏爾看來,她是那樣的偉大和神圣!
反抗義軍占領了樸拉桑市政廳,西魏爾在爭奪保安隊兵士昂佳得的馬槍時將他的右眼打破。西魏爾到圣密特廣場角落的破屋去看望外祖母第德太婆,告訴她打死了一名保安兵士。第德太婆突然眼睛像燃燒的強烈的炬火。她激動地將馬加爾的重型步槍從墻上取下給外孫說:“這就是他給我所遺留下的一切了!……你打死了一個保安隊兵士。他嗎,他卻是被一些保安隊的兵士打死的啦。”左拉對阿得拉伊德的描敘不多,但是可以透露出她是愛馬加爾的,馬加爾也未像當地人猜測的是為了巨大的財產,他具有一種反叛的精神。這位孤獨抑郁和神經昏亂的老婦人,她厭惡和憎恨兒子們,卻特別愛這由她撫養成人的外孫。當她將馬加爾留下的槍交給外孫時是帶著復仇的心情。她愛外孫即是支持共和,對一切發生的事情似乎是看得清楚的。
次日義軍向阿耳竭爾大道前進,在阿耳竭爾城停留了兩天,失去了戰機。清晨,官軍出現在平原邊上,義軍總指揮帶著佩刀,部署包抄官軍,首先發起進攻。官軍馬隊很快將平原上的義軍掃滅,總指揮逃走,義軍潰敗。西魏爾和蜜埃特的一隊義軍正面與官軍交戰,最后剩下的8個義軍,又死去3個。這時:
蜜埃特把旗子是愈高高地舉起,她始終握緊了拳頭把它向她前面舉著,就向一把光明的火炬一樣。旗子上面,是早就穿了不少的彈孔……大旗正是從蜜埃特手上折倒了。小女孩兩只拳頭緊握地放在胸前,腦袋翻向下面的,含著一種劇烈的痛苦神情,正慢慢地轉動著。她并沒有發出一聲喊叫,她向后倒下,躺在大旗的血紅的旗面之上。
左拉以痛苦而激烈的情感描寫了蜜埃特就義的悲壯的場面,象征著共和的理想的大旗倒下,反動的帝政陰謀得逞了。然而蜜埃特的純潔的熱烈的共和精神將永遠鼓舞著熱愛共和的人們。
西魏爾悲痛地抱著蜜埃特時,他被俘了。政變的勝利者們在樸拉桑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官軍決定槍斃一些重犯俘虜。黃昏時那位右眼被打破的保安隊兵士昂佳得認出了西魏爾。他帶著復仇的火焰,將西魏爾帶到圣密特廣場角落——即西魏爾與蜜埃特約會的地方槍決了。這悲慘的一幕恰恰被第德太婆在破屋附近看見。她回到家里精神病發作了,將死時,衣帶松開,白發散亂,蒼白的臉上泛出紅團,痙攣的身軀突然直挺,大聲叫道:
我這個不幸的婦人!我只會生了一群豺狼。整一家族,整一窩豺狼。……只有一個可憐的孩子,他們都要把他吃了,各人都咬了一口,他們的嘴唇上還粘滿鮮血呢!……啊,這些該死的東西。他們干了搶劫的事,他們殺害了人,然而他們都像闊老爺一般地過活著呢。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東西!
這不是瘋話。阿得拉伊德親歷了盧貢·馬加爾家族的發展變化,雖然精神昏亂卻直覺地感知是非與善惡。這個家族唯一的正直而有崇高共和理想的可愛孩子西魏爾被殺害了,她也悲痛憤怒地死了,留下了一群豺狼。這時盧貢等人正興高采烈地歡迎新的“帝政”,歡迎狂熱的貪欲的時代的降臨。
左拉以厭惡的憎恨的鄙視的情感再現了一場陰謀政變的可恥的成功;卻以同情和惋惜的情感描寫了反抗義軍的失敗,又熱烈地歌頌了偉大的共和精神。作者愛憎的態度在《盧貢家族的家運》中的表現是鮮明的。
四
林如稷自1923年冬赴法國留學,先后在里昂大學和巴黎大學法學院主攻經濟學,同時選擇了文學院的幾門功課,特別喜愛左拉的作品;于1930年秋歸國。他是中國第一位翻譯和研究左拉作品的學者,1935年受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的委托翻譯《左拉集》,于1936年翻譯出版了《盧貢家族的家運》;本來計劃將《盧貢·馬加爾家傳》中的其他八種小說譯出的,然而未果。1948年至1949年間他翻譯了《左拉傳》《左拉青年時代的生活》《內戰中的文人左拉》,寫有《關于左拉的生活》《左拉逝世四十五周年祭》和《左拉與社會主義》等論文。這部《盧貢家族的家運》的譯著是非常杰出的經典譯文,系林如稷根據兩種法文原本譯出,最能體現法文的嚴密細致,亦能忠實地表現左拉的藝術風格;尤其是使用了漢語的優雅流美和純凈的白話文學語言,這在諸種經典譯文中是罕有可比擬的。關于這部小說的名稱,林如稷據法文原意譯為《盧貢家族的家運》,它確切地表明了一個家族的家運發生的轉變。此后有譯為《盧貢家的發跡》,或譯為《盧貢家族的命運》的;但“盧貢家”“發跡”“命運”這些詞語顯然不符合左拉原意。左拉于1877年再版此部小說時加了《盧貢·馬加爾家傳總序》,我們試將林如稷和柳鳴九所譯此文的一小段作比較:
林譯:“盧貢·馬加爾家族”,這群人,即我所提出要研究的家庭,它的特征正是過度的貪欲和在我們這個追求享受的時代中的平民階級的廣泛興起。在生理方面,他們是在一個家庭之內受到第一次的機體傷害之后所造成的神經上與血統上的變態病癥的慢性繼承者,這些神經上與血統上的變態病癥,對于家庭的每個人,又隨著環境之不同,決定了各種情感、欲望、情欲,即一切屬于自然和本能的人性表露,而這些表現的具體事實,也即是一般所謂的道德和罪惡。
柳譯:我所要研究的盧貢·馬加爾家族有一個特征。那就是貪欲的放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里向享樂奔騰而去的狂潮。在生理上這個家庭的成員都是神經變態與血型變態的繼承者,這種變態來自最初一次器官的損壞,它在整個家族中都有表現,它隨著環境的不同,在每一個家族成員身上造成種種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種種不同的人態,或為自然的,或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們則以善德或罪惡相稱。[9]
這段文字,林譯為兩句,206字;柳譯為三句,180字。顯然林譯較細致,頗有法文意味,或歐化的文風;而柳譯較為簡略,具有漢語的明快風格。我以為翻譯作品仍以保存其特殊的文風為佳。從林譯的一段文字亦可見整部譯作的行文特色了。現在《盧貢家族的家運》只有林譯。它附有譯者對歷史、地理、人物、民俗等的注釋66條,長者達千余字,可供讀者閱讀時作參考;還附有左拉的女兒于1927年寫的《愛米爾·左拉略傳》,這是研究左拉生平與創作的寶貴資料。左拉這部小說乃其實驗小說的經典,林如稷的譯本更是經典的譯文。譯者說:“這一卷非但故事本身動人,而且又極完整,可以獨立,在結構技巧上面更是謹嚴不茍。至于書中所描寫的許多情節,未嘗不可以移過來作為我們現在社會的寫照。”此著的真實性、現實性、精密的構思和深刻的意義,使它永遠具有旺盛藝術生命。
注釋:
[1][2][9]左拉:《實驗小說論》,呂永真譯,見柳鳴九編《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8頁,第750頁,第828頁。
[3][8][法]阿爾芒·拉努:《左拉》,馬中林譯,黃河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頁,第155-156頁。
[4]左拉:《盧貢家族的家運》,林如稷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以下文中引用此部小說原文,不再注出。
[5][6]左拉:《關于家族史小說總體構思的札記》,《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第733頁。
[7]參見[法]皮埃爾·米蓋爾:《法國史》(1976年),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399頁。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