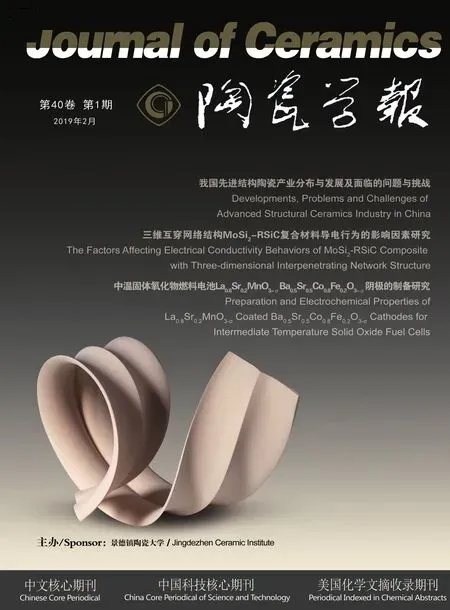在歷史田野里建構中國陶瓷科學體系
——兼論寧鋼學術團隊“百工錄”叢書的方法論意義
王洪偉
(河南大學美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0 引 言
在中國陶瓷史上,獨特的胎釉料配制、成型工藝和燒成制度是中國陶瓷文化的核心和根本。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西式的“實驗室科學”為主體的中國陶瓷科學研究逐漸占領了中國陶瓷科技研究的主體。實際上,中國陶瓷之所以延續數千年窯火不息、綿延長存,全在乎中國陶瓷獨特的“經驗科學”特質。
如果研究中國陶瓷史不研究中國陶瓷工藝或科學,那樣的中國陶瓷史體系只能觸及中國陶瓷史的皮毛;如果沿襲西式的“實驗室科學”框架構建中國陶瓷科學史體系,可能永遠難以抵達中國陶瓷工藝的真諦。以寧鋼教授為核心的景德鎮陶瓷大學學術團隊于2017年至2018年研究出版的“百工錄”叢書,以獨特的“中國性”視角,深入景德鎮陶瓷產區,以沉寂于大小作坊的杰出陶瓷工匠的工藝口述為基礎,重建門類性的景德鎮陶瓷科技史,顯得尤為難能可貴,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1 百工錄:向傳統制瓷技藝致敬
2016年,景德鎮陶瓷大學與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簽訂戰略合作,出版一套以景德鎮傳統陶瓷工藝為主題的“百工錄”叢書,以求系統整理景德鎮傳統陶瓷技藝。到2018年度,“百工錄”叢書五部專著已經完成出版。
陶瓷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科技發明與藝術創造,隨著人類文明的產生而產生,也伴隨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而變化,更伴隨著科技水平的進步而改良。唐宋以降,中國陶瓷不僅遠銷海外,也是國內高端消費追逐的奢侈品。但是19世紀末以來,曾經輝煌一時的中國陶瓷陷入低谷,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傳統的陶瓷工藝技術才逐漸受到海內外業界的重新重視,而且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復興趨勢。但是由于現代西方陶瓷科學和現代藝術形式的侵入,中國傳統的陶瓷工藝似乎被戴“落后”的代名詞為人所不屑。實際上,中國陶瓷之所以為“中國”陶瓷,就在于其悠久而內涵豐富的諸類工藝技術經驗并不為外人道,這是迥異于國外“先進”陶瓷的中國特質。
寧鋼學術團隊以“百工錄”為主題,深挖作為中國千年瓷都的景德鎮傳統陶瓷工藝內涵,從而表達對傳統制瓷技藝的尊敬,同時展現景德鎮古今陶瓷制作者如何以工藝技術為基礎的歷史創造。“百工錄”收錄了包含景德鎮陶瓷成型、裝飾在內的數十個類別,以期建構出一套完整展現景德鎮乃至中國陶瓷工藝的學術體系,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
從創造歷史者到建構歷史者
截至目前為止,“百工錄”叢書已經出版五部學術專著,寧鋼、劉樂君、蔡華菲集中梳理景德鎮陶瓷古彩工藝的歷史演化;龔保家、陳寶側重對景德鎮陶瓷高溫顏色釉工藝技術的展述;黃勝主要敘述的是景德鎮影青刻花技藝;余勇、高相坤系統整理了景德鎮釉下青花裝飾技藝;孔錚楨則圍繞景德鎮玲瓏裝飾技藝的歷史和當代轉換展開深入研究。
“百工錄”叢書的研究者和寫作者學術團隊成員,幾乎都是對景德鎮傳統陶瓷技藝深有研究并矢志不移于傳統陶瓷的現代性轉型的藝術創作者。叢書學術團隊的領軍人物寧鋼教授,出生于景德鎮,從小深受景德鎮陶瓷工藝的浸潤,跟隨陶瓷老師傅苦苦研學景德鎮諸門類傳統陶瓷技藝,成長起來后也基本立足于景德鎮傳統陶瓷工藝進行現代藝術創作和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陶瓷藝術風格。20世紀90年代初,寧鋼嘗試將民間藝術的剪紙、臉譜藝術等融入陶藝創作中,創作出“蝶舞”、“剪紙小掛盤”、“喜怒哀樂”、“京劇臉譜”和“紅杏枝頭春意鬧”等陶瓷新作,嘗試借重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的裝飾風格貫通陶藝之路。同時,寧鋼還注重陶瓷形體的塑造,通過扭曲的器物形體表現粗獷的陶瓷藝術效果。另外,寧鋼還嘗試運用不規則泥板鑲嵌,畫面題材大多以蓮花禽鳥、蓮花魚戲為主題,既有傳統功力,又富有現代陶藝情趣。歷經多年的探索之后,寧鋼陶藝創作不斷變換器物畫面裝飾風格,將豐富多彩的高溫顏色釉與梅花、荷花、荷鶴等釉上彩繪結合,表現出顏色釉色彩厚樸、鮮麗純正、質感豐富、晶瑩光潔的現代陶藝風韻,極富視覺沖擊力。在工藝技法上,寧鋼回到中國傳統陶瓷技藝的深處,利用釉上工筆、潑釉斗彩、潑釉斗彩加淺浮雕、潑釉粉彩等景德鎮傳統陶瓷工藝,并加以個性化的創造。寧鋼通過將傳統中國文人畫中擅于呈現的梅花、荷花、鶴等美好意象,運用傳統陶瓷工藝技法,紅、金等底色豐盈運用,黃、綠等色塊交錯對比配置,傳統民俗色彩與現代西洋色彩沖突效果融會貫通,再糅入頗富現代設計感和現代構成感的視覺新元素,實現了陶藝形體、釉色和瓷畫藝術的完美結合。
與寧鋼的藝術和學術經歷類似,叢書作者龔保家、劉樂君都出生于景德鎮,深受景德鎮傳統陶瓷工藝的浸染,并進一步在傳統陶瓷工藝的基礎上進一步創造性轉化,賦予傳統陶瓷以新的藝術形式。余勇、黃勝、孔錚楨也都是偏向于立足景德鎮傳統陶瓷工藝的當代陶瓷藝術家,對于景德鎮傳統陶瓷工藝都深有認知。換而言之,“百工錄”叢書作者本身就是中國陶瓷史的創造者,正因為他們身在其中,“主體寫史”就能夠更切近景德鎮陶瓷工藝的本體,由此建構的景德鎮陶瓷工藝史就顯得更貼近歷史的真實。
2 走向歷史田野,傾聽實踐者的聲音
古陶瓷技藝是最具“中國性”的傳統手工藝,景德鎮陶瓷技藝又是中國陶瓷技藝中類型最為豐富傳統手工技藝。陶瓷歷史文獻尤其是科技文獻與陶瓷工藝科技實際存在不小的差距,“學術語言”與匠師經驗之間似乎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目不識丁的陶瓷藝人仰仗其粗淺的地方陶瓷技藝承傳常識即可燒造出獨具特色的陶瓷器物,而學富五車的“專家學者”面對古瓷片是手拉坯還是注漿器件卻莫衷一是、胡言亂語。 恰如前述,中國陶瓷具有悠久的燒造傳統,具有連續性的歷史傳承關聯,這是中國陶瓷史迥異于其他國外陶瓷史的特別之處。另外,唐宋以降中國陶瓷工藝技術之所以連續性延續,也與中國陶瓷技藝獨特的內在性的傳承模式密切相關,經驗性傳承遠遠大于“實驗室”現代科學性質的傳播,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工匠之間“身體性”的面對面經驗性傳承。
“百工錄”的作者們盡管也是景德鎮陶瓷工藝的傳承者和創造者,但他們在梳理門類陶瓷工藝的歷史和科技文獻的同時,都無一例外地走向景德鎮陶瓷的“歷史田野”,走村串巷,訪談陶瓷老藝人和當代陶藝家,傾聽民間陶瓷工匠和當代學院派陶藝家的實踐聲音。當然,作為一種地方性資源依賴性很強的傳統手工藝,陶瓷匠師是陶瓷科技史建構的主體,是一種活態的科技表達,是傳統技藝的傳承者、延續者和創新者,才是歷史真正的主人。“百工錄”的寫作者們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和學術訪談,建構起切近實踐的真實的景德鎮陶瓷工藝史體系。由此,“百工錄”叢書的研究和寫作范式就具有了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傳統技藝向來是一個保守的行業,一般靠祖傳家傳或師徒傳承的言傳身教延續核心工藝技術。作為延續數百、千余年的景德鎮諸類陶瓷技藝,燒成工藝上常常帶有不可預期、非完全可控的“欠標準化”特點,作為這樣的經驗性手工技藝,傳統陶瓷技藝無法靠嚴密、受控的、可重復的實驗室實驗而成功燒制。首先,傳統陶瓷技藝更主要地是一種純粹經驗,而非受控的可重復的科學或技術,身體性特征比較突出。但每一次燒窯都有不同的經驗和體驗。其次,傳統陶瓷燒成工藝個性化、偶然性突出,同樣的泥釉料配方、同樣的窯爐結構、同樣的燒窯師傅、同樣的天氣氣候、同樣的燒成制度……每燒一窯都不可預期、也不可預測,甚至同一窯的陶瓷器物因放置窯爐內的位置不同,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釉色藝術效果。第三,基于此,景德鎮傳統陶瓷燒制技藝在經驗層面上就戛然而止了,按照現代科學試驗的研發程序顯然難以達成,經驗只能靠經驗敘述來表達。第四,盡管近現代以來,大陸甚至歐美不少飽受現代物理、化學系統學術訓練的專家學者進入景德鎮陶瓷燒造實踐,嘗試研制大量的泥釉料組成結構分析,但由于一般性的陶瓷工藝學、硅酸鹽及物理、化學知識與傳統的陶瓷燒造技藝相去甚遠。歷史地看,在景德鎮陶瓷發展史上,陶瓷技藝的傳承和創造不僅僅源自那些學富五車的“現代陶瓷科技專家學者”的貢獻,還主要來自一般性陶瓷匠師的經驗性“試錯式”研燒。諸多景德鎮乃至中國歷史名窯的陶瓷燒制技藝的難以完全提升到現代科學品質,很大程度上,景德鎮陶瓷燒制技藝依然還掌握在平凡陶瓷工匠手里,而這些陶瓷工匠基本都是能制作、能燒窯但不能說、更不會寫,他們傾其一生研究的燒造技藝可能需要下一代傾其一生去研學,陶瓷燒造技藝在一種周而復始的“研制-再研制”的低層次循環中緩慢進化。這也是中國傳統陶瓷工藝科技急需改觀、急需“現代化”的一面。基于陶瓷技藝的這種特性,于是,隱晦的普通民間陶瓷工匠“實踐意識”之中的陶瓷技藝的可視化、文本化在現代轉型的壓力下就顯得格外迫切窘急。
于是,如何將這種潛隱在景德鎮陶瓷匠師乃至陶藝家燒制經驗過程中的陶瓷工藝科技挖掘成文本、圖繪形式不僅是面對傳統文化資源現代性轉型過程面臨的切實的實際難題,也面臨著傳統技藝科技史述研究范式轉換的考量。如此一來,走向陶瓷產區的“歷史田野”,針對一線陶瓷匠師乃至陶藝家的陶瓷科技口述就是這樣一種研究范式轉型的產物。
口述科技史引起傳統技藝科技史述一場“眼光向下”的革命,引領我們建構起一種以一線陶瓷匠師和陶藝家為主體的、更接近歷史實際的景德鎮乃至中國陶瓷科技史框架體系。要完成這樣的一種史學使命:一要走進“歷史田野”,借重下“活態”的陶瓷匠師和陶藝家的技藝口述完成建構邁向人民的陶瓷科技史書寫;二是參與史述的知識分子當走向陶瓷技藝的田野實踐,結合科技文獻、匠師口述,從體驗化、經驗性的陶瓷工藝實踐中獲取陶瓷科技的真實。由此建構邁向人民、走向“歷史田野”的真實可靠的中國陶瓷科技史體系。這是“百工錄”叢書的方法論意義所在。
3 從傳統到當代:“貫通性”的陶瓷史研究
傳統中國陶瓷史研究和寫作常常限于晚清,民國陶瓷史也僅只略略提及。“百工錄”叢書的很大一個特點在于,除了對景德鎮諸類傳統陶瓷工藝在田野訪談和實踐基礎上的整理之外,進一步延續到當代的景德鎮陶瓷工藝創造,尤其是具有現代科學和現代藝術思想的“學院派”經驗的總結和梳理。余勇在縱觀性地梳理完景德鎮傳統青花工藝技術創造之后,并沒有戛然而止。在他看來,青花是我國陶瓷藝術中經典的元素與符號,但是在現代陶瓷藝術的發展中也有著廣泛的空間。傳統青花有自身系統的裝飾手法和構圖程式,經過七百年左右的發展已經十分成熟,現代青花藝術借鑒傳統經典的形式和技法的同時,創造出了許多新的裝飾手法及表現形式。尤其是現代青花裝飾與現代陶藝相結合,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藝術語言表達新時代的陶瓷藝術審美趨向,同時表現出藝術家的個人風格與內心世界。在余勇看來,現代青花的創作技法與裝飾形式,適合于表現作者的主觀情感與藝術理念、創作想法,其效果也是豐富多樣的。 于是余勇在其書中以大量的篇幅整理了像白明、干道甫、黃煥義等現代陶藝家關于青花裝飾的現代藝術創造,貫通性地反應青花史的當代面貌,為當代人寫作中國陶瓷史提供了一種歷史性貫通的新思維。
與此類似,《陶瓷古彩裝飾》也非對古代景德鎮古彩工藝技術的局限性表述,除了對康熙以降、民國以往的古彩工藝技術進行詳盡的敘述之外,還更多關注了段茂發、歐陽光、藍國華、戴榮華、方復、龔龍水等堅守傳統的古彩匠師的工藝創造風格,而且還將寫史的視野延伸到施于人、朱樂耕、寧鋼、劉樂君、劉芳等具有現代藝術思維的現當代陶藝家關于古彩裝飾的新創造 ,彌合傳統古彩藝術與現當代古彩藝術人為割裂的鴻溝,從傳統到現代,貫通性地建構起中國古彩陶瓷藝術的歷史線索。對于整體的中國陶瓷史研究和寫作都具有強烈的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