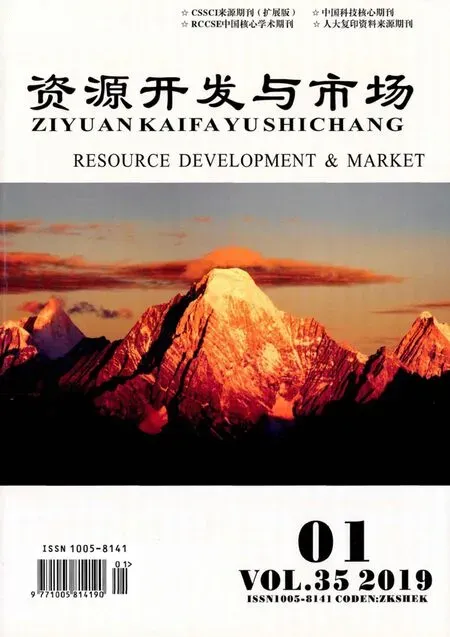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區域生態補償機制研究
——基于生態資產的視角
孔 偉,任 亮,治丹丹,王淑佳,3
(1.河北工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天津 300401;2.河北北方學院 生態建設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河北 張家口 075000;3.中山大學 旅游學院, 廣東 廣州 510275)
1 引言
生態補償是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為目的,以經濟手段為主調節利益相關者關系的制度安排[1],是保護生態環境、優化資源配置、協調區域發展的有效手段。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生態補償問題給予了廣泛關注,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2,3]。2005年,我國首倡“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4]的生態補償機制,此后的各個年度生態補償機制建設都被列為我國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我國提出要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來保護生態環境,并制定和完善生態補償的相關法律法規[5]。由此可見,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是對國家政策的具體落實,是加快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總體上來看,我國關于生態補償問題的研究,主要以生態環境保護[6,7]為基點,涉及森林[8,9]、草原[10]、濕地[11,12]、空氣[13]、流域和水資源[14,15]、礦產資源開發[16]、海洋[17]、重點生態功能區[18]等多個領域生態補償機制建設的探索,而少有從生態資產的角度進行生態補償機制的研究。所謂生態資產,通常指具有物質及環境生產能力并能為人類提供服務和福利的生物或生物衍化實體,生態資產的價值主要表現為自然資源價值、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生態經濟產品價值[19]。因此,為了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區域發展的公平性,本文運用生態資產理論,在分析生態補償利益相關者的基礎上,構建了適合京津冀發展實際的生態補償價值核算模型并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出完善京津冀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議以供決策參考。
2 京津冀生態補償現狀分析
京津冀地區是我國北方經濟規模最大、發展活力最強的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類生產生活對生態空間的占用不斷增加,京津冀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日益嚴重。基于打造全新首都經濟圈,推進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態,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范和樣板;尋求生態文明建設有效路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京津冀優勢互補,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的宏偉愿景[20],我國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重大國家戰略。
京津冀為應對生態環境危機并積極響應京津冀協同發展號召,著力開展了一系列包括生態補償在內的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工作。追溯至1998年,北京、天津兩市啟動實施了京津風沙源治理重大生態建設工程;2007年,北京市劃撥專項資金,全力支持密云水庫上游的河北省張家口市、承德市進行“稻改旱”工程,并在周邊有關市(縣)落實了6.67萬hm2水源林建設工程;2012年,北京市實施了對生態公益林每年補助600元/hm2的政策,并針對護林員建立起相應的補助制度;2010年,天津市安排專項資金,用于在河北省境內實施引灤水源保護工程;2013年,天津市又籌集專項資金,對古海岸與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由集體或個人長期委托管理的土地實施一定的經濟補償;2013年,天津市開展海洋生態補償試點工程;2014年,河北省財政廳、環保廳聯合印發了《河北省生態補償金管理辦法》,以規范生態補償金收繳與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盡管三地都采取了一系列生態補償政策和措施,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狀況有所改觀,但仍暴露出諸多問題,如補償取決于決策者意愿和當年的財政預算,沒有統一法律和政策規制;補償以政府決策為主,忽略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強調區域內管制,忽略區域間協調、可持續發展。
3 生態資產視角下生態補償利益相關者分析
3.1 補償客體
主要包括:①生態保護的貢獻者。主要包括處于資產狀態的自然資源客體和進行生態投資的居民或企業(如植樹造林、招商引資等)。②生態破壞的受損者。在發展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只有對當地受損者進行補償(屬于生態環境價值的損失補償),才能激發受損者恢復生態的主觀能動性。③生態治理的受害者。在生態治理過程中,受害者(居民或企業)為了保護和恢復生態而搬遷、停產等,應對居民的健康和直接財產損失、企業喪失的發展機會成本進行補償。
3.2 補償主體
主要是:①政府。生態環境和生態經濟產品具有公共性,通常由政府進行統一調控和治理,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政府的調控失誤,且政府代表著人民群眾和社會利益,有責任和義務對資源損失和產品輸出區的生態環境進行補償。②資源輸入區的受益者。資源輸入區是資源和生態經濟產品轉移的直接與主要受益主體,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資源輸入區的受益者應當履行一定的生態補償義務。③社會補償機構。在受益者對資源輸出區進行補償的過程中,有時會受到空間、時間的限制,這就需要相關補償機構(如環保組織、社會團體、民間組織等)對資源輸出區的生態補償提供資助或援助。
3.3 生態補償主體與客體間的利益博弈
生態補償機制目的是均衡因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引發的社會利益,調節相應的社會矛盾。但在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客體、生態保護地區與受益地區之間存在著廣泛、普遍、多樣和難以協調的博弈關系。補償客體及地區認為由于自身在生態保護、資源開發方面做出了貢獻并受到了損害,應由生態受益地區來承擔全部或部分責任,應由生態補償主體方給予其所期待的全部利益。但生態受益地區則認為收益來源于公共資源或開發經營,即使同意給予補償,也難以在補償標準上和補償客體達成共識,于是生態補償和區域內生態保護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政府作為生態補償主體中的強勢方,利益訴求為最大限度推動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源輸入區的受益企業則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補償客體及地區處于經濟、信息和政治上的弱勢地位,一旦補償機制流產,短期內補償客體得不到相應補償,長期則會影響補償客體的生態保護行為,進而影響到整體的生態保護效果和補償主體的收益,最終陷入俱損困境。博弈的焦點集中于補償范圍和標準的確定,故明確有效合理的生態補償標準和價值核算體系意義重大。
4 基于生態資產的生態補償價值核算
4.1 核算模型
生態補償價值核算始終作為生態補償研究的核心問題被學術界所關注和研究,對于此類問題國內外采用的方法主要涵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法、機會成本法、意愿調查法、市場法、經濟計量方法等[21],但按照以上方法制定的生態補償標準和措施并沒有完全解決生態效益問題,更未解決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問題。建議以生態資產為依據,構建生態補償價值核算體系,并按照資源本身的價值進行合理的價值核算,使補償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出生態環境保護的價值。
以生態資產轉移為出發點,以資源或產品輸入區為補償主體,按照輸入量比例,令輸入區對輸出區進行補償,并根據生態資產類型和輸出區產業類型,遵循“按需補償、統籌協調、補償明確”的原則,確定具體補償方式。
考慮到資源或產品輸出的特殊性和核算的準確性,本文運用生態足跡和成本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來進行生態補償價值的核算。
生態補償核算模型為[19]:
(1)
(2)
(3)
式中,V為資源輸出區生態補償總價值;Oi為第i種資源或產品足跡輸出率;Wij為第i種資源或產品第種成本(一般包括生產成本、生態修復和環境治理成本、機會成本等)權重系數;Cij為第i種資源或產品第j種成本;Ef出為總輸出生態足跡(hm2);Ef產為總生產生態足跡(hm2);ci為第i種資源或產品的消費量;pi為第i種資源或產品的平均生產能力。
運用此模型,根據京津冀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各自的生態補償標準。
4.2 實證分析
學者們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側重點,提出了多種生態系統分類方案。本文為了便于進行生態資產的評估,將京津冀區域生態系統劃分為耕地生態系統、林地生態系統、草地生態系統和濕地生態系統進行實證分析。
從2011—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獲取耕地、林地、草地和濕地面積、污染治理投資等原始數據,并結合相關研究成果[22-25],運用構建的生態補償價值核算模型,核算了京津冀區域2010—2016年的生態補償價值(表1)。

表1 2010—2016年京津冀區域生態補償價值(億元)
從表1可知,由于2010—2016年京津冀各省市每年的生態資產變動不大,其每年的生態補償價值變化也不大。其中,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的生態補償價值差距較大,分別為211.40億元、41.44億元、1452.99億元,河北的生態補償價值分別是北京的6.87倍、天津的35.06倍,在京津冀區域生態資產中河北>北京>天津,可見河北是京津冀區域最為重要的生態產品供給地,這也與《京津冀協同規劃綱要》中對河北省“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的功能定位相一致。
從圖1可知,2010—2016年京津冀區域整體生態補償價值波動較大。其中,生態補償價值由2012年的1672.39億元提高到2014年的1779.37億元,增加了106.98億元,主要原因可能是:京津冀區域空氣污染的加劇,造成了京津冀區域生態資產損失、生態修復及環境治理成本增加、生產成本和機會成本增加等問題,使區域整體生態補償價值提升。隨后,生態補償價值下降到2016年的1705.83億元,減少了73.54億元,原因可能是:國家極為重視京津冀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并發布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規劃》,通過優化產業和能源結構、提高技術水平、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推進節能減排、做強循環經濟、加強環境保護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保護了京津冀區域生態資產,降低了生態修復及環境治理成本、生產成本和機會成本等,使區域整體生態補償價值減少。

圖1 2010—2016年京津冀區域整體生態補償價值變化趨勢
5 完善京津冀生態補償機制的對策建議
5.1 成立專門協調組織機構
由于目前京津冀地區關于生態補償的認識不統一,因此要建立良好的生態補償機制并不容易,必須打破京津冀現有行政格局的局限,轉變行政理念,做好頂層設計,形成長效機制。建議成立專門的協調組織機構,協調、組織和領導京津冀生態補償工作。該機構由三地政府出面組織成立,對環保、土地、農業、水利、規劃、財政等部門進行組織協調,杜絕它們相互推諉。為了保障機構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應適時引入激勵政策,鼓勵和推動京津冀三地政府間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此外,對農田、濕地、水源地、生態公益林等生態環境特殊區域,應改變過去將經濟指標作為地區成功標準的考核模式,轉而關注其對改善生態環境作出的貢獻。建議采取綠色GDP考核政策,在對政府GDP進行考核時,考慮加入生態補償金支出數額、補償效果量化考核、出境斷面水質達標率等多項指標。
5.2 拓寬生態補償融資渠道
生態補償資金籌集是生態補償的核心問題。目前京津冀生態補償資金主要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但就當前我國國情而言,中央財政支付能力有限,不能完全達到生態補償的要求和標準。因此,需要拓寬生態補償的融資渠道,如設立生態補償的環保基金,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力量,支持和鼓勵社會資金參與生態建設、環境污染整治的投資,形成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的資金投入機制;構建生態補償市場交易平臺,最大限度地調動生態補償市場主體的積極性;著手建立碳排放權、水權交易、排污權等領域試點,引入政府綠色采購、生態彩票、生態補償債券、生態建設配額交易、生態標志制度等市場籌資手段;吸取國外生態補償的成功經驗,可考慮增收資源稅和環境稅等,依據開發者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程度或破壞與污染環境的程度來收取相應額度的稅費,然后將這部分稅收所得用于區域性的生態環境保護和受損者的補償領域,通過這種手段把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掛鉤,以提高資源的開發利用效率。
5.3 完善生態補償法律法規
完善生態補償法律法規,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根本保證。我國《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中有對生態補償原則性的專門規定,但目前尚無保障生態補償機制全面建設與實施的相關法律法規,無法在各個環節上實現有法可依。因此,建議國家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使生態補償管理制度得到進一步規范,通過法律形式徹底明確生態補償的基本原則、任務要求、補償客體和主體、補償內容、權利和義務、測算方法、補償標準(因各地經濟環境狀況不同,不能規定統一補償標準,可因地制宜分別制定)、補償范圍、補償程序、補償方式、保障措施等,一旦有違反生態補償法律法規的行為發生,責任人必將被依法懲處。在必要的情況下,還應建立生態補償的救濟制度,切實保障生態補償相關利益主體的權利能夠真正地實現,并積極引導公眾依法參與生態環境保護,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運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合法環境權益的積極性。
5.4 建立多維生態補償途徑
結合京津冀地區的實際,除經濟補償之外,生態受益區通過政策補償、技術補償、教育補償等方式對資源輸出區進行扶持與援助,通過建立多維生態補償途徑,形成直接補償與間接補償相補充、連續補償與一次性補償相結合的可持續補償體系。在政策補償層面,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與杠桿力量,從稅收、貸款、資金補貼、政策等方面給予補償客體和地區優惠措施。在技術補償層面,通過技術援助、高新技術引入、生態技術試點、生態產業示范區建設等措施,以科技與知識的注入助力補償客體和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新型生態產業發展和生態經濟繁榮。在教育補償層面,以政府轉移支付提升補償地區基礎教育的質量,免費進行農民和社區失業居民再就業素質教育培訓;加大生態高新技術人才引入,促進高校生態相關學科的人才培育與科技研發,形成源源不竭的生態發展儲備力量。構建積極的多維生態補償途徑,能夠提升被補償地區的自主發展能力,實現其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大區域發展的“雙贏”。
5.5 開展區域間合作與協作
在多數情況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都離不開地域間的合作與協作。就自然流域角度而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同屬海河流域,它們之間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自然生態系統。因此,在制定和完善京津冀生態補償機制時不能關起門來“單干”,三地應共同協商、開展合作,在對京津冀整體環境科學調研后,充分考慮三地的經濟發展、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標,最終共同規劃和制定出更加合理完善的補償方案。
北京市水資源嚴重缺乏,而河北省張承地區是京津冀重要的水源涵養地,共同實施水源保護林等合作項目,打造京津冀重要生態屏障,對改善區域環境意義重大。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加快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推動區域間產業對接合作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如傳統農業向生態農業轉變,污染工業向清潔生產工業轉變、重點發展旅游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因此必須共同搭建京津冀產業合作對接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