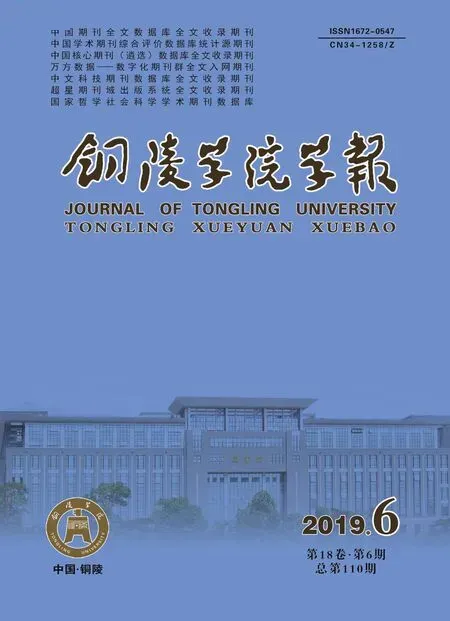論中國現代小說中安徽城市書寫的困境
瞿華兵
(銅陵學院,安徽 銅陵 244000)
現代以來,安徽城市獲得快速發展,涌現出眾多知名的城市。文學作為歷史生活和人類精神的忠實反映,對此進行積極書寫,中國現代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安徽城市意象,構成現代文學史上一道獨特的文學景觀。然而,面對這一新的異質性的文學資源,作家的城市書寫面臨著巨大的困境。
一、價值取向的矛盾
從根本上說,中國是一個鄉土型的社會,費孝通在著作《鄉土中國》中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這一點,直至現代以來都未曾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生活在“鄉土中國”里,每一個人都與鄉土有著密切聯系。“鄉土中國”特有的倫理道德、文化習俗、審美習慣形成一種強大、持久的“鄉土文化”,影響和制約著作家的題材選擇、文化趣味、價值判斷以及思維方式,并形成作家對城鄉的態度:“貴鄉村、抑城市”。浸染在鄉土文化里的作家對鄉村天然懷有一種親近和認同感,對城市則更多持一種拒斥和否定的態度。可是,現代以來,作家普遍接受了現代化的教育,經受了現代文明的洗禮,認識到鄉土文化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城市文明有其先進、合理的一面,價值取向上開始搖擺,呈現出矛盾、復雜的特征。他們對城市不再持簡單的批評和否定的態度,既有對城市文明的強烈批判,也有對城市文明的一定認同,兩種矛盾的情感匯流于現代作家的城市書寫之中,折射出作家復雜的創作心態。
這種矛盾的價值取向鮮明地體現在作家的安徽城市書寫中。例如郁達夫,小說《迷羊》描繪了A城(安慶)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和獨特民俗,呈現出寧靜、安詳的城市面貌,寄托了“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悠然、閑適的情懷。《茫茫夜》則凸顯A城的混亂與墮落,揭露出舊中國政治的腐敗與黑暗,安慶在主人公于質夫的眼中就是一座“Dead city”(死城)。蔣光慈《少年漂泊者》中的商人陰險狠毒,毫無愛國情感,不良伙計恃強凌弱,欺辱弱小者,W城(蕪湖)是一座階級對立、冷漠罪惡的城市。《沖出云圍的月亮》書寫富麗繁華、流光溢彩的現代都市圖景,批判現代都市生活的荒淫與腐朽,但不自覺又流露出對都市生活的迷戀,小說文本呈現出復雜性、多義性。有論者指出:“在這樣一種都市書寫背后,反映了蔣光慈本人對于都市的曖昧態度,一種既無法認同都市卻又離不開都市的矛盾心理。”[1]價值取向的搖擺固然可以滿足不同時尚讀者的需求,但也暴露出作家在變動不居的城市面前還無法建立起穩固的價值立場。
在這種情形下,價值取向的矛盾必然使作家對城市無法形成持久的關注與熱切的關愛,從而難以形成穩定的創作思想和獨立的創作立場,影響到他們對城市的深入發現與探究,最終限制了作品的藝術高度與思想力量。現代小說中的安徽城市書寫是“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普遍缺乏切實生動的城市生活圖景。無論是1930年代“政治化”敘事的“革命文學”,還是新時期一味向西方學習而脫離本土文化的“先鋒小說”,亦或1990年代以來蜂擁而起迎合消費潮流的“城市文學”,都突出體現了這種創作特征。這樣的書寫不可能真正揭示出城市的深層面貌,反映出城市的獨特本質。現代小說中的安徽城市書寫是表面化的,概括來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過度關注城市外在的物質景觀。相比較對鄉村的熟悉,作家對城市有著較深的隔膜,主要依靠視覺上的經驗來表現城市,高樓大廈、車水馬龍、街燈閃爍是他們眼中的城市形象。郁達夫的《迷羊》詳細地描寫了大觀亭、迎江寺、振風塔等眾多安慶城市景觀,留下了1920年代的安慶城市風情畫,但卻未能達到以城市的景觀來烘托人物的心情,揭示人物內心世界的藝術效果。王安憶的《蚌埠》如實記錄了蚌埠的百貨商店、電影院、火車站,以及干凈的“人民浴池”和整齊的街道等物質景觀,展示出蚌埠的城市風貌,因為缺乏貫穿始終的內在線索,造成散漫、堆砌的藝術弊端。許春樵的《放下武器》不遺余力地描述合安城巨型廣告牌、高檔小汽車、舒適的賓館、豪華的寫字樓等各種現代都市景觀,在展現出城市的部分面目時,城市更多的面目和真實卻遭到覆蓋與遮蔽。城市景觀并非只是作為單純的物象而存在,對人的生活和精神都有著重大影響。斯賓德在《詩學和現代城市》里指出:“環繞我們物體的形狀(房屋、汽車、服飾等)對人們都有著潛意識的影響,一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某一藝術運動的存在。然而,如果他漫步的街道產生了某種變化,他的生活也可能會直接改變”。[2]對比現代小說中的安徽城市書寫,作家的創作顯然還缺乏這種深度。
其二,極力表現城市欲望、動蕩的生活。城市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變得日益喧嘩與躁動,呈現出流動性、復雜化的特征。郁達夫的《茫茫夜》以1921年安慶法政專門學校的學潮風波為背景,描寫了軍閥和議員買通學生在學校公開鬧事;校長被攆出校門,基本教學秩序無法維持;教員們蟄居在城外的小客棧里,狎妓調娼、尋歡作樂,城市呈現出混亂與動蕩的圖景。潘軍的《對門·對面》通過發生在城市中幾對男女之間的故事,反映出現代城市的荒誕與復雜。A是一個剛離異的出租車司機,隔壁的D是一個女慣偷,B和C是住在他們對面的一對夫妻。D經常到A家里來借打電話,C在外面有情人,A則承擔了送C與情人約會的任務。原本素不相識的幾對男女之間就這樣發生了充滿戲劇性的故事。許春樵的《酒樓》從家族爭斗的角度濃墨重彩表現城市的欲望與躁動。生活在城市里的現代人為了金錢和利益,相互算計,不講道德信義;兄弟爭斗,夫妻反目,毫不顧及親情;男人嫖娼、女人出賣肉體,每個人都陷入欲望的泥潭而無法自拔。城市并非由欲望、動蕩的生活構成,日常、世俗的生活更能代表城市的本質,城市的精神更多蘊含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將本真的、鮮活的日常生活呈現出來,才能表現出城市獨特的精神面貌。
現代小說的安徽城市書寫專注于城市外在物質形象和欲望躁動生活,從外部而非內部去感受和表達城市。在作家的眼中,城市喧嘩躁動、充滿欲望,又冷漠無情,僅僅作為物質的形象存在。他們對城市的書寫停留在表層生活的復制上,沒有寫出城市對人生命造成的影響。恰如研究者在論述郁達夫的城市書寫時所說:郁達夫小說中的城市“大都是作為故事載體的抽象城市——通過對市民日常生活的疏離,抽空了中國城市的鄉土價值觀——與實際的中國城市相距甚遠。”因而“排除了郁達夫對于本地日常生活和城市精神的客觀、深入觀察的可能性。”[3]
二、地域色彩的消失
談到地域色彩,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鄉土文學,因為地域色彩是鄉土文學不可缺失的內核性特征。事實上,這是對地域色彩的褊狹認識。在新文學初期,針對當時流行的“世界民”的觀念,周作人指出:“我于別的事情都不喜歡講地方主義,唯獨在藝術上常感到這種區別。……風土的力在文藝上是極重大的”。[4]茅盾也推崇文學的地域色彩,他說:“……民族的特性是不可忽視的,比民族的特性范圍小而同樣明顯且重要的,是地方的特性。湖南人有湖南人的地方特性,上海人也有上海人的”。[5]可見,地域色彩不只是針對鄉土文學而言的,同樣也是城市文學重要的藝術質素。正因為如此,文學史家范伯群提出了“都市鄉土小說”的概念[6],強調城市書中寫應該展現民風民俗,突出地域色彩。現代文學史上,老舍因逼真刻畫北京城的民俗風情,把握住了北京的精神,顯示出藝術上的獨特價值。張愛玲在上世紀90年代為什么會被重新“發現”?主要源于張愛玲對上海世俗風情的精細描摹和獨特感受。地域色彩的描寫不但能給讀者帶來審美的享受,而且可以起到渲染氣氛、揭示人物性格的藝術功能,提升小說的藝術層次。
可是,現代小說中城市書寫地域色彩的消失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地域色彩主要來源于特殊城市風貌的描寫和特色民俗風情的展示,而迅猛發展的城市化進程正在抹殺城市的地域色彩。首先,城市外在形象的同一化。城市主要由高樓、街道、公園、廣場等人為景物構成,這些景物大多如出一轍,城市在外在形象上極其相似,且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而愈加明顯。許春樵的《放下武器》和《酒樓》分別展現了合安城與柳陽城的城市容貌,但從外形上看卻并無差異,如果不結合小說的創作背景以及小說中只言片語的暗示,根本無法判定兩座城市各自的身份。潘軍的《合同婚姻》、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放棄了對城市外在形象的刻畫,城市成為空洞的能指,僅作為故事發生的地理空間出現。其次,城市地域風情的消失。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確立起自己的價值規范、文明系統,顛覆了具有濃郁傳統色彩的民風民俗,導致城市地域風情的消失。許春樵的 《屋頂上空的愛情》《酒樓》書寫現代都市的欲望生活,揭示金錢對人性的異化,沒有涉及到任何的民俗風情。潘軍的《桃花流水》《對門·對面》揭示現代都市空間中荒誕哲學命題,幾乎不牽扯具體的日常生活,地域風情更是無從談起。地域色彩的消失導致城市書寫的抽象化和同一性,極大損害了小說的審美品格。
因為如此,一些作家干脆放棄了對城市地域色彩的挖掘,選擇用故事性來進行彌補。小說追求故事理所當然,因為“小說的基本面是故事”。[7]故事是小說的基本要素,也是小說的靈魂。特別是在市場經濟語境下,消費性成為文學的重要屬性,文學要想在市場中立足,獲得生存,必須講述精彩、好看的故事吸引讀者。但把故事性視為創作的最高審美追求和藝術法則時,作家卻陷入了某種追求故事性的誤區。小說的情節越來越曲折生動,故事越來越精彩好看,意蘊卻越來越薄弱,這種狀況在近些年的安徽城市書寫中非常明顯。造成小說意蘊的薄弱有多重原因,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把故事性作為小說的第一要義,忽略了對生活的深遠人文內涵進行思考。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開》情節架構曲折多變、跌宕起伏,故事氛圍風云突變、危機四伏,人物形象復雜多樣、活靈活現,充滿了趣味性與娛樂性。許春樵的《放下武器》《酒樓》描寫現代都市中的官場權謀、商業斗爭,展現官員、商人荒淫奢靡的生活,構造出一幅喧嘩躁動的都市圖景,滿足了讀者大眾對現代城市的欲望想象與獵奇心理。這些小說的故事都異常精彩,畫面感強烈,卻缺乏深厚的文化內涵,作品的意蘊顯得比較直白和淺陋,有著“影視劇”小說的嫌疑。
然而,故事性不但沒能解決安徽城市書寫的困境,反而產生新的問題,敘事邏輯的缺失是最突出表征。為了制造故事情節的精彩曲折,作家往往犧牲敘事的邏輯,使小說缺乏說服力,影響到接受層面的可信度。“小說中的人物性格、行為動機、情節的起承轉合都涉及邏輯,好的小說一定有好的情感邏輯,哪怕運用夸張變形,由于其堅實的邏輯力量而使小說具有了藝術真實;相反,缺乏必然如此和必要的邏輯力量,則會損害文學的說服力。”[8]例如許春樵《放下武器》中失足女孩王月玲為“我”舅舅鄭天良“服務”時,顯得異常冷靜與嫻熟,沒有絲毫不安與緊張。被包養后,卻開始復習功課,最終考上了大學。什么力量促使王月玲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小說缺乏交待。唯一能夠解釋的或許就是王月玲身上寄托了作者 “人性善”的光輝,承擔著救贖淪陷城市的希望。《酒樓》中為了故事沖突的激烈,不惜制造了許多巧合:張慧婷開幼兒商品專賣店,受到流氓的欺辱,剛好被追求者孫玉甫搭救;齊立言外出送快餐,恰巧送到被大款包養的前妻張慧婷的公寓。類似的情節還有很多。敘事邏輯的缺失使小說缺乏可信度,自然令人難以信服,這是追求小說故事性付出的沉重代價。
三、城市書寫的出路
中國現代小說中安徽城市書寫遭遇的問題與困境,有著復雜的歷史、文化原因。面對這種困境,作家進行著積極的探索,尋求解決的辦法。
對于價值取向的矛盾給城市書寫帶來的局限,作家有較深刻的認識,他們嘗試著走出困境。例如潘軍、許輝的創作超越傳統“城鄉對立”的思維模式,致力于表現城市人的生命情態與瑣碎生活。應該說,在理性層面作家已經認識到城市文明的先進性,但在感性上,他們還是難以完全接納城市。就許輝而言,《夏天的公事》等小說努力想要保持創作態度的平和,展現近乎日常的城市生活,但因為始終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的趣味中去,取得的突破是有限的。“一個顯然的事實是,躁動的都市無法給予作者也包括讀者以田園的享受,所以他呈現的意象就顯得雜亂甚至有點兒破碎。”[9]真正對這種創作困境形成突破的是王安憶。或許因為出生于城市,只有過短暫的插隊農村經歷,受鄉土文化的影響較淺,王安憶很快由早期的《雨,沙沙沙》《流逝》對城市的排斥轉向對城市的認同。《臨淮關》中出生鄉村的小杜聰明、俊俏,被借調到縣城做廣播員,后來嫁給縣革委會副主任的兒子,讓周圍的人羨慕。日常生活中,卻一次次受到上海插隊知青的“戲弄”。帶孩子到上海看病,無時無刻不感覺城市對她的“蔑視”,感覺受到傷害。小說從平常生活的角度切入城市,展現城鄉兩種文明的劇烈沖突,寫出了城市文明對鄉村人的擠壓與影響,為現代小說的城市書寫樹立了典范。
對于地域色彩消失造成城市書寫的困境,作家也已經意識到,他們積極調整傳統的藝術觀念,尋求新的書寫路徑。潘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西方現代派文化思潮的影響下,潘軍擺脫了傳統藝術觀念的束縛,對地域文化形成自己獨特的認識:地域文化不是“當地的方言、習俗、習慣等的拼盤”,而是“一種文化意識”。因此,“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人際關系,小說中營造的那種氛圍,都是特定的地域文化意識的反映。”[10]在具體的實踐中就是拋棄那種具象的地域文化書寫,地域文化不是作為一個標簽,而是滲透在小說的字里行間。長篇小說《風》《獨白與手勢》中作者大量運用了懷寧(安慶)方言俗語,營造出一定的地域文化氣息。此外,小說中的人物性格、文化氛圍、風俗景觀也體現出較強的地域色彩。因而,盡管小說用水市表述安慶,用石鎮替代懷寧,透過地理關系、文化氣息還是能夠辨識出城市的身份。客觀上說,潘軍的這種探索是可貴的,不過就產生的影響、取得的成績來看,依然相當有限。期待作家在這方面有更大的成就。
其實,“物質”并不能完全代表城市,城市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屬性和精神向度。面對這一新的異質性的文學資源,作家應該確立起穩固的價值立場,找尋到認識城市內在本質的文化通道。城市的精神更多潛隱在普通市民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日常生活和細微末節處,作家不應該被城市繁華熱鬧的外在景象所迷惑,理當深入到城市生活的背后,揭示出生活的真相和潛流,呈現出獨特的城市精神,抵達城市生活的最深處。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時代,文學成為商品,不可避免要受到市場法則的制約與影響,小說的故事性便應運而生。城市書寫因為地域色彩的消失而去追求故事性,但故事性又造成城市書寫意蘊的薄弱、邏輯的缺失,這是現代小說中安徽城市書寫的悖論型困境。作家要有超越時代語境的膽識和信念,在市場和心靈、歷史和當下之間尋求契合點,才能創作出既精彩好看而又意蘊深厚的作品。因此,擺脫這種困境,需要作家沉下心來,加強自己的藝術修養,提高自我的思維能力,現代小說的安徽城市書寫才能進入更高的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