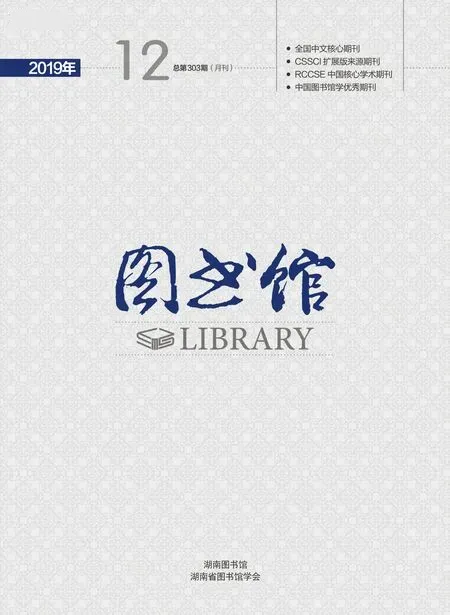王船山佚文《〈漆園放言〉序》考
龔雨璐
(湖南圖書館 長沙 410000)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一生著述豐富,經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整理標校并由岳麓書社于2011年出版的《船山全書》(全16冊)是目前王船山全書內容最完備、校勘最精良的版本。但筆者近期仍發現有散篇佚出全集之外,當加輯補。
1 王船山佚文《〈漆園放言〉序》原文及注釋
今在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同治)崇陽縣志12卷·卷11藝文志》中發現王船山撰《〈漆園放言〉序》一篇,該文不見于《船山全書》,是其佚文,茲將該文移錄、標點、注釋如下:
詩至啟禎間,歧路百岀,竟陵之門三盈三虛,云間起而爭之,竟陵不能盈矣。竟陵諱言依傍,實大有所依傍,云間妙于依傍,遂不諱言依傍,兩家皆有主盟之心,宜其所推進者,皆其曹滕。乃有不然者,方密之①弱冠即與陳青浦②定交,而其詩不入云間之壘,抑不屑似尸祝竟陵者之夢魂以之也。密之之學,以雙行為大用,于詩乃孤行托錢劉③,以離二家門戶,愚嘗竊笑密之其孤行者,正其雙行者也。不墮乃以不昧,后百丈即先百丈,癡人謂為兩百丈耳。密之善于藏身春浮④一夢,脫離再來傀儡,其感召矣。夫金道隱⑤與密之同床各夢,遂不相。至于詩,道隱猶密之也。密之胸有錢劉,道隱胸無錢劉,而不覺錢劉在焉。道隱其達矣,蓋竟陵、云間之外,又有倪文正⑥、王謔庵⑦一支橫岀,則錢劉之濯濯解紛之圣術也。勿論其胸有錢劉與否,而自然、清雄、回宕之氣不可遏抑,亦此日之勝事哉。圣功與道隱為生死道義交,胸亦無道隱,其詩乃逼。道隱與密之亦各夢,又逼密之,意薄錢劉不為,且逼錢劉自然也、清雄也、回宕也。其人、其世、其心、其才輳合而然一也。嘗讀元末國初詩,若楊孟載⑧、高季迪⑨、袁景文⑩諸公不相擬,而墨外皆同調。然則天地其有悔心乎?詩先之矣[1]。
2 王船山與蒙正發交游考
《漆園放言》為蒙正發所著,蒙正發(1617—1679),字圣功,別號樵云,湖北崇陽人。隆武時以諸生起義,永歷時官給事中,后歸楚寓居衡陽南鄉之斗嶺。王船山為何要為其書寫作序言,二人關系如何?本節將考述王船山與蒙正發之交游情況。
王船山《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中寫道:“夫之與君為患難交,自詔獄始迄于終。”從此句可知二人的友誼始于清順治七年(1650)詔獄事件。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中記錄了事情始末:“時粵僅一隅,而國命所系,則瞿公與少傅嚴公(諱起恒)實砥柱焉。行闕駐肇慶,紀綱大壞,驕帥外訌,宦幸內恣,視江、閩之覆轍而更甚。賴給諫公金(堡)同丁公(時魁)、劉公(湘客)、袁公(彭年)、蒙公(正發)等主持振刷,而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傅、內豎夏國祥等交害之,指為五虎,交煽中宮,逮獄廷杖,將置之死。亡考邀同榜中舍管公(諱嗣裘)走訴嚴公:‘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王于刀劍之下,而黨人假不測威而殺之,則君臣義絕而三綱斁,雖欲效南宋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勸公匍匐為諸君請命。緹騎掠諸君舟,仆妾驚泣,府君正色訶止之。繼諸君以嚴公哀請得不死……”[2]第16冊72-73王船山曾為解救蒙冤入獄的蒙正發四處奔走,還保護了他的家人。
二人相知相交始于清順治七年(1650),但在這之前他們也應已聽說過對方事跡。王夫之撰《永歷實錄·卷11金王李陳列傳》中記載:“成棟之迎駕也,遍致書于朝士,皆有贈遺。王化澄、朱天麟以下,皆欣躍為勸上駕。瞿式耜疏請西出,赍發,給事中蒙正發陛見抗爭。成棟復遣杜永和來扈蹕,正發與廷爭之,語侵永和。永和出,怒目睨正發曰:‘此曹倚未薙發相傲誚,吾將執而耏其鬢。’”[2]第11冊448詳細記錄了蒙正發與杜永和抗爭的經過。蒙正發在《三湘從事錄》中寫道:“總督駐東安數月,湖南節義之士莫不聞聲景從。衡州舉人王介之、夫之、鄒統魯、夏汝弼、李跨鰲、管嗣裘、吳汝潤、周士儀雖匿影南山僻谷,或密報情形,請商方略;或悲歌唱和,緘寄詩篇;風雨郵筒,閑道不絶。”[3]251對王介之、王夫之兩兄弟多有贊賞。而這兩件事均發生在清順治四年(1647)。
雖然王船山與蒙正發相識甚早,可在早年因為戰亂等原因二人交游較少,王船山《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中記載:“桂陷,降者相踵。君排邪論,竄靈溪峒,與司馬劉遠生、樞郎朱昌時、中舍管嗣裘投身猺獞間,采芑以食。已而循山徑依故人于斗嶺,授童子讀以得粟,樵汲行吟,分與草木同朽。而所依者有仇家,挾君不降為名,將搆大難,乃復走邕管避之。邕帥全節聞君誼,矜重而優全之。數年乃歸,杜門絕交游,讀書以自適。”[2]第16冊935-936蒙正發在桂林淪陷后四處漂泊,后來終于定居衡陽斗嶺。
二人交游唱和變得頻繁之契機據王敔撰《大行府君行述》記載為:“吳三桂之抗命也,一時偽將招延,亡考堅避不出,或泛舟淥、湘間,訪故人以避之……時與前諫蒙公(正發)酬答頗多。”[2]第16冊75清康熙十三年(1674)春,吳三桂逆兵陷常德、澧州、長沙,復陷岳州。湖南各郡并為其所據。王船山為避滇氛,各處漂泊。此年有《送蒙圣功暫還故山》一首。
清康熙十四年(1675)八月,王船山與蒙正發同去江西萍鄉。泛舟淥江時寫有《淥湘雜興》六首。到達萍鄉后寫有《萍鄉中秋同圣功對月》。離別回湘時寫有《留別圣功》。康和聲在《留別圣功》詩下按:“去歲回崇陽時,先生有送暫還故山詩,此次復遠送聚于萍鄉,必及滇事,故有‘興亡多事天難定,去住皆愁夢未真’之句。先生與圣功均義憤久抑,情不能忘,故有‘一枕冰魂隨故劍,飛光猶涌子胥潮’及‘寶劍孤鳴驚背珥,畫圖遙惜老麒麟’之句。然以三桂之不忠明室,反覆無常,安能有成,徒苦生靈耳。故于其留別時,回望故鄉烽火,有‘鐃吹落日喧丹嶂,西望湘煙淚眼新’之句……”[4]207認為二人此次出行與吳三桂起兵關系密切。同年九月,王船山由江西萍鄉回湖南。阻風泊湘潭,訪故將張永明。船山詩《風泊中湘訪張永明老將吊孫呂二姬烈死,讀辛卯以來諸公獎貞之篇,放歌以言情。孫呂事詳故中舍管公記(乙卯)》中寫道:“茫茫峒云結煙草,貞魂不舍蒼梧道。哀歌血淚灑青天,管子嗣裘金郎堡。而我悲吟獨待今,二十六年愁埋心。左掖蒙生俱未死,軍中彈淚秋陰深。”[2]第15冊376張永明即張國祚,湘潭人。永歷傾覆,其妾孫氏、呂氏相對自經死。劉毓崧撰《王船山先生年譜》于詩下按:“管子嗣裘即題中所云中舍管公,蒙生即蒙正發。左掖系給事所居。蓋管中舍曾為二姬作記,又與堡同作詩。二人已前歿,而正發猶存。”[2]第16冊237王船山追憶往事,故人多已逝去,只有蒙正發陪伴在他身邊○11。
清康熙十五年(1676),王船山有《雨中過蒙圣功斗嶺》五首。康和聲于詩下按:“圣功本湖北人,此詩首云‘君從吳西歸’,蓋自萍鄉歸斗嶺也。先生上年別時即望其歸,故有‘云何成迢遞,令我思無窮’之句。第二首、第三首,乃問圣功在贛密圖軍事情形。庚申重挽圣功詩,有‘詔獄名猶在,燒屯事益疑’之句可證。第四首‘龍淵老自靈’及‘君莫羨漁汀’云云,乃勉圣功及時有為……第六首末云:‘與君昨夜語,山鬼泣窗前。’則此次相晤,或于恢復大計,另有密議也。”[4]213認為二人此次于斗嶺相聚,可能秘圖恢復。同年有《中秋同圣功、庶先、翠濤、須竹飲聽月樓,諸公將送予下湘(丙辰)》,王船山于聽月樓與諸公餞飲,蒙正發等人送其泛舟遠避。
清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清兵復衡州。吳三桂起兵失敗。蒙正發去世,王船山有《聞圣功訃遽賦》一首。首句即為:“閑愁生死外,回首故人無。”[2]第15冊353和他同仕永歷朝,陪伴身邊的最后一位故人也離開了他。
清康熙十九年(1680),王船山有《重挽圣功》一首。頷聯為“故心聊自致,唯子不吾欺”,認為蒙正發是真正為二人所謀竭盡心力者。尾聯“金風還似昨,湘水泛舟時”[2]第15冊493,追憶二人泛舟湘江時的情景,雖然秋風陣陣猶如往昔,可故人卻已不在了,無限悲愴蘊含其中。
清康熙二十年(1681),王船山作《廣哀詩》。《廣哀詩》第十八有《蒙諫議正發》一首。王船山之前雖為蒙正發作悼亡詩二首,但均系短章,未盡所哀。他在此詩中敘述獨詳,即詩中所謂“傾心與君吐,不畏多言窮”也。詩中又有“我狂君不忌,非但愛彫蟲。投我漆園吟,點竄恣愚蒙”,其中“漆園吟”應指蒙正發詩集《漆園放言》,蒙正發曾將其詩稿給王船山修訂。另有“每與知者言,濁世孰昭聾。惟余船山叟,煙草吟荒蛩”[2]第15冊468,可知蒙正發不僅為王船山之密友,更是他的知音。蒙正發認為在當時混亂的時代中就只有王船山即便處于荒蕪的深山中也能用語言文字喚醒麻木的人。康和聲在此詩下按:“前節歷敘生平,末言:‘蕭條斗嶺山,遺孤未成童’;‘誰能為荀息,只自悲翟公’。其后先生教圣功長子之鴻留籍衡山,學問深造,富有著述,可謂能為茍息,不負圣功矣。”[4]254又據羅正鈞《船山師友記》:“蒙之鴻,衡山歲貢。父正發,崇陽人,寓衡陽南鄉之斗嶺,沒后子孫歸崇陽,惟之鴻以長子留守墓。從王夫之學,所造頗深。著有《遣心集詩稿》。教授鄉塾,與夫之子敔,唱酬甚多。”[5]168從此可知蒙正發逝世后王船山悉心教導他的長子蒙之鴻,蒙之鴻與船山次子王敔交游甚密,王、蒙兩家的友誼持續到了下一代。王船山撰《莊子解·卷1》在“適莽蒼者,三飱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下按:“蒙之鴻曰:‘此言游各有近遠,則所以資其游者自別。培風與不必培風,形使之然,于二蟲又何知焉?’”[2]第13冊84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船山有《五日同劉、蒙兩生小飲》五律一首。其中蒙生當為蒙之鴻○12。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船山年已七十,寫有《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文中提到:“葬七年矣,嗣子肇旻與其弟以志銘請;當葬時,皆幼孤也。”他是應蒙正發兒子的請求來寫作此文的。王船山在此文中備述了蒙正發一生之經歷,并評價蒙正發“氣宇開朗,神志果毅,而胸無宿怨,言無機巧,故所至人皆矜服。文筆暢達,善盡事理,詩雄渾不事雕琢,得錢劉風旨。”[2]第15冊936認為他文如其人,文質兼美。
另王船山在《四書箋解·卷3上論·博施章》中對孔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進行注解的時候提到:“蒙正發曰:‘立達可以身心分貼。立謂身之有以自立,達謂心之有以自達。立其身,則無小無大,隨分皆可以自成;達于心,即見淺見深,于事皆得以自遂。’”[2]第6冊198可知二人不僅有詩歌唱和,也有對經典之研習探討。
綜上所述,蒙正發為王船山四十年患難交,二人志同道合,過從甚密,并且王船山對蒙正發的詩文評價很高,那么他為好友的詩集寫作序言也就順理成章了。
3 蒙正發著述流傳情況考
對王船山詩文的整理研究由來已久,這篇《〈漆園放言〉序》為何一直沒被注意到,會成為集外佚文呢?本節將考述蒙正發著作的流傳情況,挖掘《〈漆園放言〉序》成為佚文的原因。
王船山在《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中記載蒙正發:“所著有《漆園放言》《蘆草》《龍壁吟》《欸乃聲》《三湘從事錄》藏于家。”[2]第15冊936又前文羅正鈞在《船山師友記》中提到蒙正發的六個兒子除了長子留衡陽守墓外其他均回故鄉湖北崇陽,《(同治)崇陽縣志12卷·卷7》中也記載:“衡陽王夫之志墓后三十余年,其子始歸崇,今兩邑皆有后,所著見《藝文志》。”[1]由此可推斷蒙正發逝世后他的后人帶著他的詩文稿回到了崇陽。
又據《(同治)崇陽縣志12卷·卷首凡例》中求詳一條寫道:“志有未可或簡者,若疆域、食貨、禮樂、職官、選舉諸志及建置志之學校、義所、人物志之忠義隱逸是也。……至于明季殉難,國初守節諸君子,先年未詳著事實,尤為憾事,茲一一補傳,庶足慰九泉忠義之心。”[1]由此推測清同治初年崇陽在編纂縣志時可能曾尋訪當地蒙正發后人,搜集有關蒙正發的資料,因此在該縣志的藝文志之中才會清晰地著錄蒙正發的著述情況。
《(同治)崇陽縣志12卷·卷11藝文志》中所記載蒙正發著述與王船山同,并在《三湘從事錄》后附王夫之序、蒙正發自跋,《漆園放言》后附王夫之序、潘駕檝序,《欸乃聲》后附蒙正發自序,另在《龍壁吟》《蘆草》后載:“此《草》與《龍壁吟》俱曾付梓○13,毀于火,《龍壁吟》無存稿,此《草》尚有殘篇,更名《蘆草遺灰》,其子鴻手錄藏之,今俱佚。”[1]由此可知,在清同治初年,蒙正發著述尚有三種存于世,兩種散佚。
清光緒四年(1878),《三湘從事錄》收入《屑玉叢譚》,為上海申報館鉛印本。此書在《屑玉叢譚》中名為《三湘從事紀》,書前章有謨《〈三湘從事紀〉引》載:“紀者直書也。事可取則載,人可取則錄,言可取則書,一編年紀月之例也。……是書既成,即使宏文館徵信史執簡而書,按年而考,知無易。”[6]書前另附《〈三湘從事紀〉序》,序后題“南岳孤臣王夫之程人氏識”。序中王夫之稱此書為《三湘紀事》。書后有蒙正發自跋。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此書又收入《崇陽蒙先生遺集》,為金永森刻本。此書除了收錄王夫之序和蒙正發自跋外,書前還有黃嗣東序、金永森序、王夫之撰《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題詞、例言,書后附金永森撰《五虎辨》《辨李自成之死》。另有蒙正發長子蒙之鴻所述《家乘述略》及徐登元跋。
金永森在《崇陽蒙先生遺集·卷首序言》中寫道:“先生當明季從何騰蛟、章曠諸公,奉隆武于湖南以圖恢復。聞有《三湘從事錄》一書,顧未之見。逾年,訪其后裔,始得其書及詩一卷。其中歷敘在湖南用兵事,語在書中,不具述。但傳鈔訛漏甚多,不可讀,校讎數次,始復舊觀。復取明季載記與書中相涉者為之注釋,俾承學之士熟悉形勢及當時用兵得失利鈍,大有益于經世之學。”[7]他從蒙正發后人處得到《三湘從事錄》以及詩一卷,又金永森在《崇陽蒙先生遺集·卷首例言》中有:“此書沉湮垂二百馀載,將就散失,永森下鄉宣講,所至之處,必召其故老探訪古跡,搜求遺書,此乃圣功后裔甘云峰○14所藏者。……圣功有詩二種:曰《漆園放言》、曰《欸乃聲》,船山先生作序,雅推重之。圣功原不藉詩傳,而詩又非近時急務,故置而未刊,茲擇句之佳者五言如:‘山將落日去,風送晚涼來’‘木客林端嘯,孤鴻海上來’‘寒澗蒸輕霧,高岑駐晚晴’‘檐淺高收照,林空易送聲’,七言如:‘舊句復吟如夢里,湘山重見似親人’‘荒城笳吹山遮斷,野寺疏鐘月送來’‘秋成衲子忙如俗,雨后山光凈若澄’‘天地茫茫真大瓠,行藏泛泛一浮萍’‘撥枕灘聲喧斷夢,系舟老樹托芳鄰’‘粵水南來深染碧,春山雨過盡堆藍’‘茶煙入水如云泛,帆影騫風覺岸忙’皆妙。圣功生明季,其詩不為王、李,亦不為鐘、譚,自出機杼,不屑依傍門戶,此其所以為豪杰之士也。”[7]金永森在例言中提到了蒙正發著有詩二種,那他得到的一卷詩到底為哪種?或者二者兼有之?
又蒙之鴻在《家乘述略》中寫道:“先君自乙酉離崇,忘身殉國,其于楚南與何中湘諱騰蛟、章華亭諱曠二公同心共濟,支撐數載,已著有《三湘從事錄》。其歷官諫議與金公道隱諱堡等盡忠直言,忤群小而遭黨禍,已略紀于明末鑒史。其竄跡猺獞,匿身命以全名節,艱苦萬狀,恬然甘受,間亦微露之《蘆草》詩集中。其寓居衡南斗嶺,及赴西粵友人約,往還吟詠有《漆園放言》《欸乃聲》二集。庶母舅氏蕭翁百川曾為鴻云:‘先君復寓粵時所著《龍壁吟》無存稿,不知刻本尚有留人間否,惟《蘆草》頗拾輯其殘編,更名《蘆草遺灰》。’今合上數種文集,鴻愧恨無力刊行,俱已手錄成書。”[7]其中對于蒙正發著述的記載與《(同治)崇陽縣志12卷》契合。
徐登元○15在跋中寫道:“給諫蒙先生所著《三湘從事錄》《漆園放言》二書,元既敬為之跋矣。茲讀其家乘述略而不能已于言也。……先生之子之鴻能詳其義烈,先生之孫世英能守其遺編。為之前者,仁人義士;為之后者,孝子順孫。”[7]從此跋中可得知徐登元曾從蒙正發孫蒙世英手中見到《三湘從事錄》《漆園放言》的手抄本以及蒙之鴻所撰《家乘述略》,而金永森將其刻于書后,極有可能這些都寫在他從蒙正發后人借閱來的抄本之中。徐登元將《三湘從事錄》《漆園放言》二書并跋,則二書可能抄錄在一起,豈不正與金永森前言“得其書及詩一卷”吻合?因此筆者推測金永森在清光緒年尋訪蒙正發遺書時,《漆園放言》此書并未散佚,王船山為之所寫之序言金永森也曾閱。
另清同治五年(1866)刻《(同治)崇陽縣志12卷·卷11藝文志》記載:“《欸乃聲》,蒙正發著。自序云:‘己酉冬,余自漓江南還,詠得《欸乃聲》三十首。庚戌春,復由湘入漓。居無幾,偶以家事促,歸舟中往返,又得若干首。嘻!余倦于客矣!杜若江蘺偏與幽人分韻,粵山楚水專同野客縈懷。四愁想贈瑯玕,湘妃之淚灑來筠簳斑斑;九嘆驚疑環佩,屈子之魂招入楓林黯黯,嗟將何及?歌以永言。’”[1]據上可知《欸乃聲》為蒙圣功在清康熙八年(1669)至康熙九年(1670)漂流漓江途中所作詩集。又《崇陽蒙先生遺集·卷首題詞》中傅燮鼎寫道:“風云開國下荊臺,爝火殘明大半灰。尚倚巖畺稱義旅,可憐爨舍失雄才。邨翁解認青山宅,野史難搜白骨苔。傳說扁舟蒙給諫,湘漓漂泊未歸來。”[7]味其末句詩意與《三湘從事錄》無關,而與《欸乃聲》契合,筆者疑金永森曾從蒙正發后人處得《欸乃聲》之抄本,雖未刊刻,但拿與友人傳閱,因此傅燮鼎詩中才有此句。金永森之前摘句“粵水南來深染碧,春山雨過盡堆藍”也可為一佐證。又據金永森前言:“圣功有詩二種:曰《漆園放言》、曰《欸乃聲》,船山先生作序,雅推重之。”今于《(同治)崇陽縣志12卷》中輯得王船山為《漆園放言》所作之序,不知王船山為《欸乃聲》所作之序尚存世否?金永森可曾閱?王船山《南窗漫記》記載:“蒙圣功給事(正發)《欸乃聲》九十首,曾授余訂之。其警句則有:‘片帆影掛前川月,透枕霜清五夜鐘’‘藥市藏名嫌有價,鷗群不亂信忘機’‘荊臺不樂呼先輩,高閣從來束腐儒’‘千里孤身分兩地,一天雪意釀同云’‘潭經積雪波增力,樹過重陽葉盡凋’‘更擬卜居遷赤甲,遙憐知己在丹霞(丹霞,澹歸所居。澹歸者,金道隱堡。)’詎可不謂句意雙到?”[2]第15冊888由此可知蒙正發此書確曾由王船山修訂,但《(同治)崇陽縣志12卷》中提到此書僅錄有蒙正發自序。
由上可知,筆者推測金永森曾于蒙正發后人甘云峰處得《漆園放言》與《欸乃聲》之手抄本,但他因為“詩又非近時急務”而并未將其刊刻。他在《崇陽蒙先生遺集·卷首序言》中提到了刊刻《三湘從事錄》的緣由:“永森嘗論古今忠臣孝子自大賢以下離不得一愚字,蓋愚則心志專一,至死靡他,成敗有所不知,禍福有所不計,乃能肩天下重任。方今內憂外訌,迭起環生,時事亦甚岌岌,然綜而論之,其可為之,勢實百倍于先生當日。使率土之士盡如蒙先生之愚,出而為國家執干戈,衛社稷,天下事未必不可為,此則永森刻是書之徵恉也。若夫忠臣義士其精光浩氣貫天地,薄日月,上蟠下際自有其不朽者在。”[7]他希望當時之同仁能夠效仿《三湘從事錄》中的蒙正發,為挽救國家危亡挺身而出,而蒙正發所著詩歌則不如此書可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因此他就置而未刊了。
金永森的這個選擇造成的結果就是,蒙正發所著詩歌《漆園放言》漸漸散佚,王船山為此詩集所寫的序也鮮為人知,也就未收入他的全集之中。而王船山為《三湘從事錄》所寫之序言以及王船山為蒙正發所寫之墓志銘《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隨著《三湘從事錄》的流傳得到了后人的重視。《三湘從事錄》后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收入《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由神州國光社鉛印出版;1951年改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再版;1967年廣文書局及198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繁體豎排點校本;1998年收入《四庫未收輯刊》,由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2002年收入《明代野史叢書》,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簡體橫排本,流傳甚廣。
注釋:
1.即方以智。方以智字密之。明亡后削發為僧,法名大智,號無可,又稱浮山、弘智、藥地、五老、木立、愚者大師、極丸老人等。安慶府桐城縣鳳儀里(今安徽桐城市區)人。少以文名,參加復社,為其領袖。明崇禎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十七年北京破,哭于崇禎靈前,被李自成軍俘獲,受刑至兩髁骨見,不屈。當清兵大舉南下時,曾聯絡東南抗清人士抵抗。永歷時,任左中允,充經筵講官,桂王授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知無所作為,固辭不受,隱居于廣西平樂及湖南武岡等地,與王夫之交。清順治七年(1650),平樂陷,為清兵所執,但堅貞不屈,獲釋后削發出家,清順治十年(1653)在南京皈依曹洞宗,最后入江西吉安青原山為住持。清康熙十年(1671)冬,因事牽連被逮,解往廣東,途經江西萬安惶恐灘頭,因背疽發卒于舟中,一說投水死。著述甚富,有《通雅》《浮山文集》等。
2.陳子龍字人中,更字臥子,青浦人。他的詩歌成就較高,為云間詩派首席。此處陳青浦應指陳子龍。王船山《明詩評選》中選陳子龍《江南曲》二首,其后評曰:“轉折不形,魂神自動,結句蘊藉,一字百意。此以漢人機杼更齊、梁式幅,不知者但謂之齊、梁已耳。崇禎初,竟陵惡染橫流,臥子鳴孤掌以止狂波,才實堪之,不但志也。”
3.指唐朝詩人錢起和劉長卿。王船山《唐詩評選》中選錢起詩《余干旅社》《漂母墓》《游休禪師雙峰寺》《裴迪書齋望月》《早下江寧》。其后評曰:“錢、劉詩如以上諸篇,猶得渾成。然此作一結雖情致宛切,乃移作起句,亦未見其不可。中唐之病,在謀句而不謀篇,琢字而不琢句,以故神情離脫者往往有之。如兩皇甫、郎、盧、嚴、耿諸人,乍可諷詠,旋同藞苴。五言一體,自有源流,如可別營造極,古人久已問津,奚更吝留,用俟來者?惟以比偶諧音,差為近體,至其成章遣句,則非蘇、李、陶、謝,又何以哉?大歷諸子拔本塞源、自矜獨得,夸俊于一句之安,取新于一字之別,得己自雄,不思其反,或掇拾以成章,抑乖離之不恤。故五言之體喪于大歷:惟知有律而不知有古,既叛古以成律,還持律以竄古,逸失元聲,為嗣者之捷徑。有志藝林者,自不容已于三嘆也。”
4.王船山詩《聞極丸翁兇問不禁狂哭,痛定輒吟二章》后自注“傳聞薨于泰和蕭氏春浮園。”方以智號極丸老人,此處極丸翁應指方以智。
5.即金堡。金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法名性因、今釋,號澹歸,明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任臨清知州。明亡后,仕南明桂王朝為兵科給事中,卷入南明小朝廷黨爭。清順治七年(1650),桂林陷,遂削發為僧,創韶州丹霞寺,移住廬山棲賢寺。倡儒、釋合一之說。工詩文,善填詞。著述宏富,有《遍行堂集》《嶺海焚余》《丹霞澹歸禪師語錄》等。
6.指倪元璐。王船山有仿體詩《倪司徒元璐〈書憤〉》。王船山《明詩評選》中選倪元璐《送徐水部新婚奉使荊關》《白門出城登松風閣時為清明前五日》,其后評曰:“公才本倜蕩,亦為時詩所困,此自拔而有不竭之巧。時詩猶言時文也,認題目認景認事,鉆研求肖,借客形主,以反跌正,皆科場文字手筆。竟陵以后,體屢變而要不出此,為正其名曰時詩,明其非詩也。”
7.指王思任。王船山有仿體詩《王僉事思任〈登岱〉》。王船山《明詩評選》中選王思任《薄雨》,其后評曰:“置頷聯不論,詎非作者?竟陵狂率,亦不自料遽移風化,而盧俗易親,翕然于天下。謔庵視伯敬為前輩,天姿韶令亦十倍于伯敬,且下徙而從之,余可知已。其根柢極卑劣處,在哼著題目討滋味發議論,如‘稻肥增鶴秩,沙遠討鳧盟’,皆是物也。除卻比擬鉆研,心中元無風雅,故埋頭則有,迎眸則無;借說則有,正說則無。竟陵力詆歷下,所恃以為攻具者止性靈二字。究竟此種詩,何嘗一字自性靈中來?靠古人成語,人間較量,東支西補而已。宋人詩最為詩蠹在此。彼且取精多而用物弘,猶無一語關涉性靈,矧竟陵之鮮見寡聞哉!五六十年來,求一人硬道取性靈中一句亦不可得。謔庵、鴻寶、大節、磊砢,皆豪杰之士,視鐘、譚相去河漢,而皆不能自拔,則沈雨若、張草臣、朱云子、周伯孔之沿竟陵門持竟陵缽者,又不足論已。聊為三嘆!”
8.指楊基。王船山《明詩評選》中選楊基《客中寒食有感》,其后評曰:“平潤。國初藝苑,以高、楊、張、徐并稱四才。楊之于高,聲氣之交耳,殆猶富儈之視王孫,邸妓之擬閨秀,清濁異流久矣。蒙古之末,楊廉夫始以唐體杜學救宋詩之失。顧其自命曰‘鐵’,早已搏撠張拳,非廓清之大器。然其所謂杜者,猶曲江以前、秦州以上之杜也。孟載依風附之,偏竊杜之垢膩以為芳澤,數行之間,鵝鴨充斥,三首之內,柴米喧闐,沖口市談,滿眉村皺。乃至云‘丈夫遇知己,勝如得美官’,云‘李白好痛飲,不聞目有痤;子夏與丘明,不聞飲酒過’,云‘淚粉凝啼眼,珍珠壓舞腰’(《雪中柳》),云‘溪友裁巾幘,虛人作飯包’(《荷葉》),云‘何曾費錢買,山果及溪魚’,云‘巴人與湘女,相逐買鹽歸’,云‘清流曲幾回,吃飯此山隈’,云‘人情世故看爛熟,皎不如污恭勝傲’,云‘他年大比登髦俊,應報新昌縣里多’,云‘先生種苧不種桑,布作衣裘布為褲’,如此之類,盈篇積牘,不可勝摘。嗚呼!詩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詩,又降而有學杜者,學杜者降而為孟載一流,乃栩栩然曰:‘吾學杜,杜在是,詩在是矣。’又何怪乎近者山左、兩河之間,以爛棗糕酸漿水之脾舌自鳴風雅,若張、王、劉、彭之區區者哉!操觚者有恥之心焉,姑勿言杜可也。”
9.指高啟。王船山有仿體詩《高太史啟〈梅花〉》。王船山《明詩評選》中選高啟《短歌行》《當壚曲》等詩共八十三首,在明代詩人中選詩數量僅次于劉基。他對高啟的詩歌評價甚高,認為“一代詩人,非季迪不足以當之也。”尤其是他的樂府詩,王船山認為“起八百余年之衰”,又說“唐以來不見樂府久矣,千年而得季迪,孰謂樂亡哉!”高啟詩《郊野雜賦·其一》后王船山評曰:“苦學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奪杜胎舍,以不從夔府詩入手也。”
10.指袁凱。王船山有仿體詩《袁御史凱〈白燕〉》。王船山《明詩評選》中選袁凱《獨漉篇》《與倪元鎮飲得江上雨》等詩共十九首。其中《雞鳴》詩后評曰:“李獻吉謂凱詩學杜,非也。凱詩正自沈約來。約散弱為宋人禘祖,凱澹緩中有斂束,乃賢于約。此章純純無筆墨痕,學杜者何足以及之!”
11.王船山《〈三湘從事錄〉序》中也有類似表述:“華亭公以勞愁死,義興以惋恚終,余與圣功屢不死,而今日猶然言之,則我兩人之終岀黎平與天玉下,自取之也。”認為自己與蒙正發終究比不上在明朝覆滅時就死國之人。此或船山寫詞“我自從天乞活埋”之因也。
12.王船山在《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中寫道:“君生以萬歷丁巳三月初八酉時,得年六十有二……生子六:長肇旻,從予學;次肇暠,次肇暹,次肇晟,次肇昱,次肇昇。”可知蒙正發長子應名蒙肇旻,之鴻或為其字?
13.今人介紹蒙正發著述多以《蘆草龍壁吟》為一種書,誤。
14.據王船山撰《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志銘》:“君本甘姓,世居江西宜春……以受宗少孤,為同居繼父蒙清泗所鞠,遂改姓蒙。……君既世承蒙姓,屢思復姓甘,嘗與予深嘆,未果而卒。”蒙正發祖上本姓甘,金永森言其后人為甘云峰,則他的后人有改回甘姓者。
15.據《(同治)崇陽縣志12卷·卷7》記載:“徐登元號復堂,資性穎異,一目數行俱下。中乾隆乙卯副舉,精文律,喜博覽書史,酒酣耳熱,談論風生。邑士多出其門,所著志《藝文》。”《(同治)崇陽縣志12卷·卷1》中還收錄了《徐登元石龍原懷蒙圣功給諫詩》:“半壁南天草樹荒,出山小草氣飛揚。千軍夜肅潼溪月,匹馬朝馳粵嶺霜。不恤讒言訾五虎,長懷忠悃吊三湘。石龍原上風云壯,想見當年義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