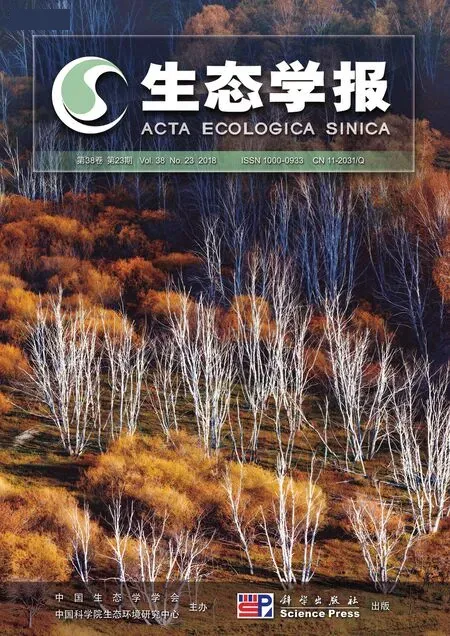黃土丘陵溝壑區生態風險動態變化及其地形梯度分析
——以陜西省米脂縣為例
劉 迪,陳 海,梁小英,馬 勝,王嘉妮
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西安 710127
目前,地球已經進入“人類世”新紀元[1],土地利用變化背景下大部分社會-生態復合系統受到人類活動的脅迫并引致諸多生態風險[2]。科學評估與緩解人類活動引發的風險,已成為當前地理學與生態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3]。黃土丘陵溝壑區等生態脆弱區對土地利用變化具有極強響應,區域內農耕活動頻繁,景觀較為破碎,生態系統穩定性及恢復力差[2,4],極大影響人類福祉賴以發展的自然根基。定量表征與評價區域內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風險,是黃土高原生態恢復及可持續發展的基礎[5]。
生態風險是生態系統組分受到外界壓力而產生不利生態影響的可能性[6]。目前,生態風險研究范式較為統一,基于景觀格局指數度量的景觀生態風險評價的研究居多[7- 11],且以土地利用變化為誘因的風險評價[12- 13]已成為研究熱點。盡管同時將風險源對生態環境的脅迫、風險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納入綜合生態風險評價的研究還不多見[14- 16],且指標間的權重大多采用層次分析法[16]、專家打分法[15]等主觀方法來確定,但在依據研究區實際情況遴選風險源指標、基于干擾度和脆弱度來表征自然系統損失度、綜合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來表征風險損失度等方面已得到諸多學者的認可[17- 19]。同時,生態風險評價研究主要聚焦流域[7- 9,14]、海岸帶[10,12,20]等自然地域以及礦區[11]、行政區[13,17,21- 22]等人文地域,黃土丘陵溝壑區風險評價研究案例較少。
基于此,本文以地處黃土丘陵溝壑區的陜西省米脂縣為例,選取農戶干擾脅迫、土壤污染脅迫、外部距離脅迫等3類風險源,基于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構建耦合農耕風險概率與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的二維風險模型,對生態風險時序變化進行分析的同時結合地形分布指數探究了生態風險時空分布特征與地形之間的關系。
1 研究區概況
米脂縣(109°49′E—110°29′E,37°39′N—38°05′N)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東南部,總面積1178 km2,地處黃土丘陵溝壑區。屬中溫帶半干旱氣候帶,全年降雨量低,氣候干燥,夏季是降雨主要季節;境內溝壑縱橫,地勢起伏較大,植被覆蓋度低,地表破碎化程度突出(圖1)。伴隨著大量農藥化肥、塑料薄膜的使用以及陡坡種植等高密度農耕行為,米脂縣農業生態系統呈現出脆弱性特征并使生態風險持續增加,及時把握風險的演變趨勢對于米脂縣十分必要。作為國家首批退耕還林示范縣,1999—2015年持續退耕使林草地面積持續增加,在區域政策與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耕地類型轉化與棄耕撂荒行為頻發;加之自然條件過渡性與多樣性,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產生較大變化,為揭示綜合生態風險的時空演化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臺。

圖1 米脂縣地理位置及其高程Fig.1 Location and DEM of the Mizhi County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與處理
數據來源涉及土地利用、地形及社會經濟數據等多個數據集。其中,2009年米脂縣土地利用類型數據基于第二次全國土地利用調查數據集獲得;2015年米脂縣土地利用數據以該年高分一號影像(321波段)為數據來源,通過ENVI 5.1進行幾何校正、影像增加處理后,進行監督分類和目視解譯獲取,解譯結果的Kappa指數達到0.86,滿足風險評價精度要求。參照全國土地利用分類標準,將土地利用類型分為耕地、果園、林地、草地、水域、城鎮村及工礦用地、荒地(含鹽堿地)7類。DEM數據源于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地理空間數據云(http://www.gscloud.cn/),重采樣為10 m DEM,利用ArcGIS鄰域分析工具建立5×5矩形移動窗口分別提取鄰域柵格高程最大值與最小值并求取差值,生成研究區地形起伏度[23]。人口密度、糧食產量及農業投入等社會經濟數據源自《米脂縣社會經濟統計年鑒》(2009年、2015年)。
2.2 生態風險評價框架
本文按照生態損失指數法,將研究區生態風險定量表征為風險概率與風險損失的乘積[6]。黃土丘陵農耕區生態風險源識別需較好地表征外部脅迫,而土地利用是農戶改造自然環境最直觀的表現形式[12],并關聯諸多生態環境問題[13],因此與土地利用密切關聯的農耕風險類型應當予以關注。基于此,黃土丘陵農耕區綜合生態風險(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isk,CER)可以通過農耕生態風險概率(Agricultural Ecological Risk Possibility,AERP)與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Natural-Social Loss Index,NSLI)共同表征[5,17]。公式如下:
CERi=AERPi×NSLIi
(1)
式中,CERi為風險小區i的綜合生態風險;AERPi為風險小區i的農耕生態風險概率;NSLIi為風險小區i的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其中:

(2)
式中,Pij為第i個風險小區的j類風險源概率;λj為j類風險源權重,農戶干擾脅迫、土壤污染脅迫、外部距離脅迫三者權重分別為0.24、0.42、0.34;NLIi為第i個風險小區自然系統損失度;SLIi為第i個風險小區社會系統損失度;權重a=0.64、b=0.36。權重通過客觀熵權法賦值得到。
為探討生態風險空間分異,本文利用等間距系統采樣將研究區劃分為362個2 km×2 km單元網格[10],將計算得到的各類風險源指標數值及損失度值賦予風險小區中心點,借助ArcGIS空間分析工具進行普通克里金插值,實現空間化。
2.2.1 農耕生態風險概率
目前,由于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關聯程度不斷加深,土地利用替代自然要素在短期內主導環境變化和區域發展已成客觀事實[19]。在黃土丘陵溝壑區,景觀演化亦具有人類主導性,結合風險動態演化的研究目標導向,生態風險概率偏重農戶耕作與生產生活引致的風險,主要包括由農戶干擾脅迫、土壤污染脅迫、外部距離脅迫三者引致的風險。
農戶干擾脅迫是指農戶從事農業活動、生產生活形成的干擾體對景觀環境施加的脅迫[24]。本文根據黃土丘陵農耕區特點,選取土地墾殖系數表示農戶對土地資源的利用與干擾程度,該系數為耕地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比例。一般情況下,土地墾殖系數較大的區域往往面臨較高的局域水土流失與土壤鹽漬化風險。考慮到研究區水資源匱乏、工業滯后,因此區域環境污染應重點關注農業土壤污染,本文選取農藥化肥施用強度與農塑薄膜覆蓋密度表征研究區農業種植行為對區域生態環境帶來的土壤污染脅迫。
外部距離脅迫是農戶對不同景觀類型干擾距離的刻畫,一般而言,距離道路越近,人類活動影響下各類景觀類型代表的生態系統面臨其生態系統服務降低的風險越大[5]。另外,外部距離脅迫值也與自身地類屬性對農戶的吸引程度有關,本文通過距離衰減系數進行衡量[25]。公式如下:
(3)
式中,d為景觀單元距道路的距離;aj為j類景觀類型的距離衰減系數,根據建筑用地、耕地、果園、水域、草地、林地和荒地對道路依賴程度的不同,分別取1000、500、500、100、10、1、1。
2.2.2 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
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包含自然系統損失度,社會系統損失度,分別表示自然系統、社會系統暴露于風險下可能帶來的損失[17- 18]。農耕行為對生態環境的干擾,使區域內所有景觀暴露在一種或多種風險源之下,其代表的生態系統都可能遭到損失[21],直觀地表現在景觀結構和功能的變化上。不同類型景觀暴露于區域的多種位置,其受到的干擾程度與自身應對外界干擾的抵抗能力均有差異[10]。本文選用基于干擾度和脆弱度的自然損失指數反映風險受體受到人為干擾時其自然屬性損失的程度[18]。公式如下:
(4)
式中,NLIi為第i個風險小區的自然系統損失度;Ek為景觀類型k的干擾度;Fk為景觀類型k的脆弱度;Sik為第i個風險小區k類景觀類型面積;Si為第i個風險小區總面積。參考前人[10,22]研究,干擾度包含破碎度、分離度、優勢度,各項指標在Fragstats 4.2中計算得到;脆弱度依據專家打分法歸一化求得。
由于不同的生態危害發生在不同的風險小區內,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因此損失度不僅要考慮受體的自然屬性,還要考慮其社會經濟屬性[16]。農耕區社會經濟系統中,人口是區域發展的根本,糧食資產是關乎農戶福祉的關鍵,兩者是研究區風險脅迫下最為敏感的損失受體。本文通過社會系統損失度SLI定量分析區域災損敏度,利用人口密度、糧食產量指標等權重綜合反映。本文依托于土地利用數據,人口密度以格網內建設用地比例與鄉鎮人口密度標準值進行分區統計獲取,糧食產量以格網內耕地面積比例與鄉鎮糧食產量標準值進行分區統計獲取。
2.3 地形起伏度及其分布指數
地形起伏度是對區域地形切割深度的數值度量,是表征地貌類型的重要指標,尤其是在黃土丘陵溝壑區等地表切割較強地區,地形起伏度的成圖成為該類區域地貌過程分析的重要步驟[26]。黃土丘陵溝壑區內地形對人類活動的限制性和對土地利用空間分布的自然選擇性,使區域內人類風險脅迫與社會財富隨地形梯度分布呈現規律的變化特征,而風險源與損失度等關聯要素的變化導致地形梯度上不同等級生態風險的遷移。本文結合分布指數[27]旨在探討地形起伏度因子與生態風險之間的時空關聯。分布指數通過消除不同地形起伏度等級面積差異和不同風險組分面積比重差異來描述各風險組分在地形起伏度梯度上的分布狀況。公式如下[27]:
P=(Sie/Si)(S/Se)
(5)
式中,P為分布指數,Sie為第e種地形起伏度下第i類風險等級面積,Si為第i類風險等級總面積;Se為第e種地形起伏度總面積,S為研究區總面積。P>1,說明特定風險等級在特定地形起伏度上處于優勢分布。
3 結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由表1可知,研究期間米脂縣土地利用總體變化不大。草地、果園、水域及城鎮用地面積比例基本維持穩定,而耕地、林地、荒地土地流轉明顯。耕地減少3168.45 hm2,變化幅度為-6.16%;林地增加1102.95 hm2,變化幅度為8.54%;荒地增加1609.47 hm2,變化幅度為183.70%,是面積比例變化最大的土地利用類型。減少的耕地,部分受退耕還林政策推動轉化為林地,部分受農戶個體拋荒轉化為荒地。拋荒行為原因多樣,大多受經濟利益驅動,年輕農戶出外打工或響應移民搬遷政策離開農村選擇主動拋荒,部分農戶因年齡增長難以負擔繁重農工而被迫拋荒。林地增加大多來源于耕地轉入,相較于耕種,部分農戶更意向于退耕還林,出外打工而獲得更高收益。鹽堿地產生于溝谷地帶,研究期間由于大面積土壤鹽漬化使鹽堿地面積增加,土壤耕性受到影響且短時間內難以恢復。

表1 2009—2015年米脂縣土地利用類型變化/%
3.2 綜合生態風險時空分異
本文基于自然斷點法將農耕生態風險概率、系統損失度以及綜合風險進行分級,等級越高表示風險概率、損失度以及綜合風險越大,結果分別如圖2、圖3和圖4所示。
3.2.1 農耕生態風險概率
農耕風險概率是農戶干擾脅迫、土壤污染脅迫與外部距離脅迫的綜合表征。由圖2可知,研究期間風險概率空間差異顯著,大致呈現中東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間分布格局。2009年最高風險概率(V級)占研究區面積的12.25%,集中分布于中部的銀州與東部的桃鎮與楊家溝;銀州位于川道,農耕與鄉鎮交通發達,農戶干擾較大,桃鎮與楊家溝因其較高的墾殖率與農肥施用而呈現較高的農耕風險。III、IV級風險概率在V級風險區域周圍呈環狀分布,占研究區面積的31.03%。I、II級風險概率占研究區面積的56.82%,主要分布于西部與北部區域;西部各鄉鎮農地耕作強度與農肥使用量較低,土壤污染有限,同時北部與西部交通相對閉塞,農戶干擾造成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降低的可能性較小。與2009年相比,2015年農耕生態風險呈現“西移北進”、中部擴張的趨勢,風險概率整體上升了13.19%。東南部風險核心有所縮小,主要是由于楊家溝土壤污染明顯減輕;西部與北部農耕風險的擴張則與石溝和沙店的道路擴張、石溝和高渠等鄉鎮土壤污染的上升密切相關。

圖2 米脂縣2009—2015年農耕生態風險概率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Risk Possibility from 2009 to 2015 in the Mizhi County
3.2.2 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
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由景觀結構損失度、社會經濟損失度綜合表征,由圖3可知,研究期間系統損失度空間差異顯著,大致呈現中西部高、南北低的空間分布格局。2009年較高損失度(IV、V級)塊狀分布于研究區中部,主要包括西部的郭興莊、石溝、中部的橋河岔等鄉鎮,占研究區面積的25.22%;郭興莊毗鄰榆林風沙區,植被稀少,土壤風蝕沙化明顯,自然損失度全縣最高;石溝與橋河岔高損失度閉合區正處米脂縣最大的兩條侵蝕溝,土地利用開發程度強,景觀破碎,且人口密集,風險造成的損失較大。I、II級損失度占研究區面積的44.53%,主要分布于東北部以及南部各鄉鎮。與2009年相比,2015年系統損失度呈現“南移東進”、中部聚集的趨勢,系統損失度整體上升3.62%。隨著城鎮化推進,中部銀州接納更多的外來鄉鎮人口,人口密度有所上升,風險損失增加。近年來石溝鄉鎮建設使得區域景觀分離度降低,損失度核心區域縮小,而東部的桃鎮由于大面積土地撂荒導致景觀趨于破碎,自然損失度增加而成為新增的損失度高值核心。

圖3 米脂縣2009—2015年自然-社會復合系統損失度空間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Social Loss Index from 2009 to 2015 in the Mizhi County
3.2.3 綜合生態風險
綜合生態風險是“概率-損失”二維模型的集成表達(圖4)。研究期間,2009年、2015年米脂縣綜合生態風險指數分別為0.1466、0.1607,風險值上升9.65%。為更好說明風險值的變化特征,本文采用風險轉移矩陣分析各個風險等級面積轉化情況(表2)。
研究期間風險轉移類型除各個風險級別面積保持不變之外,主要有I—II、I—III、II—III、II—IV、III—IV、III—V、IV—V7類等級增加的風險轉移類型以及II—I、III—II、IV—III、V—IV4類等級減小的轉移類型。將相鄰等級風險轉換面積相互抵消可得到風險面積的轉化去向:I—II的轉化面積為4679 hm2;II—III的轉化面積為20936 hm2;III—IV的轉化面積為10032 hm2;IV—V的轉化面積為2264 hm2。由轉化去向看出,風險等級均在自身等級的基礎上轉向較高一級。通過簡單統計,風險等級由低到高轉變的面積占研究區面積的40.9%,而反向轉變面積僅占6.07%,說明生態風險度雖在局部地區有所下降,但在整體上呈上升趨勢。

表2 米脂縣2009—2015年綜合生態風險轉移矩陣/hm2

圖4 米脂縣2009—2015年綜合生態風險空間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isk from 2009 to 2015 in the Mizhi County
同時,從圖4可以看出,研究區綜合生態風險空間差異性顯著,整體上呈現中間高南北低的空間分布格局。2009年I、II等級風險區約占研究區面積的一半,主要分布于東部和北部。IV、V等級風險占研究區面積的22.04%,集中于研究區中部,呈片狀直線分布。與2009年相比,2015年生態風險維持前期的空間格局,但各等級風險面積比例發生較大變化,綜合風險有明顯增加的趨勢。I、II級風險區占研究區的面積分別下降4.7%、14.85%,其中II級風險區面積的減少是研究期間風險轉移面積最大的類型。III級風險區面積擴大明顯且已聯接成片,達到研究區面積的1/3,面積比例增加8.84%。IV、V級風險區面積比例分別增加7.72%、3.01%,且空間格局變化明顯,橋河岔及銀州V級高風險核心擴大明顯,相較而言石溝高風險核心明顯縮小。
3.3 生態風險與地形起伏度的關系
為厘清生態風險與地形的耦合關系,本文以地形起伏度為單一因子,結合分布指數探討生態風險的時空分異(表3)。表3中,數字1—5表示地形起伏梯度,通過自然斷點法進行分級;數值區為分布指數P。
隨地形起伏度級別增加,生態風險變化趨勢大致分為3類:增加型,即I、II級風險區;穩定型,即III級風險區;減少型,即IV、V級風險區。從同一年份分布優勢數值變化來看,隨地形起伏度梯度增加,I、II級風險分布優勢持續升高,大致在3—5級梯度上占優勢;較高的地形起伏度說明區域相對高差較大,不適宜農戶耕作且可達性較差,農耕風險影響十分有限,且起伏度較高的區域分布大量林草地,自然損失度較小。IV、V級風險在1級地形起伏梯度上呈現優勢分布,隨梯度增加,分布優勢持續降低。較低的起伏度能夠指示較高的地形完整性與可達性,集中分布于川道河谷區及溝谷壩地區,受高密度農耕行為影響呈現為較高風險概率,且區域人口集中,糧食產量較高,系統損失度大,綜合生態風險最高。III級風險隨地形起伏度的增加變化不明顯。從不同年份分布優勢數值的變化來看,I級風險在3—5級優勢梯度上的數值明顯降低,而II級風險在4—5級優勢梯度上的數值升高,說明了高地形起伏度區域將承受更多的生態風險。V級風險除在1級起伏度上分布優勢有所升高外,在其他起伏度級別上分布優勢均降低,說明高風險區域在較低起伏度上的分布更加集聚,川道區域將承受更高的風險脅迫。

表3 綜合生態風險與地形起伏度的分布關系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1)研究區土地利用發生較大變化,充分體現了以退耕還林政策與農戶行為二元主導的農耕區土地利用格局特點。持續退耕與耕地撂荒,使耕地不斷減少,造林與拋荒面積不斷增加,受土壤鹽漬化影響河谷壩地產生大量鹽堿地。
(2)研究區2009年、2015年綜合生態風險指數分別為0.1466、0.1607,農耕風險脅迫增大。生態風險空間分布差異明顯,風險高值區片狀直線分布于研究區中部,研究期間有向川道集聚的趨勢。
(3)依托于地形分布指數分析了綜合生態風險與地形起伏度的關系。結果發現,低風險往往優勢分布于較高的地形起伏度區域內,高風險則聚集于起伏度低值區;研究期間,風險向較高地形起伏度遷移明顯,同時高風險區域在較低起伏度上的分布也更加集聚。
4.2 討論
本文基于經典的概率損失二維框架解構綜合生態風險,豐富了偏重人為風險源的生態風險評價體系,在綜合風險動態變化分析的同時探究了風險與起伏度的關系。指標體系的構建上,本文選擇具有區域代表性的農耕區土地生產投入和外部距離等指標,分別表征土壤污染和外部距離脅迫,研究結果與當地實際情況較為吻合。同時,復合系統損失度不僅綜合考慮了自然生態損失與社會經濟損失,還對其時序變化進行分析,較為充分地體現了風險受體的自然與社會經濟屬性及其變化。
同時,本文結合可有效表征研究區地形特征的地形起伏度,將其納入分布指數來分析生態風險與地理環境之間的時空關聯,相較于以往針對風險等級制定風險降低對策,本文則基于不同起伏度上優勢風險分布給出空間差別化的生態保護措施:1)在高與較高風險分布的低起伏度優勢區段,即川道河谷區以及溝谷壩地區。應嚴格管控農戶農耕行為,控制農藥化肥以及塑料薄膜施用量,控制以邊坡開挖增加的建筑用地面積,保護壩地和水田,緩解人地矛盾;2)在低與較低風險分布的高起伏度優勢區段,即深切溝谷。應禁止坡耕地開發,嚴格控制放牧樵采,積極發展經濟林果產業,降低生態環境脆弱性,提高抗風險能力。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變化的風險模型,從景觀格局方面探討受體自然損失的嘗試,為后續綜合景觀格局和生態學過程來探討生態風險奠定堅實的基礎。加之農戶行為是造成景觀格局和生態學過程變化的主要因子。因此,綜合考慮景觀格局與生態學過程,基于行為模型探討和分析生態風險的時空分異與演化,就為今后探討宏觀生態風險的微觀驅動機理提供了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