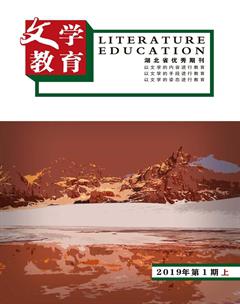生態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德羅斯特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解讀德國著名女作家德羅斯特的詩歌《紫杉籬》,通過剖析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她在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不同時間維度中與自然的相處模式,揭示詩歌中暗藏的女性與自然之間的隱喻關系,凸顯其中蘊含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萌芽,表現詩歌體現的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
關鍵詞:德羅斯特 紫杉籬 生態女性主義
德羅斯特(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1797年在德國威斯特法倫許爾斯霍夫水上城堡出生,被譽為德國19世紀最偉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詩歌為主,亦有戲劇、小說等文學類型的嘗試。近年來,她的曲作品也得到學界的重視。詩歌《紫杉籬》創作于1841年九月到1842年二月初之間,1842年三月在科塔出版社發行的《晨報》上發表,這家出版社曾經獨家出版過德國著名作家歌德、席勒的作品。《紫杉籬》是德氏的代表作,以其簡潔的語言、豐富的層次以及優美的意境受到研究者和詩歌愛好者的好評。
一.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與《紫杉籬》
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學與女性主義的結合,是女性主義的一大流派。學界一般認為這一思想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首先出現在法國女性學者弗朗索瓦·德·奧博納的兩部作品中:《女性主義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la mort,1974)和《生態女性主義:革命還是改革》(Ecologie Féminisme: Révolution oumutation,1978)。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后生態問題的凸顯,這一理論獲得了重要發展。
女性與自然的身份認同是生態女性主義的最顯著特征,即主張男(父)權制人類社會對婦女的統治、壓迫與對大自然的踐踏、掠奪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他們認為婦女和自然之間存在著某些本質上共同的特征,表現為女性的生物學構造使得她們與自然的生殖和養育功能之間的聯系比男性更為緊密。此外,女性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中處于從屬地位,被男性剝削甚至被客觀化,而自然在人類文明社會中長期受剝削、受壓制。這使得女性與自然之間產生了密切聯系,這樣的聯系以及相似的命運使女性和自然結成了聯盟。生態女性主義提出反對(男)人類中心論的主張,展開了保護、拯救自然與爭取婦女解放與男女平等的運動。
德羅斯特本人不是女性主義者。下文的詩歌分析也將顯示,詩中的女性形象“我”也并非屬于此陣營。“我”具有一定的覺醒意識、反叛精神,但最終沒有進行抗爭,只是接受了男性對自己的傷害,認可現實。不過,這并不妨礙我們清晰地看到《紫杉籬》中自然與女性的緊密聯系。紫杉籬始終陪伴著“我”,見證了“我”的快樂與痛苦,給“我”提供自省的契機,最后,它“宛如港口”,“我”在這里再也不會“遭到狂風的侵襲”。詩中明確表現了自然的中心地位和不可褻瀆的特性,反對人類中心主義。
二.《紫杉籬》中的女性形象
詩歌描寫“我”重游故地,駐足紫杉籬前,在此追憶往事,品味當下。“我”把這段紫杉籬想象為一道幕布,幕布上投射出18年前的事情,屬于“我”的榮光已經褪去,華冠已經“變冷”。幕布后面掩蓋著曾經,那里充滿了歡歌笑語,是“我”的天堂。而這道紫杉籬已經緊緊鎖閉,站在幕布前的是凄苦的現實,“我”無法回到過去,而灰暗的當下使“我”在未來看到的只有死亡。
全詩一共六個詩節,每個詩節由八個詩行構成,韻腳為abab隔行押韻,讀起來一氣呵成,朗朗上口。整首詩可以劃分為現在、過往、未來三個時間維度,“我”立足當下,追憶曾經,展望未來。詩中將紫杉籬比喻為通往天堂的門,“門后百花爭艷”,那是“我”的青春時光,“那時候,我的頭發隨風飄揚/還像金子般閃閃發亮/那時候,我的歡叫聲響徹山谷/仿佛號角回蕩”。可以推測,“我”曾意氣風發,充滿活力,度過了快樂的日子。因為愛情曾在這里萌發,像是“柔嫩的常春藤的幼芽”。不過,它并沒有能夠成長,而是“不在了”。因此,“我”總想“把十八個年頭的昏曉/從我一生的簿冊上勾掉”。詩人沒有具體展開究竟發生了何事,但可想而知,“我”在愛情中一定遭受了重大打擊,以致于想要抹去18年的時光。最后,在紫杉的氣味中依然保持清醒的“我”感到自己疲倦如一片枯葉,想回歸紫杉籬的懷抱安息。從嫩芽到枯葉,從意氣風發到疲倦不已,從充滿生機到暮氣沉沉,至此,詩歌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層次豐富的女性形象。她經受磨難,終于能夠做到平靜地審視過去,似乎與過去達成和解。她承認往事不再可追,但也無力改變當下,對未來毫無期望。
三.女性與自然的關系
詩中,“我”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值得關注。“我”的精神狀態始終通過自然界的烘托得以呈現。在第一詩節中,“我”站立在紫杉籬面前,冷靜而客觀,和自然如同好友,是一種對等的關系。紫杉籬“烏黑”且“凹凸不平”,“滿是缺口”,一如“我”飽受折磨的內心。作為過去與現在的連接點,紫杉籬讓“我”想起曾經的戀人。在第二詩節中,紫杉籬成為一道幕布,如同一面自省的鏡子,反射出“我”的過往。“我”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反映出當時“我”積極的生活狀態。詩人用“百花”的鮮艷奪目襯托“我”沉浸在愛情中的興奮與快樂。同時,用“荊棘叢生”顯示現實的崎嶇困頓。但“我”看到,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紫杉籬都如同“守衛者”一般,憂郁而敦厚,看護著“愛情的寶座”。紫杉是歐洲一種中小型常綠樹,可高達數米,不過一般被作為灌木種植。它結紅色漿果,深綠色的針形葉有毒,散發出來的味道會讓人產生幻覺,據說在其樹蔭下睡覺甚至只是休息,人也會受到其氣味的影響。詩中也提到了這一點,指出“聽說,你的針葉散發出的氣味/使得人們昏昏欲睡”。不過“我”卻認為,沉醉在紫杉的氣味中,“我”比任何時候都要清醒。不僅不會覺得受到威脅,相反,“我”感到紫杉籬如同護“我”平安的港灣,“我”只想在這里躲避風浪,直至死去。自然沒有給“我”帶來傷害。“我”受到的壓迫和痛苦另有來處。無論得意還是失意,無論順利還是不幸,“我”始終與自然息息相通,融為一體。女性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聯系得到了淋漓盡致地體現。
在第二詩節中,詩人將紫杉籬比作遮蔽圣地的“帳幕”。帳幕的主要用途是與外界隔絕,保持私密性。在基督教文化中,帳幕是侍奉神的地方,而且是神臨在的場所。它同樣象征著真正的圣殿耶穌基督(約2:21;啟21:22)。當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忽然,殿里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太27:51)。可見,帳幕具有無上的神圣性。但在詩中,“我”眼中的圣地敬拜的不再是神,而是青年時期的愛情,紫杉籬成為愛情皇冠的守衛者。這種描寫不可謂不瀆神,特別是對身為虔誠天主教信徒的詩人而言!這無論如何為“我”的形象增添了具有反叛性的特點,同時我們也看到,詩人賦予自然以極高的神圣性。它與同為受造物的人類一樣平等,一樣受神眷顧。詩中蘊含著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思想,如同詩行結尾處“我”在紫杉籬中找到遮蔽,二者命運融為一體。
四.詩人生平背景
詩歌中鮮明的今昔對比不禁讓讀者對“我”在18年中究竟經歷了什么產生了好奇。幾乎所有德羅斯特的研究者都會把這首詩與詩人的生平聯系起來。1820年,德羅斯特造訪伯肯多夫時結識了哥廷根大學生施特勞勃(Heinrich Straube),兩人相愛。為了所謂“考驗”德羅斯特的感情,施特勞勃的一位朋友也表現出在追求德氏。學界也有說法認為發生這種情況是由于信仰的教派不同,德氏家里人出手干涉。無論出于何種原因,最后這兩個男人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反過來指責德羅斯特輕浮放蕩。愛情的嫩芽就此遭到摧折。此事甚至成為當時的一樁丑聞,以致于德氏直到1837年才再次回到伯肯多夫。
德氏的這段經歷令人唏噓,或許也讓讀者對于理解詩歌內容豁然開朗,但必須指出,即便不聯系詩人的生平,我們也可以在詩歌中體會到來自男性的壓迫。詩中雖然沒有直接塑造任何男性形象,但通過戀人、愛情等詞語,我們能夠獲悉男性的存在。盡管詩人對此不著一墨,但往日歡愉與今日落寞之間的強烈對比,讓我們意識到來自男性的壓迫之強烈,傷害之巨大。即便詩中的女性體現出自覺意識,但畢竟太微弱,終于還是“疲倦”地放棄。
五.結語
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告誡我們要避免對弱者如女性、自然及第三世界的統治、剝削與破壞,喚醒人們的生態整體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建立一個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物種平等、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社會。《紫杉籬》并沒有直接提出這種充滿現代性與進步性的主張,但透過女性與自然之間緊密聯系的紅線,我們可以窺見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的萌芽。在更深刻地認識作品內涵,體味其豐富的層次的同時,生態女性主義理論也為我們提供了解決詩歌中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的答案,即基于關心、愛護、尊重、信任的互惠和負責原則的生態倫理觀,構建一個和諧相處的世界。這對于觀察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原始發展情況,對研究生態女性主義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Woesler, Winfried (Hrsg.):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Werke, Briefwechsel,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1985-2000.Bd.I,1,2.Gedichte zu Lebzeiten,Text, bearbeitet von Winfried Theiss,1985.
2.[美]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主編,蔣林譯: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3.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介紹:袁媛,北方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德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