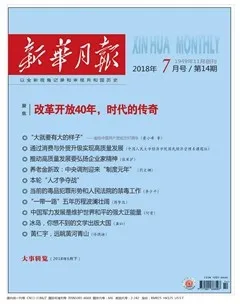在他的鏡頭里,角色是這樣誕生的
今天,當我們對某些流量明星“面癱”表演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真的應該回頭去看看謝晉的那些經典影片。那里面為何會有這么多讓人過目不忘的角色?為何這么多初出茅廬的新手能夠一片成名?《紅色娘子軍》中的吳瓊花、南霸天,《牧馬人》中的許靈均、李秀芝,《芙蓉鎮》里的秦書田、胡玉音、李國香、王秋赦、五爪辣……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角色,為何總會被后人奉為殿堂級表演的圭臬?這一切,都要從謝晉對演員職業的理解說起。
古人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晉挑演員,最先看的,是他/她的眼睛。比如《紅色娘子軍》的主演祝希娟。謝晉去上海戲劇學院物色演員,正碰上畢業班在排畢業大戲。謝晉看到,后臺的一角,一個大眼睛女生,正情緒激動地與人爭執。她那雙大眼睛,因為氣憤,好像正在往外噴火。謝晉一下子就被這雙眼睛吸引住了,這不正是劇本里描寫的瓊花的眼神嗎?于是,過不多久,我們便在銀幕上看到了這樣一雙噴火的眼睛。
日積月累下來,這些就成為kZqNuf7yBIh4hJ5UuEqQf37yKqj2zUhVY2uD0Nfw2EM=一種讓后人難以復制的謝晉方法。然而,盡管難以復制,我卻不相信它對于今天的電影工作者,就真的毫無借鑒的價值。
在謝晉眼里,各種角色都會“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對演員的基本判斷,大體接近中國傳統戲曲中的 “五行”:生、旦、凈、末、丑。譬如祝希娟,風風火火、敢打敢拼,類似京劇中的“刀馬旦”;而劉曉慶,有時潑辣、有時俏皮、有時風情,類似戲曲舞臺上的“花旦”;相比之下,王馥荔、潘虹、陳沖、張瑜、叢珊……則可歸為比較端莊、柔美的“青衣”。如果此說成立,那么,在他眼里,牛犇無疑就是一個優質的 “文丑”。他常說牛犇是個“黃金炮架子”——炮筒只有裝在合適的支架上,才能打得遠、打得準,意指牛犇屬于那種能把“紅花”襯托得格外鮮艷的“綠葉”。這樣的演員戲不在多,但沒有他們的存在,就像炒菜忘了放鹽一樣,一場戲就會少了許多滋味。在謝晉眼里,《芙蓉鎮》里的二流子王秋赦、《舞臺姐妹》里的戲班班主和尚阿鑫、《大李小李和老李》中的大力士關宏達,都屬于這一類不可或缺的“黃金炮架”。
說到關宏達和《大李小李和老李》,我曾經問過謝晉導演,為何要用他來和滑稽名家范哈哈搭戲?謝導眨眨眼睛反問我道:你看過勞拉和哈臺的戲嗎?熟悉好萊塢喜劇的觀眾,對這兩個活寶的名字,應該不會陌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影壇,曾經出現過眾多以模仿他倆著稱的演員組合,其中最有名的,當屬上海的韓蘭根、殷秀岑、關宏達他們三個。1949年后,韓蘭根、殷秀岑兩位調去了長春電影制片廠,關宏達一時孤掌難鳴。當時謝晉有些神秘兮兮地對我說,你看,范哈哈長得像不像韓蘭根?他這一說,我終于恍然大悟,以關宏達、范哈哈的胖瘦組合,恰好能夠喚起老牌影迷對于勞拉與哈臺的喜劇記憶。
謝晉對于演員的訓練、調教,過去往往也是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他對于演員的要求是,不能止步于知道,必須要做到下意識,想都不想馬上就能進入角色,這就要求熟練。
對于演員的表演,謝晉最反對的是直白淺露、一覽無余。他要的是含蓄、回味和托物言志。他經常會講到李緯在《舞臺姐妹》里的一場戲:已經小有名氣的月紅,坐在經理室的寫字臺上練簽名,李緯演的唐經理手上拿著一把折扇,上來試圖挑弄她。月紅假裝沒看見,低頭寫字。只見李緯拿起折扇一扇,桌上的紙被掀起了一紙角,月紅只好抬起頭,與他有了眼神的交流。很顯然,謝晉對這場戲不無得意,他評價李緯的表演只用了四個字:不露痕跡。在他眼里,這四個字說的其實就是表演中的極品。
至于托物言志,我最先聯想到的例證,當屬《女籃 5號》中田振華身邊的那盆蘭花。劇情中,田振華具有多重身份。他曾經是職業球隊的球員,后來參加了革命,成為西南軍區體工隊的教練,再后來,他奉命調回上海,擔任女子籃球隊的技術指導。所到之處,他都會隨身攜帶著那盆精心呵護的君子蘭。無形中,這泄露了他的秘密。君子蘭,素雅高潔,歷來是中國傳統文人人格志趣的象征——最終,他還是一位底色未脫,空谷幽蘭的精神士大夫。所有這些意涵,不著一字,境界全出。靠的是什么?不正是傳統詩學所推崇備至的言外之意和托物言志嗎?
(摘自6月15日《文匯報》,文章有刪節。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