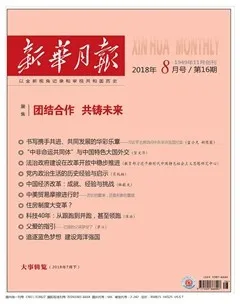科學術語的規范化與中國化

“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
2017年的秋冬之交,天文學界的熱門話題肯定少不了人類首次發現源于太陽系外的小天體。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給這個雪茄狀的小家伙取了永久性的科學名字“1I/2017 U1”。泛星計劃(PanSTARRS)的科學家們率先發現了它,用夏威夷當地的土語“‘Oumuamua”來稱呼,意指“第一位來自遠方的使者”。國內媒體在報道初期直接采納了這個單詞,少數幾家譯為“遠方使者”或是其他。沒多久,標準化的中文名字“奧陌陌”就進入新聞傳播領域,及時更新了公眾的科學認知。
發布“奧陌陌”一詞的是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天文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備選的譯名方案很多,包括“青鳥星”“遠方客”“遠游星”“訪客星”等,這些基本貼合了“‘Oumuamua”的字面意思。后來有個委員提出音譯,“奧”有神秘莫測之感,“陌”可以聯想到“遠方的信使”,組合起來又保留了單詞原有的韻味。在“天文學名詞”的網站上,“‘Oumuamua”與“奧陌陌”已經可以查詢到,狀態是“待審定”。
依據“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原則及方法”,科技新詞工作分為“發布試用”和“審定公布”兩步進行,各學科分委員會所確定的科技新詞,經全國科技名詞委審查批準后,通過相關媒體向社會發布試用。一段時間以后,分委員會根據反饋意見進行審定,然后由全國科技名詞委正式公布。這意味著,“奧陌陌”一詞是否具有權威性和約束力,還要等待天文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審定結果。
審定是為了打造標準、建立規范,那么名詞之規范究竟有多重要?物理學家嚴濟慈在上世紀30年代寫過一篇《論公分公分公分》,發表在《東方雜志》上——“度量衡法規第四條,長度單位有公分公厘,面積單位有公分公厘,重量單位亦有公分公厘,故其第六iNOoiPHVGZkl2DcmdW/02CB5huxh/VcKPIqZpAhD+t4=十二條之中西名稱對照表:有公分者centimètre也,又有公分者déciare也,更有公分者gramme也;有公厘者millimètre也,又有公厘者centiare也,更有公厘者décigramme也。此種絕不相類之單位,竟采完全同樣之譯名。夫數個名詞,表一事物,世少引為詬病;今乃一個名詞,包含三種意義,其混淆費解恐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任何民刑公私法規條例中,決不能容有如是混亂名稱之存在,而況度量衡之科學法規乎!”在嚴濟慈看來,“凡百工作,首重定名;每舉其名,即知其事,斯為上矣”。
恩格斯曾經這樣評價術語對于科學發展的重大意義:“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恩格斯所謂的“術語”其實就是上文提及的“名詞”。關于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宋小衛、張冬冬在《術語之道三題》(刊載于《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11期)進行過闡述:“‘名詞審定委員會’‘名詞審定工作’所稱的‘名詞’,均非語法意義上的名詞,而是泛指學科領域中表達各種專業概念的詞語指稱,它既包括名詞性詞語,也包含有形容詞、動詞性詞語……依常理下判,將‘名詞審定委員會’‘名詞審定工作’改稱為‘術語審定委員會’‘術語審定工作’,可能更恰切一些。實際上,在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英文名稱(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erms i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中,Terms一詞的中文通譯即為‘術語’而非‘名詞(Noun)’。”盡管名詞審定之“名詞”義同“術語”,這一點在許多語言學專家以及審定工作參與者那里取得了共識,但由于異名使用的情況延續了百年之久,顛覆習慣、重新調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要不要改回來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說:“從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中國保持了一個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輝煌、歷史久遠,與之銜接的觀念和名詞也跟隨史料流傳下來,并不斷地演化、修正和發展。曾任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副主任的吳鳳鳴在《我國自然科學名詞術語研究的歷史回顧和現狀》一文中以年代為序,梳理了古代文獻中的科技名詞,最早追溯到西周時期。《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的“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點出了谷、陵的關聯與差別,可以看作是地學的概念;《管子·地數篇》的“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說明當時對于特定的礦藏,既識外部特征又知內在屬性;《周髀·算經》使用了天文與歷法的術語,《漢書·地理志》提到了石油與天然的概念。作為中國古代第一本釋義詞典,《爾雅》收錄了包括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在內的各科術語,科學技術的內容占到一半以上,每個詞條的表述都有自己的概念體系,“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語出《經典釋文》)。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被李約瑟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書中記載了豐富的科學新知。比如數學上的隙積術(即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問題)、會圓術(一種計算圓弓形弧長的近似方法);物理學上的地磁偏角、凹面鏡成像與聲音共振;地質學上的沖積平原形成、水的侵蝕作用以及“石油”的命名。到了明代,涌現了一群代表性科學家,如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天工開物》)、李時珍(《本草綱目》)等,他們的著述匯集了大量科技術語,從農業到水利、從染色到鍛造、從植物到礦產。
自意大利人利瑪竇開始,傳教士們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熱衷于將記錄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書籍介紹到中國。通過音譯或意譯,誕生了一批新的術語,有些晦澀難懂,有些沿用至今。在利瑪竇的合作下,徐光啟把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原本》(前6卷平面幾何部分)翻譯后定名《幾何原本》,用“幾何”一詞替代“形學”,并推敲出“點”“線”“面”“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等詞匯。梁啟超對這本譯著的評價是:“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學問。”


從嚴復到傅蘭雅,晚清的科學譯介與術語規范
科學譯介之風在時局動蕩的清末依然盛行。提倡“信、達、雅”的嚴復把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譯作《天演論》,物競天擇的嶄新學說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一場震動;“北蔡南馬”之馬君武翻譯了達爾文的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種起源》),盡管自然選擇的科學觀點被當時的中國人誤讀為社會學理論,但這部生物學巨制構筑了新的世界觀,也無愧為科學寫作的范本。嚴、馬二人沿用了在語義的外延是根據概念反映事物屬性之間的關系而命名,本著內涵的語言特征而下定義,創造了一批準確反映科技內容概念的術語。
“事物之無名者,實不便于吾人之思索。”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中強調定名的重要意義,而科學定名的前提應該是準確和統一。1834年在廣州成立的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試圖確定標準,編輯科學名詞,但多數傳教士如合信(B. Hobson)、瑪高溫(D.J. Macgowen)、偉烈亞力(A. Wylie)等人在翻譯時依然各行其是,自成一派。以“科學”一詞為例,合信譯為“博物”,偉烈亞力青睞“格致”。面對陌生又拗口的名詞,讀者必須借助文末附錄的譯名對照表才有理解的可能。1872年,美國人盧公明(J.Doolittle)編輯的《英華萃林韻府》出版,最后一部分匯集了專門的譯名表,主要由從事科技翻譯的傳教士們提供。這些早期的科學術語涵蓋了力學、地質學、地理學、藥物名詞、解剖學與生理學、物理學、數學與天文學名詞、化學名詞等。
在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譯館的傅蘭雅(John Fryer)不是傳教士,他很早就意識到“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西人在華初譯格致各書時,若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則用者初時能穩妥,后亦不必大更改”。在他的積極推動下,翻譯館的同仁們經過多次討論,擬定了譯名原則,包括如何搜集中文已有之名、如何創設新名以及如何編輯中西名詞字匯。“館內譯書之中西人以此義為要務,用相同之名,則所譯之書,益尤大焉。”傅蘭雅對于名詞統一工作的重視漸漸就發展為一種共識。
1877年,在華基督教新教的全國大會在上海召開,決定成立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主要工作是為教會學校編寫教科書。一套初級、一套高級,兩者涉及的名詞理應一致,如何統一譯名的難題當即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會員們開始廣泛搜集中文譯著和原著,將其中的術語整理出來,以便后期編輯一份術語總表。譯者們在翻譯時需要把術語記下來,送到益智書會審查,若譯名不當,益智書會另行擬定并予以告知,若譯者堅持原來的主張,需要同時注明益智書會建議的譯名,以供讀者參考。根據分工,傅蘭雅負責工藝制造方面的內容,林樂知(Y.J. Allen)、偉烈亞力則分別編輯地理名詞與天文數理名詞。同為會員的狄考文(C.W. Mateer)在《教務雜志》上發表文章,批評一些譯者避免使用術語的做法,理由是每一門科學都有一套特定的術語,把科學知識及其概念準確輸入中國卻不用專業術語,這是不可想象的。

截至1890年,益智書會的譯名統一工作受人員變動的影響,進展緩慢,成果有限。同年,傅蘭雅在基督教新教士第二次大會上發言,題目是“科技術語: 當前的歧異與尋求統一的方法”。一些傳教士認為西方科學只能用西文表達,他不贊成這種觀點,指出問題的根源在于沒有充分掌握漢語,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也不夠。在介紹江南制造局的翻譯經驗時,傅蘭雅總結了科學術語的譯名原則:第一、盡可能譯意而非譯音;第二、不能譯意要盡量用合適的漢字音譯,建立一個音譯系統,基本詞素的音譯字要固定,用官話音譯;第三、新術語盡可能與漢語本來的形式建構一致;第四、譯名要簡練;第五、譯名應有準確定義;第六、譯名在各種場合都要符合原意,避免矛盾;第七、譯名具有靈活性。1891年與1896年,在益智書會的兩次會議上,譯名統一工作繼續得到了推動。前一次由出版委員會牽頭,制訂統一術語的章程,出現不同意見時,由委員會投票決定;后一次在傅蘭雅發表《中國科技術語展望》后,成立科技術語委員會。
在傅蘭雅赴美任教后,益智書會的科技術語委員會在狄考文、師圖爾(G.A.Stuart)等人的主持下開展術語統一工作,先后出版了《協定化學名目》與《術語辭匯》。《協定化學名目》有兩部分,一是命名原則,二是無機化合物的英漢名稱對照表。相比以往的元素譯名方案,《協定化學名目》給氣體元素加上“氣”字頭表示類別是一種進步,并且確定了幾個重要的化合物類屬譯名,比如acids譯為“酸”、salt譯為“鹽”、oxides譯為“銹”。此書的不足之處也是客觀存在的,尤其命名原則。《術語辭匯》作為第一部綜合性的科技術語詞典,收錄1.2萬余個名詞,包括算數、測量、航海、工程、聲學、冶金、動植物學、建筑、心理學、政治經濟學、國際法等50多個學科,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內容占比極少。全書英漢對照,按字母順序排列,盡可能收入每條術語的不同譯法(把編者推薦的那種放在首位),若干年后依然有再版的價值。
晚清中國還活躍著另外一家從事譯名統一工作的組織,這便是在上海成立的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亨特(S.A. Hunter)指出,完整、準確的名詞體系是科學知識進步的一個標志,要想把西方科學介紹給中國人,首先解決語言障礙問題,而翻譯就是一條有效的途徑。他要求傳教士醫生在統一科學名詞時,必須尋求中國學者的合作。在一些會員的呼吁下,統一負責醫學名詞工作的名詞委員會設立了。但由于認識不充分、制度不健全,前期基本只有高似蘭(P.B. Cousland)一人在堅持工作,名詞委員會陸續出版了《疾病名詞詞匯》(1894)、《眼科名詞》(1898)與《疾病名詞》(1898)等,后來增補師圖爾等人入會。1901年,名詞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審定通過了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與藥理學的名詞;1904年,第二次會議討論了病理學、內外科以及婦產科名詞;同年的第三次會議著重關注的是藥物學與細菌學名詞。審定、推廣標準化的譯名,促進了西醫在中國的傳播與教學。博醫會名詞委員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醫學詞典》,多次修訂,影響深遠。
應當指出的是,益智書會與博醫會均為西方人主導,面對科學譯名混雜的情形,清政府并非毫無作為。1909年,學部增設編訂名詞館,“惟各種名詞繁賾或辨義而識其指歸,或因音而通其假借,將欲統一文典,昭示來茲”。這是近代中國官方第一次大規模開展名詞統一工作。此前,學部審定科編撰了《物理學語匯》和《化學語匯》,兩書以中、英、日對照的方式分別收錄物理、化學學科術語近千條。編訂名詞館在成立后的兩年內完成了數學、心理學、植物學、植物生理學、辨學( 即邏輯學) 等學科的名詞統一工作。以數學為例,《數學中英名詞對照表》包含算學、代數、形學、平三角、弧三角、解析形學6份對照表,收錄約 1000 個名詞,基本覆蓋了當時中小學堂數學教學之所需。民國元年,編訂名詞館被撤銷,其編訂的各科名詞對照表被保存下來。
“對于科學名詞嚴加審定,以收統一之效;使夫學術有統系,名詞能劃一”
科技的革新帶來了觀念的更新,相比過去,民國時期的中國人越來越意識到術語規范工作的必要性。《獨立周報》在1912年刊發《論統一名詞當先組織學社》一文,指出歐洲科學名詞之所以統一是因為擁有各種學社,比如英倫的化學學社(The Chemistry Society)、蘇格蘭的地理學社(The Scotish Geographical Society)等,中國應該效仿之——“宜設立各種學社,附屬于中央學部。搜集文人學士,分門別類,以專科素有心得之人,共相討論,從事編譯,審定名詞,規定解說,刊成字典,為譯名之標準。如或譯名不備以及欠妥,則譯界中人,得將理由通告專社。倘得贊同,則可更正之,增刊之。唯不得各逞意見,私造譯名。”
志在科學救國的中國科學社把名詞審定的設想寫入社章,“編訂科學名詞,以期劃一而便學者”;其主辦的《科學》雜志亦在創刊例言中表明了名詞審定與科學事業的關系:“譯述之事, 定名為難。而在科學, 新名尤多。名詞不定, 則科學無所依倚而立。”考慮到“吾國學術之衰廢”的現狀,特別設立書籍譯著部,一方面翻譯書籍,另一方面審定名詞——“對于科學名詞嚴加審定,以收統一之效;使夫學術有統系,名詞能劃一,國中學子不必致力于西文而有所資。”
1918年,中國科學社總部搬回中國,加入從民間發起、由官方批準的科學名詞審查會(前身是醫學名詞審查會)。從1916年到1926年,科學名詞審查會吸納了10余個學術單位作為成員,包括中國科學社、中國工程學會、中華農學會、中華博物學會以及南京高師、武昌大學、同濟大學、廈門大學等。除了召集不同學科的權威學者,審定的程序也是非常嚴格,如《化學名詞·凡例》寫道:“有一名詞而費時至二三小時者,務使懷疑者有蘊必宣,然后依法表決。若兩名詞俱臻妥善,表決時俱不滿三分之二者兩存之。閉會后即以審定名詞印送海內外學術團體及化學專家征集意見,至下屆開會時,鄭重討論,加以最后之修正。”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大學院下設譯名統一委員會,管理科學名詞審查。王云五被聘為主任委員,其他委員有胡適、嚴濟慈、何炳松、秉志、郭任遠等。編譯學科名詞的工作起步沒多久,大學院改組教育部,名詞編譯事務劃歸編審處,調整后分為數學、物理、化學、醫學等18個小組。1932年,教育部成立國立編譯館,專門從事教科書審查、名詞編訂、辭典編訂、圖書編訂等,工作重點即為名詞審定。作為核心架構的審查委員會主要由相關學科最權威的學者組成,同時他們也具有名詞編譯審查的長期實踐經驗,如化學學科的曾昭掄、陳裕光、鄭貞文等人。
國立編譯館與各個科學團體展開合作(中國數學會、中國物理學會等),在編審名詞時確立了一套流程,如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的溫昌斌在《民國時期國立編譯館及其科學名詞審定工作》中所總結的,“先由國立編譯館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詞,參酌舊有譯名,慎于取舍,妥為選擇,形成草案。每種名詞的草案完成以后,分送各有關學會及各著名大學諸專家征求意見。復經教育部聘請國內專家,組織名詞審查委員會(相當于今天的名詞委)加以審定,然后請教育部公布。”到1949年為止,審定并出版了18種自然科學名詞,未完成的有29種,兩項統計均不含醫學名詞。“名詞術語的最終審定與統一,并不是國立編譯館努力的結果,編譯館在每門學科術語的審定統一中,往往僅起著聯絡與溝通的作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張劍在《近代科學名詞術語審定統一中的合作、沖突與科學發展》一文的觀點是,這項工作的成功取決于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水平,而這段歷史也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民間社團或者說民間力量如果缺乏政府強有力的支持,是難有所作為的”。

名詞委的成立與名詞審定、術語規范的中國之道
新中國誕生后,科學技術名詞的規范化工作很快被擺上了議事日程,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受委托,接管了民國編譯館擬訂的各類術語草案。1950年4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決案:在文委領導下成立學術名詞統一工作委員會,郭沫若擔任主任委員,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醫藥衛生、時事、文學藝術五個小組,分別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總署、衛生部、新聞總署、文化部對口負責。經過提名、遴選和審核,聘了150人,著名學者有嚴濟慈、華羅庚、錢三強、馮德培、茅以升、呂叔湘等。文委撤銷后,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設置名詞室,組織開展名詞審定工作。為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翻譯出版了“蘇聯科學院科技術語委員會推薦術語集譯叢”,包括《液體波動術語》(中俄)、《物理化學分析術語》(俄中)等。上世紀60年代,名詞室改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名詞編訂室,后來因為“文革”,工作基本中斷。其間,科學出版社在編訂各科詞書時,也完成了部分術語的審定與統一。
1978年3月,中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意味著科學春天的到來。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名詞編訂室的幾位工作人員聯名給方毅副總理寫了一封信,他們在信中匯報了近年來科技界名詞術語的不統一與不規范,影響新知識的傳播和學術交流,呼吁盡快恢復和建立科學名詞統一工作委員會。作為中科院的主管領導,方毅副總理在“兩科”(國家科委、中科院)的黨組會議上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由中科院牽頭,成立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從1979年到1984年,中科院副院長嚴濟慈牽頭組織籌建工作,主要是搜集材料,整理編譯館留下的術語類文獻,并積極開展調研活動、聽取各方意見。
重新出發,是為了走得更遠。1985年4月25日,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大會在京召開(1996年12月23日,獲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更名為“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方毅副總理在賀信中寫道:“自然科學名詞審定是我國科技工作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工作。盡快實現科學技術名詞術語的標準化、規范化,逐步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術語數據庫是發展科學技術,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和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生物學家朱弘復與語言學家陳原作為學者代表,在成立大會上分別做了一場報告。“先把已有的漢譯名詞收集起來,再根據抗戰期間清華大學把一本美國出版的新詞典所譯成的底稿,作為藍本,請了若干位專家,在北京討論審議,每周用一天時間,共花了3年才完成。有時可以因為不同意見,互相拍桌爭論,但終于獲得統一結果。”朱弘復回憶了自己在1950年代參加的名詞審定工作,“科學進展特別快,預料未來十年科學將會加速發展,所以新的科學名詞也隨之而迅速增加,而且可以是新生事物、新發現的原理,如何用漢文翻譯出來,困難一定會有的,須要我們努力去做。”陳原從嚴濟慈的舊文《論公分公分公分》談起,接著引申到當代術語學的一些原則,比如一詞一義、新詞不等于新字、用漢字音譯不可取以及約定俗成。他認為,“現代化過程要求科學名詞術語的規范化,而社會生活則進一步要求規范化要符合民族習慣和語言文字習慣。既要精確,又要清晰;既要創新,又要發揚民族傳統,同時不主張復古。”
大會后第2天,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并試行“審定工作條例”,明確4條審定原則:
一、自然科學名詞術語的審定與統一,應在廣義的自然科學范疇(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球科學、生物科學、技術科學、農業科學、醫學以及交叉學科等)內進行。
二、自然科學名詞術語的審定與統一,既要考慮中文構詞的獨特性和習慣,又要便于學術交流,對已約定俗成的名詞術語,一般不再強行改動,同時要注意抓好反映當代科學概念的新的名詞術語的審定和統一工作。
三、自然科學名詞術語的審定與統一,原則上由各學科名詞審定分委員會或審定小組負責進行。
四、自然科學名詞術語的審定與統一,主要依靠各有關學科的專家,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廣泛征求意見,集思廣益,力求使定名達到科學性、系統性和通俗性,而對個別有爭議者,經反復認真討論后,由名詞委員會最后作出決定。
萬事俱備,名詞委迅速布局,開始了探索。試點學科天文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用兩年時間完成了天文學名詞審定工作,為其他學科的嘗試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實踐經驗。1987年8月12日,國務院在《關于公布天文學名詞問題的批復》中指出:“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是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審定、公布各學科名詞是該委員會的職權范圍,經其審定的自然科學名詞具有權威性和約束力,全國各科研、教學、生產、經營、新聞出版等單位應遵照使用。”至1989年年底,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已經審定公布了《天文學名詞》《大氣科學名詞》《土壤學名詞》《地理學名詞》等9個學科的規范名詞。
“科技名詞的審定和統一工作是一個國家發展科學技術所必需的基礎條件之一,也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標志。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國內外科學技術交流日趨頻繁,盡快實現科學技術名詞的標準化、規范化,是我國科學技術現代化建設中的一項緊迫任務。”1990年6月23日,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國家教委、新聞出版署發布《關于使用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公布的科技名詞的通知》,要求各新聞單位要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宣傳名詞統一的重要意義,并帶頭使用已公布的名詞。編輯出版單位同樣如此,特別是各種工具書,應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規范詞,作為衡量該書質量的標準之一。
名詞委的審定工作始于自然科學的各個學科,1986年進入工程技術領域;2000年社會科學領域以語言學為先導,開始社科名詞的審定;2013年又增加了軍事科學領域。在組織各個學科名詞審定的同時,名詞委還積極推動了海峽兩岸的科技名詞協調與統一。海峽的分割,使得兩岸的科技名詞出現了嚴重的不統一,根據《兩岸科技名詞差異手冊》的統計,總體約為37.37%。
1993年的“汪辜會談”將“探討兩岸科技名詞統一”問題列入“共同協議”。1996年6月,天文學名詞對照研討會在安徽黃山召開,這是第一次兩岸工作會議。一個月后,名詞委組團赴臺參加航海科技名詞研討會。在兩岸專家的共同努力下,名詞委陸續出版的海峽兩岸對照本包括大氣科學名詞、昆蟲學名詞、藥學名詞、船舶工程名詞、航海名詞、動物學名詞、信息科技名詞等。在“鼓勵兩岸民間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的倡議下,兩岸科技學者決定共同編纂《中華科學技術大詞典》,并在2016年12月成立編輯委員會。作為首部全面收錄兩岸學科領域科技名詞的科技類綜合性詞典,《中華科學技術大詞典》計劃收錄兩岸100 個學科、約60 萬組科技名詞,實現大陸名與臺灣名、中文名和英文名的對照。
從1985年走到現在,名詞委在名詞審定與術語規范上摸索了一條中國化的道路,但有個與生俱來的短板始終沒能補上,即術語規范化的法制化水平很低。“我國科技名詞規范化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總體上欠缺,有關科技名詞規范化各項工作的開展基本上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其次,以行政手段推進科技名詞的規范化,特別是有關科技名詞的推廣和管理等也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行為。國家層面上法律依據的缺乏,加上與之相應的法律義務和責任制度的缺位,造成了我國的科技名詞規范化工作無法回應我國時代背景下提出的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等問題。科技名詞規范化工作所欲實現的社會效果也不明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楊知文看來,科技名詞規范化重要的保障和實現方式就是立法。
為保障科技術語的規范工作,名詞委在前些年設立研究課題,探討術語立法的可能性。參與課題的學者們在梳理海外術語立法、術語規范的現狀時發現:立陶宛有術語方面的專門法《術語數據庫法》,其他幾個國家開展了與術語相關的立法工作。以法國為例,規范了術語活動的主體與過程,保證了術語制定的權威性和執行效力,他們的術語立法得益于其語言保護政策,其語言立法促進了對術語的立法。再比如加拿大,特有的雙語環境和巨大的翻譯需求,對其術語學的發展和術語立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其語言立法主要體現在術語立法上。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宇明在《術語規范與術語立法》一文中強調:“術語立法與語言立法是相輔相成的,術語立法既反映著社會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認識,也是國家語言政策的重要體現;術語能否進入立法體系,與術語管理機構的工作狀況、術語學的發展狀況等有一定關系;術語立法不僅有利于科技發展和科技應用,有利于術語工作和術語規范,而且對教育和現代生活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百多年前,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為書名而傷神,“晨夕推敲,寢食俱廢,嘔心瀝血,面色憔悴”,后來就有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說法。翻譯書名尚且如此,作為學科基礎、用于規范表達的科學術語更應得到整個社會的重視與參與。學術的發展、知識的分享,一個前提就是規范表達。使社會明曉,供社會利用,做國家之學術,非各人之研究。
(摘自2月23日《文匯學人》。作者為該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