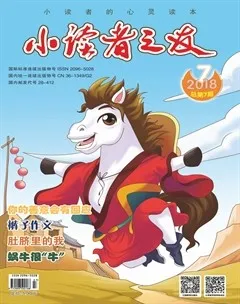壁畫
上公民課,金先生一進教室的門,沒有一個不低著頭竊笑的。因為他的大鼻頭上,不知怎的受了傷,貼著十字形的絆創膏。他的鼻頭本來大得可觀,如今加上了藥布和絆創膏,大得更可笑了。他上了講臺,也低著頭,把眼睛抬起來,向滿堂偷看一遍。看見沒有動靜,立刻翻開書來講“民權初步”一課,好像防人提出他鼻頭上的問題似的。
他正在講“集會的原則”,男同學馮士英離座,走到門邊的痰盂旁去吐痰。但當他吐好了痰回座的時候,后面幾排男同學忽然出聲地笑起來。坐在我鄰近的女同學,有的低著頭吃吃地笑,有的向門角里張望。我跟著她們的視線一望,但見教室的門正在慢慢地關攏,而門背后的墻黑板上顯出一幅線條很粗的可笑的畫:一個大頭的側形,鼻頭比頭大兩三倍,鼻頭尖上貼著一個十字形的絆創膏,鼻頭旁邊還有一個小人,手拿一把鋸子,正在鋸鼻頭。這顯然是金先生的滑稽肖像。大家對著這幅肖像公然地笑。
這畫的作者不知是誰;但把門關上,使它展覽在大眾之前的,無疑是吐痰的馮士英。
金先生看見大家對著門角笑,把頭向右轉,凝視了一會兒,臉孔一陣紅,但強裝笑顏,說道:“這算是我的肖像么?誰畫的?”大家低頭不說,也不笑。“畫得不像!我的鼻頭難道這樣大的?”大家笑不可抑。“我的鼻頭上生了一顆瘰(luǒ),就會好的,何必把鼻頭鋸去呢?”大家笑得更厲害。金先生問:“剛才吐痰的是誰?”沒有人說話,但有許多人旋轉頭去向馮士英看。馮士英低著頭看書,一動也不動。金先生向馮士英注視一會兒,接著說:“不要講了,上課吧。”級長就離座,拿揩拭把畫迅速地揩去。
下課后,金先生叫馮士英到訓育處,請他吃一頓“大菜”。圖畫教師秦先生也叫他到房間里,又請他吃頓“大菜”。馮士英吃了兩頓“大菜”回來,向我們裝個鬼臉,伸伸舌頭,說:“吃飽了,今天中飯也吃不下了。別的沒啥,就是對不起秦先生。原來大鼻頭下課就找秦先生說話,好像是秦先生叫我畫的,你看奇不奇?秦先生氣煞了,她說話時一直皺著眉頭。她說確是她教得不好,沒有預先關照我們不可用畫侮辱師長。這話使我很難受。我就向她認罪,并且表明誓不再犯。其實這并不算侮辱,你的鼻頭不是大得能夠鋸下段,算你運氣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晚上,我到秦先生房里去慰問,秦先生的氣還未消盡。她最初說馮士英太會吵;后來怪金先生多事,輕輕地對我們說:“他怪我,真是笑話。畫了他要圖畫先生負責,那么說了他要國語先生負責,打了他還要體育先生負責哩。況且這幅畫——我是沒有看見,聽他們說——也不算侮辱。卻是一幅‘漫畫肖像’。我覺得可以欣賞,用不著動怒。”
(節選自《少年美術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