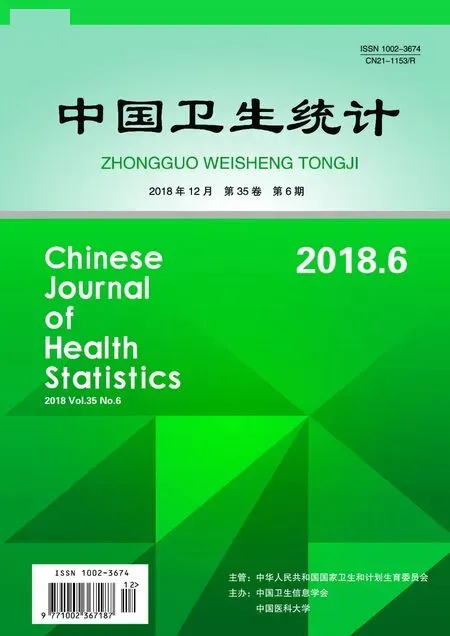孤獨感在中學生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的中介作用分析
錦州醫科大學護理學院(121000)
孫夢圓 劉 堃△
【提 要】 目的 探討孤獨感在中學生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的中介作用,為預防中學生抑郁癥狀提供干預措施。方法 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法,運用青少年孤獨感問卷、青少年社交焦慮量表和流調中心抑郁量表對1732名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抑郁癥狀與家庭關系、友誼關系和集體關系孤獨呈正相關(r=0.376、0.369、0.422,P均<0.01),社交焦慮與家庭關系、友誼關系和集體關系孤獨呈正相關(r=0.237、0.285、0.245,P均<0.01),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呈正相關(r=0.411,P<0.01)。在中介模型里,社交焦慮對抑郁癥狀正向預測作用有統計學意義(β=0.34,P<0.01),對孤獨感中的家庭關系孤獨、友誼關系孤獨和集體關系孤獨正向預測作用均有統計學意義(β=0.22,0.29,0.24,P均<0.01)。家庭關系孤獨、友誼關系孤獨和集體關系孤獨對抑郁癥狀正向預測作用均有統計學意義(β=0.28,0.06,0.22,P均<0.05)。結論 中學生孤獨感在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集體關系孤獨的中介作用最大。減少孤獨感體驗有助于預防中學生抑郁癥狀的發生。
中學生正處于個體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青春期,處于這一時期的個體由于生理、認知和情感等變化容易出現心理問題[1]。研究表明社交焦慮和抑郁往往伴隨而生,是青少年常見的心理問題[2-3],社交焦慮能夠增加抑郁癥狀的風險[4],是抑郁癥狀的一個重要預測因素[5]。Kessler[6]等人研究發現患有社交焦慮癥的青少年表現出抑郁癥狀的可能性是沒有社交焦慮癥的青少年的三倍。孤獨感是個體對自身的社會關系網絡不滿時產生的一種消極的體驗[7],有研究指出,社交焦慮與孤獨感密切相關,能夠顯著預測孤獨感[8],孤獨感與抑郁癥狀顯著相關[9]。
現有研究較多關注孤獨感或社交焦慮單一因素與抑郁癥狀的關系,鮮有研究將它們結合起來綜合考慮三者間的聯系。因此,本研究引入孤獨感作為中介變量,探討社交焦慮、抑郁癥狀和孤獨感三者間的聯系,并具體分析不同方面的孤獨情緒體驗所起的中介效應大小,通過對不同方面的孤獨感實施有側重性的干預,為有效預防和緩解中學生社交焦慮和抑郁癥狀提供理論指導。
對象與方法
1.對象
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法選取錦州市某所中學初一至初三的1732名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知情同意,可以進行有效交流者;排除標準:(1)不愿意參與者;(2)對問卷內容不理解者;(3)近期(2個月內)有經歷過負性生活事件(親人死亡、父母離婚等)或患重大疾病而導致情緒異常者。
2.調查工具
(1)一般資料調查表:包括年級、性別、是否為獨生子女、家庭狀況等。(2)青少年孤獨感問卷[10]:由西南大學楊巧芳編制,共16個條目(其中第1、4、7、8、9、10、11、13、14、15、16項反向計分),3個維度,分別為:家庭關系、集體關系、友誼關系,每個條目得分范圍為0~5分,總分范圍為0~80分,得分越高,孤獨感越強。(3)青少年社交焦慮量表[11](SAS-A):共18個條目,3個維度(害怕否定評價,陌生環境下的社會回避及苦惱,一般環境下的社會回避及苦惱),采用Liket 5級評分法,總分范圍在12~60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慮程度越嚴重。(4)流調中心抑郁量表[12](CES-D):共 20 個條目,其中 4 個條目為反向計分,包括抑郁情緒、積極情緒、軀體癥狀和人際關系4個維度,采用 0~3 計分,總分范圍為0~60 分,得分越高,抑郁水平越高。總分>16分,認為可能存在抑郁。
3.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為橫斷面調查,以班級為單位,施測前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統一指導語對整個問卷進行簡單說明,被試者采用匿名方式獨立填寫問卷,填寫過程中不允許相互交流,問卷統一發放并當場回收。回收問卷經檢查核對后,剔除無效問卷。
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Pearson相關性分析;運用AMOS 21.0和Bootstrap法對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并運用 PRODCLIN程序對特定路徑的間接效果進行估計和檢驗。
結 果
本次調查中的CES-D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09,SAS-A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99,孤獨感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數為0.866。
1.一般資料
共發放問卷2000份,回收問卷1900份,其中有效問卷1732份,有效回收率為91.16%。平均年齡(14.26±1.10)歲,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中學生的人口學特征分布情況
2.抑郁癥狀的得分情況
CES-D得分>16分者占48.7%。“持續癥狀”得分平均分為2.38分,19.0%的被試者“持續癥狀”分為0,62.3%的被試者“持續癥狀”分≤2。
3.社交焦慮、抑郁癥狀與孤獨感的相關性分析
中學生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呈正相關(P<0.01),社交焦慮與孤獨感的家庭關系、友誼關系及集體關系呈正相關(P均<0.01),抑郁癥狀與孤獨感的家庭關系、集體關系和友誼關系呈正相關(P均<0.01)。見表 2。

表2 中學生社交焦慮、抑郁癥狀與孤獨感的相關系數(n=1732)
*:P<0.01
4.孤獨感在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以社交焦慮作為自變量,抑郁癥狀作為因變量,孤獨感的三個維度家庭關系、友誼關系和集體關系分別作為中介變量,建立中介效應結構模型,結果顯示:χ2/df=11.354,RMSEA=0.077,GFI=O.964,AGFI=0.930,NFI=0.964,CFI=0.967,除χ2/df外,其余各適配指標均符合標準[13],但χ2/df值容易受到樣本量的影響,因而整體模型是否適配需要再參考其他適配指標,綜合參考其他適配指標該模型可接受。由圖1可知,社交焦慮對抑郁癥狀正向預測作用有統計學意義((β=0.34,P<0.01),對孤獨感中的家庭關系孤獨、友誼關系孤獨和集體關系孤獨正向預測作用均有統計學意義(β=0.24,0.29,0.22,P均<0.01)。家庭關系孤獨、友誼關系孤獨和集體關系孤獨對抑郁癥狀正向預測作用均有統計學意義(β=0.28,0.06,0.22,P均<0.05)。結果表明社交焦慮通過孤獨感的家庭關系孤獨、友誼關系孤獨和集體關系孤獨影響抑郁癥狀,孤獨感在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發揮中介作用。

*:F2:抑郁癥狀;FNE:害怕否定評價;SAD-New:陌生環境下的社會回避及苦;SAD-General:一般環境下的社會回避及苦惱
圖1孤獨感在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的中介模型(n=1732)
運用Bootstrap 法檢驗各路徑的效應關系,結果顯示:總效應、間接效應、直接效應的95%的置信區間均沒有包含0,Z值均大于1.96,說明中介效應有統計學意義。總體中介作用大小為0.164,其中集體關系的中介作用最大為0.073,家庭關系的中介作用次之為0.065,友誼關系的中介作用最小為0.0258。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35.42%。見表3。

表3 中介效應匯總表
討 論
調查結果顯示抑郁檢出率為48.72%,但是考慮到青少年個體比較敏感,情緒受環境影響起伏較大,且本次調查是在臨近考試前進行的,因此我們進一步分析了“持續癥狀”得分。“持續癥狀”得分是被試者選擇“大部分時間或持續(5~7天)”項的個數,通過對“持續癥狀”得分進行分析,可以避免暫時性抑郁情緒的影響,更加準確地得出是否存在持續性抑郁問題[14]。本次調查中,“持續癥狀”得分遠低于 Radloff得出的抑郁癥患者的“持續癥狀”平均分 8.83分[15],且進一步分析,19%的學生不存在持續癥狀,62.3%的學生持續癥狀≤2項,因此可知本次調查中的大多數學生不存在持續抑郁問題,明顯區別于抑郁癥患者。
造成調查中大多數學生抑郁情緒嚴重的原因可能是考試導致的緊張焦慮,個體壓力較大。
本研究顯示,社交焦慮可以正向預測抑郁癥狀。研究表明,在兒童和青少年中同時患有焦慮和抑郁癥狀是非常普遍的[16];Cummings[17]等人提出的焦慮-抑郁共同發病機制的多路徑分析模型表明,無論是抑郁癥狀或者抑郁癥其前期均有社交焦慮發生。此外,Gültekin 和 Dereboy[18]的研究也發現社交焦慮是抑郁癥狀的預測因素。以上均支持本次研究結果。本次研究還得出孤獨感也可以正向預測抑郁癥狀,這與大多數研究結果一致[19]。社交焦慮的個體不擅長社會交往和缺乏社交技能,這會增加同伴拒絕、排擠,甚至可能會遭受到欺凌[20],而所有這些負面的經歷又會導致失落感、人際關系不良,自卑和自我價值的下降,從而引起抑郁癥狀[21]。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孤獨感在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起部分中介作用。Klemanski[22]等人研究發現社交焦慮個體對自我情緒感知的能力低下,不能正常調節其情緒,而且在情緒的表達以及處理方面存在困難,這從側面說明了社交焦慮個體由于難以調節和有效處理其孤獨的情緒體驗,從而導致了抑郁癥狀的出現。
本研究結果驗證了中學生孤獨感在社交焦慮與抑郁癥狀間的中介作用,闡明了社交焦慮對抑郁癥狀的影響機制,對緩解中學生抑郁癥狀,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還提示孤獨感受里的集體孤獨是社交焦慮做用于抑郁癥狀的主要途徑,這對我們采取有針對性的、高效的干預措施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學校和老師應該注重觀察學生社交焦慮和孤獨感的表現,及時發現并及早干預,從而有效預防和緩解抑郁癥狀。學校管理者更應該多組織集體活動,鼓勵每個學生都要參與其中,同時教師也應該參與到集體活動中,杜絕和避免個別學生被集體排斥、隔離。此外,家長應采取民主性的家養方式加強對學生的情感支持,避免家庭孤獨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