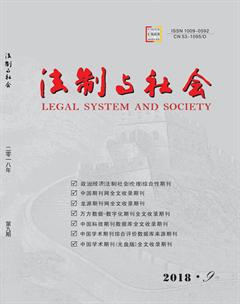從知識產權間接侵權角度構建“避風港”和“通知—移除”規則在電子商務平臺的適用
侍丹青 張毅菁
摘 要 我國引入了美國成文法制度里的“避風港”和“通知-移除”規則,但并未建立完整的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的體系與制度,因此該原則和規則在我國的適用,尤其是在電子商務領域的適用,面臨諸多的問題亟待解決。本文從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的角度出發,論述了美國成文法及司法判例中對間接侵權過錯責任的認定標準,并結合我國司法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和認識,為完善我國的相關立法提供方向和思路。
關鍵詞 知識產權 間接侵權 “通知-移除” “避風港” 電商平臺
作者簡介:侍丹青,亞馬遜法律顧問;張毅菁,上海圖書館戰略信息部副主任。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9.273
目前,我國已成為電子商務大國,有關電子商務領域的法律法規也層出不窮,其中包括借鑒了美國數字千禧年著作權法案在知識產權間接侵權領域的“避風港”原則和“通知-移除”規則。但是在我國的侵權責任、知識產權等立法領域,卻沒有任何間接侵權的概念或表述。 因此,根植于“間接侵權”理論的上述規則體系,在我國電子商務領域適用的過程中難免遇到各種問題。
一、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的歸責與免責概述
(一)間接侵權的歸責原則
王遷教授在總結各國立法與判例的基礎上,將知識產權間接侵權定義為“沒有實施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控制的行為(即沒有實施知識產權直接侵權),但故意引誘他人實施直接侵權,或在明知或應知他人即將或正在實施直接侵權時為其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以及特定情況下直接侵權的準備和擴大其侵權后果的行為”。 此定義涵蓋了間接侵權的所有情形,其中包括教唆侵權與幫助侵權兩種。鑒于兩者在“知道”的構成和過錯認定角度存在差異, 而本文僅討論電子商務平臺的幫助侵權情形,因此為本文目的,間接侵權的定義可歸納為:明知或應知他人的直接侵權行為,并提供幫助,或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侵害擴大的情形。
與知識產權直接侵權的嚴格責任不同,間接侵權這種“不受專有權利控制的行為”被認定侵權,必須具有可責備性,即行為人具有主觀過錯。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2〕20號)也明確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責任原則: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確定其是否承擔教唆、幫助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包括對于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明知或者應知。
(二)一般過錯責任原則
網絡平臺的過錯責任,應當是一般過錯責任,排除過錯推定的適用。以美國為例,在UMG v. Shelter一案中,美國法院引用Perfect 10, Inc. v. CCBill LLC 等案例的觀點,明確了權利人承擔證明網絡平臺對侵權行為“知道”的義務,以及明確具體的侵權內容并將其予以文字記錄的義務。 美國版權法僅規定了商標權的直接侵權,但是并未對未直接參與侵權行為的一方做出任何責任的規定。 在LoopNet一案中,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四巡回法庭確定了網絡平臺構成間接侵權的幫助侵權責任(contributory liability)(主要是在明知或應知的情況下仍提供侵權的便利或條件)與替代侵權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主要是指對侵權行為有控制能力但仍從侵權行為中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 而此原則在此后其他判例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我國的《侵權責任法》第6條對過錯設定的情形有兩種,即“知道”侵權行為的存在而未采取措施,以及在接到權利人通知后沒有及時采取措施。對立法中“知道”一詞的用法,根據孔祥俊教授的解釋,該用詞從第一次審議稿直到最終定稿,經歷了從“明知”到“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再到“知道”的改變,而目前的用詞“知道”,從法解釋學角度來講,包括了“明知”和“應知”兩種主觀狀態,所表達的是過錯要件。
電子商務平臺僅在事后承擔相應的注意義務,而不負有事前主動審查的義務,這個原則在美國法院的判決中已經達成共識(如本文所討論的案例均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遵循同樣的原則基本。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對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主動進行審查的,人民法院不應據此認定其具有過錯。網絡服務提供者能夠證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術措施,仍難以發現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不具有過錯。
(三)“避風港”與“通知-移除”規則
1997年,美國數字千禧年著作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以下簡稱“DMCA”)首次設定了“避風港”原則,即網絡平臺提供者在滿足下列條件的情況下無需承擔因用戶上傳著作權侵權內容而承擔責任:(1)對事實上構成侵權的內容或行為的存在沒有“明知(actual knowledge)”;(2)在不存在該“明知”的情況下,不“知道(aware)”存在構成明顯侵權的事實或情形,即“紅旗標準”(red flag knowledge);或者(3)在構成上述“明知”或“知道”的情況下,及時將侵權內容移除或斷開連接。該法典的上述定義在閱讀與理解上易于產生歧義,因此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在UMG v. Shelter一案中對此定義進行了梳理和重述:網絡平臺提供者不承擔責任的情形有二:(1)對事實上構成侵權的內容或行為的存在沒有“明知”,且不“知道”存在構成明顯侵權的事實或情形;或者(2)在構成上述“明知”或“知道”的情況下,及時將侵權內容移除或斷開連接。
美國的“避風港”原則是網絡平臺在一般過錯責任歸責原則之下的一種法定免責情形,因其有效地平衡了著作權保護與互聯網發展效率的關系,有利于促進網絡平臺與權利人達成合作,而被各國借鑒,并得以擴大到著作權之外的其他知識產權侵權領域適用。權利人可以通過發送通知的方式,抑或通過證明網絡平臺的“明知”情形,使得網絡平臺不再受“避風港”的保護,從而對其用戶侵權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不論是發送通知,還是證明“明知”,網絡平臺承擔責任的前提,均是該侵權行為已經明顯得足以使得正常理性人相信其存在,即“紅旗標準”。
在我國,國務院2006年發布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較為完整地引入了“避風港”、“通知-移除”和“反通知-恢復”規則;2009年,《侵權責任法》在第36條規定了網絡平臺對怠于行使權利人通知應承擔的責任,以及網絡平臺“知道”侵權行為存在的責任,標志著“避風港”和“通知-移除”規則在我國得以適用于著作權之外的其他知識產權領域。
二、 “避風港”和“通知-移除” 規則適用在電子商務平臺面臨的問題
在著作權領域,接到通知后的及時移除,有著客觀上的迫切性,因為侵權作品在互聯網上的傳播速度驚人,復制方法簡單,可以在極其短暫的時間內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另一方面,及時移除被通知鏈接及內容,客觀上造成被通知人經濟損失的可能性較小。但與著作權領域不同,在電子商務領域,更多發生的是商標權抑或專利權侵權主張,與前述短時間內的傳播與復制的情形有顯著不同,錯誤的移除,勢必會對電子商務經營者的經濟利益造成直接的損害。因此,“避風港原則”及“通知-移除”規則在電子商務領域的應用,存在下列問題亟待解決:
1. 通知的合格標準。《信息網絡傳播權條例》羅列了權利人通知的構成規范,但是該規范無法有效地定義在商標權、專利權侵權行為中何為合格的通知。例如,權利人是否需要提交商標證書,并提交身份證明文件以證明其對該商標權的專有權?是否需要對其商標權范圍與被控侵權產品是否在同一類別或類似群組做出說明?
2. 對通知的審查標準。《信息網絡傳播權條例》對網絡平臺接到權利人通知后的要求是“立即刪除涉嫌侵權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或者斷開與涉嫌侵權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鏈接”;《侵權責任法》也僅僅籠統規定了“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在實踐中,電子商務平臺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后,是否必須不假思索地立即采取刪除內容、斷開鏈接的操作,抑或是需要對所通知的內容進行審核,并據此作出相對獨立的判斷?
3. 反通知的合格標準及審查標準。作為“通知-移除”規則的一部分,被控侵權的產品或內容提供方可以提供反通知,以證明其不存在侵權的行為。那么,對該反通知,其合格標準以及審核標準是什么?在審核通知、反通知的過程中,電子商務平臺如何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并因此不承擔相應的責任?
4. “通知-移除”規則與訴前禁令、訴前財產保全等法定程序的關系。如果電子商務平臺對于權利人的通知不加以甄別、審核,一概采取移除或斷開鏈接的操作,是否客觀上賦予了權利人一種高于法定程序的救濟手段,從而客觀上造成了權利義務的不對等?
在電子商務領域,不僅商標權利人、品牌方存在控制銷售渠道、產品售價等超出知識產權主張之外的商業動機,更嚴重的是電子商務經營者的競爭對手,往往可以通過冒充商標權利人發送通知,以期通過電子商務平臺的移除義務,客觀上打擊競爭對手的銷售,實現自己的競爭優勢;更有甚者,會主動與電子商務經營者聯系,以撤回通知、挽救其經濟損失為條件,進行敲詐與勒索。
也正因此,楊立新教授認為,“如果沒有必要的審查,凡是被侵權人提出通知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就一律采取必要措施,有可能會侵害所謂的侵權人的合法權益,侵權人轉而追究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就要吃官司,承擔侵權責任。因此,必要的審查對網絡服務提供者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即使沒有法律規定,這樣的審查也只有益處,沒有害處。”對通知進行的審核,應當是“高于一般的形式審查,低于實質審查”。 也有觀點認為,通知移除規則在專利侵權領域的應用存在太多的問題,因此應當將“通知-移除-反通知”的順序規則,修改為“通知-反通知-移除”的順序規則,并通過立法規定電子商務平臺在“反通知”階段承擔一定的實質審查義務。 2017年底第二次征求意見的《電子商務法》草案,也在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規定電子商務平臺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后“應當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并在接到平臺內經營者的聲明(反通知)時,“應當及時終止所采取的措施”,意圖在二者之間維持平衡。
但是無論從何種角度,以何種方式對權利人的權利保護與電子商務經營者的競爭秩序進行平衡與保護,都沒有根本性地解決一個問題,即對權利人的通知進行審核并決定不采取措施后,以及對網絡經營者的反通知進行審核并決定恢復鏈接之后,若權利人最終通過司法途徑確定了其權利及其救濟途徑,那么電子商務平臺的責任認定究竟應當遵循什么原則。
三、問題的解決:“紅旗”的構成、“知道”的認定與“避風港”的排除
通過立法對電子商務平臺施加任何義務或授予任何權利,將電子商務平臺向任何一個指定的方向推動,都難以在知識產權保護與競爭秩序維護兩者之間實現平衡,從而實現最大化的社會利益。根本性地解決這個問題,實現前述目的,應當回到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的一般過錯責任認定角度,對電子商務平臺可能面臨的責任進行梳理和明確。
間接侵權以直接侵權的存在或即將發生為前提;但反之,卻并不能簡單地以直接侵權最終通過司法程序得到了認定,從而倒推認定間接侵權的存在。間接侵權的認定,仍然必須以過錯的存在為前提條件,而過錯的認定,在間接侵權角度而言,仍然需要對“明知、應知”或者“知道”加以認定。
(一)“知道”應為具體知情
不論是對侵權行為或產品的實際存在的“知道”,還是權利人通過發送通知證明的“知道”,都應當是對具體的侵權行為或侵權產品的具體知情,而不是對電子商務平臺存在侵權產品的一種籠統的知曉。在Tiffany v. eBay一案中,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認為,認定幫助侵權(contributory liability)的前提,是網絡服務商對其所提供服務可能被用于侵權的事實有高于一般的知曉,即應當對正在或即將發生侵權的具體產品信息有即時的知曉(contemporary knowledge)。此原則在其他案件中均得以認同和重述。因此法院最終認為,eBay對其網站上存在售賣假冒Tiffany產品的情況僅有“一般知曉(general knowledge)”,但并不知曉任何具體的侵權產品的信息,因此無須對該等假冒Tiffany產品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
在UMG v. Shelter 一案中,法院認為, “知道”的概念不應當是基于廣義的理解。著作權人會非常清楚地知道哪些材料是受到著作權保護的,而網絡平臺則無法立即作出此類判斷,更無法確定某些材料是否進入公有領域、經授權使用抑或在合理使用的范圍內。法官引用CCBill案中的論述 “不能將證明材料是否構成非法的責任讓網絡平臺承擔”,而據此認為被告Veoh對其網站上存在侵權材料的一般性認知,以及其所提供的服務可能被他人用于侵權的事實,并不構成“紅旗”。
(二)“知道”即“視而不見”
“視而不見”(willful blindness)并非美國DMCA的內容,而是普通法下的概念。根據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Viacom Intl, Inc. v. YouTube一案中援引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 334 F. 3d 643, 650 (7th Cir. 2003)一案中法院給出的定義,“視而不見”或者“有意回避”,是指“知曉一個高概率存在的事實而有意識地回避確認該事實”。法庭通過對DMCA的法解釋學角度論證了普通法下“視而不見”原則在知識產權間接侵權中得以適用的可能性,但指出,適用“視而不見”原則并不意味著網絡平臺有義務主動監測其網站,尋找可能的侵權行為;相反,“視而不見”是指對DMCA項下的具體侵權事實的知曉。 在Tiffany 一案中,法院同樣認為,“視而不見”等同于“知道”的原理并不新奇,但eBay對其網絡平臺存在銷售假冒Tiffany產品的事實存在一般的知曉,但該一般知曉還不足以構成其對侵權產品的“視而不見”。因此,普通法下的“視而不見”,等同于成文法下的“知道”,同樣是構成網絡平臺過錯的要件。
(三)“知道”與“紅旗”的關系及衡量標準
在證明網絡平臺“明知”侵權行為的存在或“知道”、“紅旗”的存在時,權利人的通知雖不是唯一,但卻是重要的途徑。DMCA明確規定,權利人或代表權利人發送的通知必須是書面形式,并且如果不符合本法的要求,不得作為認定網絡平臺“明知”侵權行為的存在或“知道”明顯存在的侵權事實。 如前文所述,“紅旗”是某種侵權行為的存在客觀上已經足以明顯的狀態;而“知道”則是電商平臺對侵權行為或侵權產品的該等客觀事實的主觀知曉狀態。在UMG v. Shelter一案中,法院對“明知”與“紅旗”的區別與關系做了充分的說明:二者的區別不是籠統知曉與具體知曉的區別,而是主觀與客觀標準的區別;換言之,“明知”是指網絡平臺是否實際上或“主觀上”知道某個具體的侵權行為的存在,而“紅旗標準”,則是指該網絡平臺主觀上所知曉的事實是否在“客觀上”已經足以讓一個合理的人覺得明顯。因此,為了證明網絡平臺是否“知道”、“紅旗”的存在,應當考察網絡平臺主觀上是否知曉該等事實的存在;而若證明該等事實是否構成“紅旗”,則應當從客觀角度出發,考察其是否足以使得一個正常人合理地相信侵權行為的存在。
“知道”與“紅旗”的這種主觀、客觀衡量標準的意義在于,只有網絡平臺同時滿足了主觀“知道”、“紅旗”的存在,并且客觀上該“紅旗標準”已經構成的情況下,網絡平臺的過錯才得以構成。在該案中,法院認為,非權利人的第三方用戶如果向網絡平臺發送任何關于侵權內容或行為存在的通知,應當經過“紅旗”測試。但是即便該通知通過了“紅旗”測試,證明了該侵權行為的明顯存在,該第三方的通知客觀上構成了“紅旗”,但如果權利人沒有對網絡平臺發送通知,而只是借助該第三人曾經的通知來證明網絡平臺對“紅旗”存在的知曉,則法院不認為權利人完成了對網絡平臺對該“紅旗”的知曉的證明責任。換言之,侵權行為即便已經符合“紅旗標準”,但若權利人未證明網絡平臺對此的“知道”,則網絡平臺并不因此承擔侵權責任。
(四) “知道”與“紅旗標準”在我國適用的可行性
我國的《侵權責任法》并未對“知道”的標準做出類似“紅旗標準”的設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對此的認識方向是明確的,其在新聞發布會中強調:“要根據信息網絡環境的特點和實際,準確把握網絡服務提供行為的侵權過錯認定,既要根據侵權事實明顯的過錯標準認定過錯,不使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一般性的事先審查義務和較高的注意義務,又要適當地調動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動防止侵權和與權利人合作防止侵權的積極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亦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考慮網絡服務的性質、侵權作品的知名度或明顯程度、網絡平臺是否采取了積極預防措施等因素,在此基礎上認定侵權事實是否明顯,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構成“應知”。石必勝法官將其在司法實踐中的標準總結為“高度蓋然性標準”,即“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等到能夠確認侵權可能性較大時再采取必要措施,在這種情況下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盡到了事后審查義務,不應被認定有過錯。
因此,“避風港”及“通知-移除”規則在電子商務領域的適用,應當回到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的角度來認識和定義。知識產權間接侵權適用一般過錯規則原則,僅當權利人有充分證據證明電子商務平臺存在過錯(即知道非常明顯的侵權行為或事實的存在)的情況下,才可以認定電子商務平臺的間接侵權責任。而權利人通過司法程序最終認定網絡經營者構成直接侵權的事實,并不構成電子商務平臺間接侵權的充分條件。
四、結論
我國的立法應當對知識產權的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做出明確的區分和定義,并引進類似“紅旗”的認定標準,對電子商務平臺的過錯認定和“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客觀明顯性做出進一步的明確和規定,以更好地適用“避風港”和“通知-移除”規則。
1. 在著作權侵權領域,應根據權利人對其權利的證明難度與網絡平臺對侵權行為的知曉難度做出平衡,若權利人難以使用客觀證據證明其權利的真實存在(例如攝影圖片、動畫設計等作品并未作著作權登記的情形),則網絡平臺應當在權利人描述清晰的情況下及時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權利人損失的進一步擴大。而對作品的商業化用途更為復雜的情況下,由于電子商務平臺對權利歸屬、作品相似性、許可狀態等存有疑慮,應當由權利人承擔進一步的舉證責任,而并非由電子商務平臺基于權利人的通知(此種情況下通常邏輯不清晰、證據不充分)立即將被舉報產品移除。
2. 在商標權領域,若權利人的商標標識與被舉報產品的商標標識構成相同或明顯的近似,并且權利人商標所屬類別與被舉報產品屬于相同類別或落入類似群組,則在客觀上符合了“紅旗標準”,進而可以判斷電子商務平臺的“知道”以及過錯。而對于存有爭議的情形,例如權利人的商標處于異議、被申請無效、涉及訴訟等不確定狀態時,或者權利人商標與被通知產品的比對無法得出明顯結論的情況下,以及權利人對“侵犯商標權”的主張缺乏相應的事實依據,更多體現為對被舉報商品的未授權或不認可時,則不應簡單地以通知符合形式要件為依據,直接認定電子商務平臺構成“知道”和過錯。此時,應當由權利人與電子商務經營者之間協商解決糾紛,而不宜將電子商務平臺排除于避風港之外。
3. 在專利權領域,由于對雙方證據材料的判斷需要極高的專業性,因此應當由權利人在第一時間承擔提供充分證據的義務。鑒于我國對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并不進行實質性審查,因此應當由權利人在提供專利權證書的同時,提供相應的檢索報告,以證明其專利權的新穎性,并由權利人在此基礎上完成專利權利的完整描述與證明。
因此,明確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的一般過錯責任及構成要件,可有效地敦促電子商務平臺對明顯的侵權行為及時采取措施,并且對可疑的惡意通知做出理性判斷,從而實現保護知識產權與維護良好競爭環境的平衡。
注釋:
2013年修訂的《商標法》第57條提及“故意為侵犯他人商標專用權行為提供便利條件,幫助他人實施侵犯商標專用權行為”,但并未規定此種侵權行為的性質或歸責原則。
王遷.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第5頁.
司曉.網絡服務商知識產權間接侵權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頁.
UMG Recordings, Inc. v. Shelter Capital Partners LLC, 667 F. 3d 1022 (9th Cir. 2011)。
17 U.S.C. ?01。
Costar v. Loopnet, 373 F. 3d 544(2004)。
孔祥俊.網絡著作權保護法律理念與裁判方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201.
UMG Recordings, Inc. v. Shelter Capital Partners LLC, 667 F. 3d 1022 (9th Cir. 2011), footnote No. 11。
楊立新、李佳倫.論網絡侵權責任中的通知及效果.法律適用.2011(6 ).
何瓊 、呂璐.“通知—刪除”規則在專利領域的適用困境——兼論《侵權責任法》第 36 條的彌補與完善.電子知識產權.2016(5).
Tiffany (NJ) Inc. v. eBay Inc., 600 F. 3d 93 (2010) 。
Viacom Intl, Inc. v. YouTube, 676 F. 3d 19(2d Cir. 2012)。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512(c)(3)。
Peter S. Menell, Mark A. Lemley, Robert P. Merg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2017, Volume II: Copyrights, Trademarks & State IP Protections, Clause 8 Publishing, 2017.
最高法召開《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有關情況新聞發布會,2011年12月21日。
石必勝.數字網絡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