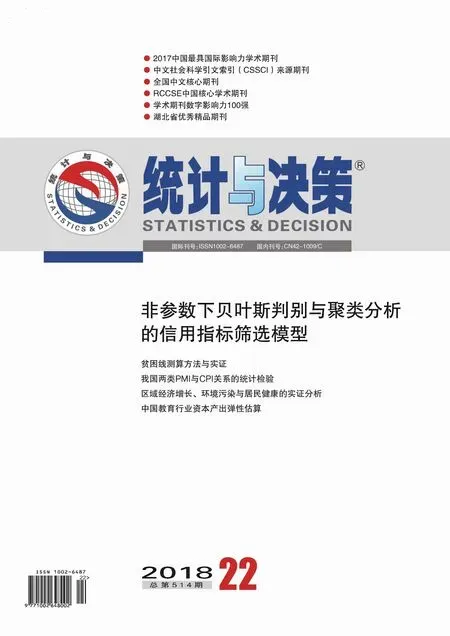中國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排放的平滑轉換研究
張 娜,李小勝
(1.蚌埠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2.安徽財經大學 統計與應用數學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0 引言
隨著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環境污染在短期內并沒有降低的趨勢。另一方面,隨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關注。那么經濟增長是否必然導致CO2排放量的增加?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簡稱 EKC)假說,經濟增長和環境之間存在“倒U”型的曲線關系,即經濟增長過程中環境質量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在經濟增長達到某一拐點時,環境污染會隨著經濟增長逐漸得到改善。中國經濟增長與CO2排放量之間是否存在EKC?這個問題對于正確看待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以及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措施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內外對EKC的實證研究比較豐富[1-6],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采用新的數據和新的計量方法來檢驗經驗假說。但是EKC從提出起就存在著的爭議。首先是對EKC思想的質疑,人類的發展是否注定要經過一個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在經濟增長沒有達到拐點之前,污染是否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其次,不同的污染指標和數據選擇得出的結論是不一致的。第三,很多學者對驗證EKC的計量方法合理性提出質疑。
縱觀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由于數據獲取問題,國內很少有文獻基于時間序列方法研究CO2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很多研究EKC的文獻,無論是面板數據模型、空間計量模型、還是時間序列模型采用的都是二次型或者是三次型,其實這種先驗的形式都是本質上線性的設定,應用線性形式的模型來檢驗非線性關系存在著一定的爭議;而且,很多模型在檢驗EKC時只考慮了收入,沒有考慮其他控制變量,有可能出現遺漏變量的問題。基于此,本文應用平滑轉換回歸模型,研究CO2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變化,彌補了以往研究采用線性的模型檢驗非線性關系的不足。并從時間序列的角度研究了CO2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從動態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長與污染排放之間的關系。此外,本文采用國際權威機構公布的CO2排放數據,研究年份為1978—2015年,擴充了研究期限。
1 模型構建和數據來源
1.1 模型構建
Ter?svirta(1994)提出的平滑轉換模型(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是平滑轉換自回歸模型(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on Model)的擴展,既可以應用自回歸模型也可以應用其他時間序列模型。平滑轉換模型更是門檻回歸模型的一般化形式,其回歸參數的變化不再是跳躍變化,而是一種緩慢轉換,與現實經濟的含義聯系更緊密。標準的有兩個極端機制轉換平滑模型可以用式(1)表示:

其中t=1,…,T,表示時期為T期,yt是一個標量,本文表示CO2的人均排放量對數,xt是人均收入的對數(當然也可以是很多變量),qt是轉換變量,用人均收入的對數表示,zt為外生變量,這些變量的系數不隨轉換變量的變化而平滑轉化,μ為截矩項,誤差項ut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常數的正態分布,g(qt;γ,c)是關于可以觀察的轉換變量qt的一個連續有界函數,取值范圍為0~1之間,0和1表明兩種極端的機制。Granger(1993)和Ter?svirta(1994)提出g(qt;γ,c)的函數可以用邏輯斯蒂形式表示:

其中,c=(c1,…,cm)′是m維的位置參數,也就是門檻值。γ>0是斜率參數,控制轉換函數轉化的快慢,數值越大轉換得越快,因為識別性問題,常設置γ>0,c1≤…≤cm。在位置參數個數為m=1時,公式(1)在代入g(qt;γ,c)函數在γ=0處一階泰勒展開,可以表示為:

對公式(3)可以將其重新記為:

在位置參數個數為m=2時,公式(1)在代入g(qt;γ,c)函數在γ=0處一階泰勒展開,可以表示為:

對公式(5)可以將其重新記為:

González等(2005)認為位置參數c取m=1或m=2足以具有代表性。當m=1時,當qt從小變大對應兩種極端機制,解釋變量的系數在β0和β0+β1之間平滑轉換,當γ→+∞ 且qt>c1時,式(2)成為示性函數,公式(1)變成門檻模型。當m=2時,由公式(2)和圖1可見轉換函數g(qt;γ,c1,c2)在 (c1+c2)2 處取得最小值,取值范圍在0~0.5之間,當qt取最小值和最大值時轉換函數均為1,此時模型存在三種極端機制,由于qt<c1和qt>c2的兩側體制是相同的,所以公式(1)仍然是兩體制模型。在γ→∞就變成三制度模型,兩邊的分布叫做外機制,中間的分布叫做中間機制。公式(2)在qt=c或γ→0時,轉換函數g(qt;γ,c)=0.5,公式(1)退化為普通的線性時間序列模型。qt為xt時,從公式(4)可以看出這種設定包含了二次多項式,公式(6)則包含了三次多項式。根據g(qt;γ,c)函數的性質,依據qt不斷變大的情況,當有β0>0和β0+β1<0成立時,表明存在EKC。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平滑轉化不需要事先確定轉折點,能分析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隨轉換變量變化而變化情況,同時這種模型是門檻模型、多項式模型和線性模型的一般化形式,也可對ECK進行檢驗,因此,本文選取這種方法進行實證研究。
1.2 數據來源
實證研究的主要數據是人均CO2排放序列的對數和人均收入的對數。對于CO2的排放,中國統計機構并沒有公布其數據。國外對全球CO2排放進行統計的機構主要有國際能源署(IEA)、美國能源信息部(EIA)、美國橡樹嶺實驗室(CDIAC)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等,國內主要有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和一些學術研究文獻[7]。但是國內機構和研究文獻估計的數據都是1985年以后的數據,很少有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

圖1 位置參數m=2時的平滑轉換函數
在比較國外幾個機構對中國CO2排放統計的數據時發現,美國橡樹嶺實驗室估計結果在1990年代前和其他機構相差不大,但是1990年代后,比其他機構稍低一些,將1990年代后期的數據與根據能源消耗的估計結果相比,發現兩者相差不大。所以本文直接采用美國橡樹嶺實驗室公布的1978—2015年的CO2排放統計的數據。經濟增長采用國內外常用的人均收入來表示。人均收入通常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GDP指代,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自2013年起統計方法和口徑發生變化,故選取人均GDP指代,通過人均GDP指數將其基期定為1978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本文還用到的數據包括了:經濟結構,用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技術進步,用不變價萬元GDP能耗表示;城鎮化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示;對外貿易,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表示,這些數據都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2 實證結果及分析
2.1 模型的非線性檢驗和位置參數的確定
為了檢驗采用平滑轉換模型是否合適,本文首先通過檢驗γ=0或β1=0是否成立來判斷模型(1)是線性還是非線性的,如果成立表明是線性模型,但是由于原假設下模型含有不能識別的參數,導致模型不服從標準分布,這個問題被 L ü ükkonen 等(1988)稱為時間序列的 Davies問題①即在原假設成立的條件下參數c、γ和β1是冗余參數,不會出現在待估計模型的似然函數中。。Ter?svirta 和 van Dick(2004)將g(qt;γ,c) 在γ=0 處一階泰勒展開,代替原模型中的轉換函數,構造輔助回歸模型進行檢驗。在一個位置參數時的一階泰勒展開下,檢驗是否具有非線性效應,就是通過檢驗公式(4)中β*1=0是否成立,當m取兩個或多個位置參數時的一階泰勒展開可以表示為:

那么檢驗模型(1)中γ=0,就相當于檢驗公式(7)中是否成立。如果本文將成立下,OLS估計的殘差平方和記為SSR0,公式(1)成立下的殘差平方和記為SSR1,可以構筑費歇爾(Fisher)F檢驗:

其中,m是位置參數的個數,k是解釋變量的個數。為了緩解數據異方差的出現,本文通過對人均收入和人均CO2排放取對數,來檢驗二者之間是否存在EKC,這里的轉換變量qt用lninct表示,即1978年價的人均收入的對數,lncot表示人均CO2排放的對數,將模型(1)修改為:

當采用人均收入的對數作為轉換變量,對人均CO2排放的對數和人均收入的對數之間關系進行檢驗,發現二者的線性假設被拒絕,從表1的第二列F值對應的P值可以看出非常小。其次,如果在沒有明確的轉換變量時,本文設置時間為轉換變量時(即時變平滑轉換模型),同樣拒絕了是線性的假定,但從F值的比較來看,本文認為采用lninct更為合理和意義明確。

表1 線性假設和位置參數個數檢驗的統計量
在上文的分析中得到人均收入與人均CO2排放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接下來還要確定模型轉換位置參數的個數,即位置參數是m=1還是m=2 。Ter?svirta(1994)利用輔助回歸(7),考慮位置參數m=3時,檢驗零假設,如果被拒絕繼續進行下列三個檢驗:,若拒絕的P值最小,則取m=2,否則m=1。上述的三個檢驗的統計量本文分別用F4、F3、F2表示,將其匯總放在表1的后三列,從表1中的統計量對應的P值可以看出F2最小,即取m=1。
2.2 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通過上文的非線性檢驗和位置參數的確定,本文認為采用非線性模型來擬合人均CO2排放和人均收入對數之間的關系,能較好地反映可能存在的突變結構。平滑轉換回歸是一個較好的選擇結構,但是上述的模型估計存在非線性數值計算問題。本文對位置參數c1在5.94~30之間采用步長為60進行格點搜索,將γ在0.5~1000之間采用步長為30進行格點搜索,得到初始的估計值分別為7.9821和19.6142,這時的殘差平方和為0.0735,較其他形式都小。在這些初始值得到后,本文對模型采用非線性估計得到最終的估計結果,記錄在表2中的模型(1)下方。從模型(1)的估計結果看,中國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發生一次轉換,由于所有數據都取的是自然對數,那么c1位置的數值大小為2930元左右,相當于1978年價格度量的2004年人均收入的水平,β0為0.3792,β1為0.0355,即人均收入對人均CO2排放的彈性在0.3792~0.4147之間,γ為21.386表明彈性從小到大轉換得較快,從R2看模型的整體擬合得較好。從β數值符號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人均排放之間并沒有出現下降的趨勢,收入的提高導致彈性逐漸增大,呈現一種單調上升的態勢,不存在“倒U”型假說。

表2 模型參數估計的結果
2.3 模型的擴展
目前實證研究EKC的文獻,很少在沒有考慮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單獨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Grossman和Krueger(1995)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是經濟增長對環境影響的三大效應;隨著對外經濟交往規模的擴大,不少研究認為貿易對一國的環境污染也產生重要影響。
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本文用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結構效應,預期這個因素的符號為負。用不變價萬元GDP能耗表示技術效應,預期這個因素的符號為負。最新的研究認為城鎮化是影響環境的重要因素,用城鎮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鎮化率,一般認為城市排放較農村多,所以預期這個因素的符號為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預期這個因素的符號為正。
根據上述考慮的因素,相應的將模型(9)擴展成模型(10):

其中,jgt表示結構變量,jst表示技術效應變量,czt表示城鎮化率,jckt表示貿易占GDP的比重。
首先,還是應用上文的非線性檢驗和位置參數個數的確定方法,直接用下頁表3列出檢驗的結果,通過表3可以看出無論是采用人均收入的對數作為轉換變量還是時間趨勢項,表3中的F統計量都是顯著的拒絕是線性的假定,從表3中的三個檢驗統計量F4、F3、F2看,F3對應的P值最小,根據理論取m=2。

表3 線性假設的統計量和位置參數個數檢驗的統計量
在得到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的對數之間非線性關系和存在兩個位置參數情況下。本文利用非線性方法,對兩個位置參數c1和c2在5.94~30之間,采用步長為60進行格點搜索,得到初始的估計值為7.5744和7.9821。對γ在0.50~1000,采用步長為30進行格點搜索,得到γ值為33.1305,這時的殘差平方和為0.0154,較其他形式都小。在得到初始值后,本文對模型采用非線性估計得到最終的估計結果,記錄在上文表2中的模型(2)下方。從模型(2)的估計結果看,中國經濟發展與CO2排放之間發生兩次轉換,由于所有數據都取的是自然對數,那么c1位置的數值大小為1940元左右,相當于1978年價格度量的1998年人均收入的水平,c2位置的數值大小為2757元左右,相當于1978年價格度量的2003年人均收入的水平。考慮這些因素后,這次估計的β0為0.70656,β1為-0.03234,β0的數值明顯變大,這主要是城鎮化這個因素的彈性比其系數更大造成的。γ為39.117表明彈性從小到大轉換的速度比上面的模型更快,從R2看模型的整體擬合比模型(1)好,在對實證結果的參數穩健性、ARCH-LM檢驗、Jarque-Bera檢驗等,表明模型(2)比模型(1)更穩健。從β0和β1數值符號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和人均排放之間并沒有“倒U”型假說所滿足的條件,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即超越轉換變量值時,由于β1為負,那么經濟增長對CO2排放的彈性是逐漸降低的,表明中國目前經濟增長是導致CO2排放的主要原因,但是這種效應的彈性是呈現逐漸降低趨勢。從表2中的模型(2)看出,經濟結構的變化確實導致CO2排放的減少,符號與預期的一致;技術效應并沒有導致排放的降低,這可能與能源消費回彈效應有關[8],即能源使用技術水平的提高,導致人們更多地使用能源,所以排放相應增加。城鎮化降低了CO2排放,與預期的符號相反,但系數不顯著,這一現象與多數的研究不一致。貿易對環境的彈性系數為0.31914,與預期的符號一致,且彈性較大,這與多數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3 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1978—2015年人均收入與人均CO2排放的時間序列數據,應用平滑轉換模型驗證二者之間是否存在EKC。實證研究發現人均收入與人均CO2排放并沒有呈現“倒U”型關系,但是發現了人均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三種機制:低收入機制,此時人均收入對二氧化碳排放彈性最低為0.67422;中收入機制,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漸上升到彈性為0.70656;高收入機制,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漸降低到彈性為0.67422。從上面收入機制對應的年份來看,在1998年前和2003年后,中國人均收入對人均CO2的彈性較1998—2003年小。可以理解為1998年以前的經濟規模較1998—2003年小,2003年以后的彈性變小是由于技術的進步較快,加之這一階段中國污染排放控制政策制定和實施比較有效,抑制了經濟規模擴大對環境的負向作用。
中國經濟增長與人均CO2排放并沒有呈現“倒U”型關系,這一結論與國內外的多數研究結論是一致的[9]。不存在EKC現象不能表明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下降是同步的,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是多樣的,加之這個時間段中國對外貿易的擴大,在世界產業轉移過程中,有可能發生污染的轉移效應。由于外部性導致全球性的污染難以治理,表明環境污染的減少并不是一個自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