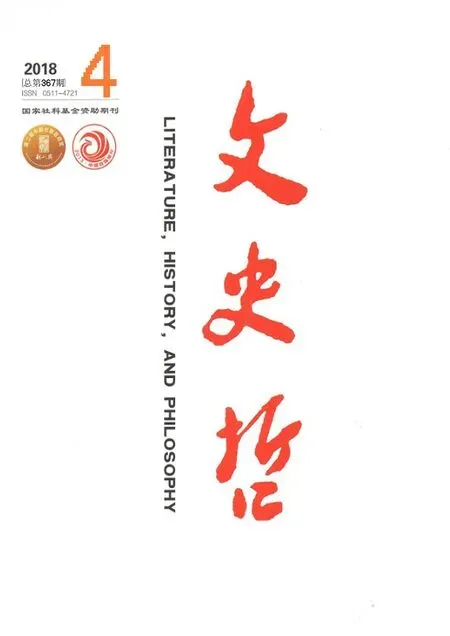《本事詩》“詩史”說與中晚唐學術脈動
吳懷東
“詩史”與“集大成”、“詩圣”幾乎被視作杜甫所專享的譽稱,也是杜詩被視作經典的主要條件或標志,其中“詩史”說出現最早,影響最大。關于“詩史”的基本內涵,今天的理解很明確,指杜甫詩歌的敘事性、紀實性,主要是其反映、記錄唐朝的軍國大事,特別是安史之亂對唐王朝的影響這一內容、性質和特點,其代表作就是“三吏”“三別”,馮至的解讀具有代表性:“杜甫的詩一向稱為詩史。我們現在也常沿用這個名稱標志杜詩的特點,它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的現實生活和時代面貌”*馮至:《詩史淺論》,《杜甫研究論文集》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59頁。,這也就是今人所稱道不已的現實主義精神。近年來,學術界對“詩史”的內涵及其演變進行了深入系統的討論,但對“詩史”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晚唐孟啟《本事詩》中的內涵、指向及產生背景沒有加以更多的關注和深究,同時,雖然目前學術界對《本事詩》的研究已很深入,卻也同樣幾乎沒有關注其中這一重要詩學概念。本文試圖進一步還原其“當代語境”,包括中晚唐時期的學術思想與詩歌創作背景,討論“詩史”的初始含義及后續轉變的關鍵環節,清理其中思想立場和詩學觀念,從而呈現杜詩經典化過程的復雜面相。
一
在現存傳世文獻中,“詩史”最早出現于南朝沈約《宋書·謝靈運傳》,但是,作為具有特定詩學含義的概念并被用來評價詩歌,則最早出現于晚唐孟啟《本事詩·高逸第三》所敘李白故事中。原文如下:
《本事詩·高逸第三》一共有三則記載,另外兩則比較簡單,記載的是晚唐著名詩人杜牧其人其詩軼事,而上述這段記載的中心人物是李白。孟啟圍繞李白高雅放曠的個性以及李白尚古、“薄聲律”、追求自由飄逸的詩學思想,敘述幾首詩歌的創作過程,其中所記事情之真偽其實還有待于討論,比如李白嘲笑杜甫的那首詩,學界一般不以為真。孟啟敘述李白的詩“本事”過程中,捎帶插敘杜甫其人其詩,一共提及四處:第一處,由賀知章對李白的評價,提到杜甫詩句“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對此事的反映。第二處,提到李白嘲笑杜甫“飯顆山前逢杜甫”那首詩,意在說明李白的詩歌理念,并批評杜甫“拘束”。第三處,提到杜甫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意在說明此詩比較完整、準確概述了李白前半生的曲折經歷。第四處,是對前述內容的總結和引申,孟啟認為杜詩不僅能記錄李白一生經歷,而且也準確呈現杜甫自己的經歷,最后引用“當時”人“詩史”之評以揭示杜詩性質和特點。
在孟啟的敘述中,李白是主角,杜甫只是陪襯,而且,孟啟刻意記錄李白嘲諷杜甫的那首詩*洪邁說:“所謂‘飯顆山’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容齋詩話》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2頁)仇兆鰲則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斷無此語,且詩詞庸俗,一望而知為贗作也。”(《杜詩詳注》附編),批評杜甫“拘束”,顯示孟啟抑杜的思想傾向。姑且不論孟啟對杜甫的態度如何,孟啟插敘杜甫其人其詩,顯然意在揭示杜詩某種性質和特點:杜甫的詩歌記載了“事”——李白之“事”和杜甫自己生平之“事”。孟啟此書記載的是他人詩歌“觸事興詠”之“本事”,而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及“流離隴蜀,畢陳于詩”之“詩”則直接記錄“事”。在孟啟的敘述中,其實隱含著對“詩史”指稱范圍的謹慎限定和具體內涵的簡略說明:從內涵看,“詩史”揭示了杜甫詩歌對個人日常生活的書寫及敘事性、寫實性特點;從范圍看,“詩史”并不包括杜甫的全部作品,只是杜甫“流離隴蜀”階段的創作。

二
“詩史”之出現被孟啟明確表述為“當時”——指杜甫生前或身后不久,由此可以斷定,“詩史”并非由孟啟發明*裴斐認為:“至于‘當時號為詩史’,一如劉昫所說‘天寶末甫與李白齊名’,并無文獻依據,實為史家稗官慣用的假托之詞。”(《唐宋杜學四大觀點述評》,《杜甫研究學刊》1990年第4期)可備一說。。雖然只此“孤證”,但是,以“史”論“詩”作為重要的文學評價顯然不是偶然行為,而是反映出中唐以來的學術思潮和文學思潮。
文、史之辨是一個歷史悠久且內涵復雜的話題*此問題涉及文(詩)、史關系這個中、外文化史上極其復雜的問題。《孟子·離婁下》記載孟子語云:“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詩經》中“頌”詩,所詠就是民族史。清代史學家顧炎武解釋說:“《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跡不可得而見,于是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后《春秋》作也。”(《日知錄》卷三)章學誠說:“六經皆史。”(《文史通義·易教上》)上述所論實涉及經學,包含著特定的政治內涵,對此錢穆有深刻而清晰的闡釋(見其《中國史學名著》對《春秋》的討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近代學人主要是從兩種不同的學術領域甚至文體立論,陳寅恪“詩史互證”的成功實踐更廣受世人推崇,而錢鐘書在《談藝錄》、《宋詩選注》、《管錐編》等著作中發掘了“史蘊詩心”的文化現象,其在詩史會通中特別強調詩的獨特性。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還從文化學角度提出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這已經不是討論具體的文體和表達,而是精神文化。概言之,詩、史關系既是復雜的歷史問題,也是深刻的理論命題,中國的文化與學術傳統是強調文、史不分,但是,本文所論是特定時段詩、史會通問題。。孔子說過:“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本文引文較多,為行文方便,常見文獻只夾注篇名,不再出注。其中“文”、“史”對舉,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不過,還不是兩種學術或文章類型的意義。從普遍共識和常識角度看,傳統史學關注社會,而文學則本能地關注個體經驗;史書強調客觀,而文學更關注主觀感受。從表面看,詩、史分屬形式與性質相差很大的兩種不同類型之文體。漢代以來,隨著社會文化活動的日益豐富和著述的增多,文體間的界限區分顯得十分必要和明顯*參見逯耀東:《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郝潤華:《六朝史籍與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這既反映在圖書編纂的分類和學術的分野(沈約《宋書·雷次宗傳》記載元嘉十五年分立儒學、玄學、史學和“文學”四科),更直接表現為文論家對文體內在規范越來越清晰的辨析(如《詩品》、《文心雕龍》、《文選》等),“文之與史,皎然異轍”(《史通·核才》)。章學誠說:“自東京以還,訖于魏晉,傳記皆分史部,論撰沿襲子流,各有成編,未嘗散著。惟是騷賦變體,碑誄雜流,銘頌連珠之倫,七林答問之屬,凡在辭流,皆標文號,于是始以屬辭稱文,而《文苑》《文選》所由撰輯。彼時所謂文者,大抵別于經傳子史,通于詩賦韻言。”(《文史通義·雜說下》)初唐史學家劉知幾正是在嚴文、史之防的基礎上討論史書諸文體的寫作規范*劉知幾《史通》論史學往往兼及文學,其實并不是認可“史之將文”,而只是著眼于史書也是文章而已,他們實際上是特別強調史書寫作與文學寫作的界限與分野。而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提出著名的“六經皆史”命題,彌綸文史、經史,強調“古無經史之分”(《丙辰劄記》,《章氏遺書》外篇三)、“文史不在道外”(《姑孰夏課甲編小引》,《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顯然,意不在討論文、史分野,而是論哲學與思想之“道”問題,其觀點是對顧炎武、戴震“經學即理學”的積極回應(詳論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內篇五之論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雖然他認可“文之將史”,但反對南朝以來史書對文學的過度學習,批評說:“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史通·載文》),還批評說:“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史通·論贊》);他贊美《左傳》之文對文學手法矜持的學習:“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史通·雜說上》)。應該說,對文、史分野的刻意強調,是當時對兩類文體特點認識的深化,也有力地促進了兩種文類的發展。文學研究界歷來注意到唐代詩、賦以及駢文創作的繁榮,卻忽略了唐代史學也相當繁榮這一重要歷史事實。據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研究,按照傳統目錄學的分類,史部“雜史”、“雜傳”以及“小說”數量極大,其中敘事類的筆記小說所占分量最大*參見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十一章“史學范圍進一步擴大”之論述。。
杜甫是否強調詩、史之辨?眾所周知,杜甫詩歌也和其他詩人的詠詩史一樣詠嘆前代、前朝歷史事實,顯然,這不構成杜甫詩歌的獨特性。杜甫具有很強的歷史感,其核心是歷史的無限性與個人生命有限性的矛盾,如其詩曰:“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百年歌自苦”(《南征》)等,不過,這種歷史感與史學書寫意識是兩回事。作為生活在劉知幾之后的詩人,杜甫對文、史邊界的理解十分明確、清晰,如其云“文包舊史善”(《八哀詩·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十五富文史”(《送李校書二十六韻》),他反復贊美秉筆直書、實錄的史臣書寫,“直筆在史臣”(《八哀詩·故司徒李公光弼》)、“波濤良史筆”(《八哀詩·故右仆射相國張公九齡》)、“不愧史臣詞”(《哭李常侍嶧二首》其二)等。從杜詩有限的用例中還可以觀察到,杜甫史學意識的核心就是“直書”,并沒有涉及史學、史書其他問題。雖然杜甫感嘆過“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貽華陽柳少府》),但是,生當盛唐詩歌大盛之際,杜甫一生甘作官員詩人而不是史學家的選擇是自覺而強烈的,他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人詩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他對自己的詩歌才華頗為自負:“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通過“鼓吹六經,先鳴諸子”(《進雕賦表》)以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人生理想。杜甫早年有詩謂“獨立蒼茫自詠詩”(《樂游園歌》),后來在《發秦州》詩中的“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兩句一語雙關,都包含著在歷史的長河和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堅持自己信念和詩歌道路之意。這也是盛唐時代詩人普遍的人生道路選擇和人格心態。杜甫詩歌畢竟是對自己時代生活的呈現,在杜甫生前、身后直到孟啟之前,是否有人從詩、史會通的角度評價杜詩?對其他詩人是否有類似闡發?從現有文獻看,杜甫生前就有人贊美其詩,并在身后逐步獲得與李白比肩的崇高地位,如“大名詩獨步”(韋迢《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新詩海內流傳遍”(郭受《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黃絹詞”(任華《雜言寄杜拾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等,卻沒有發現以“詩史”或類似概念評價杜甫的文獻證據。
三

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
孟啟喜好詩歌和詩人,此書編寫目的就是介紹詩人及其詩歌的“本事”,以增加對詩歌的理解、對詩人精神魅力的感悟。書名“本事”及前述對杜甫的評價中所使用的“推見至隱”等概念,皆來自史書之祖《春秋》。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評論云: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司馬遷撰,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1984年,第3037頁。
《春秋》是“本事”,《左傳》等則顯示了《春秋》的“隱諱”。《漢書·藝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陳國慶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4頁。
東漢桓譚《新論·正經第九》亦圍繞《春秋》及《左傳》立說:

因此可以說,孟啟對“本事”的強調以及“詩史”概念的引用,正是繼承儒家經典《春秋》之傳統。
為何孟啟獨對《春秋》異常關注?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及其思想就是治國指導思想,即使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經學治國之傳統亦未衰歇。李唐王朝生當民族大融合之際,文化開放,思想多元,儒家經典的指導地位亦未改變,但是,唐朝經學相對其前后諸朝而言整體上并不興盛,作為經學所依附的官學體制衰微,科舉考試中對側重考察詩賦能力的進士科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對明經科的重視,經學不如文學和史學活躍。正因為如此,當安史之亂平定后,當時少數先知先覺者的反思,往往追源于經學之衰微、儒學之不興;中唐時期,元、白倡導儒家美刺詩學,韓愈、柳宗元復興儒學道統,經世致用,相對于唐代前期之經學變化明顯:“蓋自大歷以后,經學新說日昌。”*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重印本,第105頁。現代學者蒙文通說:“唐初之學,沿襲六代。官修五史,皆斷代紀傳一體,故《漢書》學,于時獨顯。與‘從晉以降,喜學五經’者異也,徒能整齊舊事,無所創明。而中葉以還,風尚一變,則以唐之思想、學術、文藝之莫不變也。”*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頁。在代表中國思想文化轉型的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之思想運動中,《春秋》學具有獨特的地位。由啖助開創,趙匡開創,經陸淳的發揮、傳播,《春秋》學超越其他諸經在中唐大盛,陳弱水發現中唐“最受偏愛的對象仍然是《春秋》”*陳弱水:《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5頁。,有學者指出:“元和之后,《春秋》學已成為一個學術中心。”*查屏球:《唐學與唐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9頁。作為經學革新的一部分,中唐《春秋》學的異軍突起、異常興盛,實牽連著中唐復雜的社會政治改革運動——這也是一場重大的思想學術文化活動,當時最優秀的政治家和文學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白壽彝主編,瞿林東著:《中國史學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9頁。。總結經驗、解決現實問題是經學以及史學的基本功能,杜預說《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司馬遷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才寫作《史記》,李翰指出杜佑《通典》不同于一般“文章之事,記問之學”,是“參今古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于今”(《通典·序》)。可見,是中唐朝廷之孱弱、藩鎮之割據,刺激了《春秋》學及史學的興盛,因為其“尊王攘夷”的思想滿足中唐重振、鞏固李氏中央王朝統治的時代需求,而本來就具有深厚的史學傳統,《春秋》學的興盛則刺激中晚唐史學之發達,它們又形成合力,共同影響著當時的文學活動。
總之,安史之亂導致的政治動蕩引發政治革新運動,進而引發思想史的異動、經學的轉型與《春秋》學的興盛,《本事詩》對《春秋》的引用及其史學意識正顯示了這一重要學術動態。明確《春秋》學及史學對文學、對詩歌創作的具體影響,可以進一步討論孟啟“詩史”說的內涵。
四
文、史獨立蓬勃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著互相學習和借鑒。中唐《春秋》學和史學的發達對當時寫作活動的影響極為復雜,大而言之有兩個層面:
首先,是“文之將史”現象——筆記小說的大量涌現。
中唐時期出現大量文學化的雜史、雜傳以及筆記小說,而作為敘事文學的唐傳奇也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繁榮,魯迅云:“作者蔚起,則在開元天寶以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代之傳奇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6頁。,“惟自大歷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術文苑”*魯迅:《唐宋傳奇集·序例》,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第2頁。。陳寅恪也說:“中國文學史中別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于貞元元和之世。”*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頁。程毅中《唐代小說史》更明確指出:“小說則以中唐為高峰。”*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19頁。
正是在此潮流中,關注詩人生活及其創作過程的筆記小說開始大量出現。王運熙、楊明認為“孟啟《本事詩》之作,也反映了唐人對詩歌的喜好,同時與唐代小說的發展頗有關系”,“《本事詩》是詩與小說的結合,反映了唐人對于詩歌和小說的愛好,反映了唐人在傳誦詩作的同時津津有味地傳道有關故事的一種風氣”*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36頁。,而其他小說中詩人詩歌具體創作過程的類似記載亦所在多有*南開大學余才林先生有著作《唐詩本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他將“本事詩”作為一種文體,本人不能茍同。。前述孟啟對李白故事的記載,既說明李白詩歌創作的“本事”,也說明杜甫詩歌的“本事”。《本事詩》序言中明確說:“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略之。”孟啟刻意強調紀實,正是史學傳統影響的最好寫照。
其次,詩歌敘事性、日常性的增強。
中晚唐不少詩歌與傳奇小說配合傳播,反映出作家與讀者閱讀興趣對于外在事實本身的關注。中唐表現現實社會生活的敘事詩大量出現和詩歌的敘事性、寫實性,這是最值得關注的中唐文學現象。劉學鍇先生曾結合中唐絕句相對于盛唐的變化闡述變革的具體內容:“盛唐絕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較少敘事成分;到了中唐,敘事成分逐漸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為絕句的習見題材,風格也由盛唐的雄渾高華、富于浪漫氣息轉向寫實。”*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82頁。具體而言,中唐詩歌敘事性、紀實性的增強有多方面表現,如題目的加長,詩序的大量出現,詩歌詠嘆小說故事,詩歌開始大量表現個人日常生活與世俗社會生活,詩歌風格趨向尚俗務盡,不一而足。
追溯一下此前的詩歌意識,即可看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孟啟詩歌認識所發生的新變。“詩言志”(《尚書·舜典》)是古老的傳統。陸機說:“詩緣情而綺靡”(《文賦》)。鐘嶸說:“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詩品·序》)詩以抒情,這是杜甫之前的創作慣例,是對詩歌內容的規定。自從東漢文人自覺介入詩歌創作以來,詩歌的獨特性就是詩人和學者不斷試驗與探索的問題,詩歌形式上的特點和創作技巧不斷被探索、被發現,從曹丕提出“詩賦欲麗”(《典論·論文》)到南朝永明體,詩歌逐漸走上律化的道路;到了初唐,在沈、宋等人手中完成這一歷程。這是詩歌認識的基本歷程。可是,在《本事詩》中,詩學觀念發生變化。《本事詩》不僅關注詩歌的抒情功能,還關注引發詩人情感反應的“事”,更注意到詩本身之中的“事”:他不僅以杜甫詩歌為例,說明詩歌能比較全面呈現所感之“事”,他還直接引用幾條散文性的詩序,如“情感第二”劉禹錫游玄都觀、“情感第三”元稹贈黃丞等五條,更直白地陳述詩歌所詠之事,由此可見孟啟已注意到詩歌的敘事性、紀實性功能,特別是對作家個人日常生活的反映*在此存在一個悖論,我們認為具有很強政治性的經學、史學著作《春秋》影響了中唐文學的敘事性,可是,中唐詩歌敘事內容最突出的卻不是政治,而是世俗生活、日常生活。中唐詩歌尚俗、務盡(詳論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之內容,主要在此。孟啟“詩史”說所強調的不僅是敘事性,而且指向杜甫詩歌對詩人個人日常生活的再現。可見,中唐詩歌敘事性的生成顯然不是單一來源,《春秋》的影響只是因素之一,中唐社會結構的變化、文人人生理想的變化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關于中唐文人趨向現實(比如白居易《與元九書》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一歷史特征,在唐宋轉型論中有深入探討并形成共識,在此不贅。當然,《春秋》學的“微言大義”傳統對孟啟撰寫《本事詩》也有影響,如同中晚唐出現的大量緬懷盛唐歷史的筆記小說一樣,這也是孟啟對前代往事的追懷,其中也隱含著他對詩人不幸命運以及所處唐懿宗、僖宗父子時代政治混亂現實的感慨,《新唐書》就評論云:“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支。”(《新唐書》卷九《懿宗、僖宗紀》)這樣的現實正是敘事性很強的晚唐詠史詩同時大興的共同的社會基礎。孟啟《本事詩》將前代詩人軼事分為七類,“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大多反映了詩人浪漫的個性和不幸的遭遇,既包含著對詩人的同情,也隱含著現實針對性和政治立場,前代詩人的自由灑脫正是自己時代動蕩的對照,另如其序言介紹他撰序的時間是“光啟二年十一月”,并刻意說“大駕在褒中”,這一補述實亦涉及晚唐亂局,流露出作者的感慨:黃巢起義后,李氏朝廷已經徹底喪失對局面的控制,此時,宦官寵臣田令孜挾持唐僖宗為避各地節度使對長安的討伐而逃到漢中,邠寧節度使朱玫便將襄王李煴挾持到長安,立為傀儡皇帝,改元“建貞”。含蓄地表明了他的現實關懷,也正是作為“春秋筆法”的“微言大義”。。
杜甫詩歌的“詩史”性質和特點,正是孟啟立足于中唐文學現實、學術思潮和詩歌觀念進行溯源的意外發現和追認。在孟啟看來,杜甫“流離隴蜀”之作,具有紀實性、敘事性和日常性、個人性等特點。乾元二年(759),年近半百的杜甫“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年初,從東都洛陽回到華州,“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題》);七月,辭去華州司功參軍之職,攜家西去秦州,又輾轉到達同谷,然而,到同谷后發現,預計中的安頓無法實現,不得不在歲末天寒地凍之中再出發,翻山越嶺,于年底到達成都。杜甫攜家帶口,“流離隴蜀”,艱苦備嘗:“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發秦州》),以至于“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男呻女吟四壁靜”(《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二),一貫堅強的詩人也情不自禁產生質疑和感慨:“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四)“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空囊》)。這一年是杜甫生活的重要轉折,也是杜甫詩歌創作的重要轉折,馮至就說:這一年確是杜甫一生中“最艱苦的一年”,但是,其詩歌創作,“尤其是‘三吏’‘三別’以及隴右的一部分詩,卻達到了最高的成就”*馮至:《杜甫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35頁。。在“流離隴蜀”期間,杜甫一共創作了120多首詩,連章組詩更多達10組52首,其中還有五言律詩組詩,這種一氣呵成、酣暢淋漓的組詩形式顯然配合豐富、集中的內容表達的需要,宋人就已注意其內容的特殊性,葛立方云:“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采梠,哺糒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于詩,皆可考也。”(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這些詩充分再現了杜甫在秦州、同谷生活的艱難,而且刻畫了秦州的風俗民情以及從同谷到成都道中山川的奇險、壯麗。劉克莊說:“唐人游邊之作,數十篇中有三數篇,一篇中間有一二聯可采,若此二十篇(按,指《秦州雜詩二十首》),山川城廓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矣。網山《送蘄帥》云:‘杜陵詩卷是圖經’,豈不信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八)從秦州到同谷、從同谷到成都道中的兩組紀行詩最令人矚目,蘇軾說:“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引)王得臣說:“杜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考。”(《麈史》卷中)北宋佚名學者說:“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為先后,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引《少陵詩總目》)朱熹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四○)清代學者李因篤也說:“萬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險,歲月之暄涼,交游之違合,靡不曲盡,真詩史也。”(楊倫《杜詩鏡銓》卷七引)上述學者所強調的組詩形式、偏重客觀紀實并對秦隴山川勝景、風土人情和苦難生活加以生動呈現——“既是山水圖經,更是流民長卷”*陳貽焮:《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36頁。,構成“流離隴蜀”道中創作比較突出的特點*當然,在杜甫“流離隴蜀”期間的紀行組詩,描寫外在景物與再現詩人行止、客觀描寫與主觀抒情較好的結合。明人江盈科說:“少陵秦州以后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換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獨能象景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乃為真詩人真手筆也。”(《杜詩詳注》卷八引)清人蔣金式說:“少陵入蜀詩,與柳州柳子厚諸記,剔險搜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成此奇地奇文,令讀者應接不暇。”(《杜詩鏡銓》卷七引)莫礪鋒先生分析得很透徹:“杜甫的山水詩以詠秦隴、夔巫山川的為最多最好,因為杜甫的人品胸襟和審美傾向都使他對于雄偉壯麗的事物有著特殊的愛好,而就山水而言,只有秦隴、夔巫那樣雄奇偉麗的高山巨川才能真正撥動杜甫的心弦,從而發出最和諧的共鳴。”(《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42頁),與以往紀行詩偏重抒情不同,也與杜甫此前此后創作偏重抒情和表達社會政治關懷大不相同。這些詩歌受到后代學者的注意和肯定,既是對組詩形式的發現,也是對其獨特紀實性、敘事性、日常生活性的認可,這種認可之中其實包含著對山川壯美之欣賞和對杜甫所敘個人日常苦難生活的深深同情——這也可能是孟啟和后代學者關注杜甫“流離隴蜀”詩歌潛在的根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所敘,也偏重強調李白政治上的不遇與人生道路的艱難)。李因篤所說,也正是孟啟“詩史”說的具體內涵。孟啟的引用,是否符合事實是一回事,比如按照日常性標準理解,杜甫在草堂以及夔州時期創作的詩歌似乎更真切,而孟啟的理解和刻意強調則是另一回事,這正體現了孟啟及其時代的觀點。
孟啟認定杜甫特定階段詩歌的“詩史”特征,既是表明一種文學事實、詩歌新變的生動存在,也是對這種事實和新變的理論發現和詩學認定。從第一方面說,就是杜甫詩歌的創新和中唐以來詩歌的新變。時代的巨變帶來詩歌的變化,杜甫生活在唐代盛衰之際,獨特的時代環境和他個人生活經歷的豐富性和曲折性,使得他在詩歌創作上突破盛唐流行的風氣,開始很多探索和創新,他將目光從歌頌理想轉向再現現實,詩歌的紀實性和敘事性的增強,并再現個人日常生活細節,就是其創變之一。白居易說:“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受到史學以及杜甫經驗的影響(這也是杜甫地位在中唐迅速提升的原因之一),中唐詩歌的敘事性、紀實性進一步增強,詩歌的關注點從主觀偏向客觀,從表現偏向再現,從抒情轉向敘事紀實,從政治書寫轉向個體生活再現。從第二方面說,《春秋》學概念的使用、“詩史”概念的使用,表明孟啟基于中唐以來日漸高漲的史學思維,開始自覺從理論上觀察、理解并描述從杜甫開始到中唐詩歌領域廣泛流行的創新和變革。
總之,孟啟引用“詩史”評價杜詩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存在著深刻的政治、學術、文學背景。孟啟對“詩史”的使用,也是古代政治、經學、史學與文學密切互動的一個生動案例。
五
孟啟之后,宋人廣泛使用“詩史”這一概念,理解卻發生變化,在此亦作梳理、補述,以見其演變。
宋人以及宋代之后從敘事性、紀實性的角度對杜甫詩歌“詩史”屬性的發揮、對唐史在杜詩中的細致、豐富而準確的呈現(其中最受贊美的是“補闕”)*宋代以來,杜詩研究中以史證詩成就最杰出的無疑是錢謙益的《錢注杜詩》,錢氏亦以此自負,茲不詳論。以及在詩學中的影響,不少學者已作出大量、深入的闡釋*日本學者淺見洋二《文學的歷史學——論宋代的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及“詩史”說》、《“詩史”說新考》、《關于詩與“本事”、“本意”以及詩讖》對于宋代部分所論深入,見氏著《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金程宇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而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對于具體文獻的梳理、考證更為精細。此外,孫微《清代杜詩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第二章第二節也進行了簡明的歸納。,有的學者甚至據此將杜甫命名為“自傳詩人”*參見謝思煒:《論自傳詩人杜甫》,《文學遺產》1990年第3期。清代學者浦起龍甚至說:“少陵為詩,不啻少陵自為譜矣。”(《讀杜心解·目譜》),顯然,這些基本上是對孟啟“詩史”觀念的承襲,這里暫不置論,我們所關注和強調的是“詩史”內涵的增加、豐富及指稱對象的變化——“詩史”說內涵改變為今日流行之理解。
《舊唐書·杜甫傳》只是原文照搬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以評價杜甫詩歌,并沒有注意“詩史”概念。從現有文獻看,“詩史”最早被成書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書·杜甫傳贊》所沿用。張暉考察指出,“整個宋代的‘詩史’說,定義雖然十分繁雜,但無疑以《新唐書》的說法最具影響力。作為宋代的官修正史,《新唐書》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影響極大。宋人若運用‘詩史’概念來評論杜詩,很多都是直接從《新唐書》而來的”*張暉:《中國“詩史”傳統》,第25頁。。《新唐書·杜甫傳贊》云: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余,殘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卷二○一《文藝上·杜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38頁。
如同洪業先生所論,此傳史實記載“謬誤甚多”*洪業:《我怎樣寫杜甫》,《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第353頁。,同時,宋祁等對杜甫的評價也呈現復雜的狀態:襲用“詩史”概念,卻嫁接元稹、白居易的思想。這種綜合或合成,反映出宋初時代環境下對杜甫其人其詩的新認識。元、白到底如何認識杜詩?
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元稹在那篇著名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從詩歌史的角度評論杜甫詩歌,揭示杜詩“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的特點,贊許“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并比較了李杜異同:“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61頁。兩年后(元和十年),元稹在《敘詩寄樂天書》中進一步論述云:“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第854頁。元稹肯定杜詩“知小大之有所總萃”、回歸“雅正”風騷傳統、“鋪陳終始,排比聲韻”的長篇詩歌(特別是排律)。
白居易則始終關注杜詩的思想性。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貶官江州司馬,到任不久,其撰寫《與元九書》,追溯《詩經》、楚辭以來的詩歌史,描述儒家美刺詩教(“風雅比興”)在后代的衰歇過程,其中有云: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言,至于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著,丁如朋、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8頁。
元稹認為杜甫“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長篇最好,最為“雅正”——元稹兼顧藝術性,而在白居易的論述中,他列舉《新安》《石壕》《潼關吏》(“三吏”)和《蘆子》《花門》等數首詩歌,并表達自己的肯定,正是所謂“雅正”風騷傳統——更強調政治性,可見兩人觀點同中有異,當然,二者相同之處更值得注意: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贊美杜甫的《悲陳陶》《麗人行》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其《酬李甫見贈十首》其二云:“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白居易《與元九書》從“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詩學立場出發,高度肯定杜甫詩歌《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等詩。他們都注意到杜詩的敘事性、寫實性和對重大社會現實問題——“時事”的反映、呈現*洪業曾注意到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關于唐文宗根據杜甫《哀江頭》詩句“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對安史之亂前長安曲江繁榮景象的紀實描寫而加以重建的記載,唐文宗對杜詩的閱讀和理解具有歷史視角之意義(《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第7頁)。不過,我們認為,此記載雖涉及晚唐史實,卻是由宋人記錄的,不一定可靠。,這是杜甫與他同時代詩歌不同之處。如果我們不拘泥于“詩史”字面,我們將不得不承認,杜甫呈現的“時事”當然也屬于歷史的范疇。元、白對現實的關注,對詩歌政治功用的強調,顯然,是前述中唐政治改革運動、《春秋》學勃興以及詩歌趨向寫實思潮的反映*韓經太:《傳統“詩史”說的闡釋意向》(《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著重從宏觀上論述元、白強調以詩寫時事的用世精神,并指出這種觀點與儒家傳統詩學的關聯,不過并沒有考察孟啟“詩史”說的具體內涵。,這與孟啟“詩史”說屬于同一背景。當然,同樣是敘事,由于思想動機的差異,他們對所敘之事的關注點卻大不相同:元、白著眼于杜甫詩歌對當時重大社會現實的反映或揭露,而孟啟“詩史”說則著眼于杜甫詩歌對個人日常生活和山川風景的呈現,一偏向政治,一偏向個人生活。
明白元、白的論述,再來看《新唐書》的引申和發揮就相當明確:第一,繼承元稹“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的肯定對象,并增加“善陳時事”這一定性,并命名為“詩史”——寫政治時事且對仗精嚴、篇幅宏大。孟啟所謂“詩史”作品,是指杜甫“流離隴蜀”期間的創作,而符合元稹這一新標準的杜詩只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以及《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等,這類大容量、長篇幅的詩歌除了杜詩,在唐詩中極其罕見。沿用“詩史”概念卻承襲元、白的思想,內涵和指稱都發生改變;不同于孟啟關注個人不幸這一理解,元、白回到政治性闡釋這一儒家詩教傳統*《新唐書》作者如此理解當然也不是偶然的,這與宋人史學觀念和儒家思想復興運動有關,茲不詳論。。第二,《新唐書》的認識源自元、白的詩學觀念。元、白都從風雅傳統稱頌杜詩,他們對杜詩性質的理解完全一致,強調杜詩的倫理性、思想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崇高性。白居易給他所認可的杜甫詩歌找到的思想傳統和詩歌經驗淵源更為明確,就是儒家美刺詩學——“風雅比興”(《與元九書》)。這其實表明人們對杜甫詩歌創新活動思想資源的思考從《春秋》學、史學轉移到另一種經學——《詩經》。在唐人的詩學評論中,《詩經》當然是崇高的傳統,并被用來贊美他人詩歌,李白說“大雅久不作”(《古風十五首》其一)*天寶年間蕭穎士《江有楓》等詩、中唐前期詩人顧況《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都直接模仿《詩經》。這與杜甫借鑒《詩經》精神進行創作不同。,杜甫說“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杜甫贊美他人詩歌具有“風雅”精神,如贊美薛據、畢曜說“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型”(《秦州見敕喜薛據畢曜遷官》),贊美韋濟“詞場繼國風”(《奉寄河南韋尹丈人》),贊美元結詩歌具有“比興體制”(《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但是,他人用以評價杜甫詩歌中,指向卻比較明確,如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就以“大雅之作”(《杜工部小集序》)贊美杜甫的詩歌*樊晃編輯的《杜工部小集》雖然已經散佚,但是,據陳尚君《杜詩早期流傳考》(《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輯考,現存的詩歌選入比例(62首中,五古、七古達36首)還是反映出樊晃的價值傾向——尚古,其中收錄有“三吏”“三別”中的《新婚別》。,杜牧以“風騷”(《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趙鴻以“大雅”(《杜甫同谷茅茨》)、皮日休以“風雅”(《陸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過有褒美內揣庸陋彌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敘相得之歡亦迭和之微旨也》)等贊美杜詩。比較而言,關于杜詩與《詩經》的關聯,白居易所論最為明確而充分,他在《與元九書》中以寫時事來詮釋“風雅比興”傳統——反映、揭示社會現實的創作傳統,他以此標準肯定杜甫《石壕吏》等詩歌,認為杜甫寫“時事”的《石壕吏》等詩歌之詩學淵源是《詩經》“風雅比興”。《新唐書》用來定義“詩史”的“時事”一詞,與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中關鍵的“時”、“事”二字的對應,當然不是偶然的。
一旦將杜詩與風雅傳統建立聯系*宋人正是按照此種思維,由認為杜詩繼經,發展為視杜詩為“經”。,根據反映“時事”的標準衡量,“詩史”的指稱對象將會進一步漂移——既不是孟啟所謂“流離隴蜀”之作,也不是《新唐書》新認定的元稹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之大篇,而是另外一類詩歌,即白居易所稱頌的“《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因而與元、白所倡導的諷喻詩以及新樂府運動建立了聯系,并逐漸指向這些詩歌。在白居易、元稹看來,當時繼承《詩經》、漢樂府傳統的詩歌創作實踐就是“新題樂府”創作。元、白對《詩經》傳統的理解主要是反映、揭露現實問題這一精神,“新題樂府”創作確實是中唐出現的反映當時社會問題的一股詩歌風氣。唐肅宗之后,雖然安史之亂已被平定,社會政治問題卻日趨嚴重,這引起詩人們的高度關注和深刻反思,盛唐之后出生的一批詩人創作中有所反映并形成一股風氣。張籍、王建有此類創作,而白居易和元稹從事這類創作具有強烈的理論自覺,即自覺以儒家詩教功利思想為指導。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官拜左拾遺,諫官的身份促使他將詩歌當作諫書,創作了大量的“諷諭詩”,其中有一類詩歌可能由白居易后來整理編輯時命名為“新樂府”,“首章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新樂府詩·序》)。同在元和四年(809),作為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創作了類似詩歌,題目為“新題樂府”,不過,其《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明確說是受到李紳創作的啟發。簡言之,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的詩歌創作風氣興起于白居易、元稹之前,而明確標目為“新樂府”則始于李紳,元、白則自覺地將其提升為詩歌創作范式而加以推廣。元和十年,元稹在《敘詩寄樂天書》追述自己詩歌創作歷程,并對自己的創作“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其中一類就是“新題樂府”。元和十二年,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說:“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第674頁。元稹認為風雅傳統落實在具體的詩體中就是“樂府”,魏晉南北朝以及初盛唐時期的“樂府”只是沿襲舊名,“新樂府”或“新題樂府”*元稹兩年前《敘詩寄樂天書》觀點(“詞實樂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與《樂府古題序》文對“新題樂府”的內涵理解不同,后者更近于白居易。才真正繼承面向社會現實的風雅詩教精神和傳統——“即事名篇,無復倚傍”。按照元稹的解讀,中唐確實出現了新樂府詩創作的一股風氣,而盛唐詩人杜甫則是這個新樂府運動的開創者,并將杜甫及其創作樹立為現實的榜樣。元、白之所以追源到杜甫,確實是受到杜甫本人理論意識和創作的影響: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詩序中明確提出,要復興“比興體制”,要求詩歌反映民生疾苦、反映現實問題,這類詩在元、白看來最具有他們所倡導的“新題樂府”精神,正是沿著這個邏輯,“詩史”逐漸指向反映“時事”和現實社會問題的“新題樂府”*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單列“新樂府辭”一目,其中收錄了杜甫詩《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哀王孫》《兵車行》五首,而白居易《與元九書》所提及的“《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卻沒有收入(《樂府詩集》收錄杜甫詩歌情況是:“橫吹曲辭”2題14首,“相和歌辭”2題4首,“雜曲歌辭”1題3首,“新樂府詩”6題6首,一共收錄杜甫詩歌11題27首),同時,郭茂倩在“新樂府辭”目下列出“新題樂府”只收錄元、白的作品,這表明郭茂倩與元、白關于“新樂府”詩觀念的重大差異(葛曉音:《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近年來,學術界關于唐代“樂府”以及“新題樂府”概念的內涵、外延、指稱對象有很大的爭論),我們要強調的是二者的差異不僅是對詩歌體式的認識不同,而且在價值觀上也存在不同,質言之,元、白追認杜甫詩歌為“新樂府”,所關注的不是詩歌體式,而是詩歌的政治傾向和倫理價值。——事實證明,白居易強調風雅美刺詩學對后代的影響超過元稹。不僅如此,在后代人看來,最有代表性的“新題樂府”就是“三吏”“三別”——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只是不完整的列舉,但指向性很明確,因此,“三吏”“三別”這兩組詩此后逐漸與“詩史”概念建立堅強、穩固的聯系,從而被視作“詩史”性質詩歌的典范和代表。

杜甫從生前顛沛流離的落魄詩人到身后被萬人景仰的詩圣,在這一提升過程中,“詩史”是最早的定性評價。從孟啟到《新唐書》,“詩史”承襲敘事性、紀實性這一表達手法之意義外,還增加價值評判之意義,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今天所謂“現實主義”精神,其內涵兼顧表達方式和內容;所敘之事與指稱對象也發生了方向性的調整,由敘個人之事轉變為敘“時事”——時代之史,所指杜詩范圍也由“流離隴蜀”擴展到此前此后之杜詩,與中唐詩歌運動和詩歌類型——“新題樂府”建立了聯系,“三吏”“三別”逐步獲得了“詩史”典范的地位,這基本上奠定了我們今日對“詩史”概念的理解。從杜甫的創作到孟啟對其性質的追認,再到《新唐書》的更新理解,這一過程既是對杜詩創新性和豐富性的發現,也是對一種創作傳統的自覺建構,這一建構過程實與中晚唐五代北宋前期的政治、經學與文學運動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