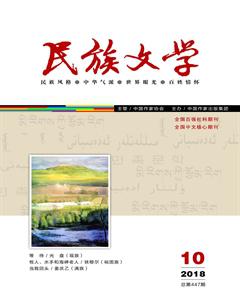窯變
普輝
腫柄菊
腫柄菊,來自遙遠的遠方
在忘記了故鄉(xiāng)的他鄉(xiāng)
與風(fēng)和草木漫過荒野、坡堤
冬天有雪,秋天有霜
這兩個季節(jié)
梅蘭竹能添風(fēng)雅
腫柄菊能添黃金一樣的顏色
可觀的花也是可藥的材
它的人間煙火味,像青蒿
再大成就,也仍叫個沾滿土氣的名字
虛 化
夜深,合上眼
從清醒到昏眠,漸虛化……
在街上
光線強烈,房屋是白的,路面是白的
行道樹無葉,光枝,長芒刺,密麻
行人面目模糊,悠閑地走
過草原
見藍天,山川,河流,飛鳥,馬鹿
沒有房屋,工廠,高鐵及硝煙
不敢呼吸,怕打碎這些靜謐
靈魂似乎騰空
看著熟睡的軀殼,告誡:
別打擾沉睡的人
意識,朦朧……
帽天山
1984年7月1日,從澄江縣城去往東邊一座山
馬車上,他的白色布帽落滿陽光
至山間,揮起地質(zhì)錘
一片電閃雷鳴、海浪呼嘯就向他撲來
厚實的眼鏡,此刻恍似精準度不足
他把敲下的石塊,一次次貼近眼底
5億3多千萬年前的海洋和月光,凝固在這座山
于是,一些數(shù)字與名詞得以面世
分布帶長20公里,寬4.5公里,深50米以上
寒武紀早期,40多門類80余種動物
生命及生物演化鏈的鼻祖海口魚
生態(tài)金字塔最高層的奇蝦
新取名的云南蟲,納羅蟲,三葉蟲,撫仙湖蟲
達爾文解釋不清的事
南高原山巖間,統(tǒng)稱化石的石頭就是答案
帽天山,從此陽光無數(shù),如同應(yīng)和了他那天戴的帽子
這個石破天驚的男人,卻一直低調(diào)而清瘦
他叫侯先光,中科院院士
晴天雨
大早,開車至醫(yī)院
拆動態(tài)心電圖,秒拆,少了等待的心焦
出醫(yī)院,天藍,陽光真暖。
上車,打火。無動靜
想來,人會生病,車也會
無妨啊。晴天,有時也下雨
芳 華
那時,不全是雨風(fēng)
現(xiàn)在,不全是明媚
人生終會有芳華
我的陽光,捧在手上
蒼蠅訴
蒼蠅停耳邊,驅(qū)趕,飛走
又來,嗡嗡嗡,在說話
蒼蠅說,這世間萬物共生,各有其道
山川河流,樹木花草,藍天白云
人類,動物,昆蟲
都是造物主的安排
中國先哲曾言,五行相生又相克
蒼蠅接說,蠅族也分幾類
家蠅,麗蠅,絲光蠅,麻蠅,大頭金蠅
就像人類各種膚色
只是,蠅族沒有歧視
沒有爾虞我詐,沒有病痛,沒有硝煙,沒有難民
蒼蠅還說,我們到處飛
就像人勞作。尋覓食物,為人類分解垃圾
卻落個蠅營狗茍之名
人啊,蒼蠅身子瘦小戴不動這頂高帽
再說一句
無縫的蛋,蒼蠅想叮也叮不了
說蠅撒布病毒,病毒可是人產(chǎn)生的
嘆一聲,作別。但愿,人間干凈
銅 匠
1
又聽見叮當(dāng)聲,從消失已久的遠方來
憨厚,零碎,也悅耳
多想返回去
讓日子,在這聲音間安頓
2
高鐵像風(fēng)
看不清窗外的模樣
都市給每個人,帶上面具
誰也不認識誰
3
銅匠,仍然是銅匠
月光一樣如初
黑褐色的鐵錘
一次一次,落上銅皮
橙黃色的錘印,沉穩(wěn),深淺不一
敲打出的銅俑,多年后進了城內(nèi)博物館
女人還在遠方,和著叮當(dāng)聲浣紗
水邊,漾起笑語,輕輕地飄
4
斜陽散開極薄一層
如銅匠和他敲打的聲音,沒入了那邊的山坳里
白 茅
在荒丘,獨立
在霜天,飲寒風(fēng)
如果,燃起一把火
那就浴火重生
撫仙湖
再多的文字,也將失去份量
詩人墨客,除了冥思,只剩故作的高深
色調(diào)和語言,都無法呈現(xiàn)它的寬厚
這一湖,206億立方的水
只管存在
就是,絕世的精彩
紅 河
血一樣的河流,日夜不息
幾千年奔騰至今
現(xiàn)在,我怕看到最后一滴
在眼前流盡
窯 變
祭司念念有詞,
窯上祭祀的豬頭,已滲出油花
隨著祭司的頌詞
油一滴又一滴,落入窯中
坯釉在窯火里蛻變
瓷器,長出了塵世的顏色
食 言
抵不住,人間的絮叨
又一次,被刺激的液體燒熱
手有些麻木,像發(fā)抖
胃和記憶在掙扎
食言是痛苦的
卻無法捏碎,所有的夜光杯
紅塔山
七百多年時日,塔,紅色
我已不想從故紙堆里尋找典故
遙想經(jīng)年,塔初誕,云一般白
像人面世,自然成男或成女
某年月,厭倦了白,塔涂紅
那座立塔的荒山卻變得很好看
山上的泥土,開始不再寂寞
煙草味滿滿地溢開
有時,改變的,不止是眼前
還可能是命運
如人挪活樹挪死
也如紅塔山,成了現(xiàn)世傳奇
不要問為什么紅
不要問為什么在荒山
紅塔——
無關(guān)顏色
只要塔在,就不缺風(fēng)雨和閃電
就能讓早行人,從頂尖上,看見佛光
責(zé)任編輯 郭金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