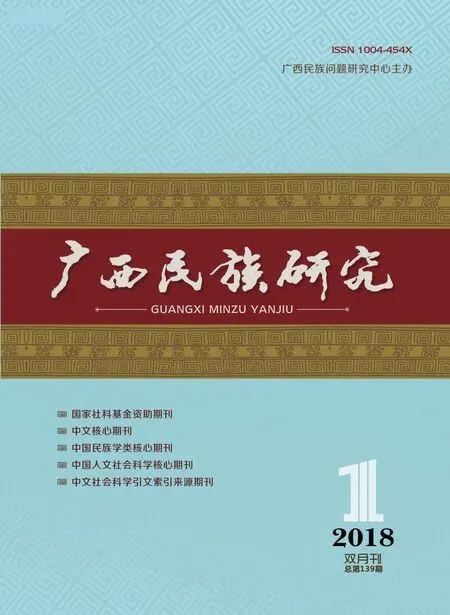夾縫中生存:清代畬民政治參與窺探*
邱開玉 廖夢雅
一、問題提出
畬族是我國境內一個較古老的民族,早在隋唐時期,就聚居于閩粵贛交界的山區,歷經千年輾轉遷徙,至明清時期,遷入閩浙贛交界區,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人類共同體。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中,畬族人民負重拼搏,創造了極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長期以來,國內學界關于畬族政治方面的研究幾乎沒有展開,鮮見相關論述的專著和論文。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畬族作為散雜居少數民族長期棲息于大山深處,生存環境惡劣閉塞,并不斷遷徙動蕩,使得畬族社會經濟遠遠落后于同時期的主流社會經濟[1]。經濟和生活環境的“邊緣化”,使得畬族在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中處于絕對“邊緣”,淪為被奴役和剝削的底層,似乎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和政治表現可言。各時期正史中偶有畬族的相關記載,大都是“作亂犯上”之“劣跡”,而地方志、筆記小說、游記雜錄等民間文獻,也大都以獵奇心理對畬族迥異與漢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習俗、語言、服飾進行闡發,帶有明顯的鄙夷色彩。而事實上,畬族雖然長期處于封建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邊緣地帶”,但在長期的社會經濟交往中,畬族與周邊的“主流”社會發生廣泛接觸,在畬漢雜居交界地區,畬族人民始終沒有停止與主流社會的交往與互動。與此同時,歷代的封建統治者為了加強對畬區的控制,實現對畬民更好的統治,往往在畬族聚居區設置政治機構,并不斷向畬民灌輸封建倫理思想進行教化。無論是主動地融入還是被動地抗爭,畬族與漢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終不曾停歇,也就構成了畬民參與主流社會政權的前提和基礎。
本文之所以在畬民前加上“清代”,主要居于三重考慮:一是明清時期是畬族遷徙的最活躍期之一,也是畬族現有分布格局的定型期。由于政治、軍事或自然等因素,畬族曾發生大規模外遷,自唐代以來,輾轉于東南數省,至清代中后期形成了現有的分布格局。逐漸定居后的畬族,與周邊漢族的交往互動愈加頻繁,其社會內部也逐漸建立起了較為先進的封建制生產方式與政治制度;二是清代作為少數民族掌權的朝代,以傳統的華夏秩序而論,是女真族、蒙古族等“異族”對“漢族”的統治。這種政治結構,使得原本極少被正史正視的原關內“異族”(包括畬族等少數民族),在政治生活中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政治空間;三是滿清統治者吸取元代“異族”統治失敗的教訓,在對待民族問題和處理民族關系上,主要延續明代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并加以完善,使得包括畬族在內的少數民族得到較快的發展,造就了畬民政治參與的社會環境,極大地激發了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
因此,本文將結合有關古文獻、漢文典籍、方志、宗族譜牒等文獻資料,對清代畬民政治參與涉及到的社會變遷、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統治者決策、畬族成長等關鍵因素進行爬梳整理,就清代畬民政治參與何有可能以及何以實現的問題,求教于大家。
二、政治參與之社會形態
“政治”在人類學視角中,多作為一個社會文化來考慮,社會文化根植于社會經濟,存在于特定的社會形態之中。因此,對畬民政治參與的歷史考察,離不開對畬族社會變遷軌跡的追溯。由于畬族在唐代之前的社會形態,缺乏文獻記載,[2]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撐畬民存在前封建社會的政治參與。因此,對畬民政治參與歷史軌跡的梳理將從封建社會開始。
畬族社會的封建化開始于唐代封建政權對畬區的政治控制。[3]177“高宗總章二年(669),泉潮間民苦蠻獠之亂,僉乞鎮帥以靖邊方……儀鳳二年(677),政卒子元光代領其眾,會廣寇陳謙等聯結諸蠻攻潮州,守帥不能制,遠光以輕騎討平之,開屯漳水之北,且耕且守。中宗嗣圣三年(683),元光請于泉潮間建一州以抗岑表。朝廷以元光父子久牧茲土,令其兼秩領州并給告身即屯所見漳郡。”[4]卷1“唐朝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居期間,今汀人呼之曰畬客。”[5]卷3以上所載,分別描述了唐代封建統治者在漳州、汀州建郡統治的過程。建郡統治,密切了畬族與周邊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系,漢族社會的先進生產技術和設備被引入畬族地區,客觀上促進了畬族社會的發展。自唐代以后,各朝代的統治者逐步在畬族集聚區建立政治機構,并要求畬民“納貢糧”“定租稅”,畬族社會逐步進入封建化的過渡過程。隨著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封建統治勢力不斷加強,封建統治范圍向更偏遠的疆域延伸,使得越來越多的畬族地區被納入封建統治范圍,畬民承受的剝削與壓迫也在劇增,使得原本就生產力水平低下、生存環境惡劣的畬民處境雪上加霜。為了生存或逃離壓迫,畬民被迫進入不斷遷居游離的動蕩歷程。至清初時期,在清代統治者廢止圈地與鼓勵墾荒政策的推動下,大量畬族遷入閩浙贛交界的山區,開始了定耕山野的定居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定居后的畬族社會,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的過程。
一是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的確立。雖然部分史料依然記載一些畬區在清代初期有“刀耕火種”的現象,但實際上,大部分定居后的畬族社會其生計模式由游耕時期的“游耕狩獵”逐漸轉變為農業經濟時期的“牛耕鋤種”。明萬歷《景寧縣志》記載:“(畬民)不喜離鄉,亦無游人異物以遷其志。男事耕耘,女務紡織,僅給衣食。”[6]120可見,早在明代,浙江景寧的部分畬民就開始進入定居的“墾田耕種”生活。清乾隆《古田縣志》記載了當地畬民生產方式和風俗習慣逐漸轉變的歷程,“邑畬民有雷、蘭二姓,男女赴山耕作……多于深山編茅為居……近則附近民居各村與民往來交歷。亦承耕民田,能自變其俗,惟疏遠者則相言舊習如故”[7]卷21。同時,鐵制農具也普遍出現于畬族地區,在福建、浙江等地的風俗記載中,犁、鋤等農具已成為畬族婚嫁的常見嫁妝。永春、德化畬區“嫁女以刀斧資送”[8]卷1,龍游畬區“婚姻亦三姓,世為之……套以鋤犢”[9]卷11,這些從側面反映當時畬區社會生產力邁上新的臺階。
二是封建制生產關系在畬區的廣泛存在。經過長期的遷徙動蕩,最終定居在閩浙贛山區的畬民,絕大多數沒有自己的土地,只能以“山哈”(山里的客人)的身份租種當地漢族地主的山林或佃田。福建畬民“所耕田皆漢人業,歲納租外,得贏余以自給”[10]卷2。江西畬民“賃田耕種……惟甚愿,田主知其無他,每納租故縱之不以時收,收或不足,則恐懼,吁祈來年出息償,至期償息如數”[11]卷14。浙江各縣畬民“力耕苦作,或佃種田畝,或杠抬山輿”[12]。畬族佃戶與漢族地主階級開始形成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使得二者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一方面,畬民不得不依附于漢人地主階級,不再是“流煙人群”,而是淪為佃農、短工、長工,忍受階級剝削;另一方面,漢族社會先進的生產技術被引入畬族社會并被廣泛運用,促使其更快封建化。
與同時期的大部分漢族地區相比,畬族地區依然處于落后的局面,畬民也基本淪為漢族地主階級剝削的對象,但是在封建統治導演下的畬族社會變遷,使得大部分畬民結束了居無定所、游耕放牧的“原始”生活狀態,其社會內部生產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封建式生產關系已逐步建立,為畬民參與封建社會政權提供了最基本的社會條件。
三、政治參與之經濟文化
薩繆爾·亨廷頓的政治參與理論認為,社會經濟雖然不是決定政治參與的最關鍵因素,但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就社會—經濟發展對政治參與的長期影響而言,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大,造成參與基礎的多樣化,并導致自動參與代替動員參與”[13]43-44。
清代畬民的政治參與,是畬族社會封建經濟發展的產物。隨著畬族社會內部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畬族內部私有制經濟不斷成長,經過數代人的努力,部分畬民家庭開始有了一定的生存資料積累,畬族社會內部階級分化加劇,出現“有田產者”的地主階級,逐漸產生一些封建式家族。《長汀縣志》記載:“其有田產者亦必輸糧而給官差,此以覘圣朝治化之隆,雖峒徭亦無異于鄉里中編氓也。”[14]卷35《遂昌縣志》記載:“遂昌之有畬民,蓋于國初時徙自廣東安插街、處、溫三府者,始來多為農民傭工……近二百年,亦有積累成家業者。”[15]卷1隨著畬族社會經濟的封建化,畬民思想意識也“漸染華風”:鼓勵和培養子弟努力向學以爭取科第成為畬民與漢人一致的政治價值追求。
為了進一步改變家族的命運,畬族封建家族組織利用有限的經濟資源,進行智力投資,為家族內貧困的優異子弟讀書應試,走上經濟仕途的道路提供一定的經濟保障和文化資源。在經濟方面,畬族家族組織廣置族田,資助族人子弟應試。族田包括義田、祭田、祠田和學田等家族公共資產。其中,學田的最重要用途就是資助家族內子弟應試。寧化縣《雷氏家譜》記載:“學田之宜設也。……至赴鄉試者,亦于眾祖嘗銀叁錢,與作卷貲,于其本房祖嘗銀出壹銀與作舟貲。至于姓中有叻祖,靈中鄉榜者,出喜銀拾兩,中甲榜者,出喜銀貳拾兩。若恩拔歲副,出喜銀叁兩,入衣冠會內,遞年存積,以為署買學田之貲。”[16]174在文化資源方面,畬族家族組織廣建家塾,鼓勵族人讀書取仕。所謂族學,是相對于政府官方舉辦的以村落為單位的社學而言,由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家族或多個家族聯合建立,其目的是通過類似于漢族文化的啟蒙教化,以便形成與漢人相類的文化傳統,為族人走上仕途之路奠定文化基礎。道光十九年(1839),福安縣潭頭前村《藍氏宗譜》載:“延師教子為父兄所當然也,茅地處鄉曲欲延師甚難,……(舉村)同心協力,可有家勿與困有家相較,況世少不教而善之人,亦不教而不善之人……”[16]211。在這種價值取向的指引下,福建畬區“鄉里家塾林立,以故科第外平民罕有不讀書識字者”[16]19。浙南地區“十縣聞,畬客且千萬,子弟秀又良,亦足備選擇。字或識九千,弓可挽五石,以之充學堂”[17]卷34。雖然詩歌或族譜的表達略顯夸張,但也反映了當時閩浙畬區“樂學好讀”的文化景象。
一言以蔽之,畬族封建式家族是推動畬民政治參與最重要的民間力量。在家族經濟的支持下,畬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在清代實現對接[18]24,畬族庶民有了向上流階層流動的可能性。“籌臺宗匠”藍鼎元家族就是典型之一。藍鼎元的家族在其曾祖父毅叟公之前也同大部分畬民一樣居住在崇山峻嶺的惡劣環境中,“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橫,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為了生存和發展,毅叟公舉家遷居平原,告別了耕山種畬的生活。在藍鼎元曾祖一代,其族人就通過與漢人聯姻、習武從戎、讀書取仕等渠道,成為講究禮樂教化的官宦人家或書香人家。
四、畬民政治參與之政治條件
薩繆爾·亨廷頓的政治參與理論進一步指出,“在任何特定社會的特定時期,政治參與的水平、基礎和形式更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而非其他因素 ”[13]30。從這個觀點出發,可以認為,在階級社會中,普通民眾政治參與的實現與否取決于統治者決策等政治因素。總體而言,較之以往的朝代,清政府在處理民族關系及其問題上采用“教化、綏撫、防范與控制”相結合的相對“開明”的民族政策,具有更高的政治遠見,更有利于境內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在客觀上也促進了畬族等少數民族的成長。
(一)“既合作又限制”的政權組織拓展了畬民政治參與空間
清代采取相對開明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進行統治,主要源于清代相對獨特的政治機制運行模式:滿漢之間既合作又限制。作為統治者的滿人尋求與漢人的合作,是基于民族自身與統治對象之間的差距而做出的選擇。在入關之前,滿族在社會形態上,仍然處在氏族崩潰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前封建社會;在政治組織上,正由家長制政權越過部落聯盟向君主專制前進。而在入關之后,面對的是一個絕對多數人口的“異族”,版圖遼闊的大帝國,無論在政治制度、經濟結構、社會組織、文化水平上,都相較自己更優、更高、更復雜的國家。這種統治對象的差異,是滿人入關后面臨的首要客觀問題,進而引發更深層次的問題:滿人如何在一個異族土地上建立政權,運用何種方式進行統治,不但可使政權牢固,保障既得利益,而且又能使國祚綿長,所得的利益廣而久?滿清的統治者選擇了一種最經濟,也是最明智的統治方式,就是與關內漢人合作共治,共同參與的模式。而在合作的基礎上,又處處限制和提防漢人,則完全是因為政治斗爭的殘酷性,使得“非吾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根深蒂固,異族之間在心理意識上和利益關系上不可觸及的忌諱,使得統治者更加依賴本族的力量。
這種既合作又限制的運行模式反映在政治層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以種族來劃分參與政治活動者的身份。《清史稿》記載:“凡滿漢入仕,有科甲、貢生、監生、蔭生、議敘、雜流、捐納、官學生、俊秀。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歲、優貢生,蔭生出身者,為正途,余為異途。”[19]志85,選舉志5單憑這一規定,似乎滿漢并無差異,但實質上,這只是清代關于官員“出身”的一般規定。在《大清會典》中,又有關于滿人任官的專門規定:“旗人免保舉,皆得同正途出身”[20]卷7。如此,旗人出仕為官,根本無所謂出身正途異途之別,皆為正途之身。從而使得滿人相較于漢人在仕途中占據明顯優勢。其二,在分配職位及名額數量上向滿人傾斜。清政府將國家統治機構的職位分為六個范疇,依照順序分別為宗室、滿洲、蒙古、漢軍、內務府包衣和漢。僅從排列順序就可以看出當時漢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劣勢”。同時,在分配職位名額時,將滿人主要安置在中央和地方的要職上,保證在京城內外文武要缺的人數上,滿人多于漢人。據《清朝文獻通考》記載,乾隆五十年(1785),中央機關官缺計:滿缺2751缺,八旗蒙古缺253 缺,八旗漢軍缺 142 缺,漢缺 558 缺。[21]28-33
這種政治機制,雖然對漢族不利,但為原本就生活在關內的包括畬族在內的少數民族創造了政治參與的生存空間。滿人除了扶持更多的本族人參與政治運行中,也需要更多的非漢人參與其中,以達到制衡的目的。畢竟滿人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素質上,與當時的漢人還有非常大的差距。特別是在一些滿人勢力難以企及的邊陲地區,清政府往往通過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扶持少數民族發展,制造地區內部的力量平衡,以此來制衡該地區的主要族群(漢族),達到維護地區安全,實現更好統治的目的。
(二)“編甲完糧”戶籍制度確立了畬民政治參與資格
在清代初期,閩浙贛交界區的一部分畬族鄉村還未進入清代統治者的視野,依然沿襲著游耕時期“載入流煙冊內,概免一切差徭”的政治文化傳統。對于這部分畬民而言,基本的政治地位都沒有,也就無所謂政治參與。這種情況并沒有存在太長時間,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畬族社會封建化不斷加速,畬族逐漸被清代當局所確認,相繼被納入了戶籍制度的圖冊,畬民享有“齊民”的政治地位,受到封建統治者的保護也承擔納稅服役的責任。《清史稿》記載:“世祖入關有編置戶口牌甲之令。……及乾隆二十二年(1757),更定十五條……各省山居棚民,按戶編冊,地主亦保甲結報。廣東寮民,每寮給牌,互相保結。”“雍正四年(1726),定例照保甲法一體編查。乾隆二十八年(1763),定各省棚民單身賃墾者,令於原籍州縣領給印票,并有親族保領,方準租種安插。倘有來歷不明,責重保人糾察報究。”[19]志85,選舉志5由此可見,清代的編戶齊民制度在雍正年間已廣泛運用于對畬民等“苗夷”的管理。“雍正年間曾奉諭旨,準其一體編入民籍,況此種山民充糧納賦,與考服官,一切齊民相同。”[22]15進入戶籍制度的畬民,“視土著之民”享受土著之民應有的權益,也承擔賦役的義務。《龍巖州志》載:“今畬客固安分,而漢綱亦寬,許其編甲完糧,視土著之民一例。”[23]卷12因此,隨著清政府“編甲完糧”戶籍制度在畬族山區的逐步施行,越來越多的畬民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也就有了參與政治活動的正式資格。
如果說,編甲完糧是畬民進入政治生活的第一步,那么在乾隆年間畬民畫像入“職貢圖”,便可以視為統治者在政治上對畬民身份的辨別與確認,由之前模糊不清等同于“土著人”(漢人)而逐漸明晰成為獨立的“民族”。乾隆十五年(1750),清政府開始籌備繪制《皇清職貢圖》,其目的是為了將“內外苗夷……匯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因此,《皇清職貢圖》的內容就是描繪“內外苗夷”的狀貌、服飾、生活習俗等,為統治者進一步了解“苗夷”提供感性直觀的素材。《皇清職貢圖》中關于畬族的描繪“福州府羅源等縣畬民,即粵之猺人……其習俗誠樸,與土著無異。古田畬民即羅源一種,散處縣之上洋等村,以耕漁為業,竹笠草履……”[24]卷三。這些文字很好地勾勒出畬族的遷徙歷史,畬民的外貌體征、生活環境以及風土民情。將畬民畫像載入《皇清職貢圖》,“以備查考”,表明清政府認定他們有別于漢人。此時,封建朝廷已經完成了對畬族鄉村的政治管理。
(三)科舉制度的鼓勵政策優化了畬民政治參與途徑
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途徑就是科舉考試。傳統的科舉考試作為主要的選官制度,是中國最古老的、最完善的文官考選制度,是庶民“進身之階”的最重要途徑,直接影響著庶民的社會政治生活和文化教育。滿清取得中原的政權后,為了籠絡知識分子,緩解民族矛盾,便于更好統治,沿襲了明代的科舉制度。
清代較開明的民族政策在少數民族參與科舉考試中得到較好的體現。一是廣設義學,為少數民族地區開科取士創造文化條件。《清史稿》記載:“又有義學,社學。社學,鄉置一區,擇問行優者充社師,免其差徭,量給廩餼。凡近鄉子弟十二歲以上令入學。義學,初由京師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州、縣各設立,教孤寒聲童,或苗、蠻、黎、瑤子弟秀異者。規制簡略,可無述也。”[19]志95二是準允并鼓勵少數民族與漢族一同應試,并給予一定的額數保證。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朝“令湖廣各州縣熟苗中有通曉文義者,準與漢人一體應試,廣西土司之民人子弟及貴州苗民并照此例”[25]卷48。雍正元年(1723)規定:“俟熟番學業有成,令往教悔生番子弟,再俟熟習通曉之后,準其報名應試。”[25]卷49同時,為了鼓勵更多的少數民族子弟應試,清政府給予少數民族地區額外的錄用名額。嘉慶十三年(1808)規定:“苗疆鳳乾、永、保四廳縣士子應鄉試者,另立邊字號,數在三十名以上,于本省額內取中一名,又苗生應鄉試者,另立田字號,數在十五名以上,于額外取中一名。”[25]卷53三是對于地處僻遠,交通不便的少數民族子弟去應試,政府給予一定的經費資助。如道光元年(1821),貴州巡撫陳若霖上奏:“給苗疆會試舉人川貴”[19]志81,選舉志1,被朝廷接受。清代科舉制度,為畬民政治參與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一部分畬族人通過科舉應試進入統治階層,有了為本民族伸張權益的參與權和話語權,為更多畬民子弟能夠參與政治提供一定機會,從而形成畬民政治參與的循環圈。
(四)政治精英的幫扶加快了畬民政治參與進程
畬民的政治參與離不開畬民政治自主意識的萌發以及對政治權利的積極爭取。同時,也應注意到,在任何社會中政治精英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可能是影響該社會政治參與性質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13]30對于長期處于被壓迫和被忽視的畬族而言,尤為如此。在畬民通過科舉考試邁進“進身之階”的道路上,離不開比較開明的政治精英支持。
在清代的史料記載中,支持畬民政治參與比較有代表性的政治精英主要有兩位:一位是處州府青田縣令吳楚椿。乾隆四十年(1776),畬族考生鐘正芳上書青田縣衙,痛斥因“畬民異類”而將畬民排斥在科舉考試之外的不公平現象,要求官方給予畬民應有的科舉考試權利。隔年,吳楚椿撰寫《畬民考》和奏折,上呈處州府。在《畬民考》中吳楚椿介紹了畬民的來歷,“順治十八年(1661),浙江巡撫朱昌祚因閩海交訌,遷濱海之民于內地,給田給牛,俾安本業。是由交趾遷瓊州,又瓊州遷處州”,指出畬民“本屬瓊海淳良,奉官遷浙,力本務農,已逾百年”。批評了當地土人(漢人)對“畬民系盤瓠遺種,獸類也”的“污蔑”,并指出“盤瓠”之說乃是“一任土民謬引荒誕不經之說,斥為異類,阻其上進之階,是草野之橫議也”,呼吁應“準許畬民一體應試”。作為當地的“父母官”,吳楚椿敢于提出“民族平等”,為畬民子弟能夠參加科舉考試而奔走呼號,實屬難得。最后,經過多方努力,鐘正芳的案子受到浙江省巡撫阮元的重視,并上奏朝廷,“準共平民一體報考應試”。第二年,雷起龍等畬族考生考中秀才。另一位是福建巡撫李殿圖。嘉慶七年(1802),福建畬族考生鐘良弼控訴縣書王萬年串通生監誣指畬民為“五姓禽養”,“不準與試”。時任福建巡撫的李殿圖了解此案后,審理果斷,“飭司道嚴訊詳復,張示士林”。李殿圖指出:“方今我國家天山南北……其南路為四疆,北路為準葛爾地,即與畬民無異。爾等將版圖之內曾經輸糧納稅,并有入學年份確據者,以為不入版圖,阻其向往之路,則又不知是何肺腑也?倡優隸卒,三世不習舊業,例尚準其應試,何獨舍民有意排擊之?”[8]卷140在他看來,畬民既然已在中國版圖之內,并向朝廷交糧納稅,在政治地位上就該與漢人一視同仁,只要“入學年份確據”,就能參與科舉考試。在他的支持下,鐘良弼次年再次應考,考取府學生員第二十名,“佳訊傳遍畬村,畬民奔走相告,引為幸聞”。
鐘正芳、鐘良弼等畬民考生維權行動的勝利,固然是畬民不甘被奴役,敢于爭取政治權利不斷斗爭的結果,同時也是類似于吳楚椿、李殿圖等政治精英不斷支持的結果,標志著畬民應試的參與權得到了政府官方支持。在此之后,越來越多的畬民參與科試,并爭得更廣泛的話語權與更普遍的生存權。
五、余論
綜上所述,清代畬民政治參與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已逐步完備。清代畬民在政治上的表現也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在畬漢交界的廣泛地區,大量畬民登科及第,改變自身和家族的命運,躋身統治階層。在現存的閩浙地區畬族家譜中關于先祖政治表現的記載(所任官職)主要集中于清代,例如福寧府霞浦縣半月里畬族村在道光至光緒的60年間連續出現了6位秀才,處州府青田縣培頭畬族村在乾隆至道光年間出現6位秀才,汀州府上杭縣在清代考取舉人8人,進士2人,間接反映了清代畬民政治參與的“盛況”。這一時期,畬族也出現了彪炳史冊的政治精英:文官中有“籌臺宗匠”藍鼎元與“閩學殿軍”雷鋐;武官中有“治臺首功”藍里和“治臺名將”藍廷珍。可見,當時極小部分較早接受漢族文化,走上仕途之路的畬民,其優異的政治表現,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也成為后人追溯清代畬民政治參與的歷史注腳。
然而,總體而言,封建統治下的清代畬族依然處于經濟上的弱勢和政治上的邊緣。畬民政治參與的經濟基礎孱弱,生存空間狹小,參與途徑有限,使得畬民的“進身之階”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曲折漫長。在畬民政治參與的進程中始終面臨著諸多的偏見與排斥,處在“身家不清,不準與試”與“本屬淳良,準許一體應試”的糾纏和抗爭中。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政治參與能力就在這樣的夾縫中,頑強地萌發、生長與延續。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畬族等少數民族同漢族人民一起推翻了封建統治,進入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參與權利和機會。黨和國家歷來重視少數民族政治參與并實踐出有效的“中國”方案。十八大以來,少數民族政治參與整體提升,政治參與范圍逐漸擴大,少數民族人大代表不斷增多,并呈現出基層化的發展趨勢。只是,由于歷史上的積貧積弱,導致部分少數民族在政治參與方面“先天不足”,其政治參與水平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生態中,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在現代化國家的政治文明建設的實際中,對類似于畬族這種政治參與“先天不足”的少數民族應給予適當的幫扶,才能彰顯現代政治文明的平等和公平。[26]19-25因此,加強對這些少數民族政治參與歷史與政治文化的研究就顯得十分必要。只有建立在本民族原有基礎上的政治扶貧才有可能對癥下藥,有效保障少數民族有序的政治參與權,消弭歷史遺留的差距,拉近民族間的政治發展距離。
參考文獻:
[1]王逍.文化透鏡下的畬族歷史[J].貴州民族研究,2006(3).
[2]蔣炳釗.解放前畬族封建社會形態[C]//民族學研究:第十二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3]蔣炳釗.畬族史稿[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4]〔清〕吳文林.云霄廳志[M].嘉慶二十一年(1817)刊本.
[5]〔清〕楊瀾.臨汀會考[M].光緒四年(1878)刊本.
[6]柳意城.景寧畬族自治縣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7]余鐘英.古田縣志[M].民國二十一年(1932).
[8]〔清〕陳壽祺.重纂福建通志[M].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本.
[9]〔清〕顧國詔.龍游縣志[M].光緒四年(1878)刊本.
[10]〔清〕江遠清,江遠涵.建陽縣志[M].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
[11]〔清〕黃聯玉.貴溪縣志[M].同治十年(1871)刊本.
[12]胡先嘯.浙江溫州處州間土民畬客述略[J].科學,1923(3).
[13][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14]黃凱元,鄧光瀛.長汀縣志[M].上海:上海書店,2000.
[15]〔清〕鄭培椿.遂昌縣志[M].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本.
[16]福建省少數民族古籍叢書編委會.畬族卷——家族譜牒[M].福州:海風出版社,2010.
[17]〔清〕周榮椿.處州府志[M].光緒三年(1877)重修本.
[18]藍炯熹.閩東畬族文化地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對接的過程[J].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
[19]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6.
[20]〔清〕吏部.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大清會典[M].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21]孫淑秋.試論清朝對漢族的政策[J].滿族研究,2011(1).
[22](福州)華美報[N].已亥(1899年)四月,第17號.
[23]龍巖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龍巖州志[M].乾隆三年(1738)鐫.
[24]〔清〕傅恒,董誥.皇清職貢圖[Z].嘉慶十年(1805)增補本.
[25]〔清〕劉錦藻.清朝文獻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6]雷振揚,陳蒙.對“去民族優惠”觀點的分析與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