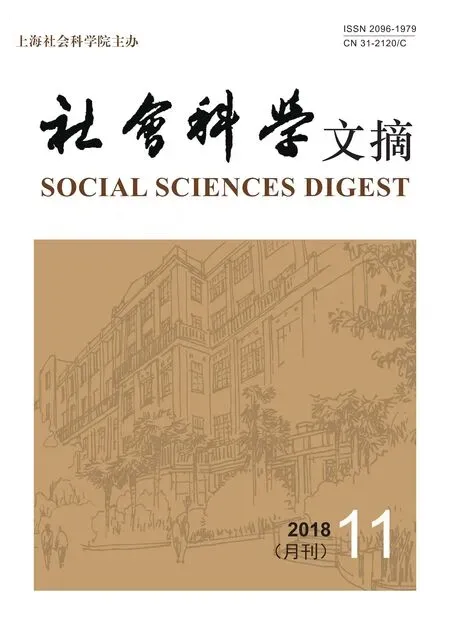鄧小平之后的中國:探索過程中的國家對外戰略
作為引言的鄧小平
鄧小平清晰地認識世界的變遷,力圖為中國的繁榮、進步和富強順應世界的變遷,這個塑造進程始于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即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自下而上的市場經濟實驗,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騰飛,鄧小平向世界表明一個共產黨能夠大大地、甚而急劇地改善它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由此顯著增進了世界的穩定和繁榮;中國對世界金融、世界貿易和國際安全的貢獻大為增長,正在邁進作為國際公益主要提供者之一的門檻;由于巨型獨立國家中國的崛起,美國沒有實現“單極世界”或“歷史終結”的想象。
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對外戰略緊隨1989年春夏的事變而落定。此前,這位善于領悟世界大勢和格外求實的政治和戰略大師已經逐步提出他關于世界的根本哲理式論斷,即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因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根本的時代條件。他還深切闡明了科技和經濟因素在國際競爭中的重大作用,提出對外開放須是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并且業已提出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去處理有關的國際爭端的新思路。與此相應,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而他倡導的中國經濟改革日益引起美國的關注,中美之間以經貿為基礎的交流與合作大大促進了雙邊關系的全面展開。主要是為應對1989年春夏風波后中國暫時的空前困難和國際風云巨變,鄧小平提出最為膾炙人口的大戰略方針,那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不扛旗、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在此基礎上就中美關系提出了增加信任、減少麻煩、加強合作、不搞對抗的方針,促使中美關系逐步走出僵局。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途中反復強調堅持和加快改革開放。還強調中國對外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即“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要反對霸權主義”。中國的經濟騰飛由此而起,中國對外戰略的一大根本環境自此生成。
急劇變化中的形勢界定與戰略探求(1999至2002年)
1989年之后,中國對外戰略、特別是對美戰略和政策制定開始了長達近15年、由“第二代領導核心”往后的代際轉變。
1999年科索沃戰爭和北約盟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等急劇事變沖擊了中國領導人原先的印象和政策模式,也引發了國內知識界和公眾對一些主要的對外政策前提假定的困惑和爭論。這些困惑和爭論因為2001年對美國的9·11恐怖襲擊而大為加劇,中國自9·11往后頗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世界形勢和外交任務。以時間先后為序,它可被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緊接9·11之后的6個月,中國在幾個重要問題領域有著非同小可的困惑、爭論和搖擺,導致中國對美國多戰線反恐戰爭的輿論、態度和政策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第二階段始于2002年3月臺灣“國防部長”湯耀明對美正式訪問,中國國內出現了對美國的強烈不滿和憤慨;在2002年夏末秋初,幾乎戲劇性地來到第三階段,中國政府對美態度和政策溫和化變遷,連同中美關系顯著改善,原因是中國講求實際的觀念、審慎的樂觀主義和優化了的戰略思維,加上美國政府對華態度的積極變化。
隨之而來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標志著中國戰略的進一步重大澄清和優化。十六大報告堅持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的主題。與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的基本政策聲明相比,報告透露出更加溫和、審慎樂觀和求實的對外政策前景。但另一方面,中國并非只是溫和。十六大報告明確地宣示了至關重要的兩點:(1)加速實現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2)決不容忍“臺獨”。與過去相比,中國現有兩大更清晰、內在更連貫的戰略決心:堅決和盡可能堅持不懈地實行溫和、審慎樂觀和求實的對外戰略;堅決加速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和決不容忍“臺獨”。這可謂“雙頭戰略”,有“軟”也有硬。
和平崛起與軍力建設:后冷戰時代的大戰略(2002至2008年)
直到晚近為止,中國的國家大戰略無疑可被濃縮為“和平發展”,依據戰略研究中的理論觀念,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對稱戰略(asymmetrical strategy),或所謂“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理論上,它意味著“揚己之長、克敵之短”和“避敵之長”。這相當于孫子式戰略方式,在中國非常悠久和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戰略傳統中有深刻的底蘊和淵源。此外,就當代中國的軍力建設和軍事現當代化而言,其戰略形態根本上說是對稱戰略(symmetrical strategy),或所謂“直接路線”(direct approach),意味著“針鋒相對”“正面攻堅”和“對陣激戰”(pitched battle)。這在精神上相當于克勞塞維茨式戰略方式。這兩類戰略方式俱非萬應靈藥,總的來說都利弊相兼。中國政府多年以言辭和實踐反復表明,它堅信中國既要大力和平發展,又要加速增強軍力和推進軍事現當代化,亦即結合使用不對稱與對稱戰略,以便盡可能兼取兩者之長和規避兩者之短。
中國多次重申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它依憑這么一個假定:為促進和平發展,一國將在絕大部分時間、絕大部分方面依靠廣義的“軟權勢”,即所有非強制性的權勢資源和權勢行使。與“硬權勢”相比,這樣的力量最不易阻擋,最少引發強烈阻力,最小成本發生,后果方面最可接受,因而一定意義上最為無敵。
然而,中國領導人顯然沒有忘記,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看,軟權勢與和平發展都有與它們的重大功能和裨益并存的局限性,從而作為對稱戰略的主要資源之一的軍力發展勢所必須,更何況還有一項歷史的經驗性常識,即世界一再證明它本身可以惡性地能動。因此,他們確信中國必須大力從事現當代軍力建設。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之后,推動軍力加速度建設和軍事加速度現當代化,實行“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后,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在繼續并加速貫徹的同時,將非戰爭軍事行動作為國家軍事力量運用的重要方式,中國的軍事戰略方針的內涵顯著豐富化,以求更加適應世界和中國的變遷。
格局大變與復雜性增生中的戰略競爭(2008至2012年)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與其為首的西方由此開始愈益顯著地相對(即使并非絕對)衰退。在此背景下,快速崛起的中國開始進入它真正當代或當前的歷史大階段。
中美兩國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影響力競爭集中于中國的緊鄰周邊,與相關的海域洋域密切相聯。這競爭一直在相當迅速地演化,而與先前若干年的圖景不同,大致直到特朗普2017年1月出任美國總統為止,美國在外交/戰略陣線上頗多斬獲,即使某些只是短暫的。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數年里,在與東亞和東南亞鄰國的關系中,中國公眾和政府兩方面的“勝利主義”顯而易見,雖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較小。“勝利主義”是關于中國對外政策方向的非傳統的理念,即中國作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國,其對外政策的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應是盡最大努力,與超級大國美國結成穩定和大體合作的關系,以便“共管”區域甚或世界,盡管實際上中國在戰略和戰略性外交方面的對外“重中之重”必須是兩個,即對美關系與近鄰關系,而不僅僅是一個即對美關系。
“戰略軍事”和“戰略經濟”:收益與風險(2013至2016年)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大力加強中國戰略性軍事力量(特別是遠洋海軍)建設,大為擴展中國的戰略活動范圍,爭取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特別是從中國海岸到第一島鏈的西太平洋西部)具有愈益增長的、無論是“軟”是“硬”的權勢影響。
服務于這目標的主要政策工具有兩大類:“戰略軍事”(strategic military)和“戰略經濟”(strategic economy)。概略地說,從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結束到2014年秋季為止,中國政府主要使用的是“戰略軍事”,它體現在中國戰略軍力建設加速推進,海上及空中軍事活動范圍顯著擴展,對美、日等國表現出強勁的競爭和強硬的反制,在南海和東海爭議地區從事密集的軍事和準軍事活動。從2014年秋天開始,中國政府實行一種有利于“戰略經濟”的戰略轉型重大決策,它基于中國巨大的經濟金融實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廣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項緊迫的國內需要,即在國內經濟增長呈緩慢但頑固的持續下行的嚴峻形勢下,力求顯著增進對中國產能的境外需求。
無論是習近平反復倡導并著力推進規模巨大的歐亞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還是中國從2014年10月起大力主導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或是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以及創設“中巴經濟走廊”和提倡“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等,都是“戰略經濟”方向上的重要事態。
然而,“戰略軍事”的某幾個重大方面依然顯要,顯見于中國基本的戰略態勢、或曰戰略復合態勢之中。中國戰略性軍力的經久急劇增強仍在繼續,甚至是以加速度繼續。中國武裝力量主要面對海洋和海陸兩棲環境的軍事斗爭準備仍加速進行。最突出的問題在于,中國對外關系和政策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兩項重中之重),即對美國和對亞洲鄰國的關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義上被“鎖在”海洋戰略競爭、海洋領土爭端以及海洋權益爭執之中。展望未來,若沒有出現可能的重大緩解或扭轉,那么結構性的戰略競爭和戰略對立很大部分將直接是關于中國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會在海洋上。
特朗普和其他事態:中國的戰略反應和初始調整(2016至2017年)
特朗普給中國政府帶來了嚴重的憂慮,因為他在競選期間就中國貿易行為和慣例發出無數次烈度空前的威脅性言辭,而這些言辭如果轉變成真實的美國政策,就將破壞中美經貿和金融關系,從而嚴重損害中國的經濟和金融。不僅如此,他蓄意逼近和觸碰中國的臺灣問題底線,明確示意他要將美國自1979年以來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當作可以舍棄的討價還價籌碼,用來逼迫中國在朝鮮和貿易等問題上對他大大退讓。這當然令中國嚴重不安。
這樣的憂慮幾乎立即產生了政策效應:習近平在應對特朗普方面采取空前耐心和審慎的做法,僅僅在臺灣和“一個中國”的核心問題上才公開表達毫無疑問的堅定,明確聲明一個中國原則不可談判。耐心、審慎、針對最核心威脅(并且只是針對這類威脅)的非常堅決的公開抵抗、純反應式方略、尋求和開發有益聯系,這些構成中國政府應對特朗普的戰略,一種幾乎急速形成的、處理意外緊急狀態似的戰略。這一戰略很快被證明頗為成功,從而成為中國多年里最精彩的對外戰略決策之一。
中國戰略態勢近乎全面的溫和化、現今的緊迫問題和仍需的戰略探求(2017年至今)
實力已顯著騰升的中國在特朗普導致美國的全球意愿和態勢雙收縮背景下參與引領世界的宏愿,中國以近乎全面的跡象,呈現出在東亞和西太平洋的新的顯著溫和化態勢,有效和顯著地廣泛改善了周邊關系,造就了十多年來中國周邊外交的最偉大成績。從戰略上說,這溫和化的性質應被認作是延宕克勞塞維茨式“勝利的頂點”(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或用通俗話說“好日子拉長著過”,因而對中國的長遠總體利益來說甚為可取,甚為積極。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對外戰略的首要困難突出體現在朝鮮半島問題和中美貿易對抗上。
2018年以來,朝鮮半島局勢發生重大變換:一方面,朝韓關系和美朝關系大為緩解;另一方面,金正恩突然訪問北京,與習近平舉行對中朝雙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級會談,中朝關系由此驟然擺脫保持得過久的歷史最低點狀態。可以認為,朝鮮徹底去核的可能性甚微,但實現部分非核化和對外政策相對和平化的前景頗可期待。在此形勢下,中國頭等要務第一是堅持中國的應有權利和作用,擴大和深化對朝鮮問題局勢劇變的實質性參與,防止和阻止中國的正當利益和關切遭到其他方面的忽視或損害;第二是維護和增進來之不易的中朝關系改善,為此首先需要適當地調整對朝經濟政策,及時和妥善地重筑現已嚴重受損的中朝關系經濟基礎。
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對抗,則不僅需要“治標”性質的綜合對策,即堅決有力的貿易報復與談判妥協意愿相結合,而且需要“治本”性質的基本認識和戰略決心,后者在一定意義上遠更重要和深刻。既有的全球化要揚長棄短、改造更新,從而獲得真正的可持續性,就不僅需要像中國政府已經反復提倡的那樣,在比較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上變得比較公正,比較均衡,而且需要多少鑒于發達國家愈益增進的抱怨甚而憤怒做出適當的調整,以便爭取它在這些國家內部恢復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會和政治基礎。當今頭號新興強國對頭號守成強國這“經典”國際政治問題不僅是國際間的權勢轉移問題,也是國際間的廣義的財富轉移問題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國內社會政治裂變問題。
中國還需要通過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調結構和全面深化改革,爭取實質性地大大開發潛能依然巨大的中國國內市場和國內資源,從而相應地降低中國對外部市場、外部資源和外部技術的依賴程度。
結語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新時代。十九大以后,中國對外政策方向將以較長期地說三個“更為大力”為特征:(1)更為大力地拓展和深化中國對全球政治經濟和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包括在某些經選擇的領域謀求中國的引領作用;(2)更為大力地爭取中國在亞洲大陸甚而更多區域的經濟優勢和外交優勢,加上與此相連的在經選擇的某些地區或要點上的戰略存在或影響;(3)更為大力地爭取盡早確立中國在西太平洋西部(即從中國海岸到第一島鏈之間的廣闊海域洋域)的戰略/軍事優勢。
放眼全球,比較中外,可謂中國大治,美國、西方和世界某些地區大亂,世界秩序變動不定,世界形勢除上述兩個基本狀態外大致撲朔迷離。因此,長期來看,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線,繼而守住底線,首先將中國自己國內的事情辦好,繼續提升中國的實力和在世界舞臺上的操作能力,以高質量發展為綱爭取實現中國國家力量和社會健康的重大升級,從而為世界秩序的進步性轉型提供一項最重要的積極條件。然而,謀遠求近,如果不能恰當地應對當前的嚴峻挑戰,將嚴重妨礙爭取盡可能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