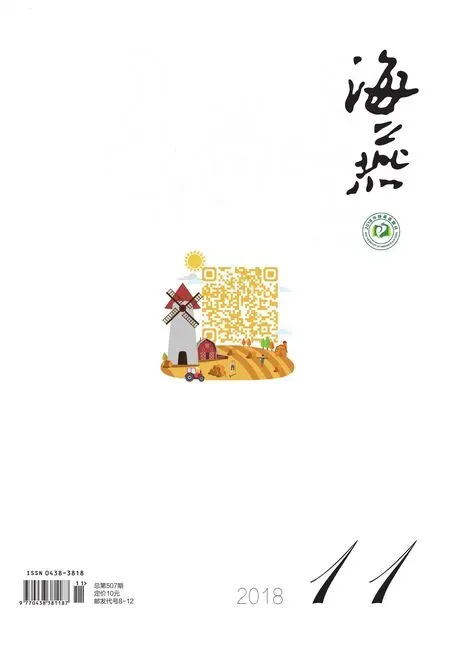柳陂是個地名
□衣向東
武漢市有個黃陂(pí)縣,是花木蘭的故鄉,我順坡滾驢,就把湖北十堰市鄖縣的柳陂(bēi)鎮,讀成了柳陂(pí)鎮。尷尬之余,我查閱漢字釋義,才知道“陂”字有四種讀音(bēi pí、 pō、 bi),大多用于地名。
我很驚訝,漢字釋義中提到了廣東陸豐市陂(bēi)洋鎮,也提到了作為方言讀音的河南南陽市社旗縣陌陂(mobi)鎮,唯獨沒有注釋柳陂鎮。
怎么會是這個樣子?有些荒謬。
柳陂生息繁衍在一條古河道上,土地肥沃,黍米豐產,植被茂盛,岸柳成蔭。柳陂的子孫們獨處一隅,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然而,20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南水北調”,柳陂成為中線水源工程的關鍵部位,柳陂的子孫們被打上了“丹江口庫區移民”的標簽,從此這個美麗富饒的小鎮,失去了世代傳承的閑適與寧靜。他們最害怕聽到“后靠”這個詞,一次次的后靠,卻總甩不掉身后上漲的江水,心里的恐慌像夏草一樣瘋長,日子過得疲憊而無序。到了21世紀初,大規模的南水北調總體工程正式啟動,柳陂鎮不但被列為“丹江口庫區移民”,還被定為最難啃的“硬骨頭”,成為各路英豪攻營拔寨的戰場。
難免有些悲情和無奈。
“湖北移民看十堰,十堰移民看鄖陽,鄖陽移民看柳陂。”原因很簡單,柳陂鎮是塊寶地,位于漢江河畔,地處鄖縣和十堰兩城區結合部,是十堰市和鄖縣城區的主要“菜籃子”基地,核心菜區的十幾個村子,人均收入過萬元。這次大移民,柳陂鎮徹底放棄了原有的居住地,整體遷移,有四萬多人在鄖縣境內就地安置,有近兩萬人要遠遷至漢南、潛江、隨縣的二十多個安置點。當然,還有一個原因,經過幾次的“后靠”,柳陂人顛沛流離,讓他們對故鄉有了特殊的理解和依戀,渴望安寧平穩的生活。好不容易安營扎寨,恢復了些元氣,卻又要背鄉離井,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本能地抵觸和掙扎,是必然的。
有人覺得,安置點有漂亮的房子,移民們卻不肯搬遷,“抵觸和掙扎”是成心鬧事,借機哄抬搬遷費。這種論調有些冷血。故土難離,窮家難舍,我從自己的父母身上,就深刻理解了這個道理。我曾經幾次把父母接到北京居住,后來又在縣城給他們買了房子,但無論多么好的居住條件,都沒有留住父母的心,即便到了80歲了,老兩口毅然回到山溝的老屋居住,他們種了一塊菜地,養了幾只雞,每日忙忙碌碌,好不快活。父親說,住在哪里都不如在老房子里睡得踏實。父親叮囑我,什么都可以賣,唯獨不能賣掉老房子。在我看來,老房子就是我的老父老母,是我生命的根。
對于柳陂移民來說,這不僅僅是一次搬遷,而是一次骨肉分離、血脈的斷裂,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很多人從此失去土地,成為打工者和手工業者,像柳絮般四處飄移。
然而,抵觸和掙扎是徒勞的,最終他們還是目睹奔涌的江水淹沒了城墻、老屋以及千年的石板路,淹沒了秦磚漢瓦、古陶和箭鏃。
這其中就有韓家洲,一個上百戶人家的古老村莊。
韓家洲坐落在江水中的孤島上,是漢江和堵河交匯處,村民都姓韓,典型的水上家族,依靠經營河沙、打魚為生,過著“桃花源”般富足而寧靜的生活。獨特的地理優勢,以及家族式的親情關系,讓他們對故土虔誠而眷戀。得知要搬遷到遙遠的隨縣,那種抵觸情緒是可以想象的。但不管怎么折騰,他們內心知道,國家意志是不可抗拒的,最終還是要告別故土。村民們編修了家譜,每戶一冊,讓子孫后代永遠記住,他們的根在韓家洲。
在一個薄霧繚繞的早晨,韓家洲村民朝江邊集結。江邊被厚重的傷感籠罩著,一切聲音都消失了,耳邊只有奔涌的江水聲。村民們默默地卸下了祖上傳下來的門板,摘下了墻上古老的相框,抱著家中的瓶瓶罐罐,牽著幾條老狗,身子搖擺著上了船。他們走的遲疑,走的拖泥帶水。
江邊,20多艘船一字排開,開動馬力駛向對岸。那一瞬間,所有人跪在船頭,凝望他們的老屋、他們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江中小島,放聲哭泣。不知是誰突然扯了一嗓《漢江號子》,隨即就有人附和,哭泣聲混合著號子聲,匯成激越的大合唱——
嗨喲 嗨喲 嗨喲嗬
趟過漩渦 喲嗬 冰冷的苦難
又爬峭壁 喲嗬 滾燙的荒涼
號子里 喲嗬
拽不完人生險灘 嗨喲嗬
號子里 拽不完歲月滄桑
……
沙啞而蒼涼的號子聲,伴隨著滾滾江水流向遠處。當年,韓家洲村民的祖先就是喊著《漢江號子》,闖過了一個個險灘,在這片江水上繁衍下來。
船靠岸,他們胸前戴上了紅花,有些局促地上了外遷的大巴車,在鑼鼓聲和掌聲中,被送出了故鄉。這個早晨,注定成為他們此生最傷感的時光。
如今,韓家洲大部分已經沉沒在江水中,只剩下一個蘑菇狀的孤島。我站在江邊,朝孤島上的韓家洲遺址眺望,似乎還能隱約聽到飄散在風中的《漢江號子》聲。我的內心泛起波瀾,有一種要登上孤島的沖動,想去尋找幾堵殘垣斷壁,尋找幾塊門板或是幾塊瓦片。據說,韓家洲的村民搬遷后,很多人看好這個美麗的小島,希望能夠建設成一個旅游度假區,然而為了呵護一江清水,柳陂鎮拒絕任何理由的開發利用,嚴禁隨意登島,一直保持著小島的自然面貌。
沿著漢江邊走去,可以看到幾個內安移民的新村,黎家店、朋儒、舒家溝臥龍崗社區……這些新村的房屋大都是聯體別墅的建筑模式,白墻灰瓦,清爽潔凈。
在去往黎家店的路上,當地朋友從路邊一棵樹上摘下幾個橢圓形的果子,遞給我說:“枇杷果,你嘗嘗。”
我生活在北方,第一次見到枇杷樹,忙去仔細打量。金黃色的枇杷果圓潤透亮,一堆一簇地夾雜在寬厚碧綠的樹葉中,像掛滿樹枝的小燈籠,煞是可愛。我原以為這是一棵野生枇杷樹,果子一定酸澀難吃,于是小心翼翼地將剝了皮的果子放在嘴里,沒想到果肉細嫩潤滑,果汁豐沛甜美。我忍不住問,野生枇杷有這么甜呀?陪同我的柳陂朋友笑了,說這不是野生的,是移民搬遷時留下來的。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在枇杷樹的后面是一個土坡,那里有殘剩的半截房基,掩埋在齊腰深的雜草中。不用問,這里曾是一個小山村,很多房屋都被江水淹沒了。
我忍不住再次打量孤單的枇杷樹,有些心酸。我無法猜想枇杷樹的主人搬遷時,是一種什么樣的心境,將這棵碗口粗的枇杷樹獨自留在這里。不過我可以肯定,這棵被遺棄的枇杷樹,一定會多次出現在主人的夢中。
我自然自語地說:“好可惜,這么好的枇杷樹……”
柳陂的朋友明白我的意思,指著腳下的江水對我說:“一江清水送北京,柳陂人為了你們北京人吃水,把祖墳都刨了,帶著祖先的尸骨遠走他鄉。”突然間,我覺得有些羞愧和內疚,似乎這些移民的命運與我有著某種聯系。
其實,有很多北京人并不知道有柳陂這個小鎮,更不知道柳陂人在南水北調中做出的犧牲。我突然想,在“陂”的漢字釋義中,應該增加這樣一個詞條:陂(bēi),地名,湖北十堰市鄖縣柳陂鎮,南水北調中線最重要的蓄水段,北京人的“大水缸”。
果真如此,才算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