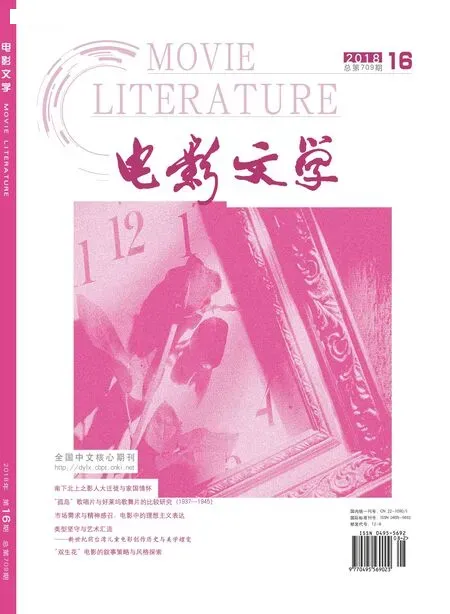國產動畫電影視覺審美文化解讀
劉 也
(武藏野美術大學,日本 東京 187-8505)
動畫電影與真人電影的視覺語言有所區別,在設置表意功能和創造藝術效果上,它有著更大的自由度。國產動畫電影迄今已有近百年歷史,當下,動畫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媒體,也是一種受眾廣泛的敘事體,尤其是在視覺時代,動畫電影更是成為這一文化生態發展中的重要推動力。這也就使得,對其視覺審美文化這一關乎其藝術本體性的研究,顯得日益關鍵和重要。
一、國產動畫電影視覺上的“傳統”與“現代”
中國動畫起步于20世紀20年代,在近一百年的發展歷程中遭遇了重重挫折,也曾有過以“中國學派”震驚世界的輝煌時段。可惜的是,“中國學派”真正大放異彩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九年,隨著“文革”的開始,中國動畫陷入了幾近停滯的困境中。而在“文革”結束之后,中國動畫盡管開始了復蘇,但是在中國社會逐漸開放的過程中,隨著《鐵臂阿童木》等外國動畫的引入,以及電視機在各個家庭中的普及,中國動畫的市場被外國動畫輕易占領,國產動畫也出現了滑坡。但外來優秀動畫的涌入也意味著其產業模式、創作方法進入到中國來,國產動畫開始以全新的面貌,在全新的產業體系中出現在觀眾的面前。那么在對比“新”與“舊”時,我們不難發現,二者最大的區別并非內容,如“中國學派”最引以為豪的《大鬧天宮》(1961)和近年來引起最大轟動的國產動畫《大圣歸來》(2015)盡管間隔了半個多世紀,但都取材于名著《西游記》。國產動畫一路走來,真正的新舊之別,在于視覺審美上。
一般來說,靜止的一幀畫面在以每秒24幀連續播放的情況下就構成了動畫,而動畫在結合了電影語言規律的安排后就成為動畫電影。和真人電影一樣,動畫電影也有著鮮明的審美風格。人們普遍認為,美式動畫電影情節幽默夸張,畫風追求寫實,蘇聯動畫電影語言詼諧,造型滑稽,而日本動畫電影則崇尚手繪及較為深刻的內容等。中國的“中國學派”則以藝術片為主,在充分吸收和借鑒了中國傳統美學的精髓之后,為世人貢獻出了集多種中國傳統藝術門類于一體,極具中華民族風格的動畫形式,如在“中國學派”的水墨動畫、剪紙動畫等中,有著美日動畫不具備的視覺審美特征。而到了當代,在商業經濟與全球化的推動下,國產動畫不得不追求經濟利益,走上了一條以商業片為主的發展道路。這使得在創作中,美學往往不得不讓位于模式化的、高效的流水線生產方式。同時由于其他動畫強國的強大影響力,美國動畫電影的尚實審美,日本動畫電影的唯美審美,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國產動畫電影。大批中國動畫人力圖在保留民族審美精髓的情況下,吸納外來審美文化,迎合視覺文化時代觀眾的趣味,將蜚聲國際的外國動畫的優點,與中國的傳統題材相結合,在全球化的同時建立本土化,打造了一批屬于新型視覺審美文化的作品。盡管其還在探索階段,但已經足夠被拈出,作為與“中國學派”相對的一種審美傾向被進行解讀。
二、國產動畫電影的傳統視覺審美文化
“中國學派”代表的正是一種根植于中國古典傳統的視覺審美文化,它有著鮮明的“中式”烙印,大量視覺審美文化來自中國古代繪畫或詩意的美學追求。
(一)虛實相生
虛實相生原指在國畫藝術中,畫布上有筆觸的地方與留白的地方以一個合理的比例存在。一旦實多而虛少,那么畫幅就會存在主體過多,分散觀者注意力,甚至讓觀者無法識別的問題,而一旦虛多實少,畫面內容又會顯得偏少,“虛”所本應承擔的“幽遠”美感也將被空無取代。在國產動畫電影中,不乏直接運用國畫藝術的水墨動畫,這一類動畫充分地發揚了虛實相生的視覺審美文化。例如在《小蝌蚪找媽媽》(1961)中,小蝌蚪在變成青蛙之前一直在水中游動,但是水在國畫中很少直接畫出,大多是通過留白來體現。在電影中,水也是“虛”的,而飄搖的水草、浮萍,動物在水面上蕩起的漣漪等,這些“實”的內容無不在提醒著觀眾清澈見底的池水的存在。正如電影理論家伊夫特·皮洛曾經指出的:“我們并不知道我們看到了什么,恰恰相反,我們知道什么才會看到什么。”美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共同證實了,人們觀看某樣事物的過程,并不是一個機械、被動的過程,而是一個主動的認識和發現的過程。人類的看是存在現在的目的和認知的。法蘭克福學派也指出,大眾的看并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的行為,而是復雜的,與文化相關的社會行為。觀眾早已有了“蝌蚪游于水中”的知識儲備,因此水并不需要畫出,觀眾也能產生水的想象。虛和實在這里形成了一種協調的互相作用。
(二)幽情逸韻
幽情逸韻也來自國畫,強調的是一種深沉、超俗的情致和韻味,在國產動畫電影中,這則體現在動畫人熱衷于繪制優美、雅致的意象,甚至在部分電影中,觀眾在視覺上獲得的享受要遠遠多于從情節中得到的娛樂。例如在《牧笛》(1963)中,電影無意講述一個情節曲折的故事,而更像是給觀眾提供了一個初夏時分,人與牛怡然自得,和諧相處的生活小品圖。電影用青山翠竹等,構成了一個幽靜深遠的鄉野環境,而牧童則身心放松,在吹了一陣自己的短笛之后,進入到夢鄉之中,來到了一個有著奇峰疊嶂,飛流瀑布,白鷺黃雀的世外仙境。牧童想要自己的水牛跟自己回家,水牛卻因為貪戀這里的美景而不愿離去。直到夢醒,牧童用短笛召喚來牛,在紅霞滿天,炊煙裊裊中遠去。與之類似的還有《山水情》(1988)等,整部電影沒有一句對白,但是古琴藝術高山流水,知音難覓的千古幽情,老琴師和少年師徒相得的厚誼和灑脫的風骨,都通過畫面傳達給了觀眾。同時,道家師法自然、與世無爭思想和禪宗明心見性,“頓悟”“不立文字”的靈感,這些極端抽象的內容,也都被電影以風雨、山巒、流水、白云等意象加以表達,即使是并不了解如《廣陵》絕響等典故的觀眾,也能從視覺上備感清新、淡雅,感受到畫面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這一類電影往往都在視覺上重申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主張,人對自然采取的是順應、尊敬的態度。
(三)奇趣靈動
無論是在角色造型,人物動作,還是在場景等的設計中,“中國學派”及其在復蘇時代的后繼者都崇尚一種奇趣與靈動的美感。同樣是讓觀眾感到有趣,國產動畫電影并不僅僅滿足于對真實物象進行變形,還強調某種“以少見多”,這與美國的夸張、蘇聯的滑稽等又是略有區別的。例如在《三個和尚》(Three
Monks
,1981)中,紅衣小和尚是廟的第一個主人,他身材適中,臉上有兩塊紅暈,意味著他最年輕,也最害羞,缺乏主見,才會在自己是最先來到廟的情況下,無法給兩個后來的和尚立規矩;第二個藍衣瘦高和尚愿意和紅衣小和尚一起抬水,瘦高身材表示了他并非懶人,長方形臉和藍色僧袍暗示了他不善變通,循規蹈矩的個性;而導致沒水喝的第三個和尚則是黃衣胖和尚,矮胖身材、厚嘴唇則顯示了他憨厚懶惰的一面,所以他才會不顧他人的感受,一來就喝光了廟里的存水。從傳統戲劇,建筑等攝取視覺元素,也是增進電影奇趣靈動性的方式。如《天書奇譚》(1983)中,縣令貪得無厭,見錢眼開,他的形象就是戲劇中的“丑”的扮相,留著三撇胡須,臉上有一大塊白色,而烏紗帽的帽翅兩端則是兩個銅錢形狀的圓。又如在《驕傲的將軍》(1956)、《大鬧天宮》中,人物的面目和武術動作,很多都來自京劇,將軍和孫悟空的臉無疑來自京劇中的“花臉”,暗示了人物的性格,而打斗則往往并不落到實處,點到為止,身段優美,飄逸靈動,讓觀眾獲得美的享受。三、國產動畫電影的現代視覺審美文化
及至20世紀90年代,多種原因使得國產動畫電影出現了新的視覺審美傾向。第一,全球都開始了從語言文化向著視覺文化的大轉型,這必然會影響到各國動畫電影在審美形態、具體繪制方式等方面的轉向;第二,全球化使得動畫電影作為文化交流的主流藝術之一,也必須在視覺審美上呼應與跟進美日動畫這樣的成功者;第三,國產動畫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迎來了自己的產業大規模、高速度發展階段。
(一)視覺文化
視覺文化最早出自匈牙利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的《電影美學》,指的是電影攝像機以一種超過印刷術的方式進行傳播,人們通過視覺來體驗事件,乃至情感、思想等。而在動畫電影中,則體現在對可視性的高度重視,一部部充斥著“景觀”的電影出現在觀眾面前。正如尼古拉斯·米爾佐夫在《視覺文化導論》中指出的:“可視性之所以被看重,是因為當今人類的經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視覺化和具象化了。”國產動畫電影開始走上一條高投入、高科技、高產出的路線,在視覺上有了對三維、高清等的明確要求。而在審美上,則逐漸由傳統的以畫面簡約,隱喻豐贍為美,變為以逼真可感,豐富炫酷為美;從崇尚意在言外,意在畫外,變為了直接強化視覺效果,給予觀眾大量信息。這在一些中美合拍的動畫電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運用了3D技術的《魔比斯環》(2005),以梯田、竹林、長城等畫面讓觀眾目不暇接的《媽媽咪鴨》(2018)等。而在純中式“血統”的動畫電影中,如《寶葫蘆的秘密》(2007)、《風云決》(2008)、《藏羚王之雪域精靈》(2015)等莫不如此,美景、魔法效果、異度空間等無處不在,中國動畫人可謂在制造可看性、娛樂性上不遺余力。
(二)后現代主義文化
后現代主義文化促成了在電影中出現各類對經典的解構、戲仿,以及各類原本屬于不同領域、不同風格的元素的拼貼,曾經的“中國學派”強調風格、視覺與敘事的高度統一,然而在后現代時代,影像的拼貼不再被排斥。例如在《寶蓮燈》(1999)中,孫悟空的形象保留了《大鬧天宮》時期的京劇臉譜形象,云霧繚繞的天宮也保留了“中國學派”時期的水墨風格,沉香的形象則是與葫蘆娃類似的典型中式少年,而嘎妹、小猴和哮天犬等的形象則顯然借鑒了迪士尼的視覺風格。此外,與劇情關系并不大的編鐘、兵馬俑,嘎妹族人的“望月節”舞蹈等,則作為中國元素被加入其中。與之類似的還有如《麥兜故事》(2001)、《兔俠傳奇》(2011)、《大魚海棠》(2016)、《小門神》(2016),在后現代的氛圍中,觀眾早已不會將電影中的拼貼視為不和諧,而只會從各類符號和影像中得到狂歡的享受。
在時間的推移中,國產動畫在視覺審美上走過了一條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之路。在娛樂化、商業化的趨勢已成必然,同時外國動畫巨頭的地位又一時不可撼動的情況下,國產動畫也一度找不準自己的定位,表現不能令人滿意。但近年來《大圣歸來》《大魚海棠》等得到市場與專家一致認可的優秀之作的涌現,為動畫人在視覺審美上昭示出一條可行之路,即國產動畫完全保留民族特色與傳統美學元素,同時兼顧現代審美中重視覺、尚綜合的傾向,在精英性和大眾性、中國風和國際化中找到平衡點,以走向第二次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