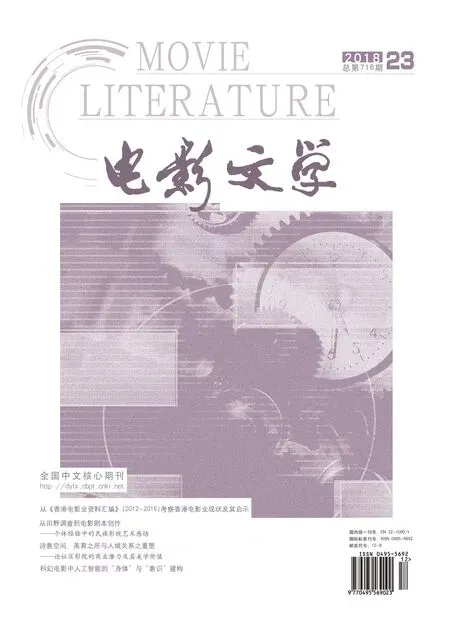呂克·貝松電影的空間建構及其美學風格
林 博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河南 三門峽 472000)
作為法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導演及編劇,呂克·貝松自20世紀就開始了電影拍攝和劇本創作的藝術生涯。包括最近上映的科幻電影《星際特工:千星之城》在內,呂克·貝松的電影主題始終圍繞著科幻、懸疑、動作的商業電影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稱之為法國乃至世界商業電影史上一顆最為璀璨的明星。呂克·貝松的電影創作沒有因為商業電影這一類型而陷入同類型題材的自我重復之中,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完成著自我的超越,其中最重要的特質就在于呂克·貝松在科幻與奇幻的電影類型中構建起來的超出常人想象的幻想世界。這種構建不僅僅在于文本上對于某一他者空間的描述,也同樣包括在電影的鏡頭對于這些空間的真實還原,或者說是對這些空間的真實表現。在此基礎上,呂克·貝松在更加注重情節的電影文本中也沒有忽視電影敘事空間對于敘事和實現觀眾對電影心理預期的重要作用,他不斷嘗試突破穩定的電影敘事,不斷拓展空間在電影中產生意義的范疇。在這種拓展的過程中,呂克·貝松逐漸形成了屬于自我的話語的審美特征,并且在這一審美特征的基礎上,穩固了自我的電影話語,形成了超越同時代大多數電影文本創作者的經典電影文本體系。
如果從空間上來看呂克·貝松的電影文本創作,實際上可以有兩個維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其一是呂克·貝松所試圖再現出來的宏闊和新奇的幻想世界。作為一位西方的電影導演,呂克·貝松不僅僅利用先進的電影工業制作技術完成了獨屬于他的幻想空間,并且在這個實現的層面上賦予了幻想空間更為深刻的故事隱喻和邏輯內涵;另一個則是呂克·貝松在一般的故事性電影文本中再現了一種豐富的法國生活,并且將這種生活巧妙地融合進了多種空間之中,在空間和人物之間形成了一條物質紐帶,將人物情感和敘事的開展聯結了起來。
在多重空間的表現之下,呂克·貝松成功地在商業電影單一化、類型化的表達中突圍,通過空間建立起來的橋梁不僅溝通了他的電影文本中人物與情節的關系,更加成為這位國際導演所處的文化背景內化到他的電影文本中的一種方式。在他獨特的空間建構過程中,人物在空間之中的情感發展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其他電影文本的邏輯關系,在這種邏輯關系之下,所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特異的人物性格,也有創作者所賦予在人本身的思考與情感。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呂克·貝松對于人本身和空間的美學思考形成了一種互文的關系,這種互文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呂克·貝松電影文本體系之中的一個主體內容,在他豐富的電影文本創造過程中成為他表達自我和自我思考的不同側面,最終構成了他電影創作的美學體系。
一、兩種空間的建構與情感邏輯
在呂克·貝松的電影文本創作過程中,關于電影空間的構造是他電影文本創作的底色,如果將文本理解為一種話語邏輯的外在形式,那么空間的建構問題無疑是這種外在形式所賦予在文本之中的一種潛在的隱喻。當我們把這種隱喻理解為更為深刻的創作心理的時候就不難發現,不論是故事情節還是人物塑造都會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規律。這種規律在文本上來看或多或少存在著偶然的因素,似乎人物的發展難以逃離一種現實命運的掌控。而作者設計的故事現實,至少是那些可以決定人物命運的偶然事件都是出于作者本人的一種欲望和沖動。但實際上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不論是故事中的現實條件還是偶然的事件都是來自一種更為復雜和隱秘的創作動機。這種動機深埋在作者的心中,而即使作為作者主觀意識的一個部分,這種動機也不是隨意操控的,它呈現在故事之中一定要符合作者的邏輯和情感立場,甚至在一般情況下連最微小的不協調也不會出現,這是作者的主觀意識驅動著作者不去破壞這種故事的內在邏輯。
這種內在邏輯在電影文本中的存在一般有別于文字文本的表達,因為電影文本的創作者一般難以運用線性的符號將文本完整地表達出來。在電影文本中,電影創作者勢必要使用那些富有意味的鏡頭和直觀的人物關系進行表達。而這些文本表達符號都必須在具體的環境中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環境的建構往往就會成為尋找到文本邏輯的重要線索。
在呂克·貝松的電影文本創作中,他所試圖營造的文本空間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個層面上是在他的電影中的一個重要題材科幻類型的電影文本所涉及的幻想型空間。這種空間類型之所以被稱為幻想型空間,不僅僅是由于在幻想類的電影中所獨具特色的文本環境,而且還在于這些表面上似以宏闊真實見長的幻想場景所具有的來自場景本身的一種隱喻關系;另外一個方面,呂克·貝松還著重摹畫了富有法國風情的人物生活場景,構建起了一個細膩多元的法國生活圖景,甚至一些沒有發生在法國的敘事場景中,這種努力也難以被故事所限制,展示出深刻的法國文化圖景。
從呂克·貝松的幻想類的電影來看,不論是新近的《星際特工:千星之城》,還是已經成為世界電影歷史中經典的電影文本《第五元素》,呂克·貝松的幻想類題材的幻想空間永遠都是別出心裁的,在還原出的幻想世界中,真實和新意永遠都是最先傳達到讀者眼前的感受。比如在他的電影《星際特工:千星之城》中營造的規模宏大的星際貿易基地,這個基地所處的位置是一個荒漠地帶,本身是一個沙漠。但是通過特定的媒介,這個現實中的荒漠成為一個多次元的空間地帶,而這些不同次元空間中本身又都是無限延展的,這個想象的空間成為一種真實的象征物,空間的廣闊所帶來的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和多元的文化融合。雖然在電影文本中,不同的空間之間原則上不能夠彼此溝通,但是在敘事上這些空間實現了跨越,形成了一種文化的融通。更為耐人尋味的是,由呂克·貝松導演或者編劇的電影文本中,這些幻想世界大多是垂直發展的,平面空間本身具有固定性的特征,或者說平面空間的邊界是不會隨意被突破的。因此在呂克·貝松的幻想世界中,世界在另一個角度實現了自我的空間突破,成為縱向的空間發展。實際上縱向的空間發展不僅僅是一種對于未來世界的科幻想象,這種縱向空間的發展圖示在呂克·貝松的其他電影文本中也有體現。比如他的經典奇幻電影《亞瑟和他的迷你王國》中,迷你世界也是呈現出縱向發展的特征。這種特征促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可能,不同的區域自然地被分為若干個區域性明顯的空間模塊,相互之間發生作用,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圖景。
與幻想類的電影文本空間不同,呂克·貝松的法國生活底色卻不算顯眼地融入他的電影文本創作過程中。在他的電影中法國文化中的回歸家庭和浪漫色彩永遠是非常濃烈的。古典主義的建筑風格和緊湊溫暖的家庭氛圍也是最為常見的空間主題。這種濃重的生活化的空間場景表達雖然不鮮見于各個國家優秀導演的自我表達中,但是依托這些空間特質進行人物表達的文本卻并不多見。換言之,在呂克·貝松的電影文本之中,人物本身通過空間的間接表達就已經成為法國文化中某些特質的代言者,這種代表性甚至超越了國別和文化背景的限制,使之本身就成了電影文本作者的法國情結表達。比如在最具有代表性的《這個殺手不太冷》中,兩個主要人物身上充滿了法國文化的浪漫色彩,甚至衍生出了一種超越生死與人性本身的情感訴求。當然這畢竟是在法國語境之下的情感表達。另外一部美國電影《致命黑蘭》在這個精神的處理上則更加具有代表性。在這部電影中,對于初到美國的卡塔麗亞在美國的成長生活涉及得很少,在一定程度上她成為一個美國文化的他者。但是在另一個角度上,她的最主要生活場景依然是在一個更加具有本土文化特質的家庭中,這個家庭空間的塑造非常接近法國和法屬殖民地的文化特點,甚至在整個文本的敘事高潮部分,空間的主要視域還是集中在一個法式的別墅之中,使得美國的本土文化并沒有過多地出現在電影文本的敘事中。
二、人性美學的最終指向
人物在空間環境中的活動在文本層面上看是遵守著一定的敘事原則不斷進行的,但實際上人物與空間環境的交互過程不僅取決于敘事的邏輯,在某種程度上也由空間本身所決定。空間本身的象征意義就如上文所論及的,不僅帶有創作者的心理偏好,更帶有一種濃烈的民族文化的情感認同。這種情感認同聯系起了創作者和敘事中的人物之間的關系,也同時聯系起了敘事人物與文本所指涉的文化背景之間的聯系。換言之,實際上從電影文本的角度出發,不難發現在呂克·貝松的系列電影中,人物始終都不是存在于一個沒有情感內核的場域之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在試圖尋找到回歸自我空間的方式。在這個尋找的過程中人物對于情感空間逐漸形成了一種依賴,人物也更加渴望和敘事空間保持某種關系,從而獲得情感上的安慰。
然而在電影文本中,敘事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要強迫人物脫離當前的穩定情感空間,進入到一個重新尋找和發現的過程中去。當然這種強迫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未必是由創作者本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創作者都會找到一個相對極端的敘事矛盾來相對草率地解決這個問題。這不僅僅是呂克·貝松某些電影的敗筆,同時也是大多數商業電影都會面臨的一個尷尬問題,那就是在人物似乎受到某種命定式的詛咒,必須離開當前的空間環境,才能展開故事的內容。因此,與其說是敘事的變化,毋寧說在一定程度上是敘事空間的變化與人在空間的脫離成為這種類型文本的敘事開端。但是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空間對于人的情感指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不論以何種原因脫離了這個穩定的環境之后,電影文本的敘事中心就都集中在了人物的情感找尋這個問題上,伴隨著個人的情感找尋,人物在敘事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就發生了空間意義上的回歸。
在上文所論及的情感回歸,在呂克·貝松的電影文本中有著一個非常明顯的形象群體,這個群體就是他鏡頭中的女性。這些女性在呂克·貝松的電影中有著共同的情感模式,她們都極力隱藏自我的真實身份和歷史,試圖去打破所處的社會身份空間界限,進入到一個更加純粹的個人情感世界,努力地營造起一個值得依戀的情感化空間。她們所扮演的獨立人格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一般的社會限制,但是她們依然渴望來自家庭的庇護,或者說她們還是極度渴望回歸到曾經擁有的穩定的情感空間中。實際上雖然脫離情感空間的文本敘事稍嫌草率,但是在彼時尚未脫離的情感空間所存在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這些曾經存在于人物生活中、最終得到回歸的情感空間,對于創作者本人或者敘事中的人物來說,是必然存在的,在脫離之后的尋找,也是事先承認了這種情感關系的穩定性和先驗性的特征。這種回歸在呂克·貝松的敘事中是必然的,比如電影《尼基塔》中,尼基塔成為殺手之后,愛上了她后來的丈夫,她渴望著回歸到家庭之中,但是嘗試卻以失敗告終。這種失敗在呂克·貝松同類型的題材中并不少見,電影《致命黑蘭》《這個殺手不太冷》《第五元素》《地下鐵》都是這種邏輯關系之下的文本代表。這實際上說明,在人物身份與空間關系互相抵觸的前提條件下,這種情感關系的終止也同樣是不可逆的。
這種不可逆轉的現象似乎是在說明,空間不僅僅是一個冰冷的建筑或者是鏡頭后景,而是通過人物的情感變化,逐漸在電影中成為一種人化的物自體。在鏡頭語言的再現下,一切電影中的物質都帶有了這種物自體所派生出來的人化色彩。人的身份與人的情感表達,都借由這種人化的象征間接地暗示了出來,形成了一種互相呼應的空間與人物之間的互動關系。以這種互動關系作為前提,作者所想表達的核心情感內容也就明確了起來,這就是關于人的表達,或者說就是關于人性美與人的情感關系的指認。這種情感關系的建立超越了一般認為的社會情感屬性,因為其背后有著復雜的社會身份作為發展的背景,因此這種情感聯系的建構顯得尤其可貴。《這個殺手不太冷》中這種情感的關系是一個殺手和一個小女孩之間超越一般情感屬性的情感紐帶,因為兩者社會身份的差異而顯示出這份情感的陌生與可貴。在《尼基塔》中,尼基塔與丈夫、上司在家中共進晚餐時的情感氛圍,也不同于普通的家庭聚會,而更加彰顯出了一種來自普遍人性中的高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