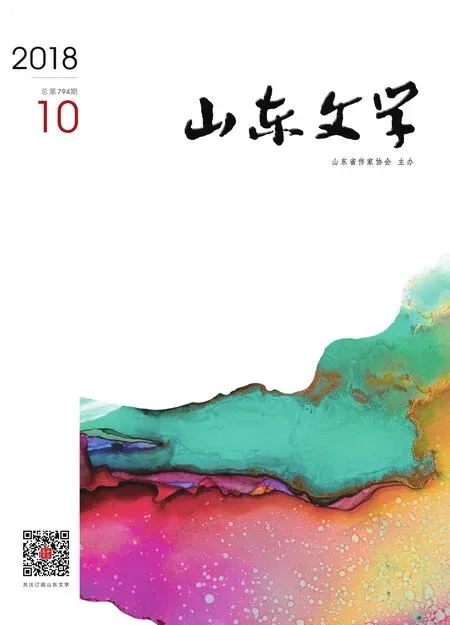娘親周年祭
夏立君
2017年,我過了一年沒娘的日子。娘用她的影子,跟了我這一年。2016年12月8日19時許,娘走完了她87歲人生。
幾十年間,娘偶爾說及的一些數字,給了我或輕或重的刺激。還有一些與娘有關的數字,是我親歷。這些數字的共同特點,一是數目小,二是都與娘的生命、生存相關。
“二十五那年,俺一年掉了五顆大牙。三十三那年,滿口牙掉得一顆不剩了。”娘25歲時,大姐4歲,大哥兩歲,二哥等待出生。娘33歲那年,二姐4歲,我兩歲,小弟出生,小妹還在后面。除了我娘,我沒見過第二位33歲就掉光滿口牙的人。到現在,年過五十的我亦缺齒數枚,都是因牙疼,一怒之下主動讓牙醫給拔掉的。娘卻從沒勞動牙醫,娘說:“一口牙,都是一顆一顆自己疼掉的。”疼,疼,記憶中未老時的娘總是這里疼那里疼。
娘艱難地活過了四十歲,活過了五十歲,身體竟漸漸好了。娘對生活的滿意度越來越高。到了晚年,娘的這一感慨我不知聽到多少回:“做夢也夢不著呀,還有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燒的日子等著俺。”
約在六七十歲時,娘就常常這樣感慨了:“活了不少了。哪敢想能活到這啊。”娘還說:“三十多歲上,俺就求神保佑,讓俺活到您姥娘那年紀。活到那年紀,孩子也就不小了。要是撂下一窩孩,還有吃奶的孩,那是多大的罪呀。”
姥娘活到什么年紀?41歲。娘說:“老年間,女人活不長啊。您姥娘姊妹六個,您姥娘是老二,俺那五個姨,只大姨比您姥娘多活了幾歲,也沒過五十,另四個姨沒一個過四十的。三姨,二十五生孩子時,大人孩子一塊沒了。四姨,十九生孩子時沒了,孩子活了……”兒時,我對人生的第一恐懼就是:單薄如紙、病體支離的娘不知哪啥就會死去。有一回,娘歪靠在堂屋門上,閉上眼睛,臉色如死。我害怕了,伸手摸娘的臉。娘睜開眼,露出異樣的笑,說:“老三啊,怕娘死了是吧?娘死不了,娘不敢死呀。”
姥娘病故時,姥爺39歲,娘23歲。姥爺十五六歲就成家了。娘是姥爺第一個孩子。娘19歲嫁到我家。又過了一些年,31歲的大舅母病故,撇下四個孩子,大的9歲,小的尚在襁褓。那年大舅才29歲。姥爺、大舅因家貧,都沒能再娶。還有個二舅,有些弱智,更無成家可能。兒時,我去沒有姥娘沒有舅母的姥娘家,見到的尋常景象就是:兩代三個悲慘男人默默勞作或默默相對,有時會聽見作為家中頂梁柱的大舅,對著雞鴨或人怒喝一聲。娘這樣感嘆她的娘家:“出門三條光棍,進門三條光棍,天底下上哪找這樣的人家呀。”
2015年8月,娘因跌倒嚴重骨折,在我堅持下,讓娘來我工作地日照做了股骨頭置換手術。風險不小,但手術成功,娘能扶助步器走路了。我樂觀地以為,娘還會有數年光景的。
2016年春節,我照例回沂蒙山老家陪娘過年。初一這天,娘表現出諸多異常。娘突然要求看送老衣,怎么勸也無用,大姐只好找出來給她看。二十多年前,娘剛六十歲,就“親自”一針一線為自己縫制好全套送老衣。娘把那衣物一一看過,笑道:“怪好哇,就這身衣裳穿不破。”娘又囑咐兒女早備下荷葉和棉花籽。沂蒙葬俗中要用到這個。娘另一異常是:對自己已邁入87歲門檻怎么也不認。不論誰問她年紀,她說出的歲數都是錯的,她總是往小里說,竟然一次也沒說出87歲。娘此前并無癡呆癥狀,對人情世事反應一切正常,并且特別清楚這一天是新年初一。難道娘活不過87歲了?
兩年多前,2014年新春,已近彌留之際且患老年癡呆癥的83歲老父,突然較清醒,癡呆癥狀亦變輕。老父一遍遍呼喚死亡的到來,好幾天早晨醒來第一句話就是:“我咋還沒死啊?”一天,爹盯著我娘問:“您什么年紀了?”娘說:“您八十三,我大您兩歲,不是八十五了?”爹異常驚訝:“俺那娘唉,您八十五了,八十五了,您能活八十五呀,您都死了好幾個死了哇。”爹這樣說著,竟無力地抽泣起來。爹咽氣前數日,我一直守在身邊。這些話與場景,是我親歷。
2016年4月,手術后扶杖而行的娘再次跌倒,雖沒重傷,卻不能下地行走了。我們兄妹七人輪流照顧,輪到我,亦請假回去。我們將娘從里間搬到外間,外間空間大,光線好。窗外屋檐下有一窩燕子。這窩燕子年年春天歸來,夏秋之交帶著新養育的兒女離開。
娘躺在床頭就能看見這窩生靈的動靜。娘一心一意看這窩燕子。一天,娘說:“這窩燕子八成是抱(孵)出小燕了。”我觀察了一下,發現果然是孵出雛燕了。我對娘說了,娘開心地笑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風燭殘年的娘,笑得竟這樣好看動人。有這感覺是因為這是我娘嗎?當然是,又不全是。我很早就特別留意到我娘的笑。我曾在兄妹中說過:你看咱娘這笑哇,哪個老年婦女能有這種笑哇。娘帶笑意的照片,都是我們偷拍的,若娘知道是照相,立即就把臉僵起來,你怎么哄勸調動都無用。娘蒙昧善良,一生與任何人都無瓜葛是非,到老來滿面慈祥,整日笑意盈盈且自言自語。若問娘說什么,娘就一臉羞怯與茫然:“說什么?俺說什么來?沒說什么呀。”娘一生羞怯,無自信。娘的笑,是老貌蒼顏加上少女般的羞怯。當下世道,不論在什么人臉上,羞怯大約都是極稀罕表情了。我從其他人臉上確實沒見過我娘那樣的笑。娘這個年紀,裹小腳的人已不多了,娘卻從七八歲時就開始裹,裹出了一雙罕見小腳。瘦小個子配上小腳,再配上永遠收收著的羞怯神情,簡直就是“傳統”所需要的女人標本。
娘笑著,抬手指指燕子窩:“兩個老燕子呀——穿梭一樣啊,飛出去——飛回來,飛回來——飛出去,那還不是為孩子打食啊。”娘又說:“老三,你看沒看見窩里有幾個小燕兒?”我說:“那得踏梯子才行。”娘說:“別,別,可別嚇著它們。當爹的、當娘的,不易啊。”
我握著娘的手,別過臉去。我的淚流了下來。我轉過臉來時,看見娘仍望著燕子窩。娘一直笑著。趁老燕子都出去打食了,我找來梯子偷窺了燕窩。我看見了人類不該看見的景象:三只連頭都懶得動的新生兒,光溜溜趴在窩底。我聞到了一種與人類迥異的氣息,它們發出了不安的唧唧聲。
我對娘說:“娘,窩里有三個小燕,還沒長毛呢。”娘又笑了:“噢,你看著了?老燕子看沒看著你?千萬別嚇著它們,千萬別把它們嚇得不敢回家了哇。要是撇下三個光溜溜的孩子,罪可不小哇。它們啊,借人家的屋檐過日子。”它們,它們,娘這一生,對牛羊豬狗螞蟻等等,總是使用“它們”。我們與它們,不就是世界嗎?兒時,我惡作劇的用腳踩踏忽然出現在我家天井的一支螞蟻大軍,娘說:“老三,你咋作這個業?它們怎么你了,你作踐它們?”應該是數十年前了,有一回,忘了是何原因,我在娘面前說了某人狠話。娘不安地望著我說:老三,可別這樣說,望人好自己才好哇。我或許終生不如娘善良,但娘這話,我不敢忘。
娘生育了八胎,四女四男,活下來七個,三女四男,一家九口。我是四男中老三。娘第一個孩子,大姐上邊的那個姐,八個月大時夭折了。娘不止一次說:“那個孩兒可好了,怪俊。肚子里長脾子,你奶奶給艾灸,肚子上灸了一個窟窿。窟窿老長不好。沒了。”兒時,又常聽見娘感慨:“九張嘴九個填不滿的窟窿啊。”娘這八胎,只生第一胎時我奶奶在場,其他七胎全是娘自己給自己接生。或床上,或地上,或院里,或灶前,或隆冬,或盛夏,或深秋,或初春。娘“以大命換小命”之時,爹竟然沒一次在家。那時的爹大約就是那不停穿梭打食的老燕子。
我再次回老家時,見滿院燕子飛。原來是老燕子領小燕子練習“出飛”。這時的娘已沒能力關心燕子了。娘已不說話了,偶爾會蹦出一兩個字。后來,一個字也沒了。娘的飯量一減再減,只能進點流質食物了。跟村醫說一說娘的情況,人家總找理由不上門。對這么老的人,持淡漠態度似乎是自然的。
11月29日,大哥來電說娘狀況不好了。我當晚驅車趕回,娘已閉嘴拒食。大哥用拔掉針頭的針管推進去點食水,娘卻順利咽下去了。就這樣喂,娘似乎又穩定了。手不動,腳不動,眼珠也幾乎不動,但還會吞咽。娘的手腫腳腫,應當是腎不行了。大哥懂點醫道,說娘呼吸平穩,脈搏還行,還能活幾天甚至更長。娘的一個叔伯妹妹也嫁在這村,天天往這跑。姨說:“俺那姐,腳腫成這樣,送老鞋還能穿上嗎?”姨命令找出送老鞋,一穿就穿上了。姨又說:“俺那姐唉,您這鞋可不小哇!”娘一生不難為人,沒有人會在娘跟前感到自己沒有余地。大家一致同意給娘穿上送老衣。姨又說:“這樣了,還喂?還喂?這還是您娘嗎?早不是您娘了。”姨又說:“俺那好姐唉,您八十七了,老壽星了,好營生也吃了,好衣裳也穿了,快走吧,別折騰孩子了,都盡孝心了,快走吧,俺那好姐。”姨又說:“姐,你一輩子好脾氣,一輩子不犟,末末了你可別犟啊。”姨這是要求俺娘提高覺悟。姨還叫姐,卻說娘不是我們的娘了。
送老衣穿上數日了。姨的驚訝焦急程度一天比一天厲害。姨無奈地看著極耐心呼吸卻不理會這個世界的娘。姨忽然說娘是邪靈附體了。姨扭頭去找我大姐商量驅邪。姨對我大姐說,找剛下過仔豬的老母豬圈里的墊圈草,在床前烤一烤熏一熏。這種草點燃后其味道一定能熏跑邪靈。只是這種草不好找了,農戶家里都不養豬了,現代化養豬場附近沒有,即使有估計也不可能胡亂墊草。幾十年前,我的一位祖輩親人,就是在這種草形成的濃煙里咽氣的。遲至今日,在我鄉,一個老人在最后關頭如不覺悟不及時咽氣,竟仍可能會被款待以煙熏火燎,且用的是人能想到的最污穢之草。
姨差不多和娘一樣單純愚昧,沒人否認她是好心。娘可能是識破了針對她的詭計,在大家都不注意時,果斷咽氣了。一直守在床前的我,注意力剛轉移了一小會兒,再看娘時,娘就咽氣了。娘對這個世界越來越重的霧霾毫不在乎,從來都是無感覺無抱怨。但單獨為她準備一場特色“霧霾”,娘大約還是在乎的吧。
我向等著娘咽氣的一群親人大喊一聲:娘——咽氣了。對娘來說,她終于放下了生存的重擔。
第二天,我目送娘那幾近干枯的肉身緩緩進入火化爐。幾十分鐘后,熱氣騰騰的骨灰就出來了。那個植入娘身體僅一年多的金屬股骨頭,被燒成了與白骨迥異的黑色。工作人員漠然地用鉗子將其鉗出,扔進旁邊水盆,隨即發出嗞的一聲微響。那盆里已另有一個這樣的股骨頭了,那戶人家不要這異物了。我不假思索地伸手把我娘的那個撈起,放進娘骨灰里。雖是異物,卻也一度成為娘身體的組成部分了。娘,你不要嫌棄。
娘,我沒對你說實話,手術實際花了五萬多元。我要是說實話,你一定會為你的命絕不值這些錢而痛苦。
在住院及出院后,娘反復問花了多少錢。我把數萬說成數千,娘仍感慨:“唉,一個就要死的老嬤嬤子了,還花這么多錢啊。”娘每見我們穿件新衣,就問多少錢買的。我們都說一個原價幾分之一乃至數十分之一的價格,娘仍感慨貴。在娘心目中,幾十幾百都是大數字,幾千幾萬是不可思議的數字。娘只能活在小數字里。娘總是極力縮小自己,娘對一切與己身有關的事都極羞怯。一位醫生高聲大氣夸這老太太好看,把娘羞壞了,娘說:“這大夫對老嬤嬤子實在是找不著話說了。”一屋子人都笑了。每當護士像喊任何病號一樣喊娘名字孟慶云時,娘都要羞怯一陣。我相信,只有我知道娘那透明單純又山重水復的心思:娘不止羞怯,心里還會咯噔震動一下。娘的名字一輩子極少被人提及,自己更羞于說出口。兒時,我第一次知娘有此大名,很新鮮好奇,就引逗娘說自己名字。娘怎么也不說。我故意喊出來,把娘羞壞了。娘對自己竟然與別人一樣擁有一個名字,也是有不安的。娘啊,就允許老三多說幾遍您的名字吧。
數月前,纏綿病榻近半年的娘已瘦得厲害。我從大姐家搬來稱糧菜的小型磅稱,抱著娘站上去,稱出了娘的體重:著秋衣51斤。娘說起過一件與她體重有關的往事:“那一回,某某發了昏,非要稱稱俺,眼看把俺丟煞了。”娘說,那回她體重是八十幾斤。娘老了后略有發福,體重能達九十多斤。到娘咽氣時,比51斤又瘦了不少,基本是骨頭的重量了。不忍心再稱。娘的慢脾氣在老死之路上也體現出來了。娘慢慢地一滴一滴地把自己熬干,似乎在考驗活人的耐心。這的確有違娘從前的意志了。
嘴還能說手還能動時,娘撫摸著床頭那一大摞褯子說:“這褯子怪好哇。你們這一窩孩子,小時一塊這么好的褯子也沒撈著使呀,窮得連塊褯子都沒有哇。”
從墓地回來,回到已沒有娘的空宅。這空宅名義上歸我有,但今后我將很少回來了。爹兩年前沒了,娘又沒了,一個“朝代”已結束,我被納入另一個坐標了。我獨自整理娘的衣物,驀然發現了我一件舊秋衣。住院時拿去給娘臨時穿的,出院時娘穿著回了家。我把這衣收起來,決定再穿。
檐下的燕窩也已成空宅。但那燕子明年還會歸來,娘卻永遠不再來了。
燕子啊,你們知道嗎?你們知道世上曾有個人怕嚇著你們嗎?那個人大名叫孟慶云。
燕子啊,明年你們再來時,對這寂寞空宅多叫兩聲吧。月亮聽不到,樹聽不到,草聽不到,石頭聽不到,人聽不到,孟慶云能聽到。
2017年年底,回老家給娘上完周年忌日墳回到日照我的家。晚上,我把自己關在書房,從電腦里找出娘的照片,面對人間永遠不會再有的笑,再次淚流滿面。2017這一年,老家兄妹的來電鈴聲不會令我心驚肉跳了。
這一年,我過了一年沒娘的日子。
這一年,娘執拗地用她的影子,跟了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