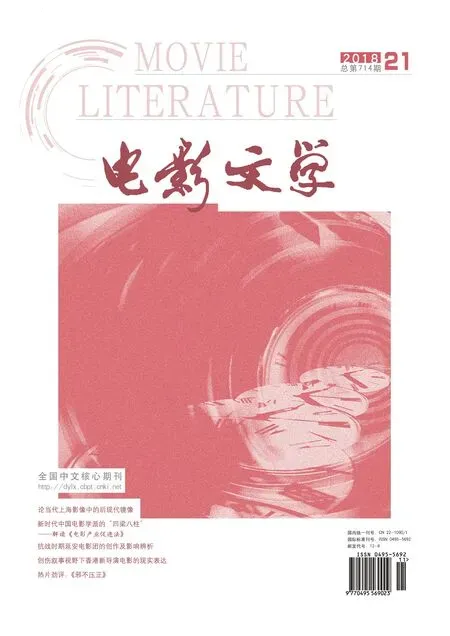《邪不壓正》的東西方文化差異探究
周 潔
(中國計量大學 現代科技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0)
《邪不壓正》如同姜文其他電影一樣,充滿了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姜文通過對現實的夸張與變形,對事件的暗喻與解構,輔以調侃戲謔的語言、沖擊力十足的畫面,將民國時期復雜多變的時局、泥沙俱下的人性與荒誕不經的故事糅合在一起,構成了電影中充滿黑色幽默,卻又浪漫疏闊的奇詭視聽奇觀。
影片中的北平城有著巍峨的城墻、莊嚴的牌樓、鱗次櫛比的屋舍,遠觀一派東方氣象。然而,城市里四通八達的街道上穿行著汽車、自行車、人力車;說著“洋文”的中國人和操著一口流利北京方言的“洋人”交談甚歡;穿著旗袍、馬褂的中國人與穿著西裝的“洋人”在六國飯店里抽著雪茄、喝著香檳……
快速切換的鏡頭與迷離曖昧的光線,交織成一番猶如醉夢般光怪陸離的民國景象。不過,恰恰因為這些場景曾真實存在于歷史當中,才形成影片中東西方場景交融,東方式武俠與西方式精神相互博弈的怪奇景觀。民國時期的“奇”“亂”與姜文的“怪”“壞”相得益彰,構成了這部令人目不暇接、忍俊不禁卻又滿目迷惘、心生悲涼的姜文式民國“奇談”。
一、“復仇”母題的東西方文化差異
北平冬季酷寒的冷夜,昏黃的燈光映照在白雪之上,帶來僅有的一絲暖意。少年李天然一臉懵懂地傾聽著師父的教誨,片刻后,他親眼目睹師兄朱潛龍伙同日本人根本一郎殺死師父全家的慘景。僥幸逃過一劫后,李天然自此背上了血海深仇。
李天然對朱潛龍與根本一郎的仇恨可分為四重:第一重,他身為孤兒被師父收養,師父師娘被朱潛龍等人殺死,此為殺父(母)之仇;第二重,師父傳道授業,教他一身武功,此為弒師之仇;第三重,師父許諾將師姐嫁他為妻,此為戮妻之恨;第四重,師兄朱潛龍向他連開數槍,誤以為他死了之后,放火焚“尸”,李天然強忍烈火焚身的劇痛才茍且偷生。殺父、弒師、戮妻,再加上試圖殺害自身,四重仇恨相加,可謂不共戴天之仇。
中國的老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十五年后,李天然帶著特殊身份與刻骨仇恨從美國歸來,意圖向朱潛龍與根本一郎“復仇”。但是,北平復雜的時局、對方目前的地位、藍青峰的暗中操作等一系列障礙,使李天然呈現出哈姆雷特式的猶豫、遲疑、膽怯、彷徨,從而導致復仇遲遲未能成功。
產生這種結果的肇因是顯而易見的,前往美國后,李天然與“仇恨”根植的土壤已經相隔甚遠。生活在西方文化環境中,學習外科醫學知識、鍛煉特工技能,唯一支撐李天然的“仇恨”還被養父亨德勒形容為情感創傷造成的偏執,認為他應該尋求醫治,而不是“復仇”。
“緣自古希臘的西方文化精神看中個體價值的自我確證意識,弘揚以榮譽、尊嚴和權力為內核的人道關懷”。可以說,西方式“復仇”母題往往出于血緣義務與家族榮譽,因此,在亨德勒看來,李天然執著于“復仇”的意識是脫離個體價值確證、缺乏內在行為動機的無意義行為。比起“復仇”,西方文化語境顯然更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可以確定的榮譽、尊嚴以及幸福。對于“復仇”敘事的關注重點,往往在于復仇的“過程”。所以,片中亨德勒多次勸說李天然放棄復仇,遠離北平,返回美國當一名普通的醫生。
影片同樣身負仇恨的還有女裁縫關巧紅,因為仇人是割據一方的軍閥,因此十年來臥薪嘗膽,隱忍不發,暗中布局。她也走過“彎路”,也曾經希望假他人之手完成自己的“復仇”,然而最后她選擇親自動手,“報仇,只能靠我自己。一個人,一把槍,足矣”。
由此可見,東方式“復仇”母題往往是孤膽英雄式、獨行俠式的,出自恩怨情仇的激烈沖突,屬于個人情感的強烈迸發,整體追求“快意恩仇”的美學效果。為此,復仇者可以不計后果、不拘泥過程,采用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只注重最終“復仇”的“結果”。只要復仇者的理由符合倫理訴求,即出自“忠、孝、仁、義、信”等目的,那么手段是否殘忍、行為是否恰當,是否符合公序良俗,都可以放置在相對次要的位置。因此,東方古典文學與藝術作品中,常可見超出“常理”與“法理”范疇的極致復仇手段,如《水滸傳》中楊雄殺妻等,多數情況下都能獲得受眾的理解和接納,只要其符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俗常信念。
《邪不壓正》中兩個“復仇”者,關巧紅與李天然,二者一明一暗。李天然為“復仇”而來,并將復仇視作自己最重要的目的,行為舉動卻輕浮跳脫,不著邊際,基本靠本能驅使,多數時間更關注自己內心的感受。而關巧紅則一直隱忍不發,暗中籌謀,聚集勢力,伺機而動。影片中,關巧紅是作為李天然的指引者、幫助者等形象出現的,在李天然迷茫時給予鼓勵與指引,在李天然的行動中進行卓有成效的協助。在這一敘事線索中,也隱現俄狄浦斯情結的端倪,即李天然認為自己應該為師父的死負有責任,而養父亨德勒實際上又是間接因他而死。最后,在挫折與傷痛中,李天然數次用武器指向精神父親藍青峰,顯現出明顯的“弒父”傾向。而他一直追隨的關巧紅,對他精神上的“撫養”已相當于“母親”的身份,自身的軟弱使他極力靠近關巧紅,以獲得精神上的支撐與滿足。
二、東西方文化沖突
《邪不壓正》從一開始便點出了“講究”二字,在其后的影片中,這兩個字也反復出現。“講究”是傳統文化中十分注重的層面。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講究”的中國,在戰亂的沖擊中,再難維系自身的“講究”。
影片中,維持著舊社會大家長體面的師父,遭遇到了沆瀣一氣的朱潛龍與根本一郎的威逼。面對來勢洶洶的二人,師父堅決地拒絕了用自己土地種鴉片的要求,隨即遭到二人的突襲。一方是手持代表西方現代科技武器的槍支的中國人,一方是手持日本武士刀的日本人,合力絞殺了代表舊日文明與武術傳承的師父一家。這是一個鮮明的符號,代表了西方文明與東方日本對傳統舊中國秩序的顛覆與殺戮。
在鮮血與烈火中,那個深諳東方“傳統”的少年李天然浴火重生,揮別慘痛的過去,與懵懂青澀的“童年”決裂,前往美國,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當“重生”后的李天然回到中國時,他對中國的了解甚至及不上養父亨德勒。“我送你去美國學醫,就是想讓你過得好。”絮絮叨叨的亨德勒,就如同每個中國父母一樣,嘮叨著“父母總不會害你,我們都是為了你好”之類的話。東方文化對他的影響如此鮮明地烙印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上,東方文化的接納性、包容性與同化性可見一斑。
在經歷了格格不入的陣痛后,李天然在關巧紅的指引下逐步成長,再次融入東方文化語境當中,正視自身的弱點與不足,重新走上“復仇”之路。影片最后,李天然換上的白色長袍,意味著李天然的“根”依然深深根植在中國。
三、結 語
一邊是飛檐走壁的武功,一邊是迅疾如電的子彈;一邊是做手術刀放開小腳的關巧紅,一邊是心心念念想當皇后娘娘的唐鳳儀……西方與東方,新與舊,激烈的沖突造成了視覺和情感上的荒謬性,而正因其真實,才顯得愈發地荒謬。喧囂紛亂的舊日北平,既體現出東西方文化差異,也有東西方文化融合的表現,在姜文的編排架構下,荒誕、離奇、血脈賁張又寥落凄涼,有喜有悲,足可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