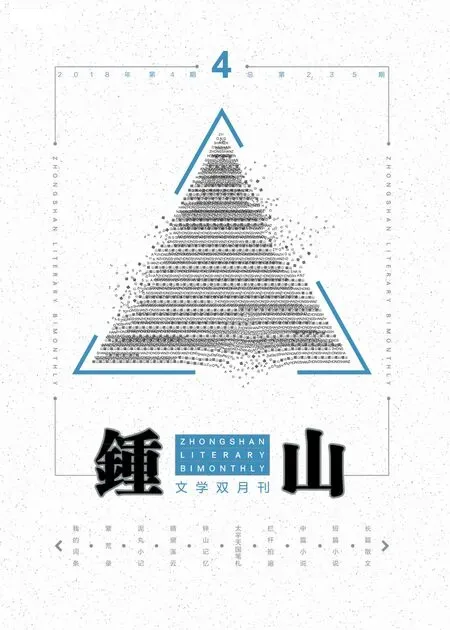香煙的故事
張新穎
ZHANGXINYING
一四月二十四日,賈植芳先生離世的日子,每年這天,陳思和老師,還有其他學(xué)生,都會(huì)去掃墓。二〇一八年逝世十周年,這一天也沒(méi)有什么特別,二十幾個(gè)人自發(fā)前往。上海寶山的仙樂(lè)息園修整得比以前好了,但平民墓地,那種擠擠挨挨的格局是變不了的。先生和師母的墓在排列整齊的墓群當(dāng)中,與周?chē)哪箍床怀龆啻蟛顒e。
我給先生點(diǎn)了一支煙。
本來(lái)也想給自己點(diǎn)一支,陪先生。墓碑前空間狹窄,不能同時(shí)站多人,我移開(kāi),轉(zhuǎn)到邊上,才也點(diǎn)上一支。
就是這么個(gè)小念頭,給先生點(diǎn)支煙,已經(jīng)在心里盤(pán)旋了好幾天。
不多久前坂井洋史教授來(lái)上海,酒桌上,談話間忽然冒出一句:那個(gè)青蛙煙灰缸,還在嗎?
我想,大概是不在了。
賈先生的書(shū)房兼做客廳,朝南的窗戶(hù)下是他的寫(xiě)字臺(tái),朝東的窗戶(hù)下放了一條長(zhǎng)沙發(fā),沙發(fā)前是一個(gè)不大的圓桌,無(wú)論來(lái)的什么人,總是一杯茶,放在桌子上(先生戲謔,說(shuō)某位名家招待客人,尊貴的請(qǐng)坐沙發(fā),叫傭人端上咖啡和糖;次之坐椅子,泡茶;再次之,一碗白開(kāi)水,站到門(mén)口喝)。坂井抽煙,自然對(duì)放在桌子上的青蛙煙灰缸印象深。
張掖的河西學(xué)院設(shè)立賈植芳藏書(shū)陳列館,館的一角復(fù)制了先生的書(shū)房,二〇一六年七月初我去那里,于遙遠(yuǎn)的大西北驀然看到熟悉的書(shū)桌書(shū)架,眼淚差點(diǎn)下來(lái)。書(shū)桌前墻面上的窗子是畫(huà)的,但窗框卻是先生家里原來(lái)的窗框,從上海運(yùn)過(guò)去的。我留意了一下,沒(méi)有見(jiàn)到青蛙煙灰缸。
最初跟先生讀書(shū)的時(shí)候,我二十二歲,只是偶爾抽煙,但坐在先生書(shū)房里的那些時(shí)光,像個(gè)熟練的煙民,先生抽一支,給我一支,沒(méi)過(guò)一會(huì)兒,再點(diǎn)上第二支,第三支。先生坐在藤椅上,不停地說(shuō)話,右手夾著煙,煙灰燃得老長(zhǎng),然后落下來(lái),落在衣襟上。師母常常提醒先生彈煙灰,先生說(shuō)著說(shuō)著,興奮起來(lái),又忘了。
二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先生給胡風(fēng)和梅志寫(xiě)信,說(shuō):“上海天天刮風(fēng),氣候不正,我每天蹲在屋子里吃煙,因此很懷念你們。”
《賈植芳致胡風(fēng)書(shū)札》(華寶齋書(shū)社,二〇〇一年)是我特別珍愛(ài)的書(shū),收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四年現(xiàn)存的全部信件,因?yàn)樘厥獾脑颍@些信件得以保存下來(lái)。一個(gè)青年——一九三八年先生才二十二歲——在抗戰(zhàn)、內(nèi)戰(zhàn)期間的流浪,戰(zhàn)斗,寫(xiě)作,“走向生活的底淵去”的歷程,單從粗拙、倔強(qiáng)、用力深重的影印筆跡,就能強(qiáng)烈地感受到。然而,忽然停止了。上面抄的“吃煙”的話,是這本書(shū)中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段話。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習(xí)慣晚上工作、睡得很遲的先生還沒(méi)有起床,師母推醒了他,說(shuō)外面有車(chē),接他去高教局開(kāi)會(huì)。上了車(chē),先生掏出大前門(mén),黨委書(shū)記楊西光馬上搶著遞給他一包中華。中華牌香煙那時(shí)候市場(chǎng)沒(méi)有供應(yīng),楊西光不抽煙,先生事后回想起來(lái)才明白,楊西光知道要抓他,特地給他帶上一包煙。當(dāng)晚,先生被宣布逮捕,押入建國(guó)西路第三看守所。
先生晚年寫(xiě)回憶錄 《獄里獄外》(上海遠(yuǎn)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香港天地圖書(shū)公司,二〇〇一年),能生敢死凜然之氣貫穿始終,筆致卻是落在具體生動(dòng)的人事上,微物如香煙,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xiàn)在對(duì)嚴(yán)酷生活的敘述中。譬如入獄之后,“一夜無(wú)眠。監(jiān)房里沒(méi)有香煙,口袋里楊西光送的那包中華牌也早已抽完了。我翻身起來(lái),心底里涌上了一種意欲惹事的惡作劇感。于是梆梆地敲打著靠走道墻一邊的那一扇門(mén)上的小窗口。一會(huì)兒,值班的解放軍看守跑過(guò)來(lái),開(kāi)了窗口上面的小門(mén)。我大聲吆喝道:‘拿香煙來(lái)!’他沒(méi)作聲,關(guān)了小門(mén),等了一會(huì)兒,回來(lái),遞進(jìn)來(lái)三支煙,三根火柴。一會(huì)兒抽完了,我再次敲窗,又向他要了三支。當(dāng)我第三次敲門(mén)吆喝‘拿香煙來(lái)’時(shí),他開(kāi)始顯得不耐煩了。可是我也嫌麻煩。我說(shuō):‘你給我一包吧,省得你跑來(lái)跑去的,你放心,我絕不會(huì)去自殺!’他這時(shí)已擺出一副冷酷的專(zhuān)政面孔,把聲音也提高了,訓(xùn)斥說(shuō):‘一〇四二(這是我的代號(hào),從此賈植芳的名字消失在我的生活史上長(zhǎng)達(dá)十二年),我是來(lái)看管你的,不是你家的傭人!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示弱,大聲說(shuō):‘我怎么知道這是什么地方?’他說(shuō):‘哼,那你是怎么進(jìn)來(lái)的?’我更火了,把一肚子怨氣怒氣全朝那個(gè)看守身上潑。我對(duì)他說(shuō):‘又不是我自己要進(jìn)來(lái)的,是你們把我抓進(jìn)來(lái)的,你怎么倒問(wèn)我?’”
監(jiān)獄里關(guān)押十一年之后,才判刑;又押回原單位復(fù)旦大學(xué)的印刷廠“監(jiān)督勞動(dòng)”,近十三年。重體力勞動(dòng),間以批斗,是日常生活。先生在《上海是個(gè)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中這么寫(xiě)道:“那時(shí)候我為自己定了些規(guī)矩:平時(shí)我抽八分錢(qián)一包的‘生產(chǎn)牌’香煙,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錢(qián)買(mǎi)一包‘勇士牌’香煙;我一般只吃幾分錢(qián)一頓的菜,每次挨批斗之后,我就買(mǎi)一塊一毛四分錢(qián)的大排或者一毛三分錢(qián)的大塊肉吃,自己犒勞自己。”
我第一次見(jiàn)賈先生,是讀本科時(shí)候,已經(jīng)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學(xué)的王瑤先生來(lái),在第四教學(xué)樓有個(gè)講座,賈先生是主人,陪坐在講臺(tái)上。這兩位山西老鄉(xiāng)坐在一起,很有意思。王先生抽煙斗,賈先生抽紙煙。我對(duì)賈先生的第一個(gè)印象就是,吸煙的頻率極快,一口接著一口,而且抽完一支,接著就點(diǎn)上另一支。大教室里人多,我坐得不夠靠前,卻特意看了一下,賈先生抽的煙,是黃盒子的鳳凰。
三先生去世十年,我沒(méi)有寫(xiě)過(guò)一篇懷念文章。
十年里,只夢(mèng)見(jiàn)先生三次。
第一次是先生離開(kāi)沒(méi)過(guò)幾天,我看見(jiàn)先生在光華樓的走廊里,腳步輕快,手杖提在手里,而不是用來(lái)拄在地上。先生在世時(shí),出門(mén)必帶手杖,卻習(xí)慣了走得快,常常是提著手杖走。我請(qǐng)先生到我的辦公室,坐在椅子上,然后泡一杯茶,點(diǎn)一支煙。
過(guò)了好幾年,第二個(gè)夢(mèng):桌子上一本嶄新的書(shū),大方精美,我仔細(xì)看暗紅色封面上的字,《悲哀的玩具》。我問(wèn),這是重新出版的嗎?有一個(gè)聲音說(shuō),對(duì),重新出版的。
醒來(lái)我想起關(guān)于這本書(shū)的事。那時(shí)候我已經(jīng)跟先生讀研究生了,北岳文藝出版社要給先生出一本作品選,先生投入熱情編好,等了好長(zhǎng)時(shí)間,一九九一年末,書(shū)終于印出來(lái),卻刪掉了好幾篇,而且印制粗劣,扉頁(yè)裁得短了一截。先生就是在這短了一截的扉頁(yè)上,給我題簽,鋼筆尖劃破了紙。
第三個(gè)夢(mèng)是最近做的,也許是因?yàn)樽x了宋明煒文章的緣故。宋明煒回憶起他是“小小宋”的時(shí)代,有一天陪先生在第九宿舍區(qū)散步,迎面碰到一個(gè)老教授,親熱地問(wèn)候,賈老怎樣怎樣。分開(kāi)后,宋明煒聽(tīng)到先生說(shuō):壞人。我比明煒在先生身邊時(shí)間長(zhǎng),先生說(shuō)誰(shuí)誰(shuí)是壞人的神情和聲音,沒(méi)有含糊的余地,給我至深的震驚感。我的這個(gè)夢(mèng)前面模糊,最后卻是清晰堅(jiān)定的:先生指著一張臉,這張臉轉(zhuǎn)來(lái)轉(zhuǎn)去,轉(zhuǎn)過(guò)去的時(shí)候是諂笑,轉(zhuǎn)過(guò)來(lái)的時(shí)候刻了兩個(gè)字,“岸然”,字上還涂了金。先生說(shuō):壞人。
先生離開(kāi)十年了,十年里這個(gè)世界的壞人沒(méi)有減少,這個(gè)世界也沒(méi)有變得更好。這樣的話,其實(shí)是不必向先生說(shuō)的,先生哪里會(huì)不清楚。就連當(dāng)年懵懂的我,也逐漸學(xué)習(xí)辨識(shí)投機(jī)、偽善,辨識(shí)惡。先生曾經(jīng)告訴我的那些壞人,我用后來(lái)的時(shí)間驗(yàn)證,我在后來(lái)的人中間認(rèn)出他們的同類(lèi)。也正因?yàn)閷?duì)惡的認(rèn)識(shí),才更能感受善,認(rèn)識(shí)善。這個(gè)世界不僅需要更多的善,而且需要善的堅(jiān)韌和勇敢,善的智慧與力量,以抗衡和搏斗。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