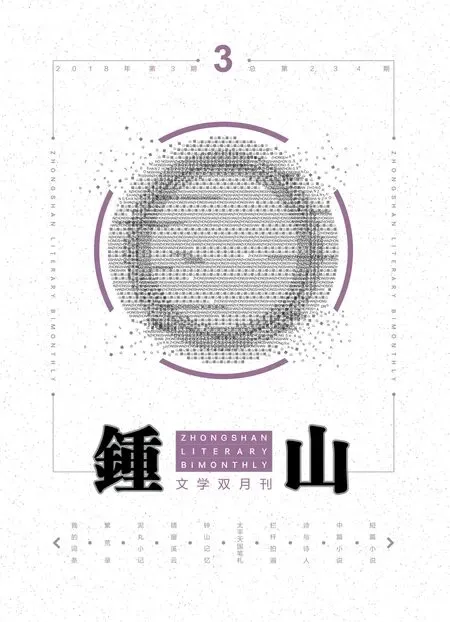虎吼
雷平陽
入冬后,大雪就沒有停過,感覺天空里的奶粉廠、鹽礦廠和面粉廠,全都打開了倉庫的大門,憤怒地向人間傾倒著經濟危機時代的積壓產品。天空之上的過剩物資,對素來饑寒得高聳著巨石般灰色骨頭的烏蒙山來說,足以滿足另一種幻象的奶粉、鹽和面粉,完全可以在蕭瑟的夢境中變成求之不得的實物。人們從用來逃避饑餓的睡眠中翻身爬起,赤著腳,興沖沖地就跑到了一座座千仞絕壁之上,打開久握的拳頭,雙掌從空中抓來一把把白雪,狠狠地往自己嘴巴里塞。邊塞,邊叫,臉上熱淚滾滾。
松樹鎮后山最高的那座山峰,名叫打虎峰。自從這個山中小鎮建立以來,每逢世上發生大事,烏蒙山里所有的老虎都會嘴巴上叼著一只羊羔趕到這座山峰上來,聚在一起,吃完鮮嫩的羊羔肉,然后就對著小鎮發現轟天炸地的雷霆之吼。吼聲經久不息,讓小鎮上的人如臨末日審判,以一家人為單位,彼此攥著對方的頭發,死死地抱在一塊兒。那些鰥夫和未亡人,無人可抱,就每人抱著石水缸,劇烈地發抖,讓水缸里的水泛起陣陣波紋。聽見虎吼聲,也有人撇下家人,拉開門,箭一樣射向距小鎮兩公里的墓地,跪在某塊墓碑下,磕頭,哀求,希望在天之靈能伸出一雙救人的巨掌,或從天上伸來一把把閃光的金樓梯。由于小鎮建在了群山的腹心,四周就有很多溪流順山而下,在小鎮的一個個角落匯聚成池塘。平時,這些池塘明亮如鏡,周邊長滿了青草和人們種植的果樹,男人在里面養魚,女人在里面洗菜或者洗衣服,夏天,孩子們則在里面嬉水。遇上干旱,人們就取池塘的水去救急,甚至可以將池塘的水灌滿一個個巨大的塑料桶,用牛車拉了,去無水的山中出售,換一點買鹽的錢。總之,它們帶給小鎮的全是好處,沒有壞處。小鎮上的人,翻山越嶺到世界上去闖蕩,變成了顯貴或乞丐,談起故里,鮮有人贊美高山,贊美打虎峰,但言及這一汪汪池塘,人人心里均會頓時涌出無盡的眷戀。然而,這些池塘,在那些經歷過虎吼的人心里,一旦想起它們,眼底立馬就會浮起一具具浮尸,它們的積水從山上流下來,仿佛承擔了另外的使命。據說,當虎吼聲傳來,小鎮上的一些外來人耳朵里就會接收到一道命令:“請你跳進池塘去藏身,快,快點!”虎吼聲消失后,這些跳進池塘的人,當他們從池塘下面漂起來,他們已經把自己徹底交付給了池塘,沒有一個濕漉漉地爬回到岸上。
下雪的時候,殺人兇手劉莊文就站在打虎峰上。他表情古怪地望著其它山巒上往空中抓雪狂嚼的人,嘴巴上叼著一支香煙,雙手上的鮮血還沒洗。把煙抽完,吐盡一團團白霧,照理說,劉慶文應該抬起血淋淋的右手,從嘴巴上摘下煙頭,用食指將煙頭彈向雪花飛舞的空中,接下來再用腳邊上的積雪擦洗手上的鮮血。可劉慶文沒有這么做,他懶得抬起右手,而是舌頭一頂,一口粗氣就把煙頭吐向了松樹鎮方向的空中。隨后,他蹲了下來,刻意讓目光變得柔和一些,帶著譏諷的微笑,用右手輕輕地掃著已經僵硬了的張佑太身上的積雪。積雪與鮮血凝結在了一起,他從旁邊的雪堆里找出了匕首,用匕首尖將一塊塊紅雪挑起來,再一塊一塊地趕開。匕首尖挑到張佑太襯衣上的金屬紐扣時,發出了輕微的響聲,他干脆手臂微微上抬,手中的匕首垂直向上,輕輕一拉,張佑太的衫衣就被劃開了,再用匕首尖左右一挑,襯衣和襯衣上的積雪倒向了身體的兩邊,淡粉色的胸脯就露了出來,血液還沒有徹底凝結的創口也露了出來,奶粉、鹽巴、面粉紛紛落在了上面。此刻,劉慶文也才收回臉上的表情,雙手和雙腿張開,茫然地向后倒向雪地,身體即將觸地的一瞬,右手向內一收,把匕首深深插入自己的心臟,然后又迅速拔出,扔在了雪地上。他的身體與張佑太組成了一個天字形。
這一場大雪下到了臘月初才停住。天空也空了,再沒有多余的素材可供烏蒙山里的人們培育想象力。人們肚腹里裝滿積雪,似乎也不想繼續跑到絕壁上去手舞足蹈,特別是當這些積雪讓他們領受到了一種內在的冰冷的時候,他們反而開始向往頭頂上那高懸著艷陽的天空,希望這夢境里的食物盡快排出體外,代之某種能夠滿足新一輪幻覺的嶄新填充物。新一輪的幻覺大抵也是古老的幻覺,不會有什么新花樣,無非仍然是布匹、火焰、食品和麻藥等等俗常之物的影子,可那“嶄新的填充物”屬于未知,人們真不知道會是什么東西。好吧,既然不知道,并且不知道什么稀罕物才能解決自己的實際問題,那就不用挖空心思去亂想象了。人們因此進入了新一輪的夢境中,用新生的沒有雜質的逃避之法,應對著時光的流逝和意念的反復涅 。能活命于意念中的人真是有福了,一個崇拜老虎的人,某天中午進入了松樹鎮,當他看到鎮上關門閉戶,人人都綣縮在被窩里等待內心的冰雪融化,忍不住大加贊嘆,把松樹鎮的寂靜歸類為墓地的寂靜。他說的墓地,是新修的無邊無際的卻又沒有死者入主的墓地:“世界如此喧鬧,只有松樹鎮是寂靜的,死一般的寂靜。”這個拜虎人其實沒有夸夸其談,也沒有故意煽情,松樹鎮確實非常的反常,小街上一個人影也看不到,更不可能有人交頭接耳,談論著打虎峰上的兇殺案。整個冬月,人們都足不出戶,誰也不可能去攀登打虎峰,自然也就不會有人知道打虎峰上的積雪下面臥著兩具尸體。所以,當這個以老虎為圖騰的人,跌跌撞撞,下了打虎峰,在空蕩蕩的街道上,邊跑邊喊“殺人嘍,殺人嘍”的時候,小鎮上的人們才知道老虎怒吼的山頂上,一個人被另一個人殺了,殺人的人又把自己殺了。第二天,有關機構的人在出過現場后,組織群眾把兩具尸體抬下山來,分別交還給他們的親屬,人們才紛紛移動自己冷颼颼的身體,走到街頭,或搖搖頭嘆一口氣,或外表麻木不仁五內則生出些奇思亂想,或從衣袋里掏出手機,把劉慶文和張佑太的手機號碼刪除了。“我以為打虎峰上,肯定有老虎的魂魄在游蕩,難說還會有老虎血染紅的石壁,沒想到氣喘吁吁地爬上去,上面竟然……”崇拜老虎的人,逢人就高聲喧嘩,一副非將小鎮從寂靜中拖出來的架勢。人們普遍都不迎合他,相反把他當成一個報送死訊的人,覺得他的身上夾雜著地獄的濕氣。劉奇文的父親年輕時曾經是松樹鎮上出了名的獵人,虎豹出沒的那些年,出任過“烏蒙山獵虎總隊”下屬的一個分隊長,伏虎、獵豹、殺狼,風頭無二,家里的虎骨酒擺滿了寬大的供桌,聽說現在的床底下都還存放著一罐子。這個人在耳朵邊上大聲嚷嚷的次數多了,終于在葬禮上猛然繃直駝背了的腰身,用混濁又不失凌厲的目光逼視著他:“你有著一副老虎一樣的嗓門,上了打虎峰,為什么在上面時不對著松樹鎮大吼幾聲?”只字不提帶來死訊的事兒,無意撂下眉毛底下一個兇手父親所承擔著的精神壓力,但又巧妙地以挖苦人的方式把人們關注的話題分了個岔兒出來,同時,也是最有意味的,這個獵虎隊的分隊長,表面上虛晃一槍,實際上十分隱蔽地就把那個大聲嚷嚷的人引上了一條重登打虎峰的小路。穿插著參加完兩個同時舉行的葬禮,回到只有他一個人住宿的春山旅社,崇拜老虎的人回想起獵虎隊分隊長的話,總覺得這話里分明在暗黑的夜幕中給自己遞過來了一道閃電,閃電的光瞬息即逝,但又是真實存在的,閃現在某條登山之路的盡頭。是啊,那天去登打虎峰,如果上面不是一個兇殺案現場,自己會不會像老虎那樣吼上一嗓子呢?一旦吼了,又會怎樣呢?他越想越是覺得這個氣氛詭異的松樹鎮,它不但有意抽走了某些驚心動魄的客觀存在于人們生活中的黑夜,而且它還將幻象與現實世界攪和在了一起,并且明顯地把真相推向了幻象的一邊。
在同一天,兩場葬禮同時舉行。一支送葬的隊伍往小街的北面緩緩移動,另一支則往南移動。小鎮上的人們堅持了他們古老的習俗,沒有空中翻飛的紙幡和紙錢,也沒有鞭炮和香炷開辟死者的超生之路,在眾花寂滅的臘月,他們幾乎砍光了山坡上剛剛引種不久的冬櫻花樹,一人扛著一棵,把整條小街裝扮得極其凄美、妖嬈。“持美而夭,何其絕美!失我心骨,何其空茫……”低沉而燦爛的送喪歌,也似鑲了金邊的烏云浮動在只有幾米高的空中。見識到這樣的場景,那個崇拜老虎的人一再對自己說,這是多么的務虛啊,幾次想扔下分發給他扛著地那棵冬櫻花,讓自己以外來人的身份呼天搶地的為兩個年輕人痛哭一場。可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耳朵里仿佛響起了一個聲音:“請你安靜一點,這冬櫻花的海洋里最適合你藏身!”聲音與虎吼時誘引外來人朝著池塘里跳的聲音是一樣的,他自然不知道,但他服從了,關上了自己令人討厭的大嗓門。神秘的聲音讓他閉上了嘴巴,接下來胡吃海喝的喪宴帶給他的印象一度又讓他差點失控,幸好他早早地回了旅社。多么匪夷所思,落雪時,人們還爬上一座座山巒和絕壁去抓飛雪果腹,這時候,人們幾乎殺光了小鎮上所有的畜牲和家禽,幾百張餐桌上肉食堆積如山,滿眼全是張開的大嘴和雪白的牙齒,嚼肉啃骨的聲音就像有一群惡虎在撕吃爪下的羊羔……是的,兩席喪宴把人們從幻覺中抓了出來,肉食和酒水終于成為了人們夢境之外滋養身體的“嶄新填充物”,人們眼底的鬼影子消失了,那腹中的冷雪,一碗烈酒下去,馬上就融化了,變成一泡熱尿,嘩嘩嘩地就沖出了體外。什么末日審判,人們沉浸在了末日的狂歡之中,直到自己找不到自己或一再把橫臥在街邊的別人當成自己為止。當然,也有兩個人什么肉也吃不下去,一口酒沒喝,他們分頭離開了兩個不同的喪宴,不約而同地來到了一個池塘邊。他們不是別人,兩位死者的父親。“知道吧,這池塘里死過很多人?”開口的是張佑太的父親。獵虎隊分隊長沒搭腔,遞給對方一支紙煙,兩人都點了火,坐到女人們用來洗衣服用的兩個石墩子上,一聲不吭地抽了起來。抽完了,又續上,冷冷的目光下,兩個人的頭上就像罩上了一團灰霧。其間有幾個醉漢騰云駕霧地從身邊飄過,見了他們,也總是把他們視為石墩子。“你說,這兩條狗命怎么就這么沒了?”沉默了兩個時辰左右,也不知這話是誰說的,也沒有另外的聲音附合。隨后,他們的對話像噴火藝人嘴巴里噴出的火焰,同樣也分辨不出哪一束火焰是誰噴出來的。
“今天,我一直在想,為什么兩個孩子會落得這樣的下場,想來想去想不明白。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把我們之間的血仇告訴了孩子!”
“血仇?什么血仇?我們之間什么時候結下了讓兒孫以死相殉的血仇?”
“請你不要裝糊涂好不好。那一天,我們十多個獵虎隊員,一人披一件虎皮進山獵虎。說好了的,大家分別埋伏在不同的地方,等著幾只老虎從打虎峰上下來,我的哥哥,他就躲在兩棵松樹之間,根本不在老虎行走的小路上,結果,老虎還沒來,你就開槍了,一槍就要了他的命!”
“不,我沒有,絕對沒有,你這是誣陷。那天晚上,月光那么亮,我肯定不會把人看成老虎。而且,那晚上,我一槍未放,老虎聽見槍聲,根本沒從打虎峰上跑下來!”
“你還要抵賴?”
“我沒有抵賴。我只聽見有人放槍了,接著就聽見了一陣亂槍。是的,你的哥哥就被打死了。”
“我知道你和我哥哥同時喜歡上了一個女人,你是借機除掉他!”
“你放屁,我他媽哪個女人也不喜歡,你哥哥喜歡誰我也不知道。我憑什么要他的命?憑什么?噢,照你這么說,后來的一天,同樣是進山獵虎,我弟弟也是被一槍斃命的,那開槍的人原來是你,是你在報仇啊!”
“不,我只殺虎,從來沒殺過人。盡管我知道你殺死了我哥哥,我有一百次機會殺了你,我都沒開槍。我為什么要殺你的弟弟?”
“你別裝了,你不殺人,我難道沒看見過你殺人?每個人都披著虎皮,我就親眼看見你把一個埋伏在溪水邊的人當成老虎,一槍就打倒在了溪水里。我真不知道你為什么要殺他?”
“唉,你真是血口噴人,獵虎隊十多號人,老虎打殺完了,人就剩下咱兩個,除了有五個被老虎撕吃了,有四個摔死了,其他全是誤殺而死,我一個也沒殺過,是的,沒有。”
“照你的說法,全是我殺的了?”
“你殺過,死去的人里也有人活著時殺過,然后被殺。”
“我再告訴你一次,我沒殺過人,聽好了,我從來沒殺過!”
“哈哈,有哪個殺人的人承認自己殺過人?現在我終于見到了一個。這個人就是你!你不僅殺人,你兒子也殺人!”
“什么?我兒子殺人?你媽的,我真想殺了你,這一分鐘,我真他媽想殺了你。我兒子分明是你兒子殺的,你把血水往我頭上潑倒也罷了,現在你又來往我兒子頭上潑!”
“哦,這個你也不承認?我兒子從來沒有過匕首,匕首肯定你兒子的,他用它殺了我兒子。”
“你兒子會沒有匕首,我相信你兒子生下來,口里就含著一把匕首。請你不要再洗白自己和自己的混蛋兒子了!”
因為有月光,池塘里倒映著打虎峰淡淡的倒影,說到獵虎行動和打虎峰,兩個黑影還會伸出手指,對著池塘指指點點。那些秘而不宣的往事,仿佛已被他們聯手沉入了池塘。事實上也是,兩個黑影沒完沒了地互噴火焰,誰也沒把誰燒焦,不僅沒有動手,彼此還互遞香煙,相互有著忌憚與默契。他們一直在說,說到黎明降臨,揭發,否認,再揭發,再否認,說的都是對方的手上沾滿了鮮血,而自己是清白的,罪惡沒有可靠的證據,清白也沒有可靠的證據。對于劉慶文和張佑太兩個孩子的惡性死恨事件,他們都力圖找出原因,“血仇”被找出來了,但血仇也是無人認領的,無非是他們兩個人之間最為隱秘的一個話題,永遠不可能向上小鎮上的人公開。你不能說他們都徹底忘記了自己作為父親的身份,沒有了老年喪子者的劇悲,說到他們第一眼看到兒子尸體那一刻的景象,其中一個人還撿了一塊石頭,惡狠狠地砸向了池塘里的打虎峰,另一個人則往自己臉上重重地擊了一拳頭。他們的悲與疼被他們藏起來了,不對,應該說他們的悲與疼,因為害怕別人從兩個孩子的死亡事件中發現什么,他們就有意地回避開了。同時,當他們將兩個孩子的命稱之為“狗命”,又說明他們又恢復了自己獵虎隊隊員的身份,擁有著獵虎時代“獵虎英雄”和“兩個光榮的幸存者”光焰之下那顆戰士的心。作為父親時,他們不相信兒子會以自己的死亡去了結“血仇”,其中必然另有隱情,可他們卻又害怕深入的調查,畢竟他們經受不了調查。所以,當辦案機構以殺人和自殺為結論草草結案,他們沒提半點異議。可是,作為獵虎隊隊員,對于兒子以命了結“血仇”之說,他們是樂于接受的,了了,一了百了,這了可以徹底地埋藏所謂血仇,可以無奈地用“狗命”去抵沖部分血債。他們不是獵虎時代血雨腥風的掀起人,但他們是馬頭卒,以前因為種種原因而被裹挾,現在因為拒絕覺醒而害怕審判。兩個兒子的死,按說給了他們接受審判的機會,他們放棄了,反而用兒子的尸體去壓住了打虎峰山頂的風雪。
葬禮之后,每天都有烈日,松樹鎮四周山上的積雪紛紛融化,流下來的雪水把每個池塘都填得滿滿的。開始的一兩天,胃里面積壓著從喪宴上獲取的過量的肉食與酒水,人們又重歸于夢境,人人都不想放下肩上扛著的那一棵冬櫻花,還想繼續行走在送葬者的隊列這中。“持美而夭,何其絕義!失我心骨,何其空茫……”那個崇拜老虎的人從空蕩蕩的小街上走過,聽見每扇窗戶里都會傳出夢囈般的歌吟。可當胃囊逐漸空掉后,漸漸才有人走出家門,提著竹籃子,準備到山上去尋找積雪。不曾想到,當他們來到小街上,還未走到山腳,就發現小鎮上的池塘在陽光照射下,那鋪天蓋地的白色反光,已經令人頭暈目眩。獵虎隊分隊長和那個崇拜老虎的人正在小街上跑來跑去,拍門打戶的召集人們,號召大家人人動手,盡快把褐色的稻草和麥桿子撒到池塘里去,或者用大棚溫室上一張張巨大的黑色塑料薄膜把池塘包扎起來。張佑太的父親神色憔悴,一看就是幾夜沒有合過眼了,顯然也是最早發現白光之災的人之一。他已經把家族里夢游之中的十多個青年男女組成了一支突擊隊,下設三個小組。第一個小組負責把兩個葬禮上用過的冬櫻花從墓地上運回來,扔到池塘里去;第二個小組負責把小鎮上的黑煤集中在一起,倒進池塘,把水攪黑;第三個小組的工作比較難做,他們得動員小鎮上的人們把黑色的衣物捐獻出來,用鐵線或者竹竿串成平躺的人樣,然后鋪架到池塘上面去。小鎮從來就不缺少悲劇性,大家都穿黑衣服,可衣物畢竟有限,捐出去了,人人就得天天赤身裸體地躺在被窩里,發生了什么急事可就出不了門了,所以,大家都猶豫不決,覺得這個方法很好但后患也很多,不愿捐獻。張佑太的父親見其它兩個小組的工作搞得如火如荼,就是這個組難以破局,步履蹣跚地前來督陣。風雨見得多,亂象經歷不少,解決難題的經驗也很豐富,他稍作民意調查,立馬就拍板:每一戶人家,男式和女式分別留一套衣服作為急用,其它全部捐獻。于是乎,很多的池塘上,迅速布滿了黑色的人影。捐獻了衣服的人們,乖乖地回家做夢去了,小街上,最后只剩下用黑色塑料薄膜嚴嚴實實地套住的三個人。他們一個池塘接一個池塘地去檢查,擔心有人疏忽了,某個池塘露出清澈的水面。三個人中,一個聲音說,只要有水面露出,太陽的光就會肆無忌憚地集中到這片水面上來,水面的反光不僅會讓白日夢里的小鎮持續升溫,將人們導入神秘無解的白色空間,繼而嘔吐、癲狂、迷亂,甚至燃燒。 同時,那座倒映在池塘里的打虎峰則會隨之陷落為深淵,既有幽靈般的呼喚聲從下面傳上來,還會產生一種陰森森的巨大吸力,讓人不可遏制地就往池塘里躍去……聽聲音,說話的是張佑太的父親,但沒等他說完,另一個聲音打斷了他。這個聲音明顯是獵虎隊分隊長的,他說,聽好了,你這個崇拜老虎的人,關鍵是,那太陽與水的反光一旦出現,特別是當小鎮上的每一個池塘都有反光,這些反光將統一照射到打虎峰上,它們就像地獄之光那樣,一眨眼就點燃了峰頂上那一座座紅色絕壁,使之就像連綿千里的烏蒙山向天空升起的反叛的、不祥的巨大火焰。也正是因為這火焰,那些嗜血的老虎才朝著這兒云集,它們都以為,沿著火焰向上攀,它們就可以進入天空,成為天空的組成部分。然而,當它們來到打虎峰上,發現一切均是陽光與水面制造的幻象,哦,對了,這個你肯定是知道的,它們認為自己受騙了,幻滅之后,便對著水面上反射而來的白光,也就是松樹鎮的方向,發出了排山倒海的怒吼。那聲音真的能滿足人們對死亡的想象與恐懼,仿佛天上的魔鬼全都發怒了,想用自己的聲音毀滅小小的松樹鎮。
太陽的光被人們阻止在了池塘之外,第二天,太陽就到其它地方去了,松樹鎮的上空先是來了幾朵烏云,隨后,雨就下了起來。獵虎隊分隊長躺在床上,聽著雨聲想事,旁邊的老伴一再催他,說下雨了,太陽跑了,得去池塘里撈幾件衣服回來,否則怎么度過這個寒冷的冬天啊。他沒有理會老伴,而老伴見他不動,只好穿上僅有的一套衣服,出了門。屋子里好靜,像那個該死的崇拜老虎的外鄉人所說,是墓地上才有的寂靜。嗯,墓地,的確是墓地,閉上眼睛,就能感覺到屋子的地面、家具、墻壁、天花板、自己躺著的床鋪,乃至自己身體的每個部位,每根骨頭上,都有青草在嗖嗖嗖地冒出來,嗖嗖嗖地朝上瘋長,嗖嗖嗖的長出了屋頂,而這屋子的正中央,分明擺著他和兒子的兩具骷髏。不止一次,他看見兒子胸口上咕咕咕地冒著熱血,站在床面前,臉上有新鮮的塵土,表情似笑非笑但明顯的帶著一股寒氣。兒子滿手的血也還沒有洗掉,沾上了泥巴和草屑,衣服的皺褶和發叢中,白雪凝結成了深灰色的冰渣。第一次見到兒子,是葬禮后第二天中午,他躺在床上,想撐起身子去抱兒子卻怎么也撐不起來,兒子似乎也不稀罕他的擁抱,冷冷地站著:“爸爸,是你教會了我殺虎的技藝,我一直想試一試。下雪那天,我去了打虎峰,奇跡般地遇上了同樣去殺虎的張佑太。唉,在我看見了一頭老虎時,抽出匕首,猛然撲擊過去的時候,老虎金色的皮毛突然不見了,它竟然變成了張佑太。而當我以為自己殺了人的時候,張佑太又變成了一只死老虎,他們不停地變來變去,我一點兒也分不清,自己殺掉的是老虎還是張佑太。到了最后,我發現自己也在不停地變,一會兒是老虎,一會兒是我,我仰面朝天,向騰空而來的老虎送出匕首,匕首卻插進了自己的心臟……”兒子陳述的事件不乏驚悚,可口氣始終冰冷,一字一句均斬釘截鐵,話音未散,人就不見了,沒有給他一分鐘的提問時間。之后又與兒子見面,兒子一句話也沒有,他問什么,兒子立馬就消失。兒子說的殺虎場景,有那么幾次,他都想與張佑太的父親作個交流,特別是太陽之光刺激池塘的那天,他們都同時嗅出了松樹鎮空氣中飄蕩著一絲血腥味,甚至隱隱覺得烏蒙山中的老虎并沒有趕盡殺絕,經過多年的繁衍,老虎早已成群結隊,正在翹首觀望,只等打虎峰上升起火焰的大旗。兒子的說法,契合了天象,與他們當年殺虎的景象也是一致的,而且他感到,兒子這一代人顯得更絕決,絕決到了連給自己也不留生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有必要與張佑太的父親說說。但那天事情多,又很緊急,獵虎隊分隊長也就打消了交流的念頭。之后,見張佑太的父親也不想在兒子之死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連慣常的經濟補償之類的話題都沒提,他就把交流的念頭摁滅了。再說,像松樹鎮這種依靠幻覺而存在的鬼地方,新一代人愈發依賴幻覺,這樣的報應也無可厚非。如果哪一天打虎峰又聚滿了老虎,相信人們也會煥發出嗜血的本能,無所顧忌的與之同歸于盡。
那個崇拜老虎的人不久也就離開了松樹鎮。走之前的頭一天,他約了獵虎隊分隊長和張佑太的父親一起登上了打虎峰。三個人坐在峰頂上,看著四面的群山和天上的云朵猶如虎群奔突,人人心里都涌入了一只接一只的老虎,人人都又不知道說什么為好。只有在他們把目光投向松樹鎮時,張佑太的父親才對崇拜老虎的人說了一句:“是你把死訊從這兒帶給了我們。”崇拜老虎的人不在意他把自己當成死神的郵差,笑了笑,掉過頭對著獵虎隊分隊長說:“你暗示過我要重登打虎峰,后來我也來過幾次,并沒有找到虎吼的秘密,而你們說的那些,我是不會信以為真的。”說完,他就模仿老虎的吼聲,對著松樹鎮大聲的吼叫起來,他的嗓門再大,聲音也像全力扔出去的一串點燃的鞭炮,轉眼就爆炸光了,不可能傳到松樹鎮的上空。待這人吼完了,獵虎隊分隊長拍了拍他的肩頭,將臉轉向張佑太的父親:“你聽,他這也叫吼?當年獵虎大隊幾百號人經常在此學習、訓練、開批斗會,沒事了,一人一個高聲喇叭,就對著松樹鎮一陣接一陣的喊口號或者作虎吼,嚇得鎮上的人們天天都疑神疑鬼、失魂落魄……”他一說完,兩個獵虎隊員都笑了起來,笑聲里夾雜著一絲絲虎吼的音質。那個崇拜老虎的人,到這個時候似乎也才知道了老虎是怎么吼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