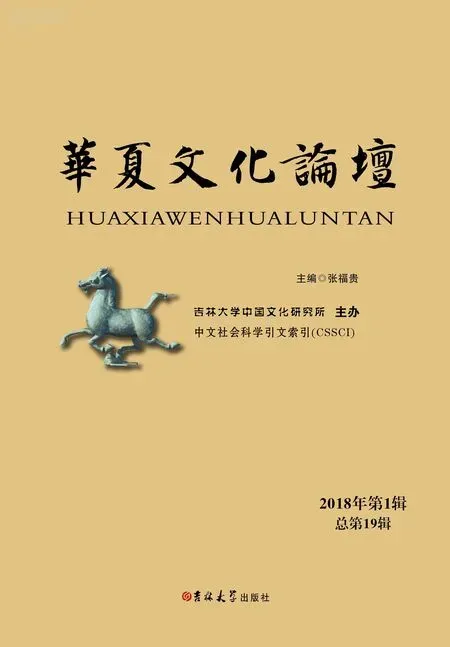跨國及跨文化視角下的生態學與生命寫作
[德] 阿爾弗雷德·霍農(Alfred Hornung) 王小木 譯
【內容提要】在本文中,我認為自然與文化的相互性是生命寫作流派的一個例證。亨利·戴維·梭羅的《瓦爾登湖》作為浪漫時期這一相互關系實際應用的典范,覆蓋了我以跨文化和跨國界的視角對于4世紀到21世紀之間的美國、亞洲、加拿大等國家與地區有關自然與生命的表述中對于生態思考的全面考察。根據梭羅對亞洲資料的解讀以及他與原住民生活的關系,這一研究包括了對以下內容的討論:中國詩人陶潛(365—427)的詩歌,明代(1368—1644)中國的園林文化,泰莉·坦皮斯特·威廉斯的女性生態主義作品《避風港》(1991),高行健的《靈山》(1990年),喜馬拉雅山脈藏族村落中關于大山的生命寫作,以及加拿大籍日裔動物學家戴維·鈴木的生態作品。
人類生命的自然過程符合所有生物普遍共享的自然循環。所有有機生命的進化原則,如果沒有被人為干預所阻止,也意味著自然的終結。很多人努力延長這一自然周期并堅持到最后。文化的形成以支持或對抗的形式伴隨著自然界的有機過程。總的來說,文化的任務是商討潛在的干擾并建立確保生命在地球上的延續。
一、作為生態文體的生命寫作
自然和文化的關聯性可能在生命寫作這類囊括了對人類生活所有形式表現的文體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比如自傳、傳記、日記、畫像,新社交媒體中的博客和自拍,旨在捕捉敘事結構和具體圖像中的短暫瞬間和生命進化階段。歷史上,代表生命過程的隱喻各不相同。因此,Peter Alheit區分了五類用于主體立場的隱喻:中世紀生命世代循環的思想;16世紀向上或向下的拱門或階梯的隱喻;現代資產階級假設在職業生涯中的上升線;在工業性作業中后資產階級的形成,以及后現代時代的拼圖或拼接物。焦慮導致了各種自我表征和精神分析的解讀,這些焦慮與生活中上升與下降階段有著無法回避的關聯,并以往往體現為中年危機的經歷。例如,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假定生命分為第一與第二兩部分,并把生命視作從自然向文化,從個人生活中不斷變化的生物因素向跨越個人意識中更為永久的精神成分的過渡。這種轉變與通過回顧所帶來的重新定位有關。榮格是這樣解釋的:
如果一切順利,保守的傾向會得到發展。人們不會向前看,而是向后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由自主的。人們也開始考慮生命發展到現在的方式。因此,真正的動機得以被尋求,真正的發現得以被進行。對自己和命運批判性地審視使得人們認識到自己的個性,但這種認識并不容易得到,而要通過最嚴重的沖擊才能獲得。
自傳作者與自傳評論家都已意識到并評價了這種對生命所做的個人評估進行回顧所具有的幻像特征。天主教堂圣奧古斯丁神父用他的作品《自白》(397—400)從永恒的角度來研究時間;美國開國元勛本杰明·富蘭克林構想的個人生平的回顧成為了他的《自傳》(1771—1790)第二版中的修改內容;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在他的自傳《詩歌與真理》(1811—1833)的題目中就強調了幻覺與現實的相互作用;自傳評論家Roy Pascal以歌德的觀點為他的學術著作《自傳中的設計與真理》命題;后現代評論家Ihab Hassan認為自傳是一個“不可能的”“致命的”“被鄙視的”寫作形式,其秘密主題是死亡。與這種存在主義的觀點相反,作為向重生的過渡,死亡的浪漫解讀也是人類生命過程與自然循環過程相關的出發點。
亨利·戴維·梭羅的《瓦爾登湖》為自然與文化的詩性關聯展現了典范。在這一系列自傳體散文中,作者將兩年零兩個月(1845—1847)的實際經驗濃縮成為一年,并將這種生活體驗與季節循環協調起來。梭羅的生命寫作始于他的小屋建成的那個夏季,經歷了秋冬兩季,并以大自然在春季的重生結束。季節的自然循環以類比的形式服務于敘述中對于生命更迭的詩意化的描述。一個相關的特征體現在政治這一方面,有愛國精神的自我在七月四日搬進小屋,并以此宣告他自己的獨立宣言。這些將肢體的經歷和政治信仰轉化為自然進程的詩意的過程,與超驗主義的哲學思想相一致。這種富有想象力的浪漫主義設計讓梭羅超越了具體經驗的現實細節,將他在瓦爾登湖的地區視野擴大到跨文化/跨國界的背景。在他的生活敘述“結束語”部分,梭羅提到非洲、南美洲和中國,只是建議他的讀者在自我想象中成為“一個新大陸和新世界的哥倫布”,“一個居家宇宙學專家”。
亨利·戴維·梭羅和他的生命寫作《瓦爾登湖》被視為有關生態關注的重要文本和主要表達方式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僅是馬薩諸塞州瓦爾登湖旁他那個被重建了的小屋變成了環境神殿,以及向自然表達敬意的場所,他的作品也成為了所有生態批評學術研究的起點。就我的目的而言,梭羅和《瓦爾登湖》為生命寫作中自然和文化的相互關聯,生態與生命寫作的一致,提供了完美的起點。同樣,Hubert Zapf支持協調的認識論和倫理價值,這種協調體現在文化生態與“符合自然和文化,人類和非人類世界基本關系的生命寫作形式”之間,他還“強調在世界范圍內的文學群體中,文學知識在生產與接受是處于跨國緯度和全球互聯的背景下的”。因此,梭羅的作品不僅在浪漫主義的模式下將整個宇宙融入到他個人的生活當中,同時他對亞洲哲學的閱讀以及對美國本土生活的觀察使《瓦爾登湖》變成了一個生態全球主義生命寫作項目。
二、梭羅的生態全球主義模式
亨利·戴維·梭羅在他的生命寫作實踐中詩意地再現了他對自然界進化過程的關注,這與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1859)中發展的進化生物學,以及德國動物學家Ernst Haeckel(1866)于1866年創造的用于描述生物環境和家務形式的生態學術語相一致。20世紀晚期對“人類生態學”的規范,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環境運動之前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文學和語言學領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并支持了對生態作家的研究。終于,生態批評得以形成,從美國傳播到歐洲,并由歐洲的Hubert Zapf發展成為文化生態學。對于生態學與生命寫作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從亨利·戴維·梭羅的《瓦爾登湖》所例證的浪漫主義模式開始,逐漸進入了被忽視的現代主義中的大自然和原住民棲息地,最終將重點落在了處在20世紀之交的后現代及后殖民背景下日益嚴重的環境危害和由此帶來的人類疾病。21世紀對生命的關注包括對所有生命機體的關注,對深層生態學的促進,以及跨文化跨國界視角下對地球視野的預測。在下面的章節中,我的討論將以美國、加拿大和亞洲為例,強調在跨文化跨國界的層面上生態學與生命寫作的相互關聯。
在梭羅的《瓦爾登湖》中,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經驗構成了整體的超驗自我,得到了廣泛的學術關注,并在最近得到了來自對自傳和自然科學相互關系研究的補充。在世界范圍的受眾中,亞洲讀本對梭羅就自然和自我的定義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于印度哲學的印度教經典。此外,Birgit Capelle“指出對于時間經驗的敘述表現出與佛教和道教對于時間的詮釋極為相似”。與單向的基于行動的時間順序概念相反,道家主張“無為或不作為”以及基于周期性的時間觀念的觀點。在引用《瓦爾登湖》的過程中,Capelle認為梭羅是“跨時代的幸運存在[…]像覺悟的佛陀”。
我愛給我的生命留有更多的余地。有時候,在一個夏天的早晨,照常洗過澡之后,我坐在陽光下的門前,從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樹、山核桃樹和黃伊樹中間,在沒有打擾的寂寞與寧靜之中,凝神沉思,那時鳥雀在四周唱歌,或者默不作聲地疾飛過我的屋子,直到太陽照上我的西窗,或者遠處公路上傳來一些旅行者的車輛的磷磷聲,提醒我時間的流逝。我在這樣的季節中生長,好像玉米生長在夜間一樣,這比任何手上的勞動好得不知道多少。這樣做不是從我的生命中減去了時間,而是在我通常的時間里增添超出了許多。我明白了東方人所謂沉思以及拋開工作的意思了。大體上,虛度歲月,我不在乎。白晝在前進,仿佛只是為了照亮我的某種工作,可是剛才還是黎明,你瞧,現在已經是晚上,我并沒有完成什么值得紀念的工作。我也沒有像鳴禽一般地歌唱,我只靜靜地微笑,笑我自己無盡的幸福。
對梭羅來說,這種自然界的生命形式是不間斷的“造物之詩歌”的一部分,他在他的生命寫作中重復了這些特點,這是他自己的造物之詩歌。Bernhard Kuhn實際上稱他為“詩人-自然主義者”,他認為“在自然界中,從無機到有機表現自我的創造力,與賦予梭羅生命和生命寫作的創造力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他的造物之詩歌與庫魯藝術家的態度和成就類似,這種永恒的努力創造了一個完美的員工梭羅,他在“結束語”中提到:“單一的目的與決心,高度的虔誠,在他不知情的條件下將永久的青春賦予了他。由于他對‘時間’毫不妥協,‘時間’為他讓路,只能在遠處嘆息,因為他無法戰勝他”。
三、道教與自然中的生命
梭羅對于沉思生活的實踐是在一種無限循環的孤獨的自然過程中進行的,這符合中國哲學家老子的道家哲學思想。老子在孤獨的自然中堅持生活的隱逸,是不同于儒家哲學在公共生活和集體社會的紀律和行為的另一種選擇。早在歐美浪漫主義之前,中國詩人就已經形象地宣揚了通過歸隱于自然的孤寂生活以實現道教的信仰。尤其是生活在魏晉時期的偉大的中國詩人陶潛,又稱陶淵明(365—427),為回歸自然隱逸的生活而辭去官職,用他的詩歌將道家生活方式和長期處于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進行了比較。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早于亨利·戴維·梭羅1500年,中國詩人陶潛就已經對美國浪漫主義作家在生命寫作與生態之間的互動進行了預示。像梭羅一樣,陶潛自傳式地將他為了自然而放棄公共生活和自己有意識的決定聯系起來,類比了自己的本性和自然景觀:“性本愛丘山”。就像梭羅在《瓦爾登湖》第一章里所寫的,他將“簡單”奉為自己的經濟原則,即使他的家比美國人的小木屋寬敞得多。相比于集體的生活,他更推崇隱居和農耕,并選擇了一些土地耕種。不過他并沒有完全異化于周遭的世界。若隱若現之間他仍然能看到村莊中人們家里升起的炊煙,聽到狗吠和雞鳴。與其被人類活動繁忙的生活所束縛,他更享受自己生活的閑暇,并樂于“回歸自然”。這種對自然的回歸既是指他自己的本性,也是指實際的自然環境。根據張隆溪的觀點,這種自然概念是指老子哲學的“自然理念”。與儒家行為相比,他認為“道家哲學家主張無為,或者說不作為,就是讓自己的行為不受干擾,讓事物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發展”。這種不作為狀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為生命的沉思方式提供了特權,相當于梭羅的“高等法則”。這個真理也作為“未受干擾的造物之詩歌”被包含在梭羅的自然觀中,既在中國有著千年傳統的園林文化中找到了其對應的部分,又在陶潛的詩中有所體現。
在中國園林文化中,創造一個大自然的微縮版本在傳統上是服務于從官職隱退之后的生活,而生命的園丁們追求的目標是取得水、植物、山石和建筑之間的平衡,以達到放松和冥想的目的。這些皇家園林工程最初是為中國的皇帝而建造的,在11世紀至19世紀間被私人、退休的官員、學者和知識分子所模仿,并在明朝(1368—1644)達到頂峰。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規劃景觀的努力似乎預示著梭羅的造物之詩歌既是整體園林環境中的生命,又是生態生命寫作的表現:
將自然景觀轉化為園林文化的實際工作,輔以各類精神文化活動,例如詩歌、繪畫、書法、音樂、古典文學研究和禪修。花園里的許多涼亭都是供個人休息或集體聚會的地方。人類建筑和自然藝術的擺放遵循所有元素相互依存的整體和諧設計。
從早期中國詩歌和園林文化表現出的沉思生活及道家哲學崇尚的不作為到梭羅的《瓦爾登湖》所體現的具有超驗主義思想的生態生命寫作,這一主張生物界所有生物和諧互動的思想脈絡在20世紀深層生態學運動中得以重現。當現代科技和城市生活方式對人類環境產生破壞性影響甚至威脅到對地球的保護時,這些深刻的生態思想浮出表面便不足為奇了。我們可以從對自然看似奇異或陌生的方面進行發掘和欣賞,看出人們對這些事態發展的反應,例如在Mary Austin《The Land of Little Rain》(1903)中出現的美國原住民的棲息地和沙漠,或者B.F.Skinner在《瓦爾登第二》(1948)中規劃的烏托邦社區。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環境運動之后,作家們以身心疾病比喻大自然的毀滅。生命寫作與生態的結合目前正在為人類與物質的自然提供彌補和治愈。
四、療愈自然與生命
泰莉·坦皮斯特·威廉斯的《避風港》代表了當代一個生態與生命寫作之間進行類比的例子,其中對自然的“非自然”對待是主要話題。在她的人生故事中,這位猶他大學環境人文學學者和生態女性主義者將她的家庭及他們所在的摩門教徒居住地與位于美國西南部以大鹽湖和沙漠地區著名的猶他州生物環境聯系在了一起。鹽湖的水位和鄰近的鳥類自然棲息地構成了全書的各個章節,而上漲的水位預示了鳥類的生存危機。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洪水毀掉了大熊河候鳥保護區后,威廉斯哀悼著穴鸮的消失,對她來說“這種鳥可以用來評估生活”。所有有機生物之間親密的相互關系是作者的重要線索:“鳥類和我分享自然歷史,這是牢不可破的事,是長期居住在一個地方的心靈和想象力的融合”。對這種和諧環境造成的干擾同樣影響著當地居民。“[…]從1951年1月27日至1962年7月11日在內華達州做陸上核彈試爆”,由此引發的湖水泛濫及對鳥類造成的災難性影響,相當于對自然的破壞性開發。基于所有有機物的相互依存關系,威廉斯感到湖水水位上漲造成鳥類消失,正如核試驗場所與患癌比例有關一樣。在序言和后記“單乳女性部落”中,她將痛失的七位家庭成員連在一起,包括她的母親、祖母和外祖母,以及她的兄弟。在與父親的對話中,她提到多年來在夢里常看到“夜晚的沙漠里有一道閃光”,而父親提醒她,她曾于1957年9月在公路上聽到過一次爆炸,看到了蘑菇云,其落塵導致了對大自然的污染,也毒害了當地居民。盡管被教育要做一名順從的摩門教女子,她仍然決定與其他九位生態女性主義者“按照郊狼、敏狐、羚黃鼠和鵪鶉的暗示”非法進入試驗基地。當她們由于這一“公民非暴力抵抗行為”被捕時,十位女性開始同唱“他們[印第安]姐妹的聲音飛過高山”。
在序言中威廉斯記錄了一個大鹽湖的發展和倒退的自然循環,這里本是大熊河候鳥保護區,被洪水破壞后,開始恢復,這也使她在自己的一代人中走上類似的循環。
正如我試圖重建我的生活,志愿者們開始重建沼澤。我坐在書房的地板上,周圍都是日記。我打開它們,羽毛從頁面落下,沙粒撕裂了書脊,白紙上的段落間壓著的鼠尾草的嫩枝增強了我的嗅覺——我記得我來自哪里以及它如何影響我的生活。[…]我借著說這個故事來治療自己[…]。
鳥類重返自然棲息地,這增強了泰莉·坦皮斯特·威廉斯對各種有機生物相互依存的信念,也引發了她的生命故事:“我曾一直退卻,這個故事使我回歸”。
為了通過重新融入有機生命循環以達到療愈的目的而退居自然這個避難所也激發了高行健沿長江而下的旅程。高行健在他的自傳體小說《靈山》中回憶了這段經歷。這位出生于中國,在1988年移居巴黎的作家和劇作家,在200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父親罹患肺癌過世,而他于1983年也被確診患了肺癌(不過后來的一次檢查將這一檢查結果證實為誤診),之后他便決定離開北京,去到位于南部的四川省偏遠林區進行自然療養,從位于喜馬拉雅山的長江源頭沿江漫游而下至東海,歷時十個月,行程總長1.5萬公里。這本代表了這段人生路程的書于1983年在北京開始創作,至1989年高行健移居巴黎后完成。盡管自傳人物以三股敘述話語進行自我陳述:客觀的敘述者“我”,熱情的敘述者“你”,還有一個中立的敘述者“他”(也包括“她”),而且因為這個敘述是由“游記,隨口說教,感受,筆記,隨筆,胡亂討論,不像寓言的寓言故事,[…]一些民歌,[…]一些貌似傳說的胡言亂語[…]”混合而成的“所謂的[…]小說!”,所以它不符合任何西方或東方的文體,但是生命寫作和生態學之間的類比是最重要的。在一次采訪中,高行健肯定地說:“在除了自然以外就別無他物的環境中生活了五個月之后,我的小說《靈山》見證了我的幸存。”這部作品的標題本身就代表了他在第一章所討論的精神生活之旅,它使“生態學家”和“原始荒地”保持著密切接觸。他從肺癌和其他約束的多重生命威脅中得以康復的決定性因素,是他與當地少數民族、佛教僧侶和道教哲學家的自然接觸。正如梭羅和威廉斯與原住民有聯系一樣,高行健從居住在山區和長江沿岸的羌族、彝族、苗族文化以及他們整體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學到了東西,他也接受了他們的佛教信仰。高行健轉而探尋佛教和道教,并重新發掘了傳統中藥的潛力,這與儒家戒律形成鮮明對比。作為治療的一部分,高行健的朋友向他推薦氣功療法,這是一種源自道教,以治療為目的,將體育鍛煉和冥想結合在一起的傳統運動方法。這種基于自然資源對整體中國傳統的信賴也體現在《靈山》這一精神之旅的整體特征和高行健的敘述結構上,這種結構重復了論述老子道家思想的《道德經》(共計八十一章)。
五、跨本土區域的環境聯盟
高行健曾去過的四川省有靈性的群山風景,似乎代表了生命寫作和生態學近乎完美的融合。這里也是藏族人的自然棲息地,他們至今仍在喜馬拉雅山上放牧牦牛,過著游牧生活。風景、人與動物之間的親密關系作為一個整體最為明顯的標志就是那些無處不在的用閃光的白色字體寫在山壁上的佛經中的神圣詞匯。五彩經幡,轉經筒,以及進燭焚香的習俗,這種自然中富有靈性的生命形式是亞洲崇拜自然的一種表現。總之,這些對自然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展現可以理解為在群山之上,以藏文咒語的形式體現了生命寫作的包容性,這咒語象征了建立信眾團體的神圣腳本,也表現了人和自然中的一切元素的關系。山壁上的神圣經文,即是生命寫作所表現出的精神富足,同時那些飛舞的經幡、儀式性地旋轉著的經筒也跨越了不同的界限。這是所有有機生命相互聯系進而擴大到與宇宙相聯的信仰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及美國的原住民社區里也發現了這類信仰。這種原住民的生活形式與日裔加拿大籍動物學家戴維·鈴木和他的合著者Amanda McConnell一起制定的深層生態學理念有共同之處,他們試圖恢復我們在自然中的位置,并重獲一種神圣的平衡:
每種世界觀都描述了一個宇宙,在這個宇宙中萬物相關。星辰,云朵,森林,海洋,和人類都是一個單一系統中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在這個系統里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孤立存在。[…]許多世界觀賦予人類一項更加偉大的任務:他們是整個系統的管理者,負責保持星辰按軌道前行,生活世界完整無缺。通過這種方式,很多早期創造了世界觀的人們構建了一種真正的生態上的可持續、可令人滿意且公正的生活方式。
在原住民習俗和自然生活中清晰可見的跨文化和跨國界的相互關系,這是加拿大日裔動物學家戴維·鈴木在中年時期認識到的寰宇視野的前提。在他的生命寫作中,他也倡導相互依存的信條。在《變形記:生命中的階段》和《戴維·鈴木:自傳》接連兩本自傳中,他把自己從一個對遺傳學感興趣的科學家變成了一個跨國生態活動家。雖然鈴木在他五十歲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時候完成的《變形記》里回憶了珍珠港事件,他們全家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遭受種族歧視的經歷,同時也回顧了他職業生涯的發展,但是在《自傳》中,他將重點轉移到了與原住民相遇后進行的跨國界跨文化分析中。在《變形記》中,他將常見的果蠅(他的第一個研究對象)與人類生命聯系起來:
三十年來,果蠅一直是我生活中的激情。在反思它們的遺傳、行為和生命周期時,我已經在許多方面都看到了我們生活中的變化與蒼蠅生命中發生的顯著變化階段相同。所有的生命形式都通過DNA從祖先那里獲得基因遺產,這是塑造我們的化學藍圖。
這種將畢生精力貢獻給科學并將人類與動物有機體進行類比是早期一種對深層生態學思想的含蓄承諾。它最終與鈴木的政治意識緊密相連,在他的第二部自傳中脫穎而出。他在田納西州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呆了兩年(1961—1962),在此期間,對于非洲裔美國人在民權運動中的訴求表示的認同,這也讓他認識到在“原子城”核武器發展中的科學發現所帶來的危險,以及在北美和納粹德國被過度傳播濫用的優生學所產生的弊端,這為他看到他與原住民之間跨文化的聯系做了鋪墊,那是他與父親的一次蘑菇采摘之旅,在弗雷澤河沿岸,靠近波士頓巴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山區:
我感到驚訝的是,與我父親相比,我覺得自己有些緊張。我是一位年輕的遺傳學教授,從來沒有見過原住民,只在媒體的片斷中了解過他們。我對爸爸的朋友或他們的背景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如何與他們交談。爸爸很放松,很容易就接受了他們是在魚類、樹林和自然方面與他有共同興趣的人[…]。
當回憶在自然中與原住民接觸的這段經歷的時候,他把學界中科研與教學視角的果斷改變與一個更廣闊的框架聯系到了一起。一方面,他認識到“我們共同的基因遺產”和“我們的身體特征”, “讓原住民立即變得更容易接受”他,也讓他看到了過去和現在的亞裔人群之間共同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邀請,于1979年將他的課堂教學擴展到面向電視觀眾,作為主持人加入了CBC電視臺非常受歡迎的節目《事物的本質》,這檔節目涵蓋了廣泛的科學和哲學問題。相信一切有機生命和跨文化原住民族群間的相互關系成為他關注環境的基礎,也為構想生命寫作中的生態使命和計劃搭建了平臺。
鈴木的《自傳》共十八章,其中有十三章描述了生態項目,其范圍從加拿大原住民的環境工作到巴西、澳大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雨林中的原住民生活。特別有啟發性的是以他的電視節目《事物的本質》為出發點與不列顛哥倫比亞群島及亞馬遜地區的原住民展開的聯合項目。在《自傳》第六章中,鈴木講述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這部作品是關于位于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夏洛特皇后群島上的一片美洲雨林。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該島的自然棲息地受到島上毀滅性采伐的威脅。在本土環保主義者與伐木公司的斗爭中,戴維·鈴木基于共同的基因遺產,支持源于自然的海達人文明。這些海達人在加拿大海岸附近的島嶼上保留了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以自然為基礎的群落生活方式形成的共同紐帶聯系起了巴西雨林,在那里鈴木的環保組織與海達活動家Guujaaw通過一起巡游的形式以支持亞馬遜地區原住民與森林砍伐之間的斗爭。這些初步接觸最終發展成為植根于巴西和加拿大的聯合項目及共同環境活動:“加拿大原住民明白,卡亞波人正在經歷他們自己曾經遭受過的苦難,于是立刻感到了他們之間的聯系”。巴西和加拿大公民之間這種跨民族的聯系,使鈴木得以成立一個跨國環保組織以及戴維·鈴木基金會。對澳大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雨林及原住民族群的進一步探訪,完善了鈴木努力促進的生態全球化方案,并使他能夠影響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峰會及京都氣候變化公約所做的政治決定。他的目標是全人類結成聯盟并以保護地球作為共同目標。他在科學和人類學方面的領悟轉化為一個生態計劃,同時也是Ursula Heise所說的“生態世界主義或環境世界公民的理想”的發展基礎。
對于亞洲、美國、加拿大從四世紀到21世紀關于自然和生命的寫作的研究顯示了不同地理位置處理所謂的自然文化鴻溝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在所有情況下,生命階段與自然進化循環的協調超越了固定的政治或文化框架的狹窄邊界,提供了跨文化的視角。為了放松、獲得安慰或休養而回歸自然,往往使人發現在自然環境中保存的原本的生命形式族群,從而獲得新的見解。在這些經驗的斡旋下,各種各樣的生命寫作似乎成為了表達生態關注的特權模式,并產生了一個以信念團結起來的全球公民跨國聯盟,他們相信生物界的共同有機基礎及參與保護地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