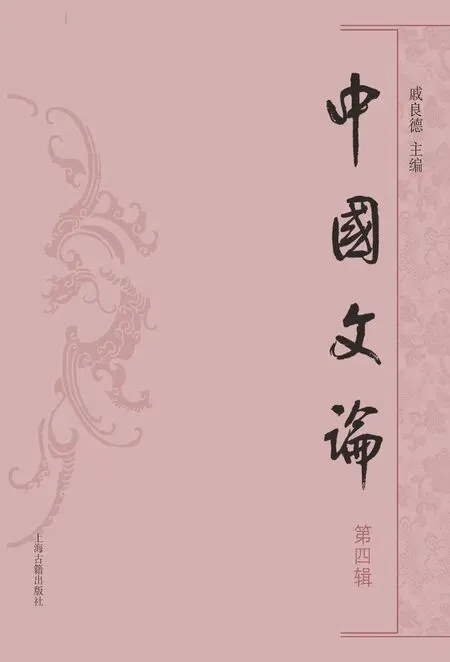生命的透支
——《文心雕龍譯注疏辨》出版感言
張 燈
經(jīng)過(guò)二十余年的苦研苦耕,終于迎來(lái)了收獲的季節(jié)——拙書《文心雕龍譯注疏辨》的繁體字本不久前已由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付梓面世了。至此,我確實(shí)長(zhǎng)長(zhǎng)地舒了一口氣,因?yàn)樗俏液蟀胼呑雍谋M心血得來(lái)的學(xué)術(shù)成果。這些年來(lái),除偶然也不得不寫一點(diǎn)懷人的、應(yīng)景的文字外,我的所有精力全都撲在這項(xiàng)作業(yè)上面了。有人或許會(huì)問(wèn),《文心雕龍》原著文本不到五萬(wàn)字,加譯加注再加辨誤析疑,真的需要花上二十倍的篇幅嗎?我要說(shuō),筆者其實(shí)是極為注重簡(jiǎn)省筆墨的。以全書485則辨條言,盡管廣征博引,鋪得較開(kāi),卻皆為前人校注訓(xùn)解的疏誤而發(fā),自信尚無(wú)廢話,即沒(méi)有一條是無(wú)的放矢、嘩眾取寵、故標(biāo)新異的產(chǎn)物。自宋元明清至當(dāng)前,前人的研究不免會(huì)留下一些空缺,校注疏解中也存在不少舛誤,更還有許多引申闡發(fā)別出心裁,反將原著讀解領(lǐng)入歧途,而且陳陳相因,以訛傳訛。這些,都是頗值得學(xué)界認(rèn)真思考的問(wèn)題。拙著的探究工作,正是從這個(gè)基點(diǎn)出發(fā),自己戲稱是學(xué)術(shù)上的“撥亂反正”。因此,我愿意寫下自己的一些感言。
跳槽的緣起
我原來(lái)是研究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和文藝?yán)碚摰模瑢懳乃囯S筆,作理論探索,主要的還是作品評(píng)述。因?yàn)榱碛斜韭殻蚪虝蜃鼍庉嫞皇菍I(yè)寫作者,只能見(jiàn)子打子,像小販一樣兜售點(diǎn)零星物兒。即便如此,也受許多限制。比如,想寫的或因犯忌而不能寫,不想寫的又不愿去作趨炎附勢(shì)的隨從。就這樣,二十余年積累下來(lái)的文稿,僅有十七萬(wàn)字,雖亦匯攏而成《藝術(shù)魅力縱橫談》的小冊(cè)子,雷達(dá)先生所作之序也說(shuō)了不少好話,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常在為自己的淺薄而慚愧。
1989年下半年起,我請(qǐng)了一年的創(chuàng)作假。當(dāng)時(shí)并無(wú)明確的選題,僅僅為擺脫煩瑣的編務(wù),想自己搞點(diǎn)研究。具體搞什么,一時(shí)尚無(wú)決斷,于是先抓武俠小說(shuō)消遣。某天讀到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龍今譯》,覺(jué)得注釋可以商兌之處頗多,譯筆也較顯生澀。隨后又找來(lái)陸侃如、牟世金先生(合著)和趙仲邑先生的同名專著《文心雕龍譯注》,比《今譯》似乎要好些確些,但仍不甚理想。這三個(gè)本子流行較廣,學(xué)人多以其為讀解《文心》的首要依據(jù)。一頭要面向眾多初學(xué)的年輕讀者,另一頭又要面對(duì)年代久遠(yuǎn)的艱深巨典,注解的準(zhǔn)確穩(wěn)實(shí)本已難甚;再加上原著以駢文寫成,譯作白話自也應(yīng)體現(xiàn)其儷對(duì)美文的風(fēng)韻吧!我有點(diǎn)躍躍欲試: 自己可不可以也來(lái)譯它一遍呢?抱著試試看的心態(tài),我翻譯了全書首三篇《原道》《征圣》《宗經(jīng)》的文字。反復(fù)潤(rùn)改后自己還覺(jué)著滿意,卻仍無(wú)把握,于是分別寄給北京和上海的兩位專家求教。碰巧的是我同一天寄稿,兩位也同一天收到,都在當(dāng)晚作復(fù),我又同一天收到了回函。他們都極表驚喜,鼓勵(lì)有加,希望我務(wù)必按自己的路子將全書譯完——他們是看到了拙稿與其他譯注本的差異。但他們也不約而同地囑我將視界放開(kāi)闊一些,譯注辨析的參照點(diǎn)不宜光局限在這三個(gè)版本上。這本來(lái)就是我的打算,試譯三則僅僅是種試驗(yàn)田而已。
在著手尋覓《文心雕龍》各種版本的同時(shí),我已展開(kāi)了自己的探究工作。雖說(shuō)資料無(wú)法像前輩學(xué)者那樣收羅詳盡,但歷來(lái)的重要刊本,尤其是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者諸多學(xué)術(shù)專著,都還算是相對(duì)完備了的,它們引領(lǐng)我去對(duì)照比較,去斟酌推敲,去辨識(shí)正誤,以求取對(duì)文本文意相對(duì)有最顯確切的訓(xùn)解闡釋,疑義疏解、去謬存真的辨析條目自然也在此過(guò)程中產(chǎn)生。
這實(shí)在是苦透苦透的差事。這里需要格外地嚴(yán)謹(jǐn)細(xì)致,絕對(duì)不可馬虎潦草,所謂要能“斷以己意”,那是務(wù)需經(jīng)過(guò)切實(shí)的詁訓(xùn),分辨出歧異而又有定見(jiàn)定識(shí)之后的一種水到渠成,與浮躁取謬、隨意圖新完全是兩碼事。即使在很小的節(jié)點(diǎn)上,我也嘗到了這樣治學(xué)的甜頭。如《序志》篇末贊辭有云:“逐物實(shí)難,憑性良易。”“逐物”一詞,各本多解指“理解、掌握事物”,兩句謂追索萬(wàn)物之理及真相本就很難,但掌握其規(guī)律則可顯得較為容易。表面看,譯解十分順暢,然又有一個(gè)不可通解處: 認(rèn)知事物之難就難在把握其“性”也即其規(guī)律上,下句再說(shuō)掌握其規(guī)律則易,豈非成了自悖式的解釋?這里或應(yīng)疑訓(xùn)解有誤。查核全書,筆者發(fā)現(xiàn)“物”“貌”等語(yǔ),實(shí)為彥和專用的寫作概念,《明詩(shī)》篇有“驅(qū)辭逐貌”句,《詮賦》篇有“品物畢圖”“寫物圖貌”諸語(yǔ),《物色》篇又有“寫氣圖貌”之說(shuō)。這里的“逐物”,也即是“寫物圖貌”,引申指寫作事業(yè),兩句應(yīng)謂: 寫作事業(yè)本就極其艱辛,掌握規(guī)律則可較顯容易。這樣解句,既顯得文順意暢,更與全書講規(guī)律、談文術(shù)的主旨緊相契合。
類似的例子尚可列舉許多。我總覺(jué)得,《文心雕龍》的字詞句、篇章表意等基礎(chǔ)性研究,確還有不少值得進(jìn)一步推勘的地方。有位專家曾肯定地說(shuō)過(guò),《文心雕龍》的研究已做得差不多了(指字詞句的基礎(chǔ)性研究)。或許是這位先生出過(guò)校勘文本,但怎可以此蓋住眾多專著而將己作樹(shù)為標(biāo)范呢?所以有專家說(shuō),此乃狂妄淺薄之見(jiàn)。我則是選定24篇重要篇目,從析疑入手,逐字逐句地斟酌,寫下辨析條目,又據(jù)已有的新見(jiàn)新識(shí)將原文重新翻譯一遍,形成了第一本專著《文心雕龍辨疑》(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1996年召開(kāi)的中國(guó)文心雕龍學(xué)會(huì)第五屆年會(huì)上,筆者提交了大會(huì)發(fā)言《關(guān)于龍學(xué)研究中的“三欠”問(wèn)題》,明確指出《文心》研究中存在著文字詁訓(xùn)欠妥、文本校勘欠慎、文意把握欠確的缺失,用事實(shí)回敬了上述說(shuō)法。這以后,自己的探索工作便始終沿此朝向前行,一直沒(méi)有停歇過(guò)。
同樣耗盡心力的還有全本的白話語(yǔ)譯工作。按比例看,譯文不過(guò)僅占全書篇幅的十分之一,花費(fèi)的時(shí)間和精力卻絕不會(huì)少于整個(gè)工程的一半。每字每句每篇譯文,我都反反復(fù)復(fù)地作了潤(rùn)改。我始終認(rèn)為,像《文心雕龍》這樣的駢儷之作,顯然不宜用一般的白話散文譯之,而更得格外地講究譯筆的遣詞、句式和文采。二十余年來(lái),我一直在摸索,想尋找一種與駢對(duì)原著能同趣互映的語(yǔ)詞句型組合,以利體現(xiàn)駢美的原文。實(shí)踐中或許算是找到了一些感覺(jué),因而對(duì)拙譯提出了兩條硬性的規(guī)定: 其一是要求譯文大體是原文的一倍。嘗試的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這二比一的比例正相合宜,拉長(zhǎng)了顯冗,壓縮了則干。其二,譯文基本都采用類乎白話文的排比句式,來(lái)對(duì)應(yīng)原作的排偶文句,力求顯現(xiàn)其獨(dú)特風(fēng)貌。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這種刻板的苛求是自己折磨自己。但是,翻譯絕對(duì)又應(yīng)是一種創(chuàng)造,我于是只能勉力為之。效果也許是好的,可以舉一段譯文作例子。《物色》的原文有以下各句: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niǎo)之聲,“喓?jiǎn)骸睂W(xué)草蟲(chóng)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連]形: 并以少總多,情貌無(wú)遺矣。
拙書的譯文則作以下譯解:
所以,“灼灼”二字寫出桃花的明麗,“依依”一語(yǔ)極盡楊柳的柔順,“杲杲”的狀寫勾畫陽(yáng)光燦燦的圖景,“瀌瀌”的描述展現(xiàn)雨雪漫漫的形貌,“喈喈”連聲仿效黃鳥(niǎo)的和鳴,“喓?jiǎn)骸悲B音模狀草蟲(chóng)的叫聲。再如“皎日”表現(xiàn)光亮,“嘒星”形容細(xì)微,一個(gè)字即已窮盡景態(tài);“參差”狀荇菜長(zhǎng)短,“沃若”言桑葉鮮潤(rùn),兩個(gè)字則又寫透物貌: 一律采用以少總多的寫法,外物情貌便都狀寫無(wú)余了。
譯解是否準(zhǔn)確妥帖,應(yīng)由學(xué)界去評(píng)說(shuō),但可以補(bǔ)充一點(diǎn)的是,原譯的“一個(gè)字即已窮盡物態(tài)……兩個(gè)字則又寫透形貌”句,付印前還更換了二字,即將“物態(tài)”易為“景態(tài)”,“形貌”改作“物貌”,目的僅僅是為了避免與上文“形貌”一語(yǔ)的重出。筆者始終認(rèn)為譯文務(wù)應(yīng)嚴(yán)謹(jǐn)考究,這個(gè)路子想是不會(huì)錯(cuò)的。眾多學(xué)者費(fèi)大力氣予注予譯,且不說(shuō)尚有信實(shí)不足處,“雅”字的目標(biāo)則恐怕大多都未能達(dá)到。這不能不說(shuō)是極大的遺憾。張光年先生或有感于此,1983年推出六篇《〈文心雕龍〉選譯》,以后增補(bǔ)至三十篇,結(jié)集稱名為《駢體語(yǔ)譯文心雕龍》。他在序言中說(shuō):“人家是那么漂亮的駢體古文,我用語(yǔ)體駢文翻譯出來(lái),力求(不能完全做到)上下句對(duì)偶相稱,平仄協(xié)調(diào)。還力求(不能完全做到)一句古文譯成一句語(yǔ)體文,不失原意。”大詩(shī)人的語(yǔ)譯,自然文筆雅麗,句型工整,對(duì)諸多注家譯文的欠缺應(yīng)是一種補(bǔ)足,甚至可以說(shuō)是樹(shù)起了一桿標(biāo)的。但因張老的語(yǔ)譯基本屬“直譯”的性質(zhì),故訓(xùn)解要求或應(yīng)嚴(yán)格些。恕我不恭,在將原著語(yǔ)辭準(zhǔn)確無(wú)漏地譯釋出來(lái)方面,個(gè)別地方似尚可值得推究。如原著首篇首句“文之為德也大矣”,張老譯作:“文的來(lái)頭大得很啊!”“文之為德”是否即為“文的來(lái)頭”意?“來(lái)頭”一語(yǔ)乃當(dāng)代口語(yǔ),不能說(shuō)口語(yǔ)不應(yīng)進(jìn)入譯文,問(wèn)題是其含義比較廣泛,可指人和事的來(lái)歷、勢(shì)頭、力度等等,盡管讀者能夠大致體察到譯句的含義,但從訓(xùn)詁嚴(yán)謹(jǐn)?shù)慕嵌妊裕硪馊钥謺?huì)有不確切感。接下去又有“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兩句,譯文作“日月交輝,高懸出天文的形象”。“疊璧”二字指日月如璧,輪番照耀大地,譯文似未予清晰地傳導(dǎo);“垂”謂布,“麗”為附著意,后句言顯示出天上無(wú)比璀璨的景象。這一訓(xùn)解若不誤,張譯是否尚有一些缺憾呢(這后一條意見(jiàn)書中雖無(wú)剖述,現(xiàn)在補(bǔ)出卻也未必嫌晚)?或許有人會(huì)說(shuō)這是挑剔,但我則認(rèn)為是對(duì)譯事該有的要求,尤其是對(duì)《文心雕龍》這樣簡(jiǎn)約而駢美的古典名著。真正嚴(yán)于詁訓(xùn)的是楊明照先生,他在《〈文心雕龍〉有重注必要》一文中引他著中的“鬼神之為德”“中庸之為德”“酒之為德”等句相較,指出“造句和用意極為相似”,“都應(yīng)作功用講”,“‘文之為德也大矣!’猶言文的功用很大啊!”釋此“德”字既確又透,堪稱訓(xùn)解古文的楷模。我開(kāi)始試譯之時(shí)尚未見(jiàn)到楊文,首句的眾多歧見(jiàn)也讓我?guī)锥确磸?fù)地推敲,最后譯定為:“文章作為一項(xiàng)德業(yè),實(shí)在是夠盛大的了”。我想,“德業(yè)”一語(yǔ)由“功用”之訓(xùn)轉(zhuǎn)來(lái),譯句又與原文語(yǔ)詞貼切相應(yīng),再三再四地斟改也應(yīng)是值得的。
審慎從事,敢于質(zhì)疑
治《文心》近三十年來(lái),我始終抱著既小心又大膽的態(tài)度,說(shuō)具體點(diǎn),那就是: 審慎從事,敢于質(zhì)疑。這是兩個(gè)基本之點(diǎn)。
不謹(jǐn)慎從事,不緊扣原著主觀隨意地闡解一通,那會(huì)將文本攪亂,錯(cuò)謬迭出,貽誤后學(xué),俗話稱之為“糟蹋圣賢”。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jiàn)。《詮賦》篇有“并體國(guó)經(jīng)野,義尚光大”兩句。“體國(guó)經(jīng)野”語(yǔ)出《周禮·天官·冢宰》:“惟王建國(guó),辨方正位,體國(guó)經(jīng)野,設(shè)官分職,以為民極。”鄭注云:“體猶分也,經(jīng)謂為之里數(shù)。”陸德明也有解釋,意謂營(yíng)建京都宮城門途,如人之有手足四體;管理郊野丘田溝洫,如機(jī)之有經(jīng)緯。這樣,“體國(guó)經(jīng)野”后來(lái)成為固定詞語(yǔ),泛指治理國(guó)家,含善規(guī)劃、有條理之意。
眾多注家訓(xùn)“體”為劃分,釋“經(jīng)”指丈量。確。但經(jīng)譯者的引申發(fā)揮轉(zhuǎn)化為譯文,意思則又與原意相距過(guò)遙,有了根本性的偏差。牟本譯為“這些都是關(guān)系到國(guó)家的大事,意義是比較廣大的”,周注又譯作“都要考察國(guó)都體制,觀看田野規(guī)劃,推重重大的意義”,其余注譯如郭本、龍本、向釋本、《義證》等等,也都未能逸出這個(gè)譯解范圍。
描摹“京殿苑獵”,了解觀察自不可免,但何以牽扯到了“國(guó)家的大事”?又何需考察“體制”并觀看“規(guī)劃”呢?似乎,辭賦家都得如當(dāng)今之各級(jí)計(jì)委主任,否則便難以命筆,這豈非成了笑話?本條二句是專對(duì)大賦而言的,篇幅長(zhǎng)大,內(nèi)容寬泛,故務(wù)應(yīng)如“體國(guó)經(jīng)野”一般來(lái)安排構(gòu)筑,以做成結(jié)構(gòu)完整、有“序”有“亂”的“鴻裁”。下句的“義”字,恐也不指含義、意義,其本訓(xùn)指容止、儀態(tài)。兩句其實(shí)是說(shuō): (那些描摹京都殿宇、游苑狩獵,敘寫從征遠(yuǎn)行、襟懷志趣的大賦)都有如經(jīng)國(guó)治疆般地經(jīng)營(yíng),體式崇尚昭明宏大。稍微細(xì)心點(diǎn)的讀者都會(huì)發(fā)現(xiàn),整個(gè)這一段介紹漢賦崛起發(fā)展,劃出長(zhǎng)篇大賦和短章小賦的區(qū)類,敘說(shuō)二者當(dāng)如何寫作,各有什么內(nèi)容和哪些特征,何來(lái)意義及影響的述說(shuō)?根本在于粗疏,不去審察整段行文的表意,不細(xì)致推究孰正孰誤,于是錯(cuò)將比喻語(yǔ)辭當(dāng)作實(shí)指來(lái)譯釋,譯意的走失也勢(shì)在必然。人們不妨比對(duì)一下,究竟哪一種譯解更顯得順貼合理些呢?
另可舉一個(gè)校勘的例子,很小,卻極能說(shuō)明《文心》研究中確實(shí)存有不少的空缺、罅漏和謬誤。《征圣》篇有“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兩句,各本的譯釋,“書契”一律解指文字。訓(xùn)釋不誤,但無(wú)論如何均不能將各句銜連起來(lái)。上文提示語(yǔ)說(shuō),圣人的著述即經(jīng)書有四種特征: 或語(yǔ)言簡(jiǎn)練,或文辭繁富,或理思明辨,或蘊(yùn)蓄隱曲。緊接著用十二句列舉若干經(jīng)書(有的為暗舉),闡述其各著的特點(diǎn),惟此排在第七、八的兩句未指何著,緊挨而言的下句“此明理以立體也”豈非成了不可落實(shí)的空話?作為大家的彥和能如此不顧前后地行文嗎?這里的讀解肯定出了毛病。經(jīng)反復(fù)思忖斟酌,終于霍然有悟: 書、契二字是否應(yīng)當(dāng)分訓(xùn)?“書”指《尚書》,“契”謂文字,此言《尚書》的文字如何如何。古文之中,“書契”二字常常聯(lián)用而訓(xùn)為文字,但單用“契”字也指文字,甲骨文至今尚有稱“契文”者。這就是說(shuō),在此處的語(yǔ)言環(huán)境中,二字分訓(xùn)最為合理,即文本校為“《書》契斷決以象夬”,這樣正能使前后十二句表述句句順暢有指,沒(méi)有任何讀解疙瘩。與下篇《宗經(jīng)》贊《尚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也完全的合拍合榫。花了許多心力,校勘僅僅添一個(gè)書名號(hào),但自己覺(jué)著值得,因?yàn)楫吘箳叱宋谋镜囊惶幷系K,也已為后出的專著所采納。僅此一則小例,或多少可以說(shuō)明,筆者是如何將小心和大膽結(jié)合在一起的。
當(dāng)然,質(zhì)疑不是目的,它僅僅是一種手段,是解開(kāi)疑團(tuán)的基礎(chǔ)。你還得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將正解(包括勝解)和闡述落到實(shí)處,才可望真正的有些學(xué)術(shù)建樹(shù)。筆者深深感到,要使學(xué)術(shù)探求有科學(xué)的推進(jìn)和提升,淺嘗輒止不行,那樣只能追隨在他人后面人云亦云;別出心裁也不妥,因?yàn)橐坏┦s嚴(yán)謹(jǐn),往往容易出現(xiàn)改正為誤的謬說(shuō)。這里,應(yīng)當(dāng)有兩個(gè)方面的突破。其一是朝著客觀的方向,即對(duì)已有的成果作鑒辨識(shí)別,認(rèn)清是非判明優(yōu)劣,學(xué)術(shù)總是在糾謬、取正、從優(yōu)的過(guò)程中前行的。其二是朝主觀的方向使勁,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學(xué)養(yǎng),深思熟慮,提煉出切實(shí)可靠的學(xué)術(shù)見(jiàn)解。這樣,質(zhì)疑便有了歸宿。
向權(quán)威挑戰(zhàn)
《文心雕龍》問(wèn)世1500年來(lái),花引蜂蝶,有眾多學(xué)者為其考訂注疏,留下的專著為后人提供了許多真知灼見(jiàn);現(xiàn)當(dāng)代出版的注本釋本譯本則更多,為普及推廣這部名著作出了突出貢獻(xiàn)。著述者多為專家學(xué)者,有的還被尊奉為權(quán)威,他們書中難道也會(huì)出錯(cuò)?是的,很遺憾,此中仍還有不少疏漏、失確,甚至是謬誤,務(wù)應(yīng)予以指出糾正。這就是說(shuō),我們首先會(huì)遇到向權(quán)威挑戰(zhàn)的問(wèn)題。筆者曾經(jīng)作過(guò)一個(gè)比喻,說(shuō)這樣做猶如輕量級(jí)找重量級(jí)比賽拳擊。但只要踏上學(xué)術(shù)探索之路,這恐怕就是難以回避的問(wèn)題了。
這里可以舉一個(gè)非常典型的例子。
《事類》篇有這樣兩句話:“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cái)?shù)千而飽矣。”字面表意清楚,疑點(diǎn)在一“千”字上。范文瀾獻(xiàn)疑曰:“彥和語(yǔ)即本《淮南》文。《淮南》又本《呂氏春秋·用眾》篇。數(shù)千似當(dāng)作數(shù)十,數(shù)千不將太多乎!”楊明照的意見(jiàn)正與之相反:“按古人為文,恒多夸飾之詞,舍人于前篇言之備矣。如雞蹠數(shù)千,即為太多,則所謂周游七十二君者,其國(guó)安在?白發(fā)三千丈者,其長(zhǎng)誰(shuí)施耶?《呂氏春秋·用眾》篇:‘善學(xué)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與蹠同)數(shù)千而后足。’是舍人此文,本《呂子》也。且本篇立論,務(wù)在博見(jiàn),故謂‘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cái)?shù)千而飽’;皆喻學(xué)者取道眾多,然后優(yōu)也。”此說(shuō)早在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心雕龍校注》新版中提出,繼后推出的注本譯本除郭注本外,文本一律據(jù)楊校寫作“數(shù)千”。盡管楊校細(xì)致精當(dāng),提供了許多卓見(jiàn)卓識(shí),但這里的一字之爭(zhēng),是應(yīng)當(dāng)肯定范注確而楊說(shuō)非的。我們?cè)摶氐綇┖偷脑渖蟻?lái)。這是駢對(duì)為文的兩句,前句說(shuō)一皮無(wú)法成裘,系實(shí)言直敘,那么,對(duì)仗工穩(wěn)的后句,也絕然不會(huì)取用夸張的修辭格。這是無(wú)可置疑的,顯而易見(jiàn)的,不然,寫出這樣的跛足文句,彥和豈能成其為理論大家?
此例之中又還套有一例。1967年臺(tái)灣學(xué)者張立齋出版的《文心雕龍注訂》取范說(shuō):“‘千’字當(dāng)為‘十’之誤”;1982年同一作者所著的《文心雕龍考異》(二著皆為正中書局版)則又校“十”為“千”,并說(shuō):“血流可以漂杵,一食何妨千蹠,皆在夸飾之列,況呂氏之作可征乎。范說(shuō)非。”學(xué)術(shù)見(jiàn)解的更改是常有的事,但將原有的追隨者轉(zhuǎn)為爭(zhēng)論對(duì)象,采用如此的口吻,實(shí)在欠妥,更何況新取的意見(jiàn)是看似依據(jù)強(qiáng)硬,卻仍有明顯的破綻,經(jīng)不起推敲的呢?
筆者將這種現(xiàn)象稱作“名人效應(yīng)”,也可稱之為“權(quán)威情結(jié)”。學(xué)界確乎普遍存在著一種跟風(fēng)的不良習(xí)氣。只要是大人物大專家講的、寫的,不對(duì)也對(duì),不深也深,一味趨從,競(jìng)相闡發(fā),甚至還奉上許多天花亂墜的贊譽(yù),殊不知這樣做不僅阻遏著學(xué)術(shù)研究的深入和提升,更還會(huì)張揚(yáng)誤識(shí)而使之成為學(xué)術(shù)定論的。
當(dāng)然,楊先生治《文心》精當(dāng)深湛,他與王利器先生被譽(yù)為校訂勘誤的“兩大功臣”是當(dāng)之無(wú)愧的,“數(shù)千”之校不過(guò)是偶然的疏失,其他校訂則又精彩紛呈。如《樂(lè)府》篇有“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兩句,前句“致”字不可通,紀(jì)(昀)評(píng)改為“制”,以后各家多沿用,1959年的楊校本也校定為“繆襲所制”。但是,唐寫本文字又作“繆朱所改”,“朱”字“改”字的出現(xiàn)想也不至于無(wú)緣無(wú)故吧!再往深處探索,《晉書·樂(lè)志下》有明確記載: 三國(guó)時(shí),魏國(guó)繆襲、吳國(guó)韋昭都曾受命改曲,那么,唐寫本“改”字不誤,“朱”字則應(yīng)為“韋”字之誤,“蓋草書‘韋’‘朱’形近”,故將文本校定為“繆韋所改”,這樣,文本與史料、異寫與辨證完整地諧合,楊校達(dá)到了何等精細(xì)的程度!
同樣為著名專家寫的《今譯》本,卻沒(méi)有楊校這樣的精度。《詮賦》篇贊辭有云:“析滯必?fù)P,言庸無(wú)隘。”王證據(jù)唐寫本改二字,校定為“抑滯必?fù)P,言曠無(wú)隘”,各本均無(wú)異見(jiàn),《選譯》《今譯》亦然,但訓(xùn)釋卻令人哭笑不得——二本注文均為“抑滯: 抑后,后面抑,即欲抑先揚(yáng)。”譯文則互有不同。《今譯》譯作:“對(duì)抑止停滯的一定要加以發(fā)揚(yáng)流動(dòng),內(nèi)容廣闊而不窄隘。”《選譯》本后句同,前句則為:“修辭下抑后一定上揚(yáng)。”盡管其注釋本作了說(shuō)明,舉司馬相如《子虛賦》寫云夢(mèng)澤即取用這種手法,但仍無(wú)法彌補(bǔ)注與譯全不相扣的疏誤,表意也模糊不清,讀者不知彥和究竟在說(shuō)些什么,哪里還有權(quán)威性可言?其實(shí),兩句言漢賦“鋪張揚(yáng)厲”(楊校語(yǔ))的風(fēng)貌特征,謂描狀靜止平板的事物都可以使之靈動(dòng)飛揚(yáng),言辭曠放又有如江河無(wú)阻無(wú)擋,毫無(wú)向后抑或先揚(yáng)后抑的含義嘛!再則,反襯手法與先揚(yáng)后抑(或先抑后揚(yáng)),恐也不該混為一談吧!
舉出不少實(shí)例,為的是說(shuō)明自己的權(quán)威觀。筆者是極其敬仰專家學(xué)者的權(quán)威論著的,全書征引他們的述說(shuō)已達(dá)數(shù)不清程度便是明證。但同時(shí)也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權(quán)威性不是天上掉下來(lái)的,也不是別人硬貼上去的,它是在學(xué)術(shù)實(shí)踐中自然形成的一種客觀存在,是經(jīng)過(guò)積累、深化、提煉后成為普遍認(rèn)同的一種真知灼見(jiàn)。另一方面,權(quán)威性并不等同于萬(wàn)能性。專家學(xué)者即便在總體上、諸多方面的論斷有其權(quán)威性,卻也無(wú)法保證在每一個(gè)節(jié)點(diǎn)上的見(jiàn)解都確鑿無(wú)疑,此即寸有所長(zhǎng)、尺有所短之謂也。所以,既要充分尊重權(quán)威,遵從他們的科學(xué)論述,但也不宜盲目迷信,將謬誤也奉為圭臬。這中間,鑒辨是必不可少的,膽識(shí)也是不可或缺的。
挖一口深井
除了朝客觀方向求取突破和推進(jìn),又務(wù)須要求自己在主觀上作出刻苦的努力。兩方面的互動(dòng)相加,才可望獲取有價(jià)值的學(xué)術(shù)建樹(shù)。筆者的探究工作也是雙管齊下的,但鑒于以往寫的文字涉足古典文學(xué)領(lǐng)域相對(duì)較少,學(xué)養(yǎng)受限,因而盡量要求夯實(shí)自己,反復(fù)審核本人見(jiàn)解的正確性合理性,也即在主觀層面上筆者花費(fèi)了更多的力氣。
如《祝盟》篇的“太史所作之贊,因周之祝文也”兩句,唐寫本則作“太祝所讀,固祝之文者也”。這里的“贊”字,具體指漢代帝王葬禮所用的哀策文字。唐寫本的后句,顯然欠合乎邏輯,哀策講究文采,其他祝文難道就不求文采了?所以,好些主張依唐寫本校訂的注譯本,譯后句仍據(jù)今本文字。前句的“太史”則有歧見(jiàn)。周注釋本說(shuō):“太祝: 《后漢書·百官志》太常卿屬下有太祝令,‘凡國(guó)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又太史令,‘掌天時(shí)星歷’,不管讀祝。”楊校說(shuō)同。看來(lái)鑿鑿有據(jù),彥和“太史”一語(yǔ)似乎是用錯(cuò)了。但是,古代職官禮儀極其繁復(fù),不同情況下有不同規(guī)定,司職也恒有交叉。為探究竟,筆者查閱了《后漢書·禮儀志下》,其中詳盡記錄了漢代大喪禮儀的過(guò)程。從太子即位到靈柩起駕再到梓宮入穴,多次頌讀謚策,有太尉讀、太史令讀、太祝跪讀等儀式。疑團(tuán)解開(kāi),能確知太史讀策的說(shuō)法并不為誤。此例看似有現(xiàn)炒熱賣的味道,但因征之于史載,細(xì)斟細(xì)酌,不斷往深處探尋開(kāi)掘,這樣得出的結(jié)論想來(lái)是準(zhǔn)確的,也應(yīng)當(dāng)是有學(xué)術(shù)力度的。
《文心雕龍》五十篇編次有無(wú)顛倒錯(cuò)亂,也是對(duì)研究者學(xué)養(yǎng)識(shí)力的一個(gè)驗(yàn)測(cè)。最初或由《物色》篇引起,范注云:“本篇當(dāng)移在《附會(huì)》篇之下,《總術(shù)》篇之上。蓋物色猶言聲色,即《聲律》篇以下諸篇之總名,與《附會(huì)》篇相對(duì)而統(tǒng)于《總術(shù)》篇,今在卷十之首,疑有誤也。”劉釋說(shuō):“此篇宜在《練字》篇后,皆論修辭之事也。今本乃淺人改編,蓋誤認(rèn)《時(shí)序》為時(shí)令,故以《物色》相次。”王證也以為:“范氏獻(xiàn)疑是。……惟此篇由何處錯(cuò)入,則不敢決言之耳。”郭本則干脆將篇次作了較大幅度的調(diào)整,原四十二、四十三篇的《養(yǎng)氣》和《附會(huì)》移前為二十九、三十篇,《事類》第三十八移至三十二篇,《物色》篇又置于《夸飾》、《隱秀》之間為第四十二篇。依據(jù)是《序志》篇有“剖情析采”語(yǔ),《養(yǎng)氣》、《附會(huì)》、《事類》皆屬“剖情”類,故前置與《神思》諸論相銜;而《物色》則屬“析采”部分,與劉釋論修辭的說(shuō)法相近,因而插入趨后。有人提出的另一個(gè)理由是全書五篇為一卷,據(jù)《序志》有“崇替于《時(shí)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長(zhǎng)懷《序志》,以馭群篇”等語(yǔ),故《物色》當(dāng)移前,《時(shí)序》則應(yīng)移于十卷之首 (參見(jiàn)臺(tái)灣版《考異》)。這一篇次訛誤說(shuō)影響甚巨,臺(tái)灣著名專家李曰剛先生撰著的《文心雕龍斠詮》(國(guó)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huì)編印,1982年),也據(jù)以重新編排了后半部篇次,只是并未完全依照郭本所列的次序。
這些均為大專家的意見(jiàn),從還是不從,確實(shí)相當(dāng)考驗(yàn)人。
細(xì)酌各說(shuō),似都不怎么經(jīng)得起推敲。據(jù)不完全的敦煌殘本看,唐時(shí)本書篇次已定,所列十五篇(完整的十三篇)與今本次第合。接下來(lái),迄今能見(jiàn)的宋元明清版本,除宋本《御覽》篇載有佚外,其余如元刊至正本、王惟儉的《訓(xùn)故》本、梅慶生的音注本,以及日本所藏的幾個(gè)版本,篇目編次也一律不見(jiàn)差錯(cuò),何以沿一千五百年而來(lái)的今本突然又有編序的訛錯(cuò)了呢?篇次誤排的版本依據(jù)絲毫未予提供,也無(wú)法提供,僅歸咎于“淺人改編”,在印刷條件很不發(fā)達(dá)的古代,這實(shí)為極難想象的事。深入一步探究,可知全書五十篇,分為十卷,每卷五篇,乃后人為編纂齊整而設(shè),并非按類剖劃(明楊升庵批點(diǎn)曹學(xué)佺評(píng)《文心雕龍》列篇而不分卷即可為證)。由于總論五篇,文體論二十篇,以致造成依類定卷的錯(cuò)覺(jué)。如若真的如此,《序志》具有“以馭群篇”的獨(dú)立性,與《時(shí)序》、《才略》等均不類,豈非也應(yīng)自成一卷?至于說(shuō)《序志》所列篇名可標(biāo)明篇第也不確。彥和是撮舉選舉,并非全列,怎可作為篇次排列的依據(jù)?紀(jì)昀總其成的《四庫(kù)全書簡(jiǎn)明目錄》其實(shí)已說(shuō)得非常明白: 《文心雕龍》“分上、下二篇。上篇二十有五,論體裁之別;下篇二十有四,論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為二十五篇。”可見(jiàn)古人亦未將卷的編排和類的歸屬完全等同起來(lái)。回到《物色》所論之內(nèi)容,劉釋的“論修辭”說(shuō)顯然欠妥,《義證》已指出:“按劉永濟(jì)在下邊對(duì)本篇的解說(shuō),也不限于‘論修辭之事’”,因《物色》并未如《比興》、《夸飾》那樣專論修辭手法,也不像郭注所言屬“析采”即論述藻采的運(yùn)用,而是闡述文學(xué)描寫與自然景色的關(guān)系,與《時(shí)序》等篇論文學(xué)與時(shí)代、與作家才分、與文學(xué)鑒賞等關(guān)系相協(xié),列于此處正得其所哉!將本篇論題縮小到僅涉藻采或修辭事,自會(huì)懷疑篇第有誤,問(wèn)題恐出在注釋家自身的理解上了。
只要不斷地深入,學(xué)術(shù)探索就可望有所進(jìn)取,筆者在《隱秀》篇的校訂上就頗有體會(huì)。全書之中,此篇最為特殊,即由于版本缺失一頁(yè),引錄不全的宋本《御覽》未列該篇,元至正本起各刊本皆缺四百余字。二百五十余年后稱找到佚文,明末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予以納入,清黃叔琳輯注本亦予采用,廣為流傳后遂有完篇的今本。但由此又帶來(lái)了補(bǔ)文真?zhèn)蔚恼摖?zhēng),至今未有結(jié)論。筆者覺(jué)得,作為學(xué)術(shù)課題,真?zhèn)沃q可以繼續(xù);但從讀解文本、把握原著論旨的角度看,補(bǔ)文理當(dāng)納入殘文,即便其并非原著之舊也應(yīng)如此。要將這兩點(diǎn)區(qū)分開(kāi)來(lái)。試想,原文論隱論秀(指復(fù)意含蓄和篇有警策的兩種手法),殘文則呈現(xiàn)一種論隱有之、舉例闕如,言秀無(wú)論、僅舉一例的狀況,如何能做到論述的完備?細(xì)酌殘文,又可發(fā)現(xiàn)為銜接殘篇文字,似已留下有文人作過(guò)文句修潤(rùn)的痕跡(如本當(dāng)有的“晦塞為深,雖奧非隱”二句八字,諸多刊本皆不列;“隱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兩句,則又簡(jiǎn)縮為“秀句所以照文苑”即值得思考)。用心良苦,意在補(bǔ)漏。但缺失逾半,怎么補(bǔ)救都無(wú)法使之成為完論;只有暫時(shí)擱置真?zhèn)沃娑鴮⒀a(bǔ)文納入篇中,方為頗佳的一種選擇。至于有的專家竭力貶斥補(bǔ)文,將其說(shuō)得一無(wú)是處,那是因?yàn)橄日J(rèn)定其屬偽而出現(xiàn)的偏執(zhí),這里就不予展開(kāi)了。
另有一則校勘或還相當(dāng)有趣。《奏啟》篇“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句,本勉強(qiáng)可通,卻不夠順溜,王證據(jù)有板本“言”下有一小寫的“二”字,以為是重字符號(hào),故添一“言”字,校句為“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言貴直也”。但筆者又想,此小寫的“二”字,可否視為乙正符號(hào)(稍有連筆即酷似“乙”字)?那么,逗號(hào)宜移前一格,校句應(yīng)作“孝成稱班伯之言,讜貴直也”。這是其他諸本皆無(wú)的校訂,非為標(biāo)新,乃是依據(jù)前人提供的點(diǎn)滴啟示,再經(jīng)獨(dú)立思考而有的結(jié)果。至于確否,自有待于學(xué)界鑒辨,但起碼做到了文順句暢,也說(shuō)明了筆者是如何對(duì)待校注譯釋工作的。2003年12月,本書上編《新注新譯》單獨(dú)由貴州教育出版社刊行后,反響確實(shí)較好,兩位專家先后在《人民日?qǐng)?bào)》、《光明日?qǐng)?bào)》發(fā)表書評(píng),肯定拙書取得的成績(jī),也透露了作者此中的艱辛和磨難。筆者并無(wú)就此歇一歇的想法,我將鼓勵(lì)當(dāng)作鞭策,又用六七年時(shí)間對(duì)全書再做精耕細(xì)作的修訂,因而有了今天奉獻(xiàn)的這本較為完整的書稿。
感言說(shuō)完,似還應(yīng)贅述一句: 為撰著這本書稿,我是付出了沉重代價(jià)的。
首先是精力心血的投入。我深知,蠟燭的光焰在燃燒中閃爍,學(xué)術(shù)的成果靠心血來(lái)澆灌,要認(rèn)真切實(shí)地做點(diǎn)學(xué)問(wèn),務(wù)須有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這是從起步直至完稿就一以貫之的認(rèn)識(shí)。再加上長(zhǎng)期以來(lái)總有編務(wù)雜務(wù)纏身,我的撰述于是不得不加倍努力,比其他同行花費(fèi)更多的時(shí)間和精力。從上文種種舉例可折射出筆者耗力之巨外,另還可提供些數(shù)據(jù)作補(bǔ)充說(shuō)明。自1992年筆者先只身調(diào)回上海后,除必不可少的本職工作和吃飯睡覺(jué)外,每天工作約十四個(gè)小時(shí),其中起碼有六到七個(gè)小時(shí)用于《文心》研探。1995年起,我受點(diǎn)照顧擺脫了行政雜務(wù),此后仍每日苦耕十來(lái)個(gè)小時(shí),并堅(jiān)持十余年之久,全書殺青、潤(rùn)改修訂都在這一時(shí)段里完成。此間筆者基本不看電視,沒(méi)有娛樂(lè),全身心地投入了治學(xué)之中。單以僅占十萬(wàn)字篇幅的譯文為例,每一篇的修改潤(rùn)色一律都在十二遍以上,多的則自己也難以計(jì)數(shù)了。可以說(shuō),筆者就像是一名手工裁縫,《譯注疏辨》乃是一針針一線線綴縫而成的成品。
其次是身體虧了垮了。竭盡思慮與元?dú)鈸p耗往往是聯(lián)袂而至的。古人早有論述,道理筆者也懂,無(wú)奈謀事未果只能顧此失彼。最初出現(xiàn)的是短暫性暈厥,大概只有幾秒鐘。詢問(wèn)醫(yī)生,說(shuō)可能是“咳嗽性暈厥”,問(wèn)題不是很大,于是并未將它當(dāng)作一回事。多少年以后作腦部CT檢查,才發(fā)覺(jué)后腦有一個(gè)腔梗灶。近幾年來(lái),眩暈來(lái)了,失眠來(lái)了,消瘦來(lái)了,耳聾也來(lái)湊上熱鬧……這些,看起來(lái)似與學(xué)術(shù)無(wú)關(guān),但我知道,它們無(wú)疑都是殫精竭慮的副產(chǎn)品。不過(guò)我并不失悔。人生一世,白駒過(guò)隙,能留下點(diǎn)有價(jià)值的東西,恐比渾渾噩噩活它百歲更有意義。所以,有人若要問(wèn)我是如何從事學(xué)術(shù)探索的,我想歸納的第一句話就是: 生命的透支!
2015年10月寫定于上海
并非贅語(yǔ)
“感言”寫完,總覺(jué)得還有一些話是應(yīng)該說(shuō)一說(shuō)的。它們不屬感言范圍,然棄之則可能會(huì)帶來(lái)缺憾,故這里還是用“贅語(yǔ)”形式將它寫出,好在文字不長(zhǎng)。
其一是要表白,今后將不準(zhǔn)備再搦筆為文了。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先是耳朵壞了,突發(fā)性的,殃及雙耳。某天早晨參加個(gè)會(huì),瞬息間發(fā)覺(jué)聽(tīng)力下降,辨音模糊。當(dāng)時(shí)我并不怎么著急。直到早年的一位學(xué)生,現(xiàn)已任三甲醫(yī)院的五官科主任,告訴我這類神經(jīng)性耳聾目前尚無(wú)治愈的辦法,這才讓我緊張起來(lái),中醫(yī)、西醫(yī)、中西結(jié)合再加偏方、秘方輪番療治,也配了價(jià)格不菲的助聽(tīng)器,均無(wú)顯效。作為一名文化人,不時(shí)要發(fā)出點(diǎn)自己的聲音,要與外界有交流、碰撞乃至于論辯,一旦聽(tīng)力受損會(huì)帶來(lái)多大的苦惱!然而禍不單行,不幾年慢阻肺又纏上賤軀。疾患的折磨已難經(jīng)受,不料更重的精神打擊有如炸雷般地劈來(lái): 2014年歲末,拙荊因猝發(fā)性心力衰竭而棄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迎來(lái)了《譯注疏辨》的出版。悲多于喜,交雜翻滾,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不知自己在做些什么,也不知下一步還要做些什么。也是在這段時(shí)日,我先后驚悉了王運(yùn)熙先生、王更生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深感痛惜,另一方面也倏忽意識(shí)到自己的年齡——在專治《文心》的同時(shí),我曾寫過(guò)多篇懷人的文章。他們往往年長(zhǎng),有的還是長(zhǎng)輩,我寫紀(jì)念文字理所當(dāng)然;現(xiàn)在,是不是已到該由他人為我寫祭文的時(shí)候了?但是,懷念兩位師尊的文章必須寫,癱在床上都務(wù)必寫。我給張文勛老師寄了書寫了信,表達(dá)了參加2015年昆明年會(huì)的意愿和顧慮。張老幾次熱情函邀我與會(huì),就這樣,我拖著支離的病體,不顧醫(yī)生勸阻,孩子反對(duì),只身從上海趕赴昆明。這實(shí)在是一次冒險(xiǎn)的遠(yuǎn)行。戚良德先生事后在文章中說(shuō)我面容、步履“清癯”而“蹣跚”(見(jiàn)《中國(guó)文論》第三輯279頁(yè)),其實(shí)又何止這些,赴昆明我只背了個(gè)雙肩包,下車時(shí)匯入人流趔趔趄趄前行,下石梯曾被人輕輕擠搡一下,幾乎跌倒釀成大禍……為的是什么??jī)H僅為將《憶王運(yùn)熙、王更生兩位師尊》的文章在年會(huì)上念一念,獻(xiàn)上晚輩深摯的哀思。或許是皇天佑我,8月8日上午,我在開(kāi)幕式上誦讀此文,下午又接上海電話,說(shuō)《文匯報(bào)》也于同日刊出。這是我三年來(lái)寫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我與友人說(shuō),這是不得不寫的文字,不寫良心難安的文字啊!因此,所謂不再為文的說(shuō)法得稍作注解,即系統(tǒng)性的課題研究已經(jīng)無(wú)力為繼了,“小令”或許會(huì)有,但也不會(huì)多。
其二,既已宣告擱筆,我似應(yīng)將筆名“張燈”的由來(lái)簡(jiǎn)述一二。此筆名是為悼念我唯一的舅父而啟用的。舅父張路先生畢業(yè)于杭州藝專,豐子愷先生弟子,全國(guó)著名的版畫家,上世紀(jì)五十年代因眾所周知的原因由北京掃至哈爾濱,又成了北大荒畫派的一名創(chuàng)始人。粉碎“四人幫”之后他興奮已極,出席除“四害”后的首屆全國(guó)美展,正值伏天,冒酷暑四處奔走,看望朋友,更兼好喝一口并亂吃亂喝,由此染上了爆發(fā)性肝炎,醫(yī)學(xué)上稱“急性黃萎縮”。回到哈爾濱便即發(fā)作,來(lái)勢(shì)迅猛,各項(xiàng)體征指標(biāo)急驟下降,一天一個(gè)樣,家母欲飛往哈市也都趕不及了。我與舅父相處時(shí)日有限,但卻知他是苦出身,杭城求學(xué)時(shí)常穿木屐過(guò)冬,原因是外公并不支持他深造……為緬懷才華卓然卻又命途多舛的舅父,我在1979年10月發(fā)表的一篇評(píng)論文章中第一次用了“張燈”的筆名,意謂: 黃泉路上張起一盞燈,舅舅您老人家走好!后來(lái)刊出的多篇拙文續(xù)用此名,賴不掉了,就這么沿用下來(lái)。
其三,回歸本書,想糾正一下錯(cuò)謬之處。因?yàn)槭俏淖终系K頗多的古文文本,又用繁體字排印,故筆者親自參與了一、二、三校的校勘工作,即使在病痛心痛最甚的終校期,我仍咬牙逐字逐句地校訂,相信錯(cuò)謬處不會(huì)很多,因辦事細(xì)心可算我的一大長(zhǎng)處。然而書稿印出翻開(kāi)扉頁(yè),即讓我大吃一驚: 短短的“作者簡(jiǎn)介”欄,連標(biāo)點(diǎn)僅三百字,竟然有了三處更動(dòng)。
“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文心雕龍學(xué)會(huì)理事,社科系列研究員”的三個(gè)短句,均為介紹作者身份語(yǔ),宜用逗號(hào)隔開(kāi),本人提供的電子版稿本正這樣標(biāo)示。出書時(shí)卻改了標(biāo)點(diǎn):“……會(huì)員。……理事,……研究員。”并列的話怎能一句末用句號(hào),二句末又用逗號(hào)呢?即使全用句號(hào)也還可以說(shuō)得過(guò)去嘛!
另一處則是改正為誤的例子,將“譯筆”改成了“釋筆”。原稿說(shuō)的“譯筆講究文采”,其實(shí)是王運(yùn)熙先生對(duì)拙著譯文的評(píng)價(jià)用語(yǔ)(參見(jiàn)2015年8月8日《文匯報(bào)》,《文心雕龍新注新譯》序言中王老也說(shuō)過(guò)同樣的話語(yǔ)),是常用詞語(yǔ);“釋筆”語(yǔ)以前則未聞未見(jiàn),表意亦不大明豁,難道是指所有的行文?那筆者是不敢接受這一恭維的。
總之,指出上述數(shù)端,純?yōu)榭闭`,希望有拙書者能作點(diǎn)更改,出版者也在付印底本上給予訂正。筆者不怨出版社,也不怨著手審定者(從未打聽(tīng)、也未提過(guò)些許意見(jiàn)即可為證),更不會(huì)怨責(zé)編杜怡順先生。他其實(shí)是一位非常稱職的編輯,既細(xì)心又有水平,為該書的校訂出力不少,將“前言”的征引部分單獨(dú)列出而設(shè)置“凡例”,顯得規(guī)范而條線分明,就是他提議并操刀的,因他深知筆者當(dāng)時(shí)正陷于身心的雙重災(zāi)情之中;接到新書,他同樣也是傻了眼的。我只能怨自己,多的精力都耗了,付印前為何不捋上一遍呢?這不是假話,書出之前我寫過(guò)一首七言“打油”,可表白當(dāng)時(shí)寧可出書、不計(jì)健康的心態(tài)和目標(biāo)。詩(shī)曰:
殘燈已屆古稀年,舊作重溫倍汗顏。
待到龍書全本出,黃昏抱病亦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