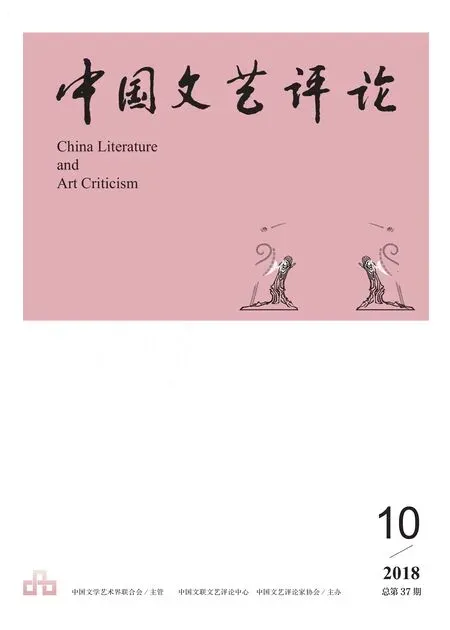現實主義的世俗相貌與時代意義
2018-11-12 18:14:15吳冠平
中國文藝評論
2018年10期
關鍵詞:現實
吳冠平
《我不是藥神》今夏熱映,引來社會各界從民生層面到藝術層面的廣泛討論。影片不僅觸發了政府高層對高價抗癌藥問題、醫保問題的關注,也為中國電影在新時代的創作導向給出了頗有意味的啟示。從2017年的現象級影片《戰狼2》,到2018年的《紅海行動》《我不是藥神》,中國電影似乎漸漸從主旋律電影、商業主流電影、類型電影的不斷試錯和摸索中,找到了如何在國家精神、民生訴求和民族利益的三結合中,講述中國故事的價值坐標。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樣一種高蹈的意義構型,在具體的創作中仍不免有被庸俗社會學邏輯、刻板的形象塑造干擾的危險,最終淪為一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夾生飯。《我不是藥神》作為一個標本,它的意義與其說是某種我們曾經熟悉的藝術觀念的重生,莫如說是借由世俗的力量,調整了寫實主義的參數。
一、實與真的現實觀
《我不是藥神》取材于真實的社會事件。縱觀中國電影史,從20世紀20年代《閻瑞生》發端的社會問題劇,到30年代左翼思潮帶起的新興電影,40年代的進步電影,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文革”反思電影、改革題材電影,莫不是把觸碰大眾敏感神經的“實”事作為電影敘事賣點,從而引發了觀眾的觀影熱潮。“實”中包含的社會信息、社會情緒通常易于滿足觀眾的欲望訴求,建立起敘事的基本信任關系。對于電影而言,“實”既是物質現實復原的本性,也是虛構得以成立的骨架。亞里士多德曾告誡劇作家,采用合理的不可能性比不合理的可能性要高明。……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18期)2024-06-07 22:40:49
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 01:53:20
人大建設(2019年12期)2019-05-21 02:55:32
語文世界(初中版)(2016年6期)2016-06-29 22:44:39
現代計算機(2016年12期)2016-02-28 18:35:29
發明與創新(2015年25期)2015-02-27 10:39:23
中國衛生(2014年12期)2014-11-12 13:12:38
杭州科技(2014年4期)2014-02-27 15:26:58
新東方英語(2014年1期)2014-01-07 20:01:29
雕塑(1999年2期)1999-06-28 05: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