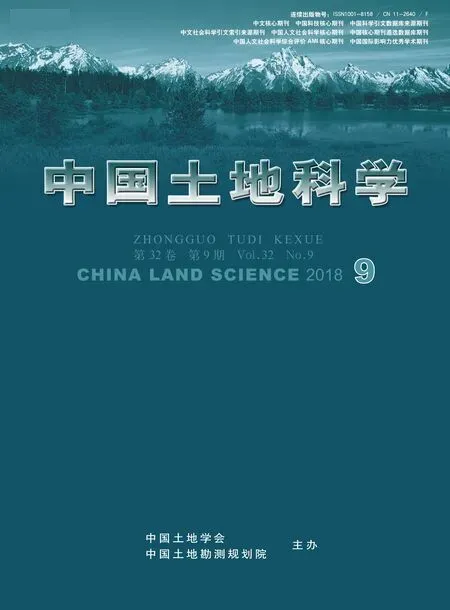農民土地抗爭的行動邏輯及其治理
王永勝,陳剩勇
(1.浙江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310018;2.浙江大學地方政府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
1 引言
土地是財富之母,歷史的長河中農民圍繞土地的爭奪和斗爭從未停息,當下農民與政府的拆遷與反拆遷抗爭仍然時有發生。農民土地抗爭行為出現表明農民土地權益在改革和利益調整中受損,農民土地抗爭危害到了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各級政府既要深化推進改革,又要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目前經濟學認為土地的產權不清晰是土地沖突的緣由,解決之法是要界定好土地產權;法學關注土地沖突背后的法律條文之間內在的不銜接,提出應該及時修訂相關土地法律法規;政治社會學認為土地規則模糊性、土地相關的利益群體變化等對地權沖突造成了重要影響;而人類學重在研究地權觀念的變化,側重于農民觀念的變遷研究。概言之:“經濟學與法學的研究主要運用了‘侵權—反抗’的分析框架;政治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則可以歸類為‘轉型—失范’的分析框架。”[1]從土地政治學角度,結合政府與農民歷史上土地關系來探討土地抗爭,是一個新的研究路徑,具體研究涉及如下幾個問題:農民基于土地展開的抗爭與政府互動是如何博弈的?他們之間歷史上形成的行動邏輯和相互形塑機制有哪些?政府應如何將農民土地抗爭引入制度化的治理渠道?
本文從情境化描述中給農民土地抗爭進行形式化建模,將三個歷史時期的土地抗爭類別化,以土地抗爭作為描述的工具和概念,以農民土地抗爭訴求、抗爭方式、政府對其的態度為次級概念,探求作為解釋工具的土地抗爭的行動邏輯和機制,最后提出現代社會政府對土地抗爭的治理方法。本文試圖從歷史的角度發現農民土地抗爭的行動邏輯和機制,為社會中土地沖突提供治理對策。
2 農民土地抗爭的一個互動解釋模型
學術界認為土地沖突是指“組織或個人為了取得、捍衛、行使土地權益或者排除他人干預而采取的謾罵、中傷、聚集、斗毆、對抗并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或較大社會影響的過激行動”[2]。筆者認為土地抗爭是指農民圍繞著土地及其附著物的歸屬展開的對土地權益被侵犯的群體反抗行為,其中政府作為利益相關方介入其中。土地抗爭在范疇上小于土地沖突,其區別于土地沖突主要有三點:一是其意為農民群體抗爭,不研究農民個體間的土地沖突和抗爭行為;二是土地抗爭中政府必介入其中,要么是直接的土地抗爭對象,要么是利益相關方,土地抗爭不包含單純村莊械斗之類的不涉及政府的斗爭;三是土地抗爭研究爭取中性立場,認為農民土地抗爭更多是理性行為,不認為土地抗爭是過激行動。
土地抗爭關注農民抗爭者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地方政府作為抗爭對象,抑或抗爭的解決方,是分析土地抗爭的必要要件。由此,筆者建構了一個農民土地抗爭訴求、農民群體抗爭方式與政府對農民土地抗爭態度的解釋模型,這個解釋模型的關鍵詞是情、理、法。情是指人之常情、順乎民心合乎民意,理是指天理、事理、社會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乃至公共道德。情、理合在一起含有現代公序良俗之意,情理存乎人心,是人們判別事件正義與否的衡量標尺;而法是世俗統治者制定的強制性規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古代以刑法為主,具有強制執行力。法一般反映社會的情和理,“法不外乎人情”表達的正是法與情、理具有相通性。在理想狀態下情、理、法是交互融合的,“天理、國法和人情三位一體”[3]。但在社會管理中統治者有時采用嚴刑峻法,違背天理人情,行的法不是良法,此種情形下儒家強調“從道不從君”即意指道高于世俗權力,理先于法。在農民土地抗爭事件中,農民往往首要考慮情和理,認為法并沒有維護他們的利益,法不責眾,有時漠視法,甚至挑戰法的權威。
筆者把農民土地抗爭訴求按照合情合理與否分為合情合理訴求和不合情不合理訴求,抗爭方式按照合法與否分為合法抗爭與非法抗爭。政府對抗爭的態度依據其認可抗爭行為的程度自高到低分為默認型、容忍型和禁止型三類。默認型是指政府認為抗爭行動合法可控,認可其行為;容忍型是指抗爭可能沖擊社會秩序,但在政府可控范圍內,政府部分認可;禁止型是政府認為抗爭涉及到抗稅等重大事項或伴隨有嚴重暴力,政府必須嚴厲禁止。他們之間的土地抗爭互動如圖1。

圖1 土地抗爭訴求、農民土地抗爭方式與政府對抗爭態度的解釋模型Fig.1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land struggle appeal,rural land struggle means and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land struggle
圖1中的橫軸代表農民土地抗爭訴求的合情合理程度,自左向右遞減,縱軸表示政府對抗爭的態度,自下而上表明政府認可抗爭的態度在遞減,圖中的虛線表示農民土地抗爭方式的合法界限,虛線之上表示農民土地抗爭方式違法,虛線之下表示農民土地抗爭方式合法。圖中的實線表示政府制度化吸納抗爭的能力,表征的是政府將抗爭訴求吸納為體制內制度化解決的能力,在這條線的左邊表示體制已經將部分抗爭吸納進體制內,有制度化的解決農民土地抗爭的渠道,在這條線的右邊表明抗爭在體制外展開。農民土地抗爭主要關注抗爭訴求的合情合理程度,政府則主要關注抗爭方式的合法程度,以決定政府對抗爭的態度。如此理論上可區分出4類不同的土地抗爭,圖中的拋物線表示抗爭類別,拋物線上的A、B、C、D分別代表不同的抗爭互動情形,具體見表1。

表1 4類不同的土地抗爭Tab.1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struggle
3 歷史維度下的農民土地抗爭
依據土地抗爭中農民主體自覺性與否將中國農民土地抗爭史分為三個時期,其中農民土地抗爭呈現認知解放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時期,在此之前,稱之為前現代社會,農民土地抗爭是基于生存本能的驅使;之后的社會稱之為現代社會,農民土地抗爭則呈現出主體自覺維權的特征。
3.1 前現代社會天災人禍引發土地抗爭
自進入階級社會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社會皇帝將土地賞賜給王侯將相,他們成為封建土地擁有者,即地主,地主靠地租剝削農民。農民耕種地主的土地繳納租金成為佃農,此外還存在自耕農。農民與地主間關系在封建社會整體上相對穩定。發生土地抗爭一般是由于兩個原因,一為天災,比如發生水災、旱災、蝗蟲災害等導致土地收益減少。古代的稅制并不高,比如兩漢時“三十稅一”,但佃農租種地主的地租可能高達土地收成的50%,唐代以后用定額租取代了分成租,但佃農一旦遇到災荒年則交定額租困難,生存受到威脅,這是引起佃農反抗的原因之一。二為人禍,比如統治者昏庸、官府的橫征暴斂、戰亂以及貪官污吏對自耕農土地的巧取豪奪等導致農民陷入生存困境。統治者“急征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4]。土地兼并“主要由封賜、圈地、投獻、權貴吞并民地等政治因素造成”[5]。農民土地抗爭的最高形態是農民起義,比如唐朝王仙芝起義緣由是關東發生旱災,官吏貪賦重稅,責任在天災和官員不體恤民情。北宋初年土地大多被官僚和豪強霸占和兼并,農民被迫淪為旁戶即佃戶,“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佃戶負擔沉重,加上天災頻仍,導致川、陜王小波李順起義爆發。實際上,漢末、宋代、元末和明末農民起義均與官僚豪強巧取豪奪兼并土地有關。
雖然抗爭不合法,但佃農認為在災荒時合情合理。針對天災,佃農往往提出減少租金的合情合理的抗爭訴求;針對人禍,佃農反對橫征暴斂,自耕農反對土地兼并。農民土地抗租斗爭一般采取簡單的“喝血酒結盟立誓”的方式聚集,奉行“武裝自衛,同心抗租”[6]。封建統治者對待抗爭的態度是恩威并施、剿撫結合,一方面采取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以“廣皇仁、遏亂蔭”;另一方面采取發放救災款、募資捐款、開倉平糶放糧等辦法賑災。但對暴力行為嚴加鎮壓,“安分待賑者為饑民,必須賑撫;乘間搶掠者為亂民,必須嚴拿[7]。”總之,前現代大部分的農民土地抗爭屬于A類抗爭,是天災人禍導致的合情合理抗爭,統治者對抗爭的態度是默認和容忍的;少部分屬于B類抗爭,采取的是暴力抗爭或農民起義,統治者采取鎮壓的禁止型態度。
3.2 革命社會農民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徹底改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這是一種革命性的土地權屬變更,但農民缺少主體的階級覺悟,農民的被解放需要從外部輸入革命的意識形態,是中國共產黨引導農民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早在大革命后期,黨對地主在政治上進行打擊的方式就有“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游鄉、關進縣監獄、驅逐、槍斃”[8]。在土地革命時期黨采取“打土豪、分田地”,掀起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浪潮。除抗日戰爭時期外,支持農民獲得土地的訴求。共產黨的輸入革命引起了農民對土地的認知解放,他們認為剝奪地主土地是合情合理的抗爭訴求,采取的是非法的抗爭方式,政府的態度是禁止型,屬于B類抗爭。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于1953—1956年掀起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帶領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土地性質從農民私有轉變為集體所有,這是一場深刻的土地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進步意義。但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推行“一大二公”,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條”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民土地權益被嚴重剝奪,因而遭到了農民的廣泛抵制。農民提出的“三自一包”等土地訴求是合情合理的訴求,他們多采取合法的抗爭方式,一般采用磨洋工等出工不出力的日常抵抗形式。政府借助于意識形態資源、強制性手段和對物質資源的全面控制[9],對農民進行壓制和打擊。如此,農民的土地抗爭是合情合理訴求,本應屬于A類抗爭,政府的態度應是默認和容忍型,但此時政府基于“左”的意識形態,認為“三自一包”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將其認定為不合情不合理的訴求,并采取鎮壓為主的策略,實際是按照D類抗爭處置策略對待之,使得這一時期農民土地抗爭遭遇到類別變異。
3.3 現代社會農民土地維權抗爭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土地的產權進行了部分分割,以農民承包的方式將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交還給農民,“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種土地經營權與所有權相分離的政策受到了農民的極大歡迎。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分稅制等改革的推進,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農村還是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抗稅費事件。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農民土地抗爭也沒有減少,隨著各地開發區和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圈地運動如火如荼,農民土地抗爭目前主要圍繞著土地征用和拆遷展開。
現代土地抗爭的解決途徑理論上有協商、調解、申請政府裁決和復議、司法途徑以及信訪等。但土地抗爭的對象很多涉及地方政府,行政和司法途徑不能使政府免于利益糾葛。農民采取以上訪為主的集體行動作為解決土地糾紛的主要方式,此外還采取訴苦、軟磨硬泡、搞關系、“按指印”的聯名請愿、泄憤、種房等多種方式。地方政府往往先是通過抗爭者的親屬側面做工作的“有限強制”,然后采取截訪、維穩等“反復消耗”手段與抗爭者之間展開博弈,最后通過低保和廉租房等“適當妥協”手段達成抗爭的和解[10]。地方政府采取這種策略主義的行為是源于壓力環境、政績需求以及財政需求[11]。為了維權,農民的土地抗爭多是在制度框架內采取合法方式的A類抗爭,少部分采取了非法方式的B類抗爭。
綜上所述,前現代社會土地抗爭的對象主要是貪官污吏和地主,抗爭并不反體制;土地革命的對象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現代社會農民土地抗爭的主要對象是基層管理者(包括基層政府和村級公共組織)以及利益相關方(招商引資的企業、房地產開發商等)。歷史維度下農民與政府之間的土地抗爭的互動關系見表2。

表2 歷史維度下的土地抗爭互動關系一覽表Tab.2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land struggle under historical dimension
4 農民土地抗爭的行動邏輯與機制
以上是不同歷史時期的農民土地抗爭的描述性分析,展現的是土地抗爭訴求、抗爭方式和政府態度等之間的互動情形和抗爭的不同面向。但抗爭政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發現隱藏在抗爭事件背后的共性知識,筆者認為土地抗爭往往遵循相同的抗爭邏輯,背后共享相似的行動機制。統治者認為可以利用權力侵占、剝奪農民的土地權益,而農民一旦遇到有利的政治機會便會開展土地抗爭行動。
4.1 農民土地抗爭的認知、動力和政治邏輯
認知邏輯是統治者和政府認為統治者權力以及公共權力優先于農民權利。政府為了統治者私利或公共利益征收農民的土地,農民往往就得讓步,這是一種統治者和公共權力至上的認知。歷史上多數時候土地并不被認為是農民的財產,而被認為是統治者的私產,“君主復于常法之外,賞賜任意”[12]。古代農民因而被迫尋求權貴豪強大地主的庇護,極端的是魏晉時期蔭蔽于士族門閥之下成為佃客、衣食客等農奴。在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也執行過沒收地主土地歸蘇維埃所有的政策。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推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戶籍制度等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民的土地權益被弱化,將農業收益轉移到國家建設和城市化發展中,這是工業化原始積累的迫切需要,是國家建設需要主導了這一政策。甚至在現代社會現行征地制度依然是一種以鄉促城發展的制度設置,在現行土地征收補償標準上,也一直依據按土地原用途加上產值倍數法給予補償,政策僅涉及具體倍數的調整,不顧及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中土地的市場價值重估。同時規定“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賦予了地方政府對土地征收爭議的單方面的最終裁決權。這背后均體現了統治者利益和公共權力的優先性。
動力邏輯是農民認為政府行為違背情、理,他們土地權益受損。農民的抗爭經驗并不支持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選擇性激勵解釋。抗爭的發生動力不是來自于內部的獎罰分明,而是更多來自于農民面臨的外部生存壓力,即是一種壓迫性反應[13]。前現代社會的農民土地抗爭往往是遭遇到天災人禍,自耕農土地被兼并,佃農土地收成被地主盤剝,農民的土地權益缺乏應有的保護。現代社會一些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土地財政維持運轉,地方政府以低價補償的方式從農民集體手中征地,然后高價出讓,從中攫取高額土地出讓金。當前農村地權沖突“仍是一個以‘利益政治’形塑,而非‘法律衡量’為基礎的秩序”[14]。農民通過抗爭表達反對統治者或公共權力侵害他們的土地權益行為,農民的抗爭是合情合理的,他們希望通過抗爭行動引起統治者和公共權力的關注,維護他們的土地權益。
政治邏輯是農民認為出現了有利于抗爭的政治機會。農民土地抗爭不只是土地權益被剝奪而產生的集體不公正感乃至怨恨累積。農民除擁有豐富的地緣社會和人情網絡、充足的時間等資源外,更重要的是農民有時擁有有利的政治機會。農民的抗爭會面臨“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的約束[15],而出現有利于抗爭的政治機遇或威脅便會促使農民土地抗爭的發生。戈德斯通和蒂利曾構建了一個抗爭的理性模型:G=(V×O)-C,G是抗爭行動的預期凈收益;V意指成功,是抗爭行動的收益價值;O指抗爭成功的可能性,即是機遇;C指包括鎮壓威脅在內的抗爭的代價;當G大于零時,抗爭才會發生[16]。前現代社會農民土地抗爭是由于天災人禍導致農民生存受到威脅;革命社會農民土地抗爭是源于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現代社會土地抗爭則是出現了諸多有利于抗爭的政治機會,比如黨為人民服務的承諾,憲法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不受非法侵犯以及地方政府保一方平安的維穩責任等。抗爭者往往利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分歧尋找有利的政治機會,比如用中央政策對抗地方政府的違法拆遷,用中央的反腐對抗基層干部的貪腐行徑等。正是中央對合法性的維護為農民土地抗爭創造了與地方政府博弈的有利政治機會[17]。
4.2 農民土地抗爭中的機制
機制是社會抗爭研究的重要目標,研究者在全球抗爭案例中發現了社會利用、居間聯絡、認同改變、合法性確認、會聚以及激進化等機制[18]。中國農民土地抗爭中至少存在著土地抗爭訴求的具體利益、農民抗爭方式的踩線偶爾越線、政府對抗爭往往采取壓制等機制。
機制一:土地抗爭訴求的具體利益機制。中國的土地抗爭不具有歐洲歷史上土地抗爭僅僅反對封建領主不反對國王的特征。歐洲歷史上的土地抗爭,農民往往與其他封建領主甚至國王聯手對抗自己的封建領主。由于國王的支持,在歐洲抗爭幫助農民在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爭取到了自身的政治權利和土地權益。而中國的農民土地抗爭一直在追求自身具體利益,并沒有在抗爭過程中建立起有效的維護自身權益的制度化的、抽象化的利益保障機制,導致農民面臨具體利益受損—抗爭—再受損—再抗爭的循環局面。農民自身追求抽象權益不夠導致相應法律制度供給不足。當下農民的土地權益也缺乏足夠的法律保護,例如,中國現有農村土地產權的主體是模糊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村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如此容易產生委托代理風險,農民事實上難以對村級代理人形成有效約束。
機制二:農民土地抗爭方式的踩線偶爾越線機制。歷史上農民與政府之間的抗爭互動多以A、B類抗爭為主,處于抗爭方式的合法與非法界限附近,合法的抗爭難以得到政府的重視,而非法的抗爭又容易引起政府的鎮壓。農民往往踩線而不越線,抗爭行動沖擊地方政府的維穩底線,但又不嚴重危害社會公共秩序,不危及自身安全。抗爭者有時也會越線抗爭,他們起先是選擇合情合理合法的A類抗爭,只是在無效情況下才選擇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B類越線抗爭。斯科特在東南亞的研究揭示存在同樣的反抗機理,在農民能夠忍受的生存極限范圍內,他們依靠弱者的武器進行日常形式的個體抵抗,而避免直接反抗權威[19],類似于A類抗爭;只有當外來侵犯觸及到農民的最后生存底線違背道義經濟時,他們的反抗才以大規模的暴力反叛呈現出來[20],此為B類抗爭。B類抗爭呈現出更多的農民與政府之間抗爭方式和政府應對措施的博弈過程。
機制三:政府對抗爭往往采取壓制的機制。土地抗爭互動中先是統治者和政府不公正地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權益,引起了農民的反抗,而統治者和政府又從社會穩定的角度更多采取了壓制的策略。筆者建構的農民土地抗爭的解釋模型是一個理性的分析框架,但歷史并不總是按照理性設計運行,實際上在抗爭互動中政府常常偏向于運用壓制來對待抗爭者,從表2可知政府在三個歷史時期對土地抗爭均有采用禁止型態度。這也是在“左”的政策下的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土地抗爭遭遇到類別變異的緣由,政府當時采用禁止代替了默認和容忍的態度。現代社會農民的土地抗爭雖然也常常遭遇到地方政府的壓制,但這是由當前的制度安排塑造的。農民選擇上訪是因為中央政府給農民留了這一制度渠道反映農民遭遇的不公,中央政府也將上訪作為評估地方政府治理績效的一個考核指標,地方政府因而必然傾向于壓制農民的土地抗爭行為。
5 研究結論
揆諸歷史,政府治理土地抗爭錯位的情形時有發生。時至今日,筆者認為用壓制為主來遣散抗爭是不適宜的,政府對土地抗爭的態度更多要從禁止型轉變為默認型和容忍型,要建構在法律框架保障下的A類理性抗爭,更多將抗爭行動轉變為體制內的協商和司法途徑解決。具體涉及以下4個方面的制度調整和策略轉變。
5.1 依法保障農民的抽象土地權益
二元體制下的城市化是不斷從農村汲取資源和人才的單向度的進程,使得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城市的高房價和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加上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土地對于農民具有生存發展和保障的特殊意義,被農民視為命根子。這就要求制定相關土地法律法規要真正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使農民在制度框架內真正獲得對土地的使用、轉讓、收益和處分權。“減少農村地權沖突的關鍵在于擴大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與土地資本化收益的權利”[21]。在公共利益確有需要的情形下征地要站在農民生存和發展的長遠角度給予農民足夠公平合理的補償。要消弭土地抗爭中合情合理與合法之間的罅隙,讓良法體現合情合理的原則,將農民的認知和行為提高到合法的層面。
5.2 增強政府制度化吸納抗爭的能力
目前“農地征收過程中,地方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其一是利益競爭者,參與農地征收的利益分配;其二是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從制度上保障自身利益”[22],一方面要增加政府制度化吸納抗爭的能力,即要將社會中合情合理的抗爭訴求吸納為體制內的常規政治行動,比如信訪部門要真正做到吸納失地農民的抗爭訴求,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在體制內引導農民依靠制度化的渠道表達訴求,減少非制度化的抗爭行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好村民自治職能,支持農民成立相應的維權機構,提高農民的議價能力和博弈實力,改變農民在利益表達和維權過程中與政府相比明顯處于弱勢的地位,改變“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農民土地抗爭某種程度上也是農民對政府行為行使監督權的表現,是倒逼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舉措。
5.3 在互動中通過協商達至“重疊共識”
要不斷完善現有的信訪制度,確保農民土地權益受損時有暢通的申訴和解決問題的渠道;政府抗爭遣散策略應以疏導為主,注重協商民主的真正落實;要避免采用暴力對抗的互動方法,防止出現因執法不當而引發惡性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面對沖突擴大時,需要采取理性的退讓策略和合作策略,避免激化策略和對抗策略”[23]。借用羅爾斯面對當今多元社會下協調行動的難題而提出的“重疊共識”概念,筆者主張公共理性,提倡寬容、妥協,找到政府和農民彼此間的最大公約數,形成“重疊共識”。
5.4 在改革中推動土地制度創新
亨廷頓認為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勢必會產生不穩定的社會因素,而這需要制度的凈化和吸納將這些因素在制度的框架內化解掉。要反思地方政府追求GDP和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模式,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治理有效”的要求,要明晰政府與市場各自的邊界和功能區分,走市場驅動、農民參與和政府服務的鄉村治理模式。比如可推廣當前試點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入市制度,讓農民能從土地入市中獲取直接的土地增值收益。應盡可能切斷地方政府與土地收益間的利益糾葛,同時要完善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才能在現代化過程中將大多數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去,才能從根本上消弭農民的土地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