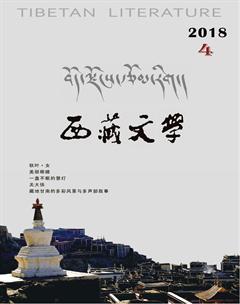事故
2018-10-29 11:03:22王小忠
西藏文學
2018年4期
王小忠
一
溫保國從雞鴨魚鵝火鍋店出來時,已近午后。最后一批上班的人流過后,瓦寨大街稍稍顯得空閑了些。
保險要買足,單靠交強險,毬大的事情都頂不了。溫保國摸了摸剛剛填得圓圓的肚子,一邊想著下周親戚朋友們前來賀喜的情景,一邊又想起同事們經常說到的事故賠償——傾家蕩產,或在涼房里安度晚年。
一輛嶄新的別克,這是溫保國幾乎全部的積蓄。雖然說村里不缺小車,但都不上十萬。開著幾十萬的車,一腳油門,山道上留一串塵霧,村里人再也不會小看他的。按理說,有一份工作,月月能領到工資,縣城里也有樓房,村里人哪有理由看不起?只因頑石一樣的父親。溫保國一想起父親,心里就生出無名的怨氣。他知道父親脾氣暴躁,可不明白他怎么對牛羊那么溫和?這對母親而言,是極不公平的。但溫保國不敢在父親面前說三道四,就這次買車,和媳婦商量起來,鬧了半年才得到允許的。溫保國父親幾十年來一直守著村里的水庫,住在家里的次數都能數得過來。除了水庫,父親唯一操心的就是給村里的牛配種。除了恪守盡職,父親還得到村里人贈送的一個小名——種牛。可他不以為然。溫保國知道,父親眼里只有責任,可配牛也不是他的責任呀。也有一部分村里人對他所做的一切并不看重——不就是看水庫嗎?水庫不看,別人也背不回自己家去。不就是配種嗎?他不操心,牛自己也會爬上去的。
溫保國聽到很多不該聽到的,但他覺得,要想活到眾人前頭,就要換個方式。……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