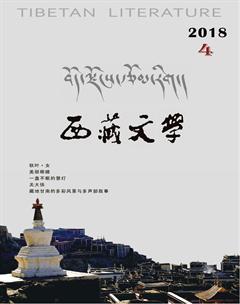秋葉?女
2018-10-29 11:03:22通嘎
西藏文學
2018年4期
這篇短文涉及龔喬明、田文的內容是二十年前我在美國東部康涅迪克州維斯連大學任教時觸景生情寫下的,英文原稿早已在大學文學刊物發表,差點被《紐約客》選載。在那之前的十幾年,正被魔幻現實主義折騰的西藏文壇,很多的朋友,以傳統情感和現實主義手法悲情四射抒發對英年早逝的文壇知己和摯友龔巧明、田文的懷念、追思。當時我沒有機會太多情和煽情,有的只是默默把她們放在心靈一塊平靜的地方,希望在那里更長時間存活她們鮮活的情感生命和絢爛的倩影。很久以來,她們就像自己謝世的林芝深處的秋葉渾身印染斑斕的色彩,一會兒走進我的心靈牧場,說唱格薩爾般與我對話,感染我的情感和思想,一會兒又在半空中飄零飄落,任憑風雨把自己戲弄。
當我看到吳雨初把往昔經歷,與不同民族間的相處、相融的經歷以文學形式樸素表達時觸動很大,啟發很大。在漫長的思考和思念中我又不得不接受另一位非凡女性,又是原西藏文聯的,又是作家的央珍的謝世,不同的是她在自己最為信賴和憧憬的北京,與我們不辭而別。悲痛過后,更多時間里留給自己的是體驗大家一起時的歡樂時光。因為當時我并沒有全面體驗那個歡樂時光,還剩很多。因為當時沒有覺著那時光有多歡樂,一切發生了,過去了,當我們不得不面對很多很多諸如龍冬他們要面對的“往后”,才驀然回首,我們有那么多值得回憶和回味的東西。……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