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獎后這20年
苗千
杰拉德·特·胡夫特(Gerard't Hooft)出生在荷蘭的一個學者家庭。他的舅舅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這位物理學家也成為了特·胡夫特的人生榜樣。在舅舅的影響下,特·胡夫特進入烏特勒支大學學習物理學,他在碩士期間就與導師馬丁紐斯·韋爾特曼(Martinus Veltman)進行基本粒子物理學的研究,并且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論文。
特·胡夫特在物理學領域的天才逐漸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他在1981年獲得沃爾夫獎,在1986年獲得洛倫茲獎章,在1995年獲得斯賓諾莎獎和富蘭克林獎章。到了1999年,特·胡夫特終于和自己的導師共同獲得了物理學領域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物理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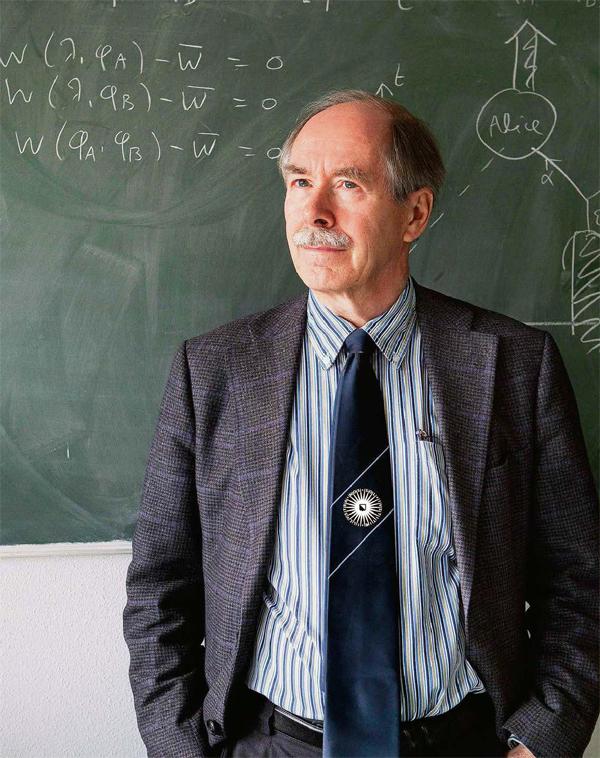
杰拉德·特·胡夫特
這位已經70多歲的物理學家如何展望物理學的發展?在獲得了諾貝爾獎這樣的至高榮譽之后,這20年,他個人的研究和生活都受到了怎樣的影響?“你可以選擇在榮譽中生活,但是請有尊嚴地去面對這樣的榮譽。”胡夫特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說到他的態度。
發現自然力的秘密
三聯生活周刊:是從什么時候起,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你決定當一個物理學家?
特·胡夫特:奇怪的是,關于這方面我自己也記不清了。我只能回憶起,在我4歲或5歲的時候,我就開始覺得我周圍的一切東西都遠遠比人更有意思,我想知道它們是怎么運作的,又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比如說,輪子就讓我著迷,在有輪子的情況下運輸重物,要比沒有輪子容易得多。而且輪子都是由人制造出來的,也就是說,最初一定是有人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發明。我非常想做出類似的發明,當然在當時我還不知道,還將有像宇宙飛船這樣的東西可以把我送上月球。我的家庭里有人是物理學教授,我也想成為他那樣的人,去發現自然力的秘密。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1999年因為“解釋了關于電弱相互作用的量子結構”而和你的導師韋爾特曼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你是否期待人類還能夠發現自然界中更多的基本相互作用,甚至是更多的基本粒子?
特·胡夫特:這看上去不大可能了。在今天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如何理解這些已知相互作用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有什么聯系,是否有共同的起源?我們怎樣才能夠對它們有更深的理解?比如它們之間強弱的對比,對于粒子質量的影響,等等類似的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多年來,你一直在研究量子引力理論以及黑洞的性質,目前你的研究興趣主要在哪些方面?現在量子引力領域已經有了一些理論,比如弦論(String Theory),圈量子引力(Loop Quantum Gravity)以及你自己所研究的全息原理(Holographic Principle)。你認為人類是否能夠很快就發現可以囊括所有物理現象的“大統一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
特·胡夫特:我對于量子力學在黑洞上的應用非常感興趣。黑洞涉及了在量子力學中通常不那么活躍的部分。黑洞造成了時空的扭曲,通過這樣,它們又產生出了新的宇宙——而這在量子力學中又是不被允許的,所以一定存在著一些(目前我們還不理解的)細節,使黑洞必須遵守量子力學的規則。
我發現很多研究者對于我所發現的問題都沒有發覺,比如說因為量子力學的原因,黑洞對于時空拓撲的改變,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時間和空間并不是它們所看上去的樣子。我想在這個領域還有很多東西需要發現。
量子引力的理論會變得可以被驗證。很有可能引力作用與其他我們知道如何量子化的相互作用是相互聯系的。我想,解決量子引力問題,起碼是在這個領域做出一些新的發現,會對我們理解其他的相互作用有很大幫助。目前,引力之外的其他相互作用都是通過標準模型進行描述的,但是在標準模型里我們有超過了20個無法計算的常數。量子引力理論可能可以解釋這個問題:這些常數是從何而來,我們又該怎樣去計算它們?對于這些常數進行的一些預測是可以通過實驗來驗證的。量子效應在其他一些物理現象中可能也會被觀測到,比如說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臺(LIGO)觀測到黑洞相互碰撞合并所釋放的引力波。所謂的“大統一理論”是人們的追求,但它很有可能與我們現在所想象的并不一樣。
黑洞戰爭
三聯生活周刊:盡管量子力學的數學形式已經非常清晰,但是它仍然顯得非常神秘。目前關于量子力學有各種各樣的“詮釋”,例如“哥本哈根詮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多重宇宙理論”(Multiverse Theory),“量子達爾文主義”(Quantum Darwinism),“量子貝葉斯主義”(Quantum Bayesianism)等等。你認為對于量子力學的詮釋是一個重要的物理學問題,或只是一個哲學層面的問題?
特·胡夫特:對于量子力學的詮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不能把它只留給哲學家,因為哲學家可能并沒有足夠的數學工具去進行研究。“哥本哈根詮釋”本身很好,因為它是由物理學家而非哲學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但在20世紀上半葉的哥本哈根,這些物理學家們有一句話我無法贊同:“關于真實,你不應該去追問什么是真實,因為答案可能沒有辦法通過實驗去驗證。”其中有道理的地方在于,關于真實的答案可能確實沒有辦法通過實驗來直接驗證,但是實驗會帶給你一些線索,幫助你構造一個新的量子理論去描述目前人們還無法解釋的現象(比如說黑洞)。因此在這方面我不同意哥本哈根學派。我會去問這些問題。
我對量子力學的理解是:如果我們使用了正確的物理學變量,就不會引起任何干涉效應。產生干涉效應是因為我們使用了與我們這個世界的終極理論并不直接相關的變量——例如原子或是電子的位置和動量等等。但那些“真正的”變量是什么,我并不知道。因為我無法解釋這些現象,也就讓我非常難以解釋我的理論,但我相信我對于量子力學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萊納德·薩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的《黑洞戰爭》(The Black Hole Wars)一書中,你是其中的三個主角之一。薩斯坎德、霍金和你,三個人關于黑洞信息悖論進行了很多的爭論。那么你是否同意薩斯坎德在書中所做的結論?關于黑洞信息悖論你又有了什么新的思考?
特·胡夫特:我并沒有看那本書,我不喜歡看任何寫到了我的書。我通常會部分地同意萊尼(薩斯坎德),而并不會完全同意他的觀點。在關于黑洞信息悖論方面的爭論,我和他站在了同一條戰線,與霍金爭論。但是現在萊尼走在了一個我并不贊同的方向上,他對于弦論過于熱衷了。現在他關于黑洞信息的言論我并不同意。
實際上,對于人們所說的關于黑洞的“信息悖論”,我有自己的看法。這個信息悖論很容易解決,但是你需要理解引力對于“進”和“出”黑洞的粒子有什么樣的影響,這對于時空的拓撲又有什么樣的影響,我們又怎樣才能進行精確的計算。有人認為弦論可以提供所有的答案,但實際上弦論只會帶來混淆。我們并不需要弦論來解釋這個悖論,人們需要的是進行非常細致、謹慎的物理學分析。
三聯生活周刊:關于中國是否應該建造更大的粒子對撞機以尋找新的粒子,在中國社會產生了激烈的討論。你是否認為中國應該建造一個比大型強子對撞機(LHC)更大的粒子對撞機?這樣的設備對于高能物理學的發展和量子引力研究會有怎樣的影響?
特·胡夫特:我當然希望中國能夠建造這樣的一個超級對撞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由我來決定中國是否建造這樣的機器,我又會有很多疑慮。因為存在很大的可能,就是新的粒子對撞機并不能做出重要發現,從這一點上來說,建造超級對撞機的資金完全可以被用在其他一些更有希望的研究項目上。我希望一個超級對撞機可以為這個問題給出答案:到底還有沒有新粒子?一個否定的答案可能和一個肯定的答案同樣有價值。但我也不想因此就讓中國人去做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探險。
有些科學家對于諾貝爾獎過于執迷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是否認為獲得諾貝爾獎是對一位科學家最高的榮譽和認可?
特·胡夫特:有點奇怪的是,看起來確實是這樣的。(在我獲得諾貝爾獎之后)從公眾,包括我的朋友和同事們的反應來看,好像真的是這樣的。
三聯生活周刊:有很多科學家進行研究工作,實際上是被一種想要贏得諾貝爾獎的雄心壯志所驅動,你認為對于科學研究來說,這是否算是一種合理的、積極的態度?
特·胡夫特:并不是。每一年都有一些科學家對于諾貝爾獎過于執迷了。有一些科學家認為他們應該獲得諾貝爾獎,但是實際上并沒有,這種情況就會讓他們非常易怒,并且成為非常差的人。他們應該明白,每一年在諾貝爾委員會進行選擇和決定的時候,都會有很多偶然的影響因素,而且沒有任何人應當聲稱自己有“資格”,“理應”獲得諾貝爾獎。對于研究者來說,諾貝爾獎本來應該是一個激勵和靈感的來源,鼓勵人們做出更好的研究工作。這個獎項把科學研究與瑞典王室聯系在一起,如果能夠讓研究者們受到鼓舞,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應該為此執迷。大多數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原因都是想要做出無論大小的發現,這才應該是激勵所有科學家進行研究的動力所在。
三聯生活周刊:獲得諾貝爾獎讓你成為了一個世界名人,這對你的個人生活和研究工作有什么影響?比如讓你的研究更容易獲得更多的資源,或是分散了你的精力,還是兩者都有?
特·胡夫特:毫無疑問,獲得諾貝爾獎確實對一個人的生活有很大影響。我收到了太多太多進行演講的邀請,我根本不可能做得到。我的研究工作并不需要投入很多資金,但是我估計,假如需要的話,(相比于其他人,作為一個諾貝爾獎得主)我應該可以更容易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這意味著如果我成了一個實驗室的主任,我將成為一個職業的資金申請人,而這并不是我想做的。我希望能夠自己做科學研究,因為我不可能告訴任何人如何去進行我的研究。在這方面,也可能我是一個例外吧。
三聯生活周刊:你對于今年新的諾貝爾獎得主有什么建議?
特·胡夫特:盡情享受。你可以選擇在榮譽中生活,但是請有尊嚴地去面對這樣的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