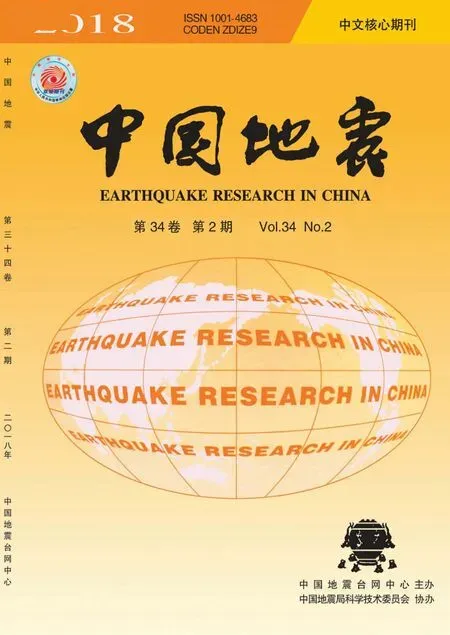中國近代地震學史綱要
馮銳
中國地震臺網中心,北京市西城區三里河南橫街5號 100045
0 引言
1900~1949年的半個世紀,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即百年中國近代歷史(1840~1949)的后半段。費正清等英美學者在其鴻篇巨著《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的開篇有個重要觀點: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人類。
這是中國從山河破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轉換到民族獨立的時期,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也是一部斗爭史和光榮史。既然“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中國的地震科學怎樣在白紙上畫出的第一筆,其苦難與輝煌、經驗與教訓,從世界潮流的角度加以考察與分析,是后人應做的工作。
在這50年間,世界上發生了3次前所未有的特大地震災難:1906年美國舊金山8.3級地震、1920年中國海原8.5級地震、1923年日本關東8.3級地震,災難空前,影響巨大,均對中國近代地震科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中國的另外2次大地震分別是1927年古浪8級地震和1933年疊溪7.5級地震,傷亡人數均為萬人以上。中、美、日3國又是如何渡過的難關,值得厘清脈絡,溫故知新。
近年,《中國近代地震文獻編要(1900-1949)》(陳尚平等,1995)和《中國近代地震目錄(1912-1990)》(中國地震局災害防御司,1999)相繼整理和發掘出了一些新材料,相關研究結果已發表(吳瑾冰,1997;劉寶誠等,1999;崔艷紅,2010;高繼宗,2013)。但還缺乏對民國時期地震工作的整體評述,也就是說,沒有從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角度來觀察、說明其歷史地位和作用。地震,不是個單純的數學物理問題,它還是災害,更涉及到抗震救援和社會責任。因此,近代地震史的研究存在著中西文化融合、新舊觀念沖突、多學科交叉等相關問題。
這段歷史的主體在“中華民國”(1912~1949)期間,分北洋政府(1912~1927)和國民政府(1928~1949)2大時段。地震科學的發展也受到政治、經濟的影響,或正面或反面。一則內外戰爭不斷,經歷了一戰(1914~1918)和抗日戰爭(1931~1945)的洗禮;二則近代科學傳入,中西文化在碰撞中融合(茅家琦,2004)。特別是1918年一戰結束后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段“文化復興”時期。于是,地震學的發展便表現出了三階梯狀特點。不過與地質學、氣象學等相鄰學科相比,中國地震學的發展更為年輕和緩慢。
本文作為拋磚引玉的概述,期望得到多方指正。
1 近代地震學前史
首先在意大利興起的文藝復興是一個偉大的思想文化運動,盛行于14~17世紀的歐洲,此時正值中國的明朝(1368~1644)。就在伽利略(1564~1642)積極開展科學研究的同期,西方的地震知識也首先由意大利傳教士們傳播到東方。時間在明末,也即文藝復興的晚期。
最早向中國介紹地震知識的是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在他1612年撰寫的《泰西水法》一書中就介紹了西方的“氣致震論”。其后,還有2位與伽利略同齡的學者——龍華民(Nicola Longobardo)(圖1)和高一志(Alfonso Vagnone)(圖2),都是通曉中文的意大利學者,為繼利瑪竇(Matteo Ricci,l552~1610)之后在中國教會里學識地位最高的傳教士。上述3人分別在中國傳教15、56、44年,卒于澳門、北京和山西絳縣。

圖1 龍華民(Nicola Longobardo,1559~1654)

圖2 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
據黃興濤(2008)的考證,龍華民1626年編譯了《地震解》一書,該書共9章,影響很大。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寶貴遺產,該書近年首次被意大利學者由中文翻譯成意大利文。高一志1633年撰寫的《空際格致》一書,專辟了“地震”篇,內容與《地震解》大體相同。2本書不僅介紹了亞里士多德的地震觀點,指出要區分地面運動“搖”(水平搖晃)和“踴”(上下顛動)的特點,還講解了地震起因、地震等級、發震的季節和時辰、地震前兆、震后災情、地震地點、持續時間等知識。對地震的這些早期認識,反映了文藝復興后期科學和迷信混雜的地震觀念。
《地震解》和《空際格致》2本書,最早向中國民眾介紹了地震的6條預兆——井水混濁、發臭、沸騰,海水無風而漲,天空異常清瑩……。從明朝起,“震兆六端”便在我國廣泛而長久地傳播開來。正如1935年重修的《寧夏隆德縣縣志》的“震災”篇所述:“余讀龍華民之書,竊知地震兆約有六端”,其中的文字:“海面遇風,波浪高涌,奔騰萍淘,此常情。若風日晴和,臺颶不作,海水忽然繞起,洶涌異常,勢必地震。”很顯然,是中國人根據龍華民傳來的意大利地震知識所改寫,并不是地處內陸的寧夏人的實踐經驗。
時至清朝,影響較大的是欽天監監正、傳教士南懷仁1674年所著的《坤輿圖說》一書。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是比利時傳教士、康熙皇帝的科學啟蒙老師,在華30年,卒于北京。該書在“地震”一節里進一步介紹和發揮了《空際格致》的內容,影響到康熙在1679年三河-平谷8級地震后的深思,促使其于1721年寫出重要的《地震》一文。
隨著1889年德國Paschwitz發現地震波,1883年英國Milne研究了張衡地動儀后,進而在1893年發明地震儀、記錄到P波和S波,地震學的研究方向已明確。其后,1893年美國傳教士李安德(Leander WPilcher)著書《地勢略解》,向國人介紹了地震成因學說、地震波動、日本地震學成果、有關地震的一些基本概念。Leander 1870年來華,曾任美駐天津副領事、北京匯文書院院長。
在這個時期,1898年日本大森房吉(Omori)改進和推廣了Milne地震儀,國際上地震學的發展趨勢已然清晰。而中國正處于一種被動地接受西方地震學基本知識的啟蒙階段,文人學士并沒有認識到張衡地動儀的科學價值。
2 清末和北洋政府前期(1900~1918)
清末的甲午戰爭(1894)、八國聯軍入侵(1900)、日俄戰爭(1905)使中國愈加深重地陷入殖民地的泥沼,西方列強的控制已從政治文化領域發展到經濟和財政結構上。此間,日本崛起,一直是侵略中國的最兇惡的強盜。
清王朝被推翻,軍權成為政權,專制統治由袁世凱延續下來。共和、民主并未實現(張憲文,1985;茅家琦,2004)。
20世紀初,西方完成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由“蒸汽時代”進步到“電氣時代”,深刻地沖擊了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隨著1900年國際地震學的起步,以傳教士為主體的零散的近代地震學研究也逐漸在中國展開。
2.1 文化觀念的改變
2.1.1 近代科學思想的傳入
19世紀中葉~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歷史。西方取得了一系列偉大的科學成就,奠定了現代科學的基礎。比如,電磁感應(1831)、電報(1836)、進化論(1859)、發電機(1866)、元素周期表(1869)、免疫理論(1880)、電燈電話(1880)、遺傳定律(1886)、放射性(1895)、量子論(1900)、釙和鐳(1902)、相對論(1905)等等,目不暇接。世界處于巨變之中。
相形之下,閉關自守的中國尚渾渾噩噩,對激流勇進的世界大潮茫然無知。畢竟,“中央之國”的政治體制過于深厚,從未有過與另一強國在平等基礎上長期交往的經驗,竟將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南京條約》視為用小錢和通商安撫了未教化的蠻夷。直到1860年圓明園被大火燒盡的次年,才被迫搞了個應急的外事部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海關總稅務的大權居然交由英國人赫德(R Hart,1835~1911)絕對統管了45年。中國讀書人仍迷戀的1200年前建立的科舉制度,直到1906年才被廢除。一系列的割地賠款,終于讓中國感到自己不再處于世界體系中的至尊地位了。
外來文化在中國的重大傳入有過2次,一次是東漢初期的印度佛教;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西方基督教。太平天國的洪秀全(1814~1864)就是用基督教動員群眾的,他自稱是耶穌的弟弟。而1899~1900年的義和團則以反對基督教和天主教起事。這導致1901年與日、英、德、法、美等11國簽訂的《辛丑條約》中,特別加強了對傳教士傳教和教會的治外法權保護,包括保護教堂的財產、土地和中國雇員等,也促進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傳教重點開始從宮廷走入民間。
中外傳教士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現代科學知識,在當時的高級知識階層中占有很大比例甚至教父的地位,傳教的同時也帶來了現代科學,并成為先驅的力量,教堂的神父們能長期開展氣象和地震監測便是明證之一。相比之下,中國的寺廟道觀千百萬座,從來都是閉門修行,只供佛祖不測地震的。1901年,中外傳教士1575人,皈依天主教者72.1萬人;到1920年,激增至1.3萬傳教士、200萬信徒,還有18萬的天主教學生。中國當時共有1740個縣,除掉邊遠地區的106個縣外,全都有西方的傳教活動。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滲入的程度幾乎與1931年后日本在東北的情況相差無幾(費正清,1994)。
此時,介紹西方科學思想的報刊學堂、出版翻譯、出國留學、科學小說蔚然成風,輸入的數量和質量前所未有,甚至連魯迅也在1903年撰寫了有關放射性和居里夫人的故事。鎮撫四海幾千年的天朝帝國,終于不得不向“西洋蠻夷”禮賢下士了。問題在于,學什么,怎么學。
中國知識界真正開始吸收西方思想,是在1900年以后。嚴復在甲午海戰后的1898年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產生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反響。國人被民族之間居然也存在著適者生存、物競天擇的原則所震撼,明白了西方強大的關鍵在于思想和觀念,科學才是富國強兵之本,并非洋務運動表面上追逐的鋼鐵和鐘表(史革新,2001)。早期的種種托庇于“西學源于我華夏”的心理慰藉被粉碎,傳統的實用觀念遭顛覆,傳教士和儒家對“格物致知”的演繹也轉向了Science——源自日文的“科學”——詞義為按照“科目”系統地研究機理、量化分析、抽象思維、實驗檢驗以達到理性認識之“學問”,旨在掌握自然與社會的客觀規律。
新的世界里,需要把Earthquake單獨提取出來,作為Seismology的內容之一加以系統地、全面地研究。中國在《五行志》里將地震等同于怪異、水旱的傳統做法,用陰陽五行、天譴地氣來分析的觀點顯然需要徹底改變(馮銳,2009)。事實上,近代地震學以1900年為標志已站住了腳跟:一則在1900年,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用80多臺Milne地震儀建起了第1個全球地震臺網(圖3);二則1901年4月11日,國際地震協會在法國Strasbourg成立。隨后,1901年德國Wiechert發明倒立擺地震儀,1906年俄國Galitzin發明電磁地震儀,在世界范圍得到推廣,測震學和理論地震學快速發展起來。
時不我待,中國已經不能繼續躺在張衡地動儀的歷史光環里了。如何跟上世界潮流,遂成幾代人的奮斗目標。

圖3 1900年用Milne地震儀組建的第1個全球地震臺網
2.1.2 科技人才的培養
中國的面孔,長期是矛盾的。一方面,國家積貧積弱。《辛丑條約》的“庚子賠款”4.5億兩白銀每人攤1兩,付款期從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9.8億兩白銀(約7.39億美元);另一方面,人民偉大聰明。1905年孫中山成立了同盟會發起革命,1909年不僅詹天佑建成了鐵路,馮如還造出了飛機。
同樣是這個1909年,在美國國內民眾的強烈批評之下,美國國會遂決定將庚款所定賠款的余額——本利1471.7萬美元退回中國,旨在“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促進國民融入現代社會”(羅斯福國會咨文,1908),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掌管這筆經費和其他學術捐款的使用。1924年后,其它諸國亦效仿美國陸續退回余額,定向用于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后來發展到基金會每年至少約有100萬美元的預算。國內當時的大學(堂)屈指可數,北洋大學(1895年盛宣懷)、京師大學(1898年孫家鼐)、齊魯大學(1901年周學熙)、山西大學(1902年岑春煊)等最早開啟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以后又利用庚子退款,在1911~1912年間建立了清華大學、協和醫院、北京圖書館等學術機構,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
辛亥革命后,被動接受西方科學的格局被打破,大批青年出國留學。1901~1920年間約有2400人進入美國大學,1920~1940年間約有5500人在美國370所學校里學習,主攻工程學或經濟管理等實用學科,留日學生在1906年達到1.3萬以上。基督教教會又在中國投入巨資,創辦和支持了13所大學,如燕京大學(北京)、圣約翰大學(上海)、金陵大學(南京)、齊魯大學(濟南)、華西協和大學(成都)、嶺南大學(廣州)、東吳大學(蘇州)、華中大學等。1919年的各級公立學校已達12萬所,在讀學生400萬人,教會學校約50萬人(費正清,1994、2015)。同期,還出現了3所私立大學——復旦大學(即震旦大學;1903年馬相伯)、南開大學(1904年張伯苓)和廈門大學(1921年陳嘉庚)。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以及農學、醫學、航空學、無線電學等開始引入課堂。
與西方相似,中國的地震學也是先從地質學入手的。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實業部礦務司設立了地質科(科長章鴻釗,1877~1951),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帶有科研任務的行政單位。后歸屬工商部礦政司(科長丁文江,1887~1936),又在北京大學開辦講習班培養地質學人才。1913年工商部(次年稱農商部)設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1916年地質講習班畢業了謝家榮、劉季辰、王竹泉等第1批技術骨干22人。1918年北京大學恢復地質系(王仰之,1983),還創辦了《地學雜志》《北京西山地質志》《地質學報》等地學期刊。
第1批庚款資助的留美學生于1920年畢業,以后每年都有從歐美學成的人員回國。對近代地震學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一些科學家,如翁文灝、袁復禮、謝家榮、李善邦、丁文江、蔣丙然、王應偉、竺可楨、顧功敘、秦馨菱、傅承義、翁文波、方俊、張文佑等都是這樣培養起來的。他們既熟稔于中國傳統文化,又較多地接受了西方現代科學的影響和學術訓練,成為現代地球科學在中國傳播的主體和先驅。當然,除少數科學家外,地震僅僅是作為一種地質現象來認識的,其物理學和理論地震學的研究基礎一直比較薄弱,是中國早期科研工作的一個弱項。

圖4 黃伯祿于1905年(據黃啟揚等(2015))
2.2 現代地震學萌生
2.2.1 新的認識觀念
據筆者查閱,地震觀念的最早變化恐怕出現在1886年6月13日的北京地震中。
從記述這次地震的全部報章66份來看(謝毓壽等,1987),幾乎都是幾千年傳統的定性描述:“人皆迷惑,波翻浪涌,溢出黑水,天旋地轉,屋宇動搖,搖如旌旗,迎風欲倒,地震有聲,鈴語叮鐺,上徹霄漢……”從中很難抽取科學的信息。惟有1篇文章例外,是由傳教士皮爾遜從保定寫給《中國時報》的:
這次震動的間隔差不多是有節奏的,所有的燈都一致地順著南北線搖擺。從掛鉤到懸掛燈的最低點長50英寸,擺動量是約5至6英寸的一個弧,震動持續4~5min,從4時15分開始至4時20分停止。我還看到一個大缸里的水面呈波浪式搖晃,濺濕了水缸邊緣并留下濕痕,它的最高點約3/4英寸,周邊濕痕的高度幾乎相等。就是說,晃動沒有出現明顯地轉向。4時27分又感到二、三次震動,方向相繼是北、西北、偏南、東南……
對于同一次地震,傳教士也見到了“鈴語叮鐺,波翻浪涌”現象,但他更關注的是天然驗震器——吊燈和液面的反應,而且是用長度、周期、時間、振幅、方向等物理參數來描述的客觀現象,做到了定量化。這就把西方發展起來的、科學地觀察和研究地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讓中國人更容易學習,也體會到了一種全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2.2.2 中國地震目錄
最早的中國地震目錄(法文)為何人所編?這多少是個長期不甚明了的事情。直到最近,在高繼宗(2015)和江蘇省海門市民族宗教局(黃啟揚等,2015)的努力下,才得以澄清。第1位編制中國地震目錄的并不是外國人,而是黃伯祿先生(1830~1909)(圖4)。
黃伯祿,江蘇海門人,清末天主教江南教區的主教,杰出的學者和教育學家。通曉中、法、英和拉丁文,論著30多種,曾任上海天主教修道院的司鐸(Priest,即神父)、徐匯公學校長、復旦大學(前身震旦大學)校長(費正清,1994)。他參考大森房吉編纂的地震目錄里有關中國的數據,利用了中國10種史書和391種地方志,在76歲高齡時開始編輯法文版《中國地震年表》,嘔心瀝血3年完成了第1卷,《Hoang:Catalogue d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signals en Chine》(公元前1767~公元1895年)含3322條地震記載。黃先生在1909年10月7日該書出版后的第2天去世,是首位為中國地震科學獻出生命的學者,葬于上海圣母堂。黃伯祿神父在徐家匯觀象臺有兩位外籍助手:西班牙人管宜穆(J Tobar)和法國人田國柱(H Gauthier),他們遵照黃先生去世前夜的囑托又對遺稿作了補充和校訂,歷時四載,仍以黃伯祿作為第一作者于1913年10月出版了第2卷,對第1卷中的地震作了簡要說明,還補充了138次地震有感區域的地點分布圖。
這兩卷書均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以后又在法國傳教士1892年創刊的《漢學叢書》上發表,通行于歐洲各國,奠定了中國地震學的基礎資料①1949年后,《中國地震資料年表》于1957年完成,含8000余種文獻、15000余條地震記載、8100余次地震。《中國地震目錄》于1960年完成,含破壞性地震1180次。。黃伯祿的學術貢獻被法國文學院2次授予儒蓮獎。

圖5 1897年架設在臺北測候所的地震儀② 鄭世楠等,2013,臺灣地區地震儀沿革(1897-1972)。www.gdms.cwb.gov.tw/HisEq/new_page_5.htm
2.2.3 地震臺站
法國耶穌會(天主教)于1870年在上海徐家匯建立了天文授時、氣象觀測臺,以后增加了地磁(1874)和地震觀測項目(1904),黃伯祿即為該臺神父。
日本于1897年在臺北安裝了Milne-Gray水平擺地震儀(圖5),首次記錄到1906年3月17日臺灣梅山7.1級地震。又在臺南(1898)、臺中(1902)、臺東(1903)、恒春(1907)、花蓮(1919)、高雄(1925)以及阿里山、澎湖等地設臺,初步形成區域地震臺網。后期,還增設了宜蘭、新竹、嘉義、新港、蘭嶼、玉山和大武等地震臺②。
此外,俄國在大連和營口(1904),日本在沈陽(1905)和長春(1908),德國在青島(1908),意大利在陜西通遠坊(1922)分別設臺,天津中法工商學院也短期安置過地震儀。至1925年,中國共有15個地震臺(圖6)。早期使用Milne和Omori地震儀,20世紀20年代逐漸改用Wiechert和Galitzin地震儀。這些地震臺全部由外國建立和掌控(1905年日俄戰爭后,幾乎都被日本控制),主要為港口的水文氣象服務,也未組成統一臺網。
2.2.4 地震烈度表
歷史上,地震烈度表是在這個時期編成的。自1564年意大利地圖繪制學家Gastaldi開創這項工作之后,經過多位學者的改進,直到1878年Rossi、1881年Forel和1902年Mercalli的系統工作,才完善了地震烈度表。
我國最早的等震線圖由黃伯祿神父的助手Tobar和Gauthier繪制,他們根據1668年7月25日郯城地震的歷史資料,按照Rossi-Forel表繪制了Ⅵ~Ⅹ度等震線圖,發表在1913年《中國地震年表》(法文)第2卷(高繼宗等,2015)。
1913年12月21日云南峨山7級地震,昆明甲種農業學校校長張鴻翼率5人于1914年1月赴現場調查。查明了災情與地質、地形的關系,繪制了受災村鎮分布圖。
首次在地震現場開展烈度評估的是劉季辰(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17)。他對1917年1月24日安徽霍山6.3級地震繪制出等震線圖(震中烈度VII),揭示了地質構造的控震作用。這次調查工作比較順利,當時的北洋政府由皖(安徽)系軍閥掌控,而震中區又恰發生在總理段祺瑞(皖系頭目)的故里——六安,加之地震死亡數十人,余震持續1個月有余,政府頗為重視。僅調查表就發至各省財政技術員、各鐵路路長、海關稅務司、各縣知事等,補充了125處地點的信息。最后,由翁文灝親自執筆,以地質調查所的名義上報了政府(農商公報第35期)。
1年后1918年2月13日廣東南澳-汕頭地震的境遇就迥然不同了(圖6)。地震更強烈,災情更嚴重,南澳全縣倒為平地,汕頭死傷高達千人,僅招安、潮安二地便死亡數百人。其時,孫中山正在廣東發起反北洋政府的護法運動,南澳-汕頭地區是粵軍抗擊桂軍的地盤,總統馮國璋、總理段祺瑞對廣東的事件自無興趣。致使南京中央氣象臺的現場調查極難展開,烈度圖甚糙(王應偉,1931),亦無調研報告。這次地震的震級7.3,震中烈度X,死亡人數粗估為二三千。

圖6 1922年前的地震臺站、鐵路和7級以上強震震中略圖
2.2.5 震災救援
1918年前,北洋政府從未搞過震災救援。有過救援行動的反倒是滿清政府,只對外不對內,甚至還奴顏婢膝地提出過“量中華之物力,結列強之歡心”的方針。
1906年日本偶遇自然災害,慈禧搞起賑濟來。史載:“光緒三十二年,二月戊辰,詔各省保護教堂及外人身家。是月,頒帑十萬助賑日本災”。意即皇恩“賞賜日本”白銀十萬兩(約合7.5萬美元)救災。次年,再撥糧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壬寅,日本以水災來告,輸江、皖、浙、鄂諸省米糧六十萬石濟之”(《清史稿·本紀二十四(八)》)。擺出一副天朝大國普度眾生的架勢,全然不顧百年禁止輸出糧米類物資的嚴令。
1906年4月18日,美國舊金山8.3級地震。美國迅速在舊金山地區組織救援,采取嚴格的抗震措施,對急救、消防、治安、飲水、食物分配,以及重建家園等都有具體規范。當年秋季,美國地震學會在舊金山成立。1909年美國會決定向中國退回庚款余額。1910年里德(Reid)根據對舊金山地震的研究提出了“彈性回跳”理論。隨后,沿圣安德烈斯斷層組建起地震監測網,迅速開展起地震學的研究。糊涂透頂的慈禧太后又要賞賜美國10萬兩白銀,《清史稿》有載:“美國舊金山地震,頒帑十萬賑華民”。不過,此等荒唐迅即被美國國會明確地“辭謝”掉(圖7)。
1908年12月28日,即在光緒和慈禧死后的1個月零24天,意大利梅西納(Messina)發生7.5級地震。清廷又搞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國際賑濟”,史載:“癸酉,意大利地震災,出帑銀五萬兩助賑”(《清史稿·本紀二十五(一)》)。
清廷做法在當時惹得天怒人怨,群情沸鼎。中國在1874~1905年間曾連續對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等,對日賠款共3.24億兩白銀,1901年《辛丑條約》又要對意大利賠款9千萬兩……。中國處于年年向外行舉新債還舊款的窘境,海關、鹽務、稅收、郵政等已經全部由外國把持變成了償貸機構(費正清,2015)。據當時的《申報》披露,僅1906年徐淮海地區的水災,流離災民就達730萬人,而1907年全國又遇水災,餓殍遍野,大量災民漂洋過海到歐、美、澳去乞討求生。清廷無視國民生死,竟然拿著外債去外援,如此“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黑暗腐敗,進一步激發了推翻清廷的革命浪潮。

圖7 美國辭謝了慈禧太后的地震賑濟(1906年《申報》)
3 北洋政府后期(1918~1927)
1916~1919年,每年出一件大事:袁世凱死、十月革命、一戰結束、五四運動。中國轉入封建軍閥割據時期(圖8)。
各國列強既失去了共同的袁氏工具,便各尋自己的新代理人,軍閥亦擁兵自重。北洋政府相繼由皖系(段祺瑞,1916~1920)、直系(曹錕、吳佩孚,1920~1924)和奉系(張作霖,1924~1927)軍人控制。在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環境下,便出現了封建割據的局面(張憲文,1985;費正清,2015)。
全國一盤散沙的另一面,是為思想開放、百家爭鳴提供了一個短暫又難得的機遇。馬列主義傳播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科學、民主”促進了民族覺醒,推動了中國科學社和群眾性專業學會的成立,傳播科學的主動權逐漸從外國傳教士向中國學者轉移。應對地震,既學到了西方的新理念,也嘗到了新教訓。

圖8 近代地震史的重大事件和階段劃分
3.1 新文化運動
1915年,《科學》和《新青年》這兩份并駕齊驅的重要刊物問世,分別由中國科學社任鴻雋(圖9、10)和北京大學陳獨秀創辦,為我國現代出版史上創刊時間最早、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兩份綜合性科學期刊。同年,日本提出了亡我中華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死前竟然同意簽訂。
火山終于爆發。高舉反帝反封大旗的1919年五四運動,將舊民主主義革命推進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科學與民主”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響亮口號。以《新青年》為中心的人文思想家和以《科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家起了主導作用,影響和改造了一代人(張焱等,2007;李侃等,2004)。它是中國近代思想、政治、文學發展史的里程碑,出現了思想解放、探索新道路最為活躍的時期,史稱“文化復興”。
任鴻雋(1886~1961)曾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的秘書,1915年與其他留美學生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成立中國科學社。1918年回國,曾任四川大學校長(1935)和中央研究院秘書長(1938)。他自1929年起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總干事10年,掌管“庚子退款”的審批和使用,精打細算地支持了中國的科學研究、教育事業,建立了中國最大的上海科技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北京地震臺和南京地震臺在1930年購買Wiechert和Galitzin地震儀的經費,就是在他任內給予資助的。當有人責備基金會不通過國民政府使用庚款時,任鴻雋鏗鏘地回答:“這正是中華基金會的力量所在,杜絕了政府濫用基金去打內戰!”(費正清,1994)。
中國科學社的座右銘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最早提出了“科學救國”的口號,迅速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積極響應。這個時期對“科學”的理解,有了比清朝末年更為深刻的升華。科學已經是一個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內的完整知識體系、改造社會的力量,科學家的個人命運開始與民族獨立、祖國富強緊密地聯系到一起。先進的思想被群眾所掌握后,一場比辛亥革命還要深刻的思想躍遷和社會變革,已然孕育。
中國科學社還是中國科學體制化的拓荒者和探索者,它大力引進了西方科學的社會建制——科學學會和組織機構(潘丙國,2009),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圖書館和研究所,出版《科學》《科學畫報》《科學季刊》《科學叢書》等多種刊物,使政治民主、學術民主、結社自由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至1925年,中國已經相繼成立了天文學會(1922年高魯)、地質學會(1922年章鴻釗)、氣象學會(1924年蔣丙然)等共計44個群眾性科學學會。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科學社已擁有3700余名社員,匯聚了各學科的代表人物。很快成為我國科學事業最權威的領導機構。
《科學》是當時水準最高的學術期刊,以美國科學促進會《科學》和英國皇家學會《自然》兩刊物為模版,倡導學術民主和科學創新,國內最重要的地震學文章大多發表于此刊(表1),至2018年已經出版到70卷。第1篇地震學的文章刊于1917年第3卷,是留美學生、中山陵設計者呂彥直(1894~1929)的“漢張衡候風地動儀”的復原模型,時年23歲。

圖9 任鴻雋(1886~1961)

圖10 《科學》1915年第1期
3.2 1920年海原8.5級地震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記載中,8.5級的地震僅有過3次:1668年山東郯城、1920年甘肅海原、1950年西藏察隅等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時05分的海原地震,是中國唯一的震中烈度達到Ⅻ度的特大災難(中國地震局災害防御司,1999),24.6萬以上的災民死于冬雪大漠,留下了地震史里的永遠傷痛。
據翁文灝(1922)(表1)所述,上海、日本地震臺和外國報章推測的“震中在甘肅東部、隴山之東的平涼……,都不準確”。12月19、28日甘肅省時任省長張廣建2次“十萬火急”致電總統徐世昌、總理、內務部、財政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文獻),以953字的電文泣血求援。1921年1月初,固原電報局從災區發出首份告急電報。北洋政府竟然對這3份急電一概棄之不理。
此刻的北京,皖系段祺瑞政府剛倒臺,經1920年7月的直皖戰爭,皖系已敗北。直系軍閥曹錕一上臺,便首先在1921年1月免去了張廣建的甘肅省省長和督軍2職務,理由倒也簡單——他是安徽(皖)合肥人。其后的兩年多,甘肅省省長之職從張廣建、陸洪濤、尹陳誾、潘齡皋到林錫光等走馬燈般更換,無不撈一把就走,而地震災區無一政府要員“蒞臨現場”。拖拖拖,一直拖到1921年3月才把甘肅震災與五省旱災并列,5月份才在公文上允許從交通賑災捐款中撥出2萬元給甘肅(高繼宗,2013)。能否落實,無人知曉。據說,當時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機關人員欠薪數月至20個月不等,連總統府的辦公費亦數月無有著落(崔艷紅,2010)。孫中山怒斥軍閥們讓百姓“跳出了熱鍋,跳進了火爐”(見孫中山1920年《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在這種黑暗腐敗的政治形勢下,社會救助被緊急推上歷史舞臺。

表1 《科學》(1915~1949)刊登的地震學文章
3.2.1 第1次現場調查
1920年前后,華北出現1877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冀、魯、豫、晉、陜等5省370個縣近2000萬人受災,死亡50萬人。寧夏也有13個月滴雨未落,赤地千里,哀鴻遍野。
熊希齡(1870~1937)是1913年民國政府的首任民選總理,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在他1920年9月的倡議下,北方5省災荒協濟會與各國救災傳教士迅即于10月組成了 “國際聯合賑災總會”(United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亦稱北京國際聯合救災總會),牧師艾德敷(DWEdwards)為總干事。熊希齡先生隨即創辦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接收災區兒童。12月的海原地震后,賑災的重點從旱災轉向了震災救援。
賑災總會的甘肅分會首先派員于1921年2月趕到平涼、隆德、靜寧、會寧等地,急電北京:震災超乎想象的嚴重。隨即,賑災總會的北京分會委托美國牧師霍爾(JWHall)、海斯(JD Hayes)、克勞斯(U Close)和麥克考麥(E McCormick)赴現場調查,由留美學者、北京政法大學教授柴春霖(1888~1952)全程陪同(高繼宗,2013)。
調查組1921年3月6日由北京乘火車走南線,抵隴海鐵路的西終點——洛陽西的觀音堂(圖6),再徒步由涇川、平涼向西至隆德-靜寧-會寧,向北到固原、黑城鎮、楊郎鄉、海原,至黃河邊(圖11)。查明了極震區位置,確定了嚴重的山體破裂、移動、滑坡以及堰塞湖,首次披露死亡人數逾20萬,親見人畜尸橫、狼狗噬人的浩劫,滿目瘡痍,慘絕人寰。極震區還包含了中華人文始祖伏羲的家鄉——成紀(天水北),波及到西王母的降生地——涇川,西王母本是掌管災荒和瘟疫的女神,漢武帝曾11次到涇川來祭拜。這些情況最早公布于1921年3月16日中國最具影響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該調查組經內蒙于5月27日回到北京,于同年6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公布了災區照片、放映了災情紀錄片。

圖11 美國傳教士Hall繪制的第1幅海原地震災情圖(據Close等(1922))
1922年5月,美國《國家地理》頭版刊出Close等(1922)的文章《群山走動的地方》,并附24幅災情圖片(圖11),特別注明是受“國際聯合賑災總會”委托的震災調查。作者還以西方人的筆法提到一個感人情節:
在極震區的靜寧縣,災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居然遇到了兩位來自美國的女傳教士,她們住在一個極其簡陋破舊的茅草棚里,女士們拒絕當地的特殊照顧而寧愿與災民同甘共苦,堅持救災工作。
《國家地理》由著名的電話發明人貝爾(AG Bell)創辦,1929年會員已高達125萬,屬全球發行量最大的雜志之一。該文報道了海原地震如世界末日般的災難,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反響。

圖12 翁文灝(1889~1971)
3.2.2 第2次現場調查
翁文灝(1889~1971)(圖12)是我國首位地質學博士,中國地球科學的創始人和學術領頭人,新文化運動的積極響應者。1908年留學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1913年回國。曾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1922)、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30)、清華大學代理校長(1931)、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1935)(黃汲清,1989)。
隴西,系指南北走向的隴山以西的廣袤地區(圖11)。隴山的最高峰為六盤山,位于甘肅省靜寧北側,不過現今已經把隴山的整體統稱為六盤山了。這里千山萬壑,人煙稀少,很難確定地震的具體位置,自古便把這里的地震統稱 “隴西地震”。翁文灝(1922)(表1)最早指出:隴山之東、西兩側的地震活動強弱迥然不同,西側多震、東側極少,故而外電講的“震中在隴山之東”的說法不可能成立。張衡地動儀測到的134年12月天水一帶的地震即為“隴西地震”,1920年12月的海原地震也屬 “隴西地震”。當時,翁文灝以張衡地動儀來激勵大家:
漢書張衡傳,衡造地動機……,我國原為地震儀發明最早之國,惜繼起無人,遂至失傳。近代歐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計,則視古代地震儀尤大進步,本國毫無設備。我們更應急起直追,期有進步。
鑒于美國牧師Hall和Close已經先行考察了震中區,翁先生便極力推動我國的地震地質工作上馬:
我們自己的材料、自己的問題,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貢獻于世界,卻要勞動他外國人來代我們研究,我們應該感覺十二分的慚愧,應該自加十二分的策勵。
1921年4月15日翁文灝親自帶隊,北洋政府的3個部亦均派員:(內務部)蘇源泉、易榮膺,(教育部)王烈、楊鐸,(農商部)翁文灝、謝家榮等共6人,其中,王烈和謝家榮分別是留德、留美的地質學者。他們從北京乘火車走北線,抵京綏鐵路的西終點——歸綏(今呼和浩特),再步行至皋蘭、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圖6)。歷時4個多月的艱苦考察,實現了我國第1次大規模的地震科學考察(翁文灝,1921;謝家榮,1922;李灼華,1986)。全面總結了研究結果,繪制出等震線圖,研究了現代地震科學的基本問題,如強度、位置、烈度、地震活動序列、前兆現象、災害特征、救災賑濟、地震成因、地震地質等方面。
以后,翁文灝又做出一系列地震學的新貢獻,比如:
·整理出了該區的地震目錄,共266個事件(前780~1909年)。列出了該區240條地震的時間、地點和強度的分布。劃分出甘肅強震的6個分區——武都區、隴西區、涇原區、寧夏區、西寧區和武威區,粗估遷移周期平均約30年;
·首次提出利用史料來研究地震活動性的方法,以及對震中遷移的新認識;
·提出了建立“地震史料烈度表”的雛形,以及烈度異常區的概念;
·最早分析了我國地震區劃問題。首次繪制了地震與構造的關系分布圖,劃出16條地震構造帶,性質上分4種類型:地殼陷落的垂直斷裂地震帶;沿海錯斷地震帶;秦嶺山脈的突轉和平移構造地震帶;逆掩構造或推覆地震帶(翁文灝,1923b);
·首先把國際地學的最新進展——魏格納(Wegener)的“大陸漂移說”(1912)引進我國。
從今天的眼光看,他的很多分析和推斷都是合理的,為我國地震地質研究奠定了基礎(黃汲清等,1989)。
1949年后,郭增建等6人在1958年、彼得魯舍夫斯基在1959年還分別對海原地震開展了地震前兆和地震地質研究。在20世紀里,闞榮舉在60年代、李玉龍和康哲民等在70年代、環文林等在80年代都對海原作了現場徒步考察,90年代還開展過多重破裂特征、減災對策的研究(國家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等,1980;環文林,2015)。
3.3 地震救災
3.3.1 華洋義賑會
對海原地震,國內首次組織了大型震災募捐,新聞媒體和民間團體發揮了積極作用(崔艷紅,2010)。僅《辛壬震災記》記載的募集捐銀共計247 782兩(高繼宗,2013)。令人發指的是,募集的賑款卻橫遭貪官污吏的層層克扣。1921年9月4日《申報》載:“賑濟局人員,只知抽大煙,叉麻雀,吃花酒”,華洋義賑會來調查時,他們竟說沒有災況。甚至連直系軍閥曹餛也侵吞了地震賑濟款300余萬元,地震災民每人僅得到12枚銅板(鄭正偉,2000)。直到3年后的1923年3月19日,杯水車薪的政府賑款仍然“尚未及半”。老弱災民瑟縮露宿,狼狗群出噬虐婦孺,不為餓殍即為僵尸。蘭州的受施粥災民已超過萬人,賣妻鬻子屢見不鮮,“竟有賣人肉包子之事”,喪生人數已無法統計。
鑒于中國的災荒頻發,救災需要長期進行,有必要把1920年成立的“國際聯合賑災總會”提升至永久性組織。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簡稱華洋義賑會,后稱樂施會),外方人士為西方傳教士。總會主席梁如浩,副主席是圣公會主教懷履光(WCWhite),總干事仍為牧師艾德敷(D WEdwards)。參與震災-旱災救援的外籍人士來自美、英、法、德、意、加、俄、奧和北歐的瑞、挪、丹、芬等國800多人,其中的650余人是在華傳教士。賑款以美國居多,特別是由美國各界知名人士組織的對華援助機構——美國華災協濟會(United Relief to China,亦稱聯合援華會)給予了常年捐款,僅1927~1933年的捐款就達1.41億元(141i599i971.02元)又630美元。美國紅十字會、洛克菲勒基金會也都給予了資助。華洋義賑會是中國在民國時期最大的、最有影響的民間性國際慈善組織,分會遍及全國,藍底白十字為會旗,不涉及政治、宗教與派別。
華洋義賑會在海原地震的救災工作中最為突出,他們在各大城市連續發起了義賑義演,募捐款共17i358i633元,超過了北洋政府的撥款11i337i751元(為防范官吏的貪污克扣,政府還不得不把其中的400萬元委托華洋義賑會下發),北京義賑分會募集到捐款14萬元(謝家榮,1922)。僅1920年12月~1921年8月,各地華洋義賑團體共支出賑款15i230i787元,救濟災民7i731i611名,占全部災民的1/4以上(蔡勤禹,2006、2009;劉招成,2003)。
15年后的海原地震區,變成了星火燎原的革命之地。1935年10月7日毛澤東率紅軍在隆德-瓦亭的北側翻越了六盤山,寫下“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清平樂·六盤山)的詠懷名句。1936年10月紅軍3大主力會師于海原地震的震中區——會寧和靜寧北的將臺堡(圖11)。據地震幸存者回憶,紅軍在當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還領導群眾批斗過當年貪污地震賑災款的奸官污吏(國家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1980)。
3.3.2 地震救災中的新觀念
歷史表明,中國震災的損失程度長期位居全球首位,缺乏有效的救災機制是一個重要因素。正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后,傳教士把西方的人權平等、福利思想和社會救助觀念帶入中國。
(1)科學救災的原則
“籌辦賑濟天災,提倡防災事業”是華洋義賑會的賑濟原則,防災減災勝于救災,賑濟不涉及內戰等“人禍”所致災難。針對1920年海原地震,他們工作的重點有二:一是以工代賑,辦工程、修道路,恢復生產;二是建立農村合作社,讓災民擺脫高利貸的枷鎖。這種新方案,很快成了被廣泛接受的科學救災良方,并具有重建家園的性質(蔡勤禹,2009;楊琪,2009)。災民被組織起來,投入到會寧、靜寧、通渭、德隆等縣的開挖河道、整修土地等工程中,既修復了家園,又獲得了救濟款糧,至1921年11月共用款10萬元左右(謝家榮,1922)。還修筑了公路、筑堤、開渠、掘井等,僅1921~1929年間的項目就達62項,尤以修筑穿經海原地震區的西安-蘭州公路為最大工程,斯堪的納維亞傳教士Gustaf Tornvall還在施工中獻出了寶貴生命。至1935年,筑新路1993英里,修舊路1296英里(劉招成,2003)。民國時期的大規模修筑公路,就始于華洋義賑會,推動著中國從閉關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現代。
(2)積極靈活的行動
意大利方濟各會(Franciscains Italiens)是天主教中提倡過清貧生活的一派,主要傳教于山東、山西和陜甘窮鄉僻壤,頗有群眾基礎,其延安天主教堂曾被魯藝選為校址。方濟各會在陜西通遠坊永樂店的教堂也遭海原地震的損傷,屬烈度Ⅵ度區。地震后,天主教堂于1922年自費購置了Wiechert地震儀(擺錘200kg),先后由戴神父和賈神父負責監測地震,試圖發揮警示地震的作用,堅持工作到日本入侵的1937年(謝毓壽,1990)。
籌款方式走向了國際。華洋義賑會迅速在國內外發行了震災募款的郵票和印花(圖13、14),至1936年已募集到外國捐款5000萬美元,部分款項還可以轉為改善農村生活條件之用。此外,華洋義賑會的美國人貝克(John Earl Baker)在1916~1926年間是北洋政府交通部的顧問,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5位外方董事之一,還促進庚款資助過一些農村水利等項目(費正清,1994、2015)。
(3)外國傳教士的貢獻
1919年基督教新教的在華傳教士已達6i636人(其中的4i500余人來自美國),天主教傳教士在1920年達2000余名(蔡勤禹,2006)。自1881年以來,美國一直推行高校學生志愿海外布道活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截止1918年,派往中國的已達2524人。他們并非臨時性地投入震災救援,而是長年地、持續性地開展救助工作,涉及地震、水旱災后的家園重建,還有育孤、濟貧、賑災等慈善事業。1929年海原以北的綏遠一帶遭遇旱災,在華洋義賑會開展救災的3個月內,就有14名中外傳教士染上疫病或犧牲了生命。他們的救援行動,受到勞苦大眾的高度贊揚。

圖13 華洋義賑會1920年12月發行的募款郵票

圖14 華洋義賑會1924年發行的賑災募款印花
被譽為“中國十大國際友人”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也是華洋義賑會的成員,1927年4月來華,1929年在包頭東的薩拉齊鎮參加賑災,實施鐙口村民生水渠渠口的工程。以后到了延安和新四軍軍部,積極投入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與斯諾等創辦“中國工業合作社”,還在陜西和甘肅山丹創辦培黎工藝學校。艾黎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60年,死后被安葬在他的戰友——英國人喬治·何克(George Hogg,1915~1945)的墓旁——甘肅山丹。艾黎出生于新西蘭的基督城(Christchurch),當地在2010年9月和2011年2月發生7.1級和6.3級強烈地震。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山東濰坊基督教長老會的“樂道院”被日軍改成國內最大的外僑集中營(圖15),1200多名英美等國在華傳教士被日軍關進集中營,上至90歲的老人,下至8歲的兒童。其中就包括華北神學院院長赫士(Hayes)、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Stuart)、齊魯大學教務長戴維斯(Davis),以及輔仁大學附中教師后來為美國首任駐華大使(1981~1986)的恒安石(Hummel)等。留下來的傳教士仍冒著生命危險為救濟難民而工作,艾德敷(Edwards)繼續擔任華洋義賑會副會長,還服務于美國華災協濟會(United Relief to China),負責將美國援華物資分配給難民和其他救濟機構。他們又在1937年11月的淞滬會戰后聯合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貝克率華洋義賑會總干事辦事處的同仁全體加入進來,并擔任總干事一職,他們不畏懼寧滬等地日占區的極度險惡,直接參與或資助建立的收容所達30個,收容難民不下30萬人(蔡勤禹,2006、2009)。日本的侵華戰爭迫使傳教士大量回國,輝煌于20世紀20~30年代的華洋義賑會隨之隕落。
這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和志愿者們,縱然懷抱傳播福音的真誠,不領報酬,不怕犧牲,毅然決然地拋棄西方舒適的生活,扎根于中國窮困破落的農村,奔走在地震、水旱的荒蕪災區,幫助那些一貧如洗、無人問津的百姓恢復生計,抗震救災,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們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尊重,他們的精神和業績已融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永駐華夏大地。十分遺憾的是,在我們以往的地震科學史研究中,他們在傳播科學知識和救災扶貧方面的貢獻長期被忽略甚至貶低了。

圖15 山東濰坊的日軍西方僑民集中營(1942~1945年)(新華網圖片)
3.4 1927年古浪8級地震
在中國近代史上人員傷亡第2位嚴重的震災,是1927年5月23日的古浪地震。震中在海原地震的西側不過百余千米,二者位于同一構造。
按理說,1920年海原地震的考察和救災已取得經驗,古浪地震又是與它相距咫尺的8級大震,學者們本期待“地質調查所正式負調查地震之責任”(李善邦,1948)(表1),實際上卻做不到。馮玉祥為配合北伐(1926年7月廣州~1928年6月北京),其西北軍屆時占據了陜甘寧豫,北洋政府自不會理睬這里的震災。而蔣介石和汪精衛在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又相繼發動了政變。故而古浪地震發生后,縱然新聞媒體作過宣傳和大力募捐,終究變成了白色恐怖下的邊陲孤煙,無人問津。震中烈度Ⅺ度,41 400余人罹難,牲畜損失27.5萬頭(中國地震局災害防御司,1999)。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7月30日《字林西報》的現場報道:古浪地震不僅毀掉了武威城圣白勞特教堂,西鄉村天主教堂亦倒塌(圖16),當地的育嬰堂里有100余名孤兒,地震時20名小孩喪生,主任修女康斯但丁罹難。文中寫道:
主任修女勇敢地來回救護被埋葬的孩子,她也被磚土所打。當于土堆中覓得康斯但丁教師的尸體時,其兩臂之下尚挾二孩,此二孩安然無恙,康教師臨死尚救二孩之命,真可敬也……
這是筆者在史料中第一次見到的地震中舍身救人的英勇事跡,后人將永遠敬重:一位外國女士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2個中國孤兒。主震后的6月16日,黑溝峽堰塞湖潰堤,當地天主教會又開展了救災活動,還繪制了僅有的外圍等震線圖(布登博羅克,1927)。
1949年后,周光和劉秉俊在1954年、張生源在1974年踏勘了地震遺跡,尋訪了幸存者。1980年蘭州地震研究所編寫了研究報告。

圖16 西鄉村天主教堂在古浪地震中倒塌(1927年《字林西報》)
3.5 1923年關東地震
3.5.1 中國的救援
1923年9月1日11點58分,日本關東地區發生8.3級地震。午飯時分的爐火引發木質房屋火災,損失嚴重。按日本官方公布,地震死亡105i385人。另有報道,“中國留學生當時在東京者共有千余人,幸在暑假中,歸國者不少,因此死傷較少。至于橫濱地方,我國商人很多,約有4600人,其中死者2000余人,只剩半數生存”(顧仲超,1995)。
當時中國的震情也很緊張,1920年海原地震中至少24.6萬人死亡,1923年3月24日四川爐霍-道孚發生7.3級地震,6000余人罹難。兩次大震的強余震一直延續到日本關東地震之時,“造成200里內炊煙幾斷,損失甚巨”(翁文灝,1923a;中國地震局災害防御司,1999)。匪夷所思的是,北洋政府對這一切竟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反倒舉全國之力去為日本救災了。
孫中山致電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北洋政府緊急調派了2艘軍艦、10艘商船,載運糧食、藥品分赴東京、橫濱、神戶等處接濟,免去了所有出口日本的食品、服裝、藥品、衛生材料等的關稅,迅速運去大米30萬石,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動員了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各大城市義賑義演,京劇名角紛紛登場,末代皇帝溥儀還把價值70萬元的清宮金、銀、玉器珍品變賣賑災。就這樣,全國為日本募集了總額約150多萬元的賑災款,其中,財政部撥款20萬元、民間團體及個人50多萬元、紅十字會中華總會5萬元、江浙地區51萬元等,華洋義賑會也投入賑災。滿載面粉和大米的中國“新銘”號救援船、中國紅十字會上海醫療隊26人、北京紅十字總會5位專家等是首批抵日的國際救援隊伍(圖17)。從日接回華僑6321人,減輕了日方負擔(代華等,2012)。據《申報》《大公報》,日本的輪船甚至直放溫州,將木炭、煙葉、菜籽、鮮蛋等物品運載回去,一次的價值就高達51萬元……。中國全民動員、“捐棄前嫌”的力度實在太大了,連廟里的僧人和尚都給折騰起來,至今在東京都慰靈紀念堂還存放著一口中國梵鐘,那是我國眾多寺院舉行道場法事、專為日本地震的死難者在杭州鑄造的吊祭大鐘。

圖17 中國醫療隊在日本關東地震現場救護傷員(1923年中國紅十字會攝)
中國人民太純潔、太善良!
豈料,日本當局竟在地震現場制造謠言:“朝鮮人要舉行暴亂,是朝鮮人放的火,以后還有大震”等,東京與神奈川立即宣布戒嚴命令,日本各地的軍隊、警察和市民組織起來,成立“自衛團”,開始屠殺朝鮮人和中國人(圖18),死亡者包括未滿10歲的兒童。據木戶四郎回憶:
中國勞工被集中后,日本人手持斧頭、鐵鉤、竹槍、日本刀等,從一側屠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眾一起,像瘋了一樣實施屠殺,其間還有兩聲槍響,可能是射殺逃亡者,我當時都不敢正視自己同胞的殘虐行為。
韓國國家記錄院2014年6月2日首次公布了《日本關東大地震被害者名單》,被殺害的朝鮮人約6000名。日本宋慶齡基金會副理事長仁木富美子也在戰后作了詳細查證,撰寫了《關東大地震中國人民遭虐殺》,指出被害的中國人758人,其中,死656人,傷91人,失蹤11人,90%是溫州人,著名華工領袖王希天也遇害。在寺田寅彥和鈴木三重吉的《關東地震火災記》和華洋義賑會的當時文件里,都明確記載了上述民族屠殺的殘暴事實。日本在關東地震中蒙受的痛苦,居然以屠殺中朝平民的方式野蠻地渲泄了。
2002年中、日、韓3國53名歷史學家組成了共同編寫委員會,利用3個國家73家單位提供的歷史資料,歷時3年的反復爭議與討論,按照達成歷史共識的原則編寫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學者與教師,2005),并在3個國家同時出版發行(圖19)。書中專辟有一節《關東大地震和在日朝鮮人、中國人》,客觀記述了中朝投入地震救災卻遭到屠殺的事實,指出:“大屠殺是無顏面對國際社會的奇恥大辱”。結尾如下:

圖18 關東地震時日本軍警在屠殺中朝平民(1923年韓國《朝鮮日報》)
1970年開始,日本的市民團體對朝鮮人和中國人被屠殺的事實進行調查,發掘了遺骨,進行了追悼。雖然這一事實已過去了80年,日本政府仍未對屠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事件進行正式的調查,也沒有謝罪和給予補償。

圖19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里1923年關東地震時屠殺中朝百姓一節
中國的災難,僅僅是開始。
日本國內久存的法西斯觀念在關東地震中被觸發和強化了,并很快主宰了全民意志:關東大地震時死了3個皇族成員,兩百年江戶文化的成果瞬間毀滅殆盡。如此強烈的地震還會再次復發,日本狹小的國土完全沒有搬遷的空間余地。欲保障日本人的生存空間,只能對內講“開拓”——占領孱弱落后的中國,移民開拓;對外講“共榮”——搶占東亞的資源,實現共榮。
日本在關東地震之后的侵略步伐急速加快。1924年迅速控制清末代皇帝溥儀,籌備“滿洲國”;1927年確定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方針;1928年炸死不愿當傀儡的張作霖,無情地嘲笑了張大帥的愚蠢——1923年關東地震時他剛向日本送去2萬袋面粉和100頭牛以救災;1931年日本出兵侵略中國;1945年移民到東北的人數已高達166萬,外加近百萬人的關東軍和家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5.2 歷史教訓
清末以來,中國屢屢搞起過“對外震災救援”,以1923年的對日賑濟達到頂點。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尚待研究。現實的教訓卻十分深刻,歷久彌新:
(1)自不量力。中國在1918~1923年間頻發水、旱、震災,死亡人員百萬之眾,大大超過關東地震,自顧不暇卻舉國救日。而日本的經濟實力遠在我之上,隔岸觀火,從不對我實施過救助。中國的這種自不量力的人道救援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道德準則,明顯含有“別有所圖、只待回報”的政治意圖,受援國不會買賬。于是,當美、英、德、法等10個國家于1924年已經全部放棄了庚子賠款的余額并實施退款之時,唯有日本在1923年關東地震后堅持原強硬立場,迫使中國在1923~1937年的14年間,只能持續不斷地年年付給日本庚款賠償。從1902年到1937年全面抗戰時為止,中國對日實際付出的賠款數額共計45 731 181日元,已經達到對日庚款的99%。其中,真正用于留日學生補助、助華文化活動之費用,還不到19%,其余的經費全部被日本用于侵略中國的戰爭了。
(2)混淆界限。1923年關東地震時,日本對租期屆滿的旅順、大連仍然強行霸占,拒絕歸還;是年初,日軍射殺了主張“抵制日貨”的中國民眾,造成的“宜昌慘案”和“長沙慘案”未得解決;遭全國人民唾罵的1915年《二十一條》未作廢除;日本在關東地震的損失約100億日元,但日本乘一戰之機侵略我山東,又收入了30億日元的利益(顧仲超,1995)……。關東地震后,北洋政府將上述各項重大政治問題束之高閣,再不抗爭和追究,反而連篇累牘地號召全中國人民“捐棄前嫌,中日提攜,停止抵制日貨,恢復中日親善”,混淆了人道救援與維護國家主權的界限。
當然,這次舉國援日的發動也與孫中山有關。中國在1918年夏季有146個縣水災,美國給了賑濟,孫中山曾有過表態:“回憶中國水災饑饉之秋,彼時災黎遍野,美國紅十字會嘗由函電匯款數十萬元,分發災區,實行拯救。”“今日中國之士若能樂于輸將,倘他日反有所求,美國人士自可觸引此次之援手,亦必踴躍資助也”(孫中山1918年《中國應協助美國紅十字會之理由》),這可能是孫先生1923年愿意對日賑濟的隱性因素。不過,日本對中朝百姓的民族屠殺讓他頓然清醒、刻骨銘心,故而在1924年底孫中山離粵北上時,乘船途經日本,在1924年11月28日神戶的歡迎會上表明了堅定的立場:“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張憲文,1985)。孫中山到北京后不久去世(1925年3月12日),這句話成為他對日關系的政治遺言,警鐘長鳴。
4 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
1928年底東北易幟——北洋政府的“漢滿蒙回藏”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中國形式上統一,進入國民黨執政時期。
史學界稱1928~1937年為“黃金十年”,雖有1929~1931年間各派新軍閥的反蔣之戰,但全國的關稅、鹽稅和統稅權已經從外國手中收回,貨幣、交通、郵政、航運等已統一,工業平均年增長率達8.4%,工農業總產值達到清末以來的最高水準(張憲文,1985;費正清,1994;路瑞鎖,2012)。中央研究院和多個研究所成立,中國科學家最終取代了外國傳教士的學術主體地位,地震學進入有科研體制為依托的幼年發展階段,進展顯著。
1937年的日本侵略打斷了中國科學發展的進程。科學救國上升為抗日救亡,科學前輩們為抗戰勝利和民族解放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4.1 中央研究院
科學學會是科學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不過中國科學社和各專業學會的體制關系,畢竟松散。
為解決科學研究的實體支撐,1928年6月9日在南京成立了國家性質的學術中心——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1868~1940),聚集了中國科學社的重要成員(如任鴻雋、竺可楨、王家楫等),融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于一體,取代了中國科學社的最高組織領導地位(圖20)。1949年中央研究院遷臺,大陸于同年11月1日成立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1892~1978)。中央研究院的初期僅有理化實業所、地質調查所(所長李四光)、社會科學所和觀象臺等4個機構。以后,觀象臺分成天文、氣象2個研究所,設在南京,理化實業所在上海分成物理、化學、工程3個研究所(潘丙國,2009),至1935年共設立10個研究所。1929年還成立了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1881~1973)。為彰顯學術特點,中央研究院對外采用拉丁文Academia Sinica,各專業學報也一律照辦,如天文學報Acta Astronomica Sinica、地質學報Acta Geologica Sinica、氣象學報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等,以及今日的地震學報Acta Seismologica Sinica。
1930年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聘請了美、德、法、瑞典的著名地質學家,建立了地震研究室(鷲峰地震臺),還陸續成立了河南、湖南、兩廣、四川等省級地質調查所。南京地震臺隸屬于中央氣象研究所,傅承義先生1947年回國后便就職于該所。青島地震臺自1924年從日本收回后,設有氣象地震科、天文磁力科和海洋科3部分(中國氣象學會,2008)。上海徐家匯觀象臺已轉由地方當局、航業公司、各電報公司資助,設天文、氣象、地震、地磁、大氣物理、校準時刻等6大部分(陳岳生,1947)。從此,地震工作有了體制上的依托。
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10名中國董事之一,基金會的庚款獨立于國民政府。1926~1945年間為大學、研究所和文教組織等共計96個機構撥款,資助總額24i250i893元以及392i795美元。7位公認的杰出科學家還獲得了長期研究經費,翁文灝榜上有名(費正清,1994)。
4.2 測震學的開展
4.2.1 中國自主的地震臺站
(1)青島臺
青島觀象臺由德國于1898年建立,1908年增設了地震、地磁和授時項目,配備Wiecher地震儀(擺錘200kg)。1909年1月23日首次記錄到青島附近的中小地震,以及同年4月15日的臺灣地震,曾出版《青島市觀象臺地震報告》(德文)。一戰時被日管轄,1924年2月由中央觀象臺收回。留學比利時的氣象學博士蔣丙然(1883~1966)為首任臺長(圖21),并在同年10月10日在青島創建了中國氣象學會,他1946年任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授,1966年病逝臺北。在他的促進下,1926年9月購進小型Wiechert地震儀(擺錘80kg),成為中國人自己掌握的第1個地震臺。1937~1946年8月期間中斷工作(吳瑾冰,1997;中國氣象學會,2008)。
王應偉(1877~1964)(圖22),早年留學日本東京物理學校數學科,曾任東京中央氣象臺臺長。1915年回國,次年任北京中央觀象臺氣象科科長,中國天文學會創始人之一。1929年調青島觀象臺任氣象地震科科長,后兼任天文磁力科科長,在天文、氣象、地球物理等領域的著述甚豐。1917年研究了根據S-P時差推算震中距的方法,發表“地震之震度及震源距離”“甘肅地震概說”等論文,出版了《近世地震學》《地球磁力學》《氣象器械論》《中國古歷通解》等重要專著。他是中國首位開展地震儀器觀測和理論分析的學者,測震結果刊于由他任主編的《青島觀象月報》。1938年后,在北京潛心于中國古天文歷書的研究。

圖21 蔣丙然(1883~1966)

圖22 王應偉(1877~1964)
(2)北京臺
林行規(1882~1944),留英的法學博士、翁文灝同鄉,1912年回國,曾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法律顧問、司法部部長、北京大學法科學長。1929年把自己在北京鷲峰山莊的一塊地產捐給了地質調查所,還資助了觀測室的建設,觀測室于1930年3月完工(高繼宗,2010)。鷲峰臺同時掛靠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和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均為翁文灝),李善邦負責,助手賈連亨。1930年配備Wiechert百倍級地震儀(錘重200、80kg),同年9月20日記錄到第1個地震。1932年8月增添Galitzin-Willip千倍級地震儀。
李善邦(1902~1980)(圖23),出生于廣東興寧縣的農民家庭,1926年從南京東南大學物理系畢業后回原籍中學教書,經葉企孫先生推薦進入地質調查所。1931年前后,李善邦先后向上海臺的意大利人龍相齊(P′ere E Gherji)和東京地震研究所的今村明恒(IAkitsune)學習地震學。秦馨菱(1915~2003)(圖24)1937年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到臺工作,來臺實習過的還有翁文波和陳國達。

圖23 李善邦在北京地震臺(1931)

圖24 秦馨菱(1915~2003)
北京地震臺按月出版了《地震專報》(英文)與世界各地震臺交換,1932年7月開始出版《鷲峰地震季報》,每年4期,深入研究的震例約300個。到1937年共記錄2472次地震,是當時世界一流水平的臺站(李善邦,1980、1989)。

圖25 南京北極閣觀象臺的原貌(1912年《真相畫報》)
(3)南京臺
南京北側的欽天山(今稱北極閣)(圖25)自南北朝便設有觀象臺(后稱欽天臺、司天臺)。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Ricci)在明朝1598年登頂時,曾見到該臺有“銅制天球,日晷,相風桿,渾天儀,簡儀等器”(《利瑪竇來華始末記》)。1928年在北極閣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留美氣象學博士竺可楨(1890~1974)任所長。為研究地震、海嘯與氣象的關系,1930年訂購了地震儀器。金詠深負責測震,助手孫儒范。
金詠深(1905~1953),1929年國立中央大學畢業,1930~1937年任氣象所測候員,在《科學》《氣象雜志》發表過3篇地震學文章。抗戰期間曾在航空公司工作(秦馨菱,2005)。
北極閣臺1932年6月安裝Wiechert地震儀(水平向放大1500倍,錘重17t;垂直向放大150倍,錘重1300kg),同年7月8日記錄到首次地震。1934年3月配置Galitzin-Wilip電磁式地震儀。1932~1936年出版《地震季報》4卷共16期,與國內外四五十個地震機構和臺站交換觀測資料。1931~1935年間,逐年發布《地震測候》于國立中央研究院年度總報告中,共記錄地震1410次。1947~1948年南京的北極閣臺和水晶地震臺恢復工作(秦馨菱,2005;劉廣寬等,2006;中國地震局監測預報司,2005)。
前述3個地震臺的儀器都十分先進。1897~1910年間,世界各臺站的儀器均為Milne地震儀和Omori地震儀,屬于第1代儀器。Wiechert倒立擺地震儀和Galitzin電磁地震儀屬于第2代地震儀器,更適合監測微小近震,對遠震的初動亦有良好反映。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庚款資助下(北京臺獲4000余元),3個地震臺均配置了當時最先進的第2代儀器(表2)。臺灣地區自1933年后地震儀亦全部升級,一直用到1988年。

表2 中國自主的地震臺一覽表
4.2.2 中國地震儀的研制
1937年“七七”事變,北京鷲峰臺的交流電線被日軍炮火打斷。當日,賈連亨和他老父冒著危險把臺站資料和地震儀裝箱,連夜用人拉平板車走出十幾里山路,一直走到天朦朦亮才運到燕京大學和協和醫院藏匿起來,他父親因此病倒而為地震事業獻出生命。鷲峰臺后來變成抗日游擊隊的指揮部,Wiechert地震儀的重錘被制成手榴彈打擊日寇。在南京,李善邦與金詠深等搶運和隱藏了地震儀,Galitzin地震儀在運輸途中被日機炸毀。李善邦被戰爭害得妻離子散,與其他研究人員于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之前匆匆撤離。1939年春,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入重慶北碚。1938年2月~1943年6月,日軍對重慶實施了9000多架次轟炸,萬余房屋盡成瓦礫,地質調查所辦公室亦被炸,工業實驗所竟成火海……重慶出現了南京大屠殺后平民最嚴重的死傷。
李善邦、秦馨菱等歷經千辛萬苦終于1938年9月抵渝,冒著日軍的戰火奮力研制中國的地震儀。所需材料從舊貨攤上買東西改裝,用石磨當飛輪,人力帶動車床加工零件,阻尼器用鐵片放進油里實現,時號用橡皮夾放個小鉛片,繼電器的白金觸點用經常需要擦洗的白銀來替代,沒電源時就開啟手搖發電機,熏煙記錄紙反復使用,日機轟炸后又繼續工作……,李約瑟看到這種情況非常感動,表示回英國后要幫助他們解決殷鋼材料。長期的艱苦勞累導致李善邦肺病復發,多次吐血,秦馨菱成“萬能博士”……。1942年冬中國第1臺地震儀制造成功(圖26),為水平機械杠桿放大熏煙式,放大倍率152。命名為“霓式”地震儀,以紀念我國地震學先驅翁文灝(字詠霓)(李善邦,1945;秦馨菱,2005)。

圖26 中國第1臺地震儀的基本結構(李善邦,1945)
1943年8月重慶北碚地震臺正式工作,記錄到四川、淮河流域及土耳其等地109個地震,出版報告,與Gutenberg、ISS、法國斯特拉斯堡國際地震中心交換資料。謝毓壽(1917~2014)四川大學畢業后,1944年到臺工作。二戰期間,蘇聯所有地震臺都停止了工作,北碚地震臺竟能在戰爭中建立起來,向世界傳達出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
李善邦地震儀于1951年改進加工,遂命名51型,裝備了我國黃河流域20多個地震臺,一直用到1966年邢臺地震之后(秦馨菱,2005)。
4.2.3 地震監測
1927~1933年的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項目,對內蒙古、甘肅、新疆地區作地質、地球物理、考古、測繪等綜合研究,袁復禮(1893~1987)和陳宗器(1898~1960)亦參加,成果頗豐。此間,該地區發生2次震中烈度大于Ⅹ度的強震。
對1931年8月10日的8級地震,李善邦(1934b)利用全球65個臺的數據,在新疆9月初來電之前就確定了震中——北疆富蘊,袁復禮也立刻在當地作了調查。可貴的是,李善邦已經用上美國麥氏走時表,而Jeffreys地震走時曲線是在1935年才完成的。1932年12月25日甘肅玉門的7.6級強震亦為西北科考團員親歷,金詠深(1933)(表1)利用東亞32個臺資料確定了震中在玉門-昌馬,隨后作了通信調查。
1933年8月25日四川疊溪發生7.5級地震。李善邦(1934a)又根據北京、南京臺P波到時相同的特點,簡單及時地推斷了震中位置,隨后用多臺數據修訂了震中坐標,確定了發震時刻和深度,分析了地震的構造背景。上述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科考和震災救援。
4.3 地震調查
4.3.1 1933年疊溪7.5級地震
中國近代史上人員傷亡第3位嚴重的震災,是1933年8月25日的四川省疊溪地震。
疊溪臺地高出岷江270m(圖27),1300年前的唐代在其上建有疊溪重鎮,地震時整個臺地轟然塌陷,古鎮亦蕩然無存,全城517人遇難,僅逃出1男1女。陷落和山石垮塌又造成20余個羌寨覆沒,周圍15km內的所有房屋皆被摧毀殆盡(圖28),還形成3個堰塞湖……。10月9日晚7時許,高出岷江河床160余米的疊溪堰塞湖潰堤,大定以上的水頭高達60m,水流濃濁如爛泥,腥臭刺鼻。洶涌的濁浪于是夜9時到茂汶,水頭高約26m。11時到威舊,子夜沖到汶川,水頭高約20m。次日凌晨3時抵達灌縣,洪峰仍高12m,沖壞了都江堰的飛沙堰,灌縣2500多人死于洪水,成最為嚴重的次生災害(洪時中等,2014)。罹難于地震的總計9293人(中國地震局災害防御司,1999)。

圖27 1933年疊溪地震之前的疊溪臺地原貌(E H Wilson攝于1910年8月3日,洪時中提供)

圖28 疊溪地震中的魚兒寨震災難民(1933年茂縣政府司法曾伯衡攝,洪時中提供)
疊溪地震時,國內正處于嚴重的外患內憂之中。日本在1932年2月建立偽“滿洲國”后,1933年已把侵略戰火全面向南推進到山海關、延慶、承德至熱和省的長城一線,5月逼簽的《塘沽協定》和7月的《何梅協定》成為“九一八”之后重大的入侵新階段;與此同時,蔣介石在1933年9月調集了一百萬軍隊對中央蘇區展開第五次“圍剿”。這個時候,社會關注點已轉移,疊溪震災得不到國家層面上的救援。
地震調查全靠四川當地來進行,成都水利知事公署全睛川率隊10余人,于9月27日前往震區調查。返程途中遭遇10月9日的疊溪潰決。除全睛川與寺廟老僧因夜晚聊天而僥幸逃脫外,周郁如、郭西中、諸有斌等其余同事皆遇難,再次出現為地震事業殉職的科技人員。其中,諸有斌是四川大學史學系3年級學生,為救同伴而犧牲,年僅23歲。1934年3月,技術員胡權五在對疊溪積水疏導施工中,也因余震獻出了生命(洪時中等,2009)。

表3 1900~1949年震中烈度大于Ⅹ度的地震
1933年10月25日,西部科學院地質調查所所長常隆慶(1904~1979)與羅西伊等人再次實地調查。初步查明了疊溪及其周圍震區的崩塌滑坡、人員傷亡、水災過程、余震序列等,編寫了考查報告(常隆慶,1934、1938)。地震之后,當地政府曾采取過有限的救助和以工代賑措施(李德英等,2010)。
對疊溪地震的系統研究,是在1949年以后開展的(四川省地震局,1983)。
4.3.2 強震調查概述
1900~1949年間的地震調查共有13次(表3),只是未達人跡罕至的西部5次強震區。研究內容很寬泛,諸如分析地震與地質構造的關系,統計有感震的區域(烈度、影響)、震聲(區域、特性)、前兆現象(地下水、動物、地光、氣候變化),分析極震區和震源的地質環境、地質災害(山崩、地裂、地陷、噴砂、冒水),研究建筑物破壞和人員傷亡原因,總結地震活動序列和歷史地震背景等,留下了寶貴經驗(李時若,1991)。
對一些中強地震,如福建上杭(1922),云南大理(1925),隴東、廈門(1936),兩廣(1938)和云南石屏(1940),報章曾作新聞報道。
4.4 地震學研究的進展
在中央研究院時期,地震學研究的進展較大。
1928年以前的20年,僅檢索到23篇地震學文章,屬于初級內容,涉及到的刊物不足10種,諸如《學生雜志》《地學雜志》《觀象叢報》等。有分量的僅是1918年霍山地震報告和《科學》上刊登的文章。1928年以后的20年,檢索到63篇地震學文章,刊物30余種,如《科學時報》《地質評論》《氣象雜志》《氣象學報》《地球物理專刊》《地球物理學報》《燕京學報》等,在《中國地質學會志》《中央研究院年度報告》《北平研究院匯報》《農商公報》等也有一些文章,大多可從《中國近代地震文獻編要》(陳尚平等,1995)中查到。較重要的進展簡述如下:
(1)理論地震學
王應偉(1931)的《近世地震學》,是國內第一本系統介紹現代地震學的理論著作。他根據Gutenberg和Jeffreys的地震波著作,以及Wiechert、Sieberg和Galitzin地震儀的材料撰寫而成。全書11章,含彈性波動、地震波傳播、地震儀、地震記錄、地震波的觀測、震中與震源等基本理論,該書學術價值很高。留學加、美的地球物理學博士傅承義(1909~2000)1947年回國,曾于1946~1947年在美發表過3篇有關地震縱橫波、面波傳播的經典文章。
(2)測震學
對測震儀器,從原理、構造、阻尼、頻率響應、計時和記錄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翁文波,1934;李善邦,1934a;孫儒范,1935(表1))。對霓式地震儀亦有詳盡介紹(李善邦,1945)。結合1931~1933年富蘊、昌馬和疊溪等地震,討論了相應的測震技術和計算方法(金詠深,1933(表1);李善邦,1934b)。1936年王振鐸還根據懸垂擺原理提出了張衡地動儀的復原模型,年僅24歲。
(3)地震地質學
1925年以后的強震共11次,調查了9次(表3)。烈度評估已普遍采用,利用了測震學的數據,整理了相應地區的歷史地震資料,探討了發震的構造背景、余震活動序列、地形和地質對烈度的影響和前兆現象等。特別是地方的科研機構和學校都投入進來,河北、兩廣和云南地區甚至對余震活動作了研究。對于1936年廣東靈山地震,24歲的陳國達使用了Mercalli地震烈度表,據等震線形狀推斷了斷層的產狀。據他回憶,正是這次工作,使他發現了地槽-地臺說與中國地質現象之間的矛盾,萌生了“地洼學說”的最初想法(劉寶誠等,1999)。
(4)抗震減災
學術研究開始考慮抗震問題。分析了地震時倒塌民房的結構、材質等因素,討論了地基條件、斷層避讓、松軟土層間的關系,強調了對黃土層窯洞的減災、次生災害的預防問題。加大宣傳了“防災減災勝于救災”的概念,呼吁建立震后救災機制,甚至提出了地震預報的想法(翁文灝,1924;王應偉,1931)。
(5)學術交往
翁文灝1922年在比利時參加第13屆國際地質大會,宣讀《中國地質構造對于地震區分布的影響》一文,這是我國地震學成果的首次對外交流。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是第一次開展的國際地學合作。李善邦1934~1936年赴德國波茨坦(Potsdam)地球物理所、耶那(Jena)地震所和美國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考察學習,1946年又應英國文化委員會和劍橋大學的邀請訪英1年。秦馨菱在美國《對外經濟援助法案》的資助下,1945赴美學習1年。抗戰勝利后,海峽兩岸學者相聚于臺北,1947年臺灣氣象局贈送給大陸Weichert、Omori型地震儀各1套(秦馨菱,2005)。
針對早期在外文翻譯和日文借用上的混亂情況,地震學名詞的使用開始漸趨規范化(表4)。

表4 民國時期已漸趨規范的地震學名詞
4.5 科學前輩的貢獻
抗戰需要鋼鐵,國家需要資源。抗日戰爭,把科學家與祖國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到一起,地震研究與地球物理學的工作結合到一起。
劉慶齡1937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開展了地磁研究,編制了中國第一幅地磁圖。留學德、美的方俊、顧功敘在1938年的嚴峻時刻迅即回國,方俊等編纂了《中華民國地形掛圖》與《中國分省新圖》,顧功敘帶領助手曾融生研究了全國重力均衡。留英的翁文波沖破阻力于1939年趕回國內,奔赴玉門找石油。李善邦、秦馨菱等先后在湖南水口山鉛鋅礦區、川南和貴州鐵礦金礦區、以及攀枝花磁鐵礦區開展物探……。我國的白云鄂博主礦、玉門油礦、攀枝花鐵礦、江西南嶺鎢礦等幾個重大礦藏都是此時期發現和證實的。科學前輩們為祖國解放、民族獨立做出了貢獻。
1947年8月2日中國地球物理學會成立(理事長陳宗器,1898~1960),地震學研究從氣象學和地質學的“代管”狀態分離出來,作為9項獨立學科之一納入。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舉出首屆81位院士,地球科學領域有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謝家榮、竺可楨(潘丙國,2009)。此時,國際地震學又取得新進展,諸如發現了地核(1914)、液態內核(1936),發展了地震勘探技術(1923),建立了震級標度(1935)等。
5 啟迪與思考
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這是魯迅1925年在《華蓋集》所言。隨著1924、1925年列寧和孫中山相繼離世,國共開始第一次合作,魯迅深思著國家的靈魂和前途。這個靈魂,也同樣寫在近代中國地震學史上。
5.1 科學救國是歷史的選擇
“學而優則仕”本是中國的一個落后腐朽觀念——讀書為做官。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1915年提出了“科學救國”的口號,把讀書人的個人命運與祖國前途、科學研究與民族獨立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改造了人們的心靈。我們聽到考察海原、疊溪等地震的科研人員們渴望民族獨立的吶喊,體會到李善邦等在日機轟炸下研制地震儀的奮起決心。中國地震學是在九州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之際由前輩們砥礪奮斗而開創的,后人會永遠牢記:研究報告里存留著可歌可泣的抗戰篇章,地震臺站上閃爍著愛國主義的輝煌。百年屈辱給華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記,愛國、救國、興國的高尚靈魂遂成為世代中國學人扭轉乾坤的力量源泉。
5.2 科學與民主需要同時提倡、相互輔翼
“科學與民主”的提出已然百年,只有二者同時提倡、相互輔翼,社會才能進步。學術民主相對容易,而政治民主卻沒有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扎根,從遠古時代沿襲下來的專制思想和文字獄的流毒,在中國極其牢固(茅家琦,2004),直接損害著科學和藝術創新的靈感和土壤。1916~1926年間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正值袁世凱死去、列強多元化、新專制未建立,即專制權力的低點時期。各種群眾性學術團體和報刊相繼出現,出國留學蔚成風氣,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得以迅速傳入和實踐,出現了近代史上思想開放包容和中國文學創作的輝煌高峰(費正清,1994)。這段“文化復興”的時間雖然不長,成就有限,但青史明鑒,值得汲取。

圖29 常隆慶(1904~1979)
5.3 地震研究是個長期的認識過程
地震的重復率極低,又搬不進實驗室。這種類型的研究,個案的、現象性的分析相對容易,普適的、規律性的確認十分困難。常隆慶(1904~1979)(圖29)是位功勛地質學家,1935年首先發現四川攀枝花大型釩鈦磁鐵礦(王仰之,1983),礦山投入開采,后來還為他豎立了全身雕像。他早在1933年就考察過疊溪地震,但對地震的認識卻遠未結束,以致謝世前的1978年還在伏案耕耘《疊溪地震和地震地質概說》一文(常隆慶,2012)。甚至在疊溪地震80多年以后,我們仍然會讀到有關這次地震的研究成果(洪時中,2014)。西方也是如此,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的里斯本發生8.7級大地震,在2005年里斯本地震250周年之際歐洲仍然要舉行學術會議,繼續研究這個地震的相關問題。美國對于1906年舊金山地震、日本對于1923年關東地震、意大利對于1908年梅西納地震的研究,也都是這樣。可以說,長期性是地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特點。一次大地震的孕育會歷時幾百年至上千年,而人類在幾十年間的研究結果只不過觸及到了構造運動的短期或瞬間現象,要以此來準確預測地震畢竟不夠充分。預測問題,民國初年已提出,無疑是個長期的任務。
1979年11月21日中國地震學會在大連成立(理事長顧功敘,1908~1992),要比1880年日本地震學會、1901年國際地震協會的成立時間,分別晚了100年和80年。
6 結論
隨著西方科學在清朝末年的傳入,中國近代地震學逐漸發展起來。可大體劃分成的3個階段,與社會背景緊密相關。辛亥革命深刻地推動了近代科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以中外傳教士為主體的零散性地震研究;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中國科學社和專業學會出現,以海原地震為標志的地震地質研究首先起步,積累了地震的救災經驗,但也有深刻教訓;國民政府期間,中央研究院和專業研究所建立,中國科學家取代了外國傳教士的學術主體地位,地震學進入有科研體制為依托的幼年發展階段,進展顯著。科學前輩們把個人與祖國、科學研究與民族獨立緊密聯系在一起,為國家做出了不朽的貢獻。科學救國是歷史的選擇,科學與民主需要同時提倡,地震研究是個長期過程。
筆者謹以此文紀念恩師李善邦先生去世40年。他生前幾度表示過想寫中國地震史,但因年事已高未能成稿。幸好,在先生謝世前完成的《中國地震》的“自述”一節里,已經寫明了我國早期地震發展史的要點(李善邦,1981),本文遵循他的總思路來撰寫。李善邦先生為中國地震學的發展貢獻了一生,后人將永遠紀念他的功績。對筆者的工作,洪時中教授提供了珍貴的歷史照片及相關資料,謹表誠摯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