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爾蘭學豎琴
彭李菁
導語:奇奇怪怪的人們出于一份對愛爾蘭文化的熱愛在世界盡頭處的峽谷聚首,度過歡樂如夢的一段夏日時光。
科倫基爾峽谷(Glencolmcille)是愛爾蘭多尼戈爾郡西南部的愛爾蘭語區(Gaeltacht),即愛爾蘭政府認定的以愛爾蘭語為主要使用語言的地區。因地處偏遠,科倫基爾峽谷在經歷過近代的殖民、饑荒和戰亂之后,仍然保留了相當的愛爾蘭語使用者人口。愛爾蘭在1922年建國后國家有意保護愛爾蘭語,所以經濟上大力資助愛爾蘭語區,期望愛爾蘭語使用者們能夠在原生的生態環境下繼續相對傳統的生活方式,保存這門語言的生命力。多年以來,全球化的影響和英語的強大地位仍然漸漸改變了愛爾蘭境內所有愛爾蘭語區的面貌。年輕人紛紛離家到世界各國闖蕩,本地群體中英語也漸漸成為更重要的日常生活語言了。然而新舊結合的文化和商業模式紛紛興起,讓本土語言和文化又煥發生機。在科倫基爾峽谷,每年夏日的遠足朝圣旅途和橫跨夏秋二季的愛爾蘭語及愛爾蘭音樂學校帶來了許多國內外訪客。他們或是虔誠的信徒,或是對愛爾蘭語和愛爾蘭文化抱有極大熱情的新時代實踐者。他們來到科倫基爾峽谷感受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原生語境中學習語言,向本土樂師學習各種傳統樂器和曲調。然而他們同時也帶來了各種語言保護和語言復興的本國經驗,以及在世界各國教授愛爾蘭語的經驗;樂師們紛紛帶來自己國家或居住地的樂器和曲子,與多尼戈爾樂師們彼此交流學習,其樂融融。
每年7月初到薩文節(11月1日愛爾蘭人在進入冬季前過的傳統節日)之前,科倫基爾峽谷的愛爾蘭語學校會接待一批又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教授愛爾蘭語和兩種愛爾蘭傳統樂器:哨笛和愛爾蘭豎琴。學生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和計劃選擇不同長度的語言課程,從一周到兩個月不等,音樂課程則一般只有一周。十一年前我初到愛爾蘭時就深深為愛爾蘭豎琴著迷,最早聽的就是有名的多尼戈爾郡樂隊Clannad的歌。跟古典豎琴相比,愛爾蘭豎琴更接近中世紀歐洲游吟詩人使用的詩琴,更多是為彈唱設計的。其弦音更低,能與人聲更好地交融,也能與其它愛爾蘭傳統樂隊的樂器更好地配合。雖是對愛爾蘭豎琴一見鐘情,但十年間博士學業、畢業后實習和工作、結婚生子,時間就這么過去了。直到聽聞科倫基爾峽谷的豎琴課,終于下定決心報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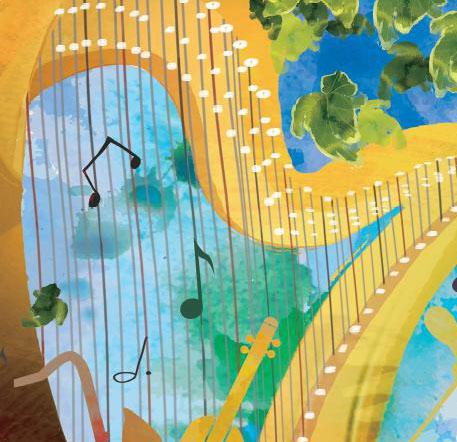
在科倫基爾峽谷度過的一周美好得簡直不真實。每天早晨向樂師學習兩首曲調,每日午后與同學們一起遠足,漸漸走遍了科倫基爾峽谷的古跡,圣徒科倫巴的圣跡,懸崖邊的壯闊風景,和近代大饑荒和戰亂時期廢杞的漁村。傍晚時分回到學校溫習當日所學的曲調,向同學們作展演。每天晚上學校都會安排各種活動,或是詩歌朗誦,或是歌唱會,或是樂器交流聚會,許多國際知名的民俗音樂家都遠道而來,一是支持科倫基爾峽谷學校的辦學,二是與各國的歌手和樂師交流。晚上學校的活動后一般同學好友們會相約到幾個不同的小酒館去談天說地直到深夜。在這些小酒館度過的夜晚讓我真正體會到民間音樂的魅力。每個小酒館都為樂師們設一個聚會的長桌,上面放一堆飲料,常見的包括淡啤酒、黑啤、西打酒、威士忌等等。樂師們往往其中一個即興起一個調,其他人隨自己的興致和關于那個曲調的知識在演奏的不同階段隨意加入,如果演奏時覺得哪里不順暢也可以隨時停止,任由其它樂器繼續。不時也有酒館中的客人興致來了想要高歌一曲,只要給樂師們一個調或者是起頭唱幾句,很快就有不同樂器開始伴奏,非常隨興。還有本地人聽著聽著演奏臨場編歌唱的,不外乎家長里短妯娌糾紛,但就編成詩韻用十分幽默的方式唱出,往往博得哄堂大笑。這些樂師們在每晚聚會前大都不相識或者沒有合作過,樂器也不拘泥于愛爾蘭樂器,我有見過來自南美、亞洲或是北美爵士樂樂器用自己的方式加入表演的,即興的演唱者更加不專于任何種類的歌曲。音樂的語言沒有國界,隨性的演出不沾任何名利,人們只為在某一時刻抒發來自心底或日常生活的一聲嘆息,并獲得些許共鳴,這或許就是音樂最人性化的時刻。
學習的過程也相當有意思,我一向看慣古典樂譜,對這種完全師徒間面對面傳授,全憑記憶演奏的民俗音樂教學模式感到相當新奇。老師說愛爾蘭豎琴樂師們每年會在各類音樂節上互相學習曲調,并同場演奏交流,這就是他們學習的方式。每年最大的兩個音樂節,一個在愛爾蘭境內的基達爾郡(County Kildare),一個在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往往人流洶涌,露天搭棚的民俗藝人日夜流連,把自己的腦子塞滿新曲調,也不吝于教授自己所知的音樂。這類交流往往不止于音樂,樂師們教授曲調時,會講述背后的歷史和故事,所以每一曲都是獨一無二的,其音樂有自身的歷史和生命。我們在第三日上課時學到一曲相當幽默的小調,這是老師給我們講的故事:據說愛爾蘭人制作小提琴使用特殊的木板,使其可以承受極快的指法。這種木板越是震顫得多,提琴的音色就越好。于是有一位多尼戈爾郡的樂師除了每日白天勤加練習之外,晚上還把提琴放在老式電視機上,讓電視機運轉時的顫動不斷震顫提琴。結果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回來把提琴放進了金魚缸里……這首歌就叫《電視機上的提琴》。我們大笑一番之余,也在練習時彈得更加有滋有味。不過,口頭傳授的音樂往往相當簡潔,變化不多,主旋律不斷循環。這也是關于愛爾蘭民間音樂的負面評價中出現得比較多的一點:相對模式化,缺少有力的變化。
在科倫基爾峽谷碰到的人們都非常有意思。豎琴班的同學里就有剛完成蘇格爾蓋爾語博士學業的匈牙利姑娘;另一位同學是哈佛大學古愛爾蘭語方向的博士生,再下一位又是為聯合國工作的荷蘭妹子。幾天的遠足路途里,我碰見過來自捷克布拉格大學的愛爾蘭語教授,自德國的人類學博物館館員,都柏林的著名兒童戲劇教授,來自美國的知名愛爾蘭豎琴演奏家,等等等等。這些奇奇怪怪的人們都不過是出于一份對愛爾蘭文化的熱愛在世界盡頭處的峽谷聚首,度過歡樂如夢的一段夏日時光。若說圣徒科倫巴千年前有意眷佑這片土地,這美好的時光就是跨越時間而來的最好禮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