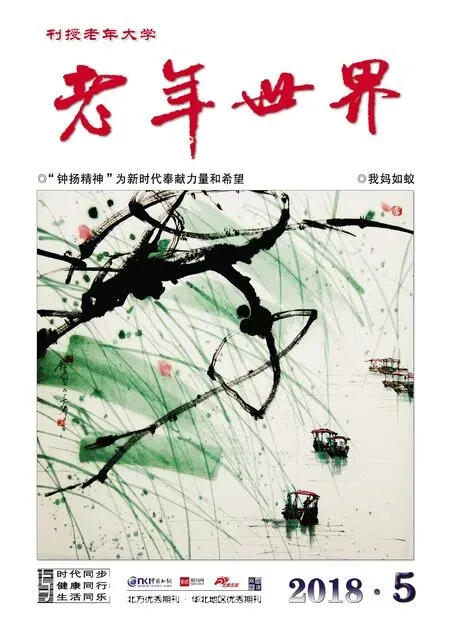那年聽陳忠實唱陜北民歌
張 鳳
當時大陸作家來哈佛的屈指可數。忠實先生雖名聲在外,卻因當時大陸作家出國者少,鮮有機會認識。我初次返回大陸尋根的1993年8月,正值文壇陜軍東征,他6月出書,年內印刷7次,總數達56萬多冊。
捧讀忠實先生簽贈的《白鹿原》,想起同先生曾數度歡聚,在哈佛附近,我所熟悉的王劉伉儷家中,開心地品賞他們地道的西北酒菜。忠實先生談起這次出訪,沒有翻譯,全憑手中的幾張紙條,寫著:請問火車站怎么走?請問衛生間在哪?請帶我去哪兒等等。居然也走了一路。
越三年,“北美華文作家作品研討會”于9月下旬在華僑大學舉行。我與陳忠實再度相逢。恰逢中秋,中秋晚會主題是“月是故鄉明”。晚會上,忠實先生即興登場,一展三秦大地的厚土民風。他的表演是陜北民歌,只見他放聲高歌:“人人都說咱們兩個好,自幼兒還沒有拉過你的手;頭一回到你家你不在,你家的黃狗把我咬出來;二一回到你家又不在,你爸爸打了我一煙袋;三一回到你家還不在,你媽媽砸了我一鍋蓋……”

唱得酸味詼諧十足!
忠實先生腰桿兒端直,他說自己就像《白鹿原》里的主人翁,他的曾祖父——個子很高,因為腰挺著,顯得威嚴,村子里走一趟,那些門樓下袒胸露懷給小孩喂奶的女人都被嚇回家。
理應是彪悍瘦硬雄奇的關中漢子,卻仿佛反復受盡辛苦,皺紋縱橫交錯,眼神里有點憂思。忠實先生總是一臉可掬的笑容,大氣豪邁,懂禮重義。他主張朋友之交刪繁就簡,心眼實,人厚道,常木訥無語,多人聚會,也完全不改脾性。在開元寺、清源山、彌陀巖、承天寺,大家隨著導游,他總是靜默地待在最邊緣、最后面,或研究外面的楹聯牌樓,或抽他的煙。
忠實先生坦然于寵辱憂歡,寫《白鹿原》時,全身心沉浸于那個時代。令他自信且心里覺得踏實的,就是整個創作過程沒有經過任何的干擾和炒作,“饃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鍋蓋。因為鍋蓋一揭,氣就放了,所以饃就生了。”對作家而言,最終都要與讀者完成交流,而獲得最廣泛的讀者喜愛,是高于任何獎項的安慰。這部作品被秦腔、話劇、舞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改編,小說被譯為英、日、韓、越、蒙等文字出版。
2009年秋我應邀去陜西師大演講,沒敢驚擾諸位老友。他得知后,立即趕來相敘并邀我翌日同游白鹿原,這可真是令我出乎意料。
那時,借著“作家之鄉”的美譽,白鹿原已成景點。當地鄉親們還在此立下了一座高高的、刻有陳忠實親書“白鹿原”的瓷碑。從“白鹿原”碑望向西安城,日走云遷,有些薄霧,極目眺望,灞橋煙柳卻都看不到了。陳忠實見此喟嘆:“廢氣污染后柳色盡失。”
表2的數據說明38%的英語四級分數大于等于500分的學生會在閱讀附錄后再查詞,而英語四級分數小于500分的學生只有14%會去閱讀詞典附錄。但在是否閱讀詞典使用說明這方面兩組學生就不存在很大差別,只是英語四級分數大于等于500分的學生稍微多2個百分點。總之,絕大部分學生在查詞之前并不閱讀詞典附錄和詞典使用說明,這一點說明學生在詞典使用技巧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欠缺。
此刻,流淌著黃土血脈、矢志塑造渭河流域深厚鄉黨史的陳忠實,站在入秋的長堤上遠眺灞陵,認真地傾訴:“漢文帝就葬在白鹿原西端北坡畔,坡根下便是自東向西倒流著的灞水,距我村子不過17里路。文帝陵史稱灞陵,依著灞水而命名。地處長安東郊,自周代就以白鹿得名的原,漸漸被灞陵原、灞陵、灞上之名取代。灞橋距文帝陵不過三四公里,《史記》里的灞陵原又稱灞上,泛指白鹿原以及原下的灞河小河川,灞橋在其中……”
談吐間,我能真切感受到他對這高緩的黃土原的無限依戀,寸寸黃土河山都飽含著他承載的心念。
接著,我們再隨忠實先生去白鹿原上的農家。忠實視民如親,他對鄉村的體驗及生活積累,對農民天地的見證了解,為他的創作打下了最自然和堅實的基礎。他曾說:“有時在路邊的樹蔭下蹲下來,和鄉黨一扯就是兩個鐘頭,談到的獨特農家的事情,常常牽動深深感情。”
原上一馬平川望不到盡頭,多是平展展的土地;綠樹小村、裊裊炊煙,院落石墻犬吠雞鳴,槽頭的高騾大馬一頭頭都像昭陵六駿;秋氣緩掃落葉,舒適的農莊水井,令人感受到寧靜的韻致。這是他鐘愛的新農家大四合院,淳風漫逸。
下原后,我們前往藍田。所謂百里不同風,忠實經常開玩笑說自己是半個藍田人。他小學高年級時在灞河北岸藍田縣油坊鎮就讀,當然不會忽略這“日暖玉生煙”的藍田。一路上他娓娓而談,說:“藍田有‘廚鄉’美譽,正所謂一把鐵勺走天下。當年的御廚王承恩、李芹溪、侯治榮等,都是藍田人……”他還為此專門題詞“讓藍田勺勺攪香世界”。看得出,藍田美食早已成為他時刻惦念傳承的三秦文化之一了。
2012年,我獲邀在世界華文文學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并因此再度來到西安。演講完畢,有人俯首悄悄在我耳邊說:“張老師,請來外面一下。”出去一見,陳忠實正在外面等候,他說:“我是專程來看你們這些老朋友的!”
歡敘之間,陳忠實主動為我題下:
和張鳳在西安第三次握手,深以為幸。
陳忠實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西安
這三次溫暖的握手,想來是指2009年在西安的兩次和這一次。實際上,何止于此:1995年哈佛春天之約《白鹿原》作品上的題書,1998年泉州仲秋在我日記小本上寫下的陜北民歌……在我心中,多年來與他的翰墨往來(哪怕是傳真)都已成無價之寶。依依不舍地離別之時,我心里默默祈盼哪年哪月幸能再聚,但萬萬未料到這竟是最后一面。
忠實先生行事為人都厚道。他的行事,正如寫在《白鹿原》里的那些話: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其實天知道地也知道,記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