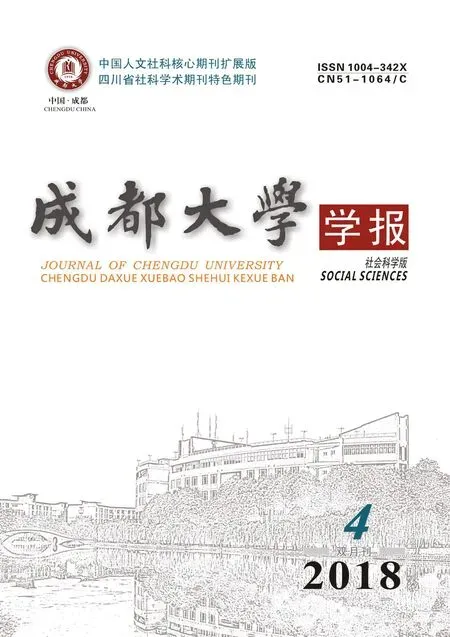川西南—滇北地區三國文化遺存研究
郭的非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 四川 成都 610041)
三國文化是以三國時期的歷史為根基,包含其所衍生的文學、祠廟、故事傳說、民俗等多種文化因素的綜合性文化。三國歷史雖短,卻深入人心、影響深遠,使三國文化在歷代得以不斷豐富,呈現出復雜而親民的表現形式。因此,三國文化遺存既包括三國時期的歷史遺存,也包括帶有濃厚三國文化因素的其他歷史時期遺存。

一、遺存概況
經多年調查研究,本區域內三國文化遺存已有很多資料。本文以有明確地理位置指向、有實存載體的故事傳說和有實存遺址遺跡為標準,統計選取點位16處,如表1所示①:
可以看出,這些點位被視為三國文化遺存,一部分是直接對應三國時期的歷史事件,一部分是長期存在關于三國人物和歷史的故事傳說。
(一)對應三國時期歷史事件的遺存

渡口所在交通線在蜀漢時期即為川滇互通的主要道路,時屬靈關道(一名零關道,秦時稱旄牛道,唐以后稱清溪道),于邛都(西昌)后分支,一支經攀枝花,至三縫、青蛉(大姚)和弄棟(姚安)一帶。


表1

(二)對應三國故事和傳說的遺存

一為“營盤文化”類遺存。川西南—滇北地區的金沙江流域峽谷交錯,山區中分布著數十處大小營盤,當地廣泛流傳著諸葛亮南征駐軍于各營盤的故事和平南中戰事的傳說,形成了獨特的“營盤文化”現象。
一為“打箭巖”類遺存。在本區域,如“一箭之地”、“諸葛神箭”、“一箭定邊界”等諸葛亮與“箭”的故事和傳說極為常見。所見遺跡或現象基本由山崖、巖石、“竹箭”或“木箭”等因素構成,其巖石多被稱為“打箭巖”。
然至今為止,對這兩類遺存年代、性質、族屬等相關研究甚少,甚至多被直接認定為三國時期的遺存,本文就此略論一二。
二、“營盤文化”類遺存
“營盤文化”類遺存以營盤山古軍營、萬寶營、巖神山營、寶興營、保安營、先鋒營、方山諸葛營為代表,被稱為“七大連營”②。各營由北向南,沿金沙江兩岸展開,布局方式和現存遺跡均相似,應為同一時期所建。其中,以營盤山古軍營和方山諸葛營規模最大,又以營盤山古軍營現存遺跡最為豐富,可作為其中代表。
營盤山古軍營遺址現存烽火臺兩處、土城墻兩段、營盤兩處、護城河、石城墻、指揮所、采石場、半地穴式魚鱗狀兵坑等遺跡,③現從遺址結構、自然條件和歷史背景、同類遺址遺跡比較、文獻研究等方面分述。
(一)遺址結構
各處遺跡中,石城墻明確為有組織性的人工修筑,其他遺跡處雖未發現建筑痕跡,但按其特征,亦應有人為建造因素。這些遺跡基本沿上山之路分布,各處遺跡之間當有一定聯系。然而,如以現主流觀點謂之軍營,有矛盾之處。首先,指揮所、半地穴式兵坑均位于石城墻以北,烽火臺、營盤位于石城墻以南。若如是,則不可知城墻所防衛目標是北向還是南向。其次,營盤山所處之地并非絕對制高點,交通亦非不便,山下兩側均有通暢道路,此地形幾無駐軍山上而孤困自身之可能。第三,整個營盤山遺址山勢變化較大,現存遺跡處即為人可活動處,面積不大,無法滿足大規模駐軍的需求。
加之以現有調查發現情況來看,各處遺跡的具體性質待考,是否實如其名猶未可知。如是,則整個營盤山遺址性質是否為軍事設施都需進一步研究,論其為諸葛南征之軍營恐依據不足。
(二)自然條件和歷史背景
金沙江本區內一段江水湍急,眾小股水道匯之,周圍山巒疊錯,峽谷交集,春夏時酷熱難當,尤其易生瘴氣。《水經注》云:“(瀘津)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徑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無害。”又引《益州記》云:“(瀘水)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4]826又《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建興)三年(225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5]919可知,諸葛南征歷時半年左右,部隊由成都終至滇池,時間與路程相照,應無專門筑營駐扎之時機。加之金沙江沿岸氣候環境如此,扎營營盤山更難合情理。《諸葛亮集·將苑·南蠻》:“南蠻多種,性不能教……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6]328雖有認為此非孔明所作而為后人偽作,然時人于當地環境及用兵之術之評判為客觀,亦可為一旁證。
(三)同類遺址遺跡比較
方山諸葛營在地形條件、遺址結構、遺跡類型等方面同營盤山遺址大同小異,現存有三段城墻、兩處烽火臺、營盤、指揮所,④各處遺跡面貌與營盤山亦基本相同。當地流傳大量關于諸葛南征時駐軍、戰斗于此的故事和傳說,《大姚縣志·古跡志》:“在方山麓馬鞍山上有土城基,舊指為武侯營壘。又苴跛江坡頭亦有廢壘,指為諸葛營。又江巖絕陡有石壁,上下俱數十丈,中間人不能到處有嵌碑形,傳為武侯陣圖。”[7]331又有年代較近時事敘述,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阿文成公桂為將軍,由金川移師征緬甸駐此,令軍士掘廢壘基,得銅鼓二。”[8]331阿文成公桂即清名將阿桂,時為四川總督,而于方山得銅鼓之說由清始至今仍有,20世紀50年代也曾出土一銅鼓,民眾稱“諸葛鼓”,然這些銅鼓現已不存,事跡、年代均不可考。[9]167-169據當地文物部門介紹,此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方山諸葛營開展過調查和試掘,未發現三國時期遺物遺跡,只發現有清代前期遺物,因而定其時代為清初。⑤地方的旅游開放則利用了當地三國文化故事和傳說,以諸葛營命名。
米易縣普威鎮保留有當地彝族土司吉家的衙門遺址。院落外有碉樓,現存三面墻,下為石墻,高2-3米;上有土墻,高2米左右。院前有演武場,為土司官兵操練場所,內有大堂、廂房、衛隊駐地、倉庫和景觀,院外有院墻。其中碉樓、演武場之設置和面貌特點同營盤山石城墻哨崗、營盤、烽火臺較為相似。
論營盤山古軍營面貌類似土司遺址非此一例,貴州遵義海龍囤遺址,是明代播州楊氏土司的城堡。發現有關隘及門址13處,城垣總長近5300米,主要為石砌。其中第一期城垣現存墻體寬0.5-11.9米、高0.1-6米,中有一段土埂,殘存最高處近3米;第二期城垣中“土城”城垣寬0.5-2.3米、殘高0.1-2.6米。第二期城垣始建年代大致在明萬歷年間,第一期在宋末元初。[10]另有“新王宮”,發現有環“宮”城墻,墻體由土、石混筑,長504米、寬1.9-2.4米,局部地段高出地面0.5-1.5米,年代為明末崇禎至南明隆武年間。[11]上述城墻、宮墻的發現,其規模規制同營盤山遺址石城墻、土城墻均有相似。另海龍囤處地勢極端之處,四面絕壁,下山僅有一石道,過數關隘;營盤山地形雖非至險,亦與其有相似之處。
(四)文獻研究
土司制度始于元,盛行于明至清初,后逐漸式微,一直延續至建國后。明中期后推行改土歸流,配合有明一朝一貫實行的軍屯、民屯政策,或以所改土司之地屯田,或改當地土司為地方官。總體上講,本區土司制度自實行至消亡,過程較為平穩,土司與中央政府無較大沖突,土司制、屯田制二制協調并行。


至明末清初,本區內尤其是金沙江以南一帶土司分治。《大姚縣志·地里志下》:“論曰苴卻十六里,在前明中葉尚屬夷境……自萬歷元年蕩平以后,土司得而鉗制之。”[17]523-524這種局面號稱“苴卻十馬”,“馬”指土司領地。然按地方志,苴卻一帶實有十一馬或十二馬,《大姚縣志·地里志下》:“按苴卻十一馬地方,自古為荒服,每年納馬,故地以馬名。”[18]491(《雜異志》中言:“苴卻十二馬地方……故地以馬名。”[19]550)至康熙末雍正初改土歸流后,“十一馬”改為一鄉十一里。這些大小土司“各轄數村或數十村不等,皆謂之馬腳莊,明初始定,地畝錢糧歸縣征解。”[20]491然實際上這些土司各筑其城,圈其地,掌管財務,自有衙署。至清初,地方財政上不通于朝,下嚴苛于民,才讓朝廷下決心大規模改土歸流。現存土司衙署如前文述米易吉家土司,此外還有姚安高氏土司(姚安軍民總管府)等。
綜上所述,在對營盤山古軍營遺址整體結構的分析基礎上,以方山諸葛營年代為參考,結合同類遺址遺跡對比和相關文獻記載,可以初步推定營盤山遺址為明清時期遺存,明中期至清初可能性較大,當地其他各營盤亦同,均為土司制、屯田制二制并行的產物。
三、“打箭巖”類遺存
“打箭巖”類遺存以四川巖子、白巖子、尖山巖子、觀音巖、張家巖子、蒿枝灣打箭巖為代表,這些巖石均被當地人稱為“打箭巖”,其遺跡現象極為相似。有學者實地調查了上述幾處遺跡,并記:“發現了‘箭’及陰刻圓環標志,一般都是人工鑿孔,孔的直徑為10厘米,深約30厘米,還有一些利用巖壁裂縫插箭的孔洞。箭的原料為當地易采的半實心黃竹。”[21]72
關于諸葛亮及其射箭的傳說,以四川巖子為例,觀察即可知,以巖石高度、“箭”所處位置和距地面道路距離,言諸葛亮射箭于石上絕無可信,定屬傳說。

川西南—滇北地區又有所不同,這里幾未發現崖墓和懸棺,以各處打箭巖現存情況看,更未見有開鑿巖壁以成墓室或置棺洞穴的傾向。然細考可知,本地民族仍有天神崇拜和崖葬之俗,唯形式略有差異而已。

柏興府屬羅羅斯宣慰司,治所鹽源,鹽邊亦屬其轄地。但納西族各部落在元時并未統一,至元末明初,通安州(今麗江)的貴族勢力才逐漸兼并了各部落,并得中央政府冊封。[30]納西族有祭天傳統和崖葬風俗,已有研究考證,認為“摩沙”“麼些”的本義為祭天人,引申義為天之子民,并論祭天及其產生的文化貫穿了整個納西族的歷史發展過程,至今仍有保留。[31]《云南志略》:“末些蠻,在大理北,與吐蕃接界,臨金沙江……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日登山祭天,極嚴潔。”[32]93并論及葬俗,云“人死,則用竹簀舁至山下,無棺槨,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33]94其實火葬只是其亡人歸葬的第一步,火葬后則取其一骨,置于山崖巖石之孔洞或縫隙中。《滇小記·柙骨》:“麗江,于外夷中傳獨久且盛……乃觀其死后喪葬之故俗……舁棺置于其中,舉火盡焚之成灰,然后遣人馳健馬過燼中,于馬上俯身拾一骨……須可置小柙中,以便塞于山巖石罅之中,不擇地,不選年,且所柙藏者,但就一物寄意。”[34]125亦有將骨直接掛于懸崖上之例,《寧遠府志·九夷考》:“麼些,其人……死葬不用棺槨,富者以綾絹,貧者以布纏裹,用竹笆舁去。殺豬帶毛壓扁,名曰豬膘,同尸燒之。取其頭顱及手足骨,掛于懸崖之上。”[35]122清寧遠府治所西昌,鹽源、鹽邊均為其所轄。能夠看出,這種插桿掛肢的葬法屬于二次葬,是火葬后的進一步工作,也可視為火葬的延伸。
綜上所述,打箭巖所存遺跡可能同當地民族葬俗有一定關系,是其特殊葬俗形式的表現。
四、類型和特點
總的來講,三國文化遺存可分為兩個大類,即歷史類和附會類。歷史類遺存最突出的特性即該遺存年代必須為三國時期或可推定為三國時期,包括兩個小類:1.三國時期的遺存;2.有充分、可信文獻記載相證的三國時期遺存。附會類遺存共性在于三國文化因素以某種方式附會在特定遺存之上,包括四個小類(序號接歷史類遺存所分小類):3.帶有濃厚三國文化因素的歷史時期遺存;4.由故事、傳說流傳并附會的遺存(地點);5.近現代以來改建、遷建、重建的遺存;6.非遺類遺存。
注釋:
①9-13號點位資料來源于唐世貴、唐曉梅:《〈山海經〉與西羌遷徙——摩梭女兒國新探》,《西羌文化》,總第20期;其他點位資料均為成都武侯祠博物館、攀枝花市文物局聯合調查隊調查所得。
②“七大連營”另一說包括營盤山古軍營、萬寶營、保安營、巖神山營、寶興營、方山諸葛營和長營(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區中壩鄉,現無遺跡)。
③遺跡均沿用當地文物部門命名,與本文遺址年代、性質推斷無關。
④遺跡均沿用當地文物部門命名。
⑤內容由云南省永仁縣文管所所長唐福秀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