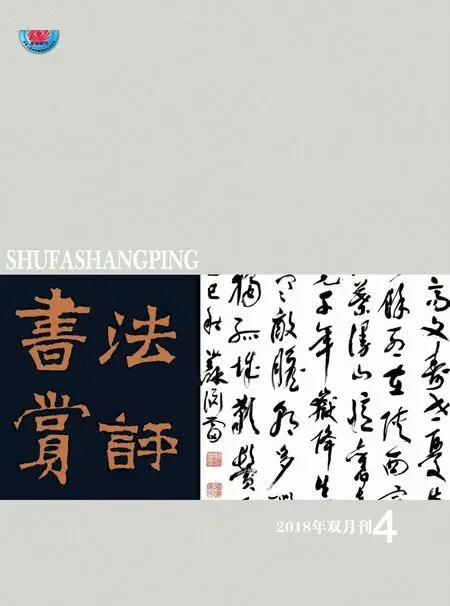漲墨的根源以及對于書法本體語言的影響
董其昌在其 《畫禪室隨筆》中說:“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茖 (nong音農(nóng))肥,肥則大惡道矣。”用現(xiàn)代漢語說是:“用墨一定要滋潤,不要因為缺少水分而枯燥。更要忌諱墨色又深又濃,用墨肥胖無力,用墨肥胖無力是不正之道!”
在古代書法世界里,宣紙與墨錠之間的媒介是水。當(dāng)水融合墨,與紙相呼應(yīng),出現(xiàn) “濃、淡、干、濕、焦”的層次時,墨法成為一種重要的書法藝術(shù)造型語言。它在中國畫黑白世界里的重要地位是無法取代的,但在書法領(lǐng)域里,與筆法、字法、章法相比較,墨法在書法造型的語言上的獨立性顯然不如前三者,客觀地講,只有在前三者的基礎(chǔ)上,墨法才能彰顯其造型的意義。與此相反,有人把 “墨法”作為董其昌的重要貢獻之一,認為這是董其昌對書法理論領(lǐng)域的擴展。對于書法理論來講,這無可厚非,因為理論需要將整個體系分割為幾個要件,分別加以研究。但對于書寫來講可能是個誤區(qū),因為一筆下去,筆法、字法、章法俱在,難以分割,無法單獨實現(xiàn)。近年來,有人專用淡墨書寫,但在筆法、字法皆不精的前提下,所謂的 “墨法”無法單獨支撐起整件作品。
那么,墨法是否可有可無,對書法本體語言影響是什么呢?
首先,墨法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書法語言,是由于它在書法傳達與表現(xiàn)的領(lǐng)域里無可替代。“中國人對語言持有一種觀念:‘言不盡意’。人們認為語言無法詳盡、準(zhǔn)確地表述與事物接觸時的所有感覺,因此致力于在語言之外發(fā)展幫助表達的符號系統(tǒng)。”[1]墨法正是幫助表達的符號系統(tǒng)。沒有淡墨的參與,董其昌難以形成秀潤淡雅的書法風(fēng)格;沒有漲墨的出現(xiàn),王鐸難以縱橫開合,抒發(fā)心中塊壘。但是,墨法成為一種書法語言本身也需要時間,需要過程。其實,書家對于墨法的關(guān)注很早就開始了。漢末書家已經(jīng)利用焦墨枯筆,即在墨汁不足的情況下繼續(xù)行筆而形成 “飛白”,創(chuàng)造了特殊的書體——飛白體。蕭子良說“飛白”始于蔡邕。相傳東漢靈帝時,修飾鴻都門,工匠以刷白粉之帚寫字,蔡邕因之受到啟迪,乃作 “飛白書”,這種書體多見于漢魏宮闕題字。在宋代姜夔 《續(xù)書譜》里有一章論墨:“凡作楷書,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這是對墨法方法論比較詳實的記載。清周星蓮在 《臨池管見》中說:“用墨之法,濃欲其活,淡欲其華……不善用墨者,濃則易枯,淡則近薄,不數(shù)年已淹淹無生氣矣。”按照董其昌的想法,墨法“肥則大惡道矣”,肥而溢出的 “漲墨”更是野狐禪與邪魔外道。墨法與紙法一樣,是隨著書學(xué)的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比如 “漲墨”是指墨汁浸潤到筆畫以外,也稱 “湮墨”。這種 “漲墨”直到明代都被認為是書法的禁忌,到了清代才有書法家打破這一清規(guī),如何紹基、張裕釗。但即便在這個時代,與何紹基同時的朱和羹也在反對 “漲墨”,他在《臨池心解》中說:“墨不旁出為書家上乘……有余墨旁出,字之累也。”
其次,水墨不分與水墨相分。嚴格來講,墨離不開水,無水難以談墨。今人與古人用墨的最大差別是古人研磨,即在硯臺中倒入水,然后用固體的墨塊進行研磨,形成水墨,以供書寫。這也常常是古代文人常常書童隨行,其主要的任務(wù)是 “抻紙研磨”。然而,現(xiàn)代人書寫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用墨汁兌水,少了古人“研磨”的程序。其實,紙、墨、硯是三位一體的,因為無硯難以 “發(fā)墨”,墨無紙難以盡現(xiàn)其精髓。換句話說,水是媒介,缺乏媒介,紙、墨、硯難以結(jié)合到一起。發(fā)的本義是開弓射箭,引申為開啟。硯臺以端硯和歙硯為好,因為這些石頭的石質(zhì)油滑細膩,不吸水,發(fā)墨效果好。盡管現(xiàn)代的墨汁仍然少不了水,但缺少了研磨就缺少了對媒介的把握與控制,缺少了水墨相合的物理變化。當(dāng)代人使用墨汁書寫所省略的研磨過程對于墨法是重要的,因為研磨的作用不僅在于水墨相合,還在于去除墨的滯性,無論墨色如何黝黑都能行走自如。還有一點是研磨隨心,即研磨的過程也是靜心的過程,也是心與水、與墨、與硯相融合的過程,此中奧妙需要書家自己體會。簡單來講,研墨的過程就是使水墨不分的過程。
講清水墨相分的道理需要從墨的由來開始。墨由墨煙而來,墨煙的原料包括桐油、菜油、豆油、豬油和松木;其中以松木占十分之九,其余占十分之一。燒松取墨煙,輔以動物膠等材料加工而成。好墨的標(biāo)準(zhǔn)是黑而不滯,以水研磨易化為上。研好的墨時間長了會脫膠,即墨煙與動物膠脫離,故古人不喜歡使用隔夜墨。因為水墨脫離,成為宿墨。運用這樣的墨書寫,由于墨膠沉淀,而水分活躍,故有中鋒線條兩側(cè)漲出的效果,產(chǎn)生一種特殊的立體效果,后人將這種效果發(fā)展成為一種用墨方法,稱 “漲墨”。只是使用這種方法完成的作品在裝裱時需要注意,因為水性活躍,有可能造成 “跑墨”現(xiàn)象。
其三,運用漲墨的書家并不多,而理論上把這類嘗試說明白的就更少。無論濃、淡、干、濕、焦怎樣變化,它都與水分有關(guān)。書法有筋骨血肉之說,其中血是指水,肉是指墨,墨無水則成干柴,水太多則臃腫無力。漲墨與墨豬最大的區(qū)別是漲墨的筆法清晰而不臃腫,勁利內(nèi)涵而不無力。從筆法上來講,漲墨只是運用膠水分離的特點在墨法上別開生面;而墨豬是運用水墨在紙面的擴張而掩蓋筆法的不到位。由于筆法不到位而水墨擴散,必然臃腫無力。直白地講,這是大力士與虛胖子的區(qū)別。

唐,武則天, 《升仙太子之碑》碑額選字。字體采用“飛白”,俗稱 “筆花”的手法,是采用墨法和字法變化進行書寫的書法。

宋,蘇軾, 《李白上清寶鼎詩二首卷》局部。在“用墨須使有潤”的方面,蘇軾是一個典范。在字里行間的從容與優(yōu)雅之間,墨氣淋漓而不肥厚,氣息潤澤而不乏力。

明,董其昌, 《書畫合冊》。墨法上無論濃、淡、干、濕,筆筆到位,整體來看,自有一種爽朗的精神氣。

清,何紹基,對聯(lián)。加入北碑內(nèi)容的何紹基書法對于董其昌為代表的帖學(xué)傳統(tǒng)是一種突破。
從藝術(shù)發(fā)展的角度來看,漲墨運用水墨分離的特點進行墨法拓展是一件有意義的探索。從藝術(shù)欣賞的角度來講,濃、淡、干、濕、焦都屬于感性欣賞的范疇,超出傳統(tǒng)墨法的漲墨反應(yīng)了水墨不受書寫者的控制而溢出的效果,這與董其昌理性派 “意在筆先,字居心后”的主張相違背。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往往是在古人認為無路可走的地方,后人加以開拓進取,另創(chuàng)天地。何紹基在運用漲墨的時候,在內(nèi)心里也是有意識的控制著,只是控制的內(nèi)容與傳統(tǒng)不一樣,而是把似乎超出控制的 “漲墨”控制到自己的書法語言體系之內(nèi)。確切地講,他在執(zhí)筆上選擇 “回腕高懸”的特別方法,運起筆來很不自然而且吃力,他自己也說 “通身力到,方能成字,行不及半,汗浹衣襦”。 (跋 《張黑女墓志》)所以,他故意使理性不能充分控制毛筆運行,進而達到書法稚拙而活潑的效果。試問,這是真的是失去控制了嗎?顯然不是,漲墨顯然被整合為理性的書法語言,甚至何紹基選擇 “回腕高懸”這種不自然而且吃力的方法都是理性的結(jié)果。
那么,漲墨對于書法本體語言的影響是什么呢?
首先,漲墨對于筆法本身沒有新突破,但對筆法應(yīng)用的情緒產(chǎn)生了影響。也就是說,漲墨并沒有影響毛筆的運行軌跡,但在筆墨交融的直覺層面上豐富了水墨傾注而下的快感,對于書寫者來講,這是一個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情感體驗。從技術(shù)上來講,運筆動作要在水墨傾注而下的時間內(nèi)完成,這既是一種挑戰(zhàn),也是一種自我認知,在水墨俱下感性世界與完成運筆軌跡的理性世界交融的狀態(tài)里成就一種書寫者人格上的自我滿足。這種滿足既有對世界難以言表的認知,又有自我實現(xiàn)的價值。具體來講,漲墨邊緣千變?nèi)f化盡顯于理性世界之外,傾注而下的胸中塊壘、萬馬千軍隱于墨色之中,這種出于規(guī)矩又超越于規(guī)矩的漲墨,與書寫者的內(nèi)心構(gòu)成了一種超越束縛、一吐為快的心理同構(gòu)。即人類渴望感性對于理性的超越,又渴望在理性中找到自我的存在。

日本江戶時代后期高僧,良寬, 《屏風(fēng)書》。良寬將漲墨法作為重要的造型語言,成就境外之象。這種墨法語言直到明代都被認為是禁忌。

清,王鐸,行書立軸局部。漲墨為清代書壇帶來了新的面貌,這源于對碑學(xué)書法的深入。
其次,漲墨改變了傳統(tǒng)的以單字為核心的微觀結(jié)字法,代之多字組合關(guān)系為核心的宏觀結(jié)字法。從現(xiàn)象上來講,漲墨為字法中提供了一種邊緣模糊的筆畫形態(tài)。這種形態(tài)與清晰的點畫邊緣相比具有一種來自點畫內(nèi)部的運動擴張感,這與碑學(xué)書法強調(diào)筆道自身的內(nèi)涵是分不開的。從字法規(guī)則來講,這是對既有規(guī)則的突破,這種突破導(dǎo)致了以單字為核心考量點畫結(jié)體的方法轉(zhuǎn)變?yōu)橐远嘧株P(guān)系為核心的單字結(jié)體法。在這種新的方法里,隨著視域的廣度增加,單字的結(jié)體等同于原有方法里對于單個點畫的考量。這種新型的結(jié)字觀從傳統(tǒng)的、主要以單個漢字的完美考量過渡到多個漢字聯(lián)動的、對比相生的結(jié)字觀。
其三,漲墨在章法上成為整件作品的視覺聚焦點,這與傳統(tǒng)書法平面化的視覺相比形成了一種突破。確切來講,漲墨為章法增添了視覺的音樂感和節(jié)奏感。這種節(jié)奏感以漲墨形成的墨塊為核心,以周圍點畫為輔向四周蕩漾開去。這與唐楷從一而終的節(jié)奏感截然不同。具體來講,漲墨在一幅作品中可以多次出現(xiàn),但每一次的形態(tài)隨著字形不同,用墨量不同以及紙的承載力不同而變化各異。這形成了類似于交響樂的多聲部合唱和多聲部輪唱,整個書法作品的視覺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得以大大加強。書法從這時起更加明確了藝術(shù)的自覺。
基于以上提到的漲墨對于書法本體語言的影響,可以清晰地看到漲墨的出現(xiàn)影響了書法創(chuàng)作的意圖,即以書寫記錄為主的傳統(tǒng)型書寫向著以表現(xiàn)抒發(fā)為主的藝術(shù)型書法轉(zhuǎn)變。在這個過程里,點畫已經(jīng)由主要為識別的功能進化到漲墨為藝術(shù)的視覺語言,換句話講,漲墨標(biāo)志著書法功能從實用轉(zhuǎn)向了藝術(shù)。客觀來講,這并不是一個偉大的時刻,因為歷史都是如此這般一步一步推進的,只是這一點上發(fā)生了質(zhì)變而已。深入來講,書法史的面貌往往是由于不同的觀念導(dǎo)致不同觀察視角,比如清代阮元與包世臣從筆法的角度重新追溯歷史,提出了碑學(xué)書法方為正宗的觀念。由不同的觀念導(dǎo)致不同的理解,比如,碑學(xué)書法認為北碑是書法正途,帖學(xué)書法只是以訛傳訛的等外之物。由不同的理解導(dǎo)致不同的架構(gòu),比如以轉(zhuǎn)折為主的帖學(xué)框架讓位于以筆道為主的碑學(xué)框架。而不同的架構(gòu)導(dǎo)致不同的面貌,比如董其昌書法與何紹基書法的面貌截然不同。
然而,無論操持著什么樣的觀念,運用什么樣的筆法,創(chuàng)造出多么與眾不同的面貌,書法藝術(shù)核心的內(nèi)容仍然是精神的高度。也就是說,藝術(shù)的自覺和藝術(shù)語言的豐富并不意味著藝術(shù)內(nèi)涵隨之遞增,相反,依附于書寫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由于擺脫了功利目的的直接干擾而顯得更加具有精神的高度與力度。

唐,柳公權(quán), 《玄秘塔》局部。漲墨只是一種方法的創(chuàng)造,盡管它意味著書法作為藝術(shù)的自覺,但一種方法的創(chuàng)造并不能代表藝術(shù)高度的提高。在唐代柳公權(quán) 《玄秘塔》面前,王鐸顯得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