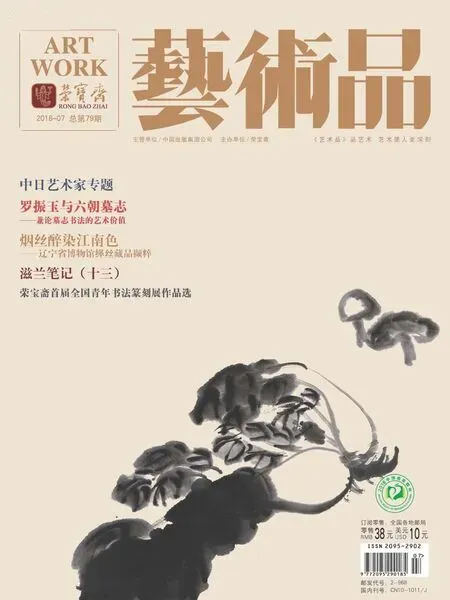吉金夜話(七)·大盂鼎
文/叢文俊
大盂鼎,西周康王時器,清季出土于陜西郿縣。歷宋金鑒、左宗棠、潘祖蔭等弆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潘氏后人捐贈上海博物館,復轉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銘文291字,記敘康王二十三年在宗周訓誥盂并有賞賜之事。字有泐損,然氣象宏大,精神不減,被清賢譽為西周“四大重器”之首,學者評其書為“殷派”風格的代表作。學此書者頗多,卻罕有成就,亦怪事也。
西周康王之世,金文中的“篆引”曲線初露端倪,為數亦稀,而大宗是自殷商金文承襲下來的風格,應該是武王克商之后挾掠商人百工而使其金文書法得以延續。當然,這種承襲要面臨商、周兩種不同文化和藝術精神的碰撞與融合,所展示的精粗與程度,則往往會因人而異。如能在這種大的文化藝術背景下考察大盂鼎的美感與風格,將對臨帖大有裨益。

大盂鼎 拓片

臨《大盂鼎》 局部

臨《大盂鼎》 局部


臨《大盂鼎》 68cm×68cm 紙本水墨 2017年



臨《大盂鼎》 局部

臨《大盂鼎》 局部

臨《大盂鼎》 局部
首先,此器為西周早期作品,文字的象形程度較高,與后來日益趨近正體規范的大篆有明顯的差異。從字形結構,到偏旁樣式、數量、位置,以及圖案化程度,都是涇渭分明。如以書法例之,則此器的古拙一望即知。其中有些字的肥筆,直接承自商金文的書制習慣;一些方筆直畫,也與同時期周人題銘崇尚曲線的風氣有別。如果視其為商金文風格的嫡傳,大體似之。昔日學者評此器曰“方筆之最”、視之為“殷派”風格嗣繼者,雖有表面化之嫌,但以書法為言,還是很有道理的。其次,商金文崇尚修飾、甚至夸張,考其用意,既有修飾字范的工藝需求,也是出自一種淵源久遠的古老審美習慣,包含了比較濃郁的原始宗教觀念和情結在內。大盂鼎完整地保留了這一特色,與同時的庚嬴卣相比,后者雖然也有些修飾痕跡,卻功在曲線,二者意趣迥異,在方、圓的背后,還應該有更深層次的文化選擇因素在發揮作用。此后方筆傳承日漸式微,而圓筆則蒸蒸日上成為主流、成為大篆的基本形質,正是商、周這種文化興衰更替的真實寫照。第三,大盂鼎的點畫線條起筆、收筆皆尖,有些還帶有頭粗尾細的變化,以之與商陶文中的墨書、甲骨文中的朱書相較,即不難發現此器殘存的手寫體風格痕跡,只是在書制金文的過程中化曲為直、別裁偽體而不易被人覺察罷了。實際上,從商金文到大盂鼎最典型的肥筆“捺刀”,也是出自手寫體,在刻意地修飾夸張之后,成為一種標志性的風格樣式。此后如晉、楚等國鳥蟲書凡線條做肥瘦變化的作品,也都是以手寫體為基礎,加以修飾改作而成。明乎此,即可以很好地避免臨帖時需要反復描畫的弊端。換言之,臨大盂鼎,不可畫字,也不能用中晚期成熟的大篆筆法,要使商、周金文兼收并蓄,正體與手寫體交互為用,方圓共出,乃可窺其門徑。
筆者多見三代秦漢金文實物,仔細研味其鑄、刻痕跡與制作工藝,考察銹蝕泐損之狀,比照拓本優劣得失,對臨習其書頗有助益。即以拓本為言,無論線條鈍銳、纖壯、曲直,都能體現出金石文字所固有的堅質骨感,是超越于軟毫墨跡之上的書制工藝及銹蝕泐損的附加美,這也正是臨帖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問題是,軟毫如何能達成這種效果呢?在筆者看來,金石拓本能提供墨跡所不具備的美感,也會使人易受表象誤導而喪失對墨跡價值的準確判斷,昔賢曾經倚重的抖筆斷畫擬金石氣之法即緣出于此。依照常理,用器之時造成的磨損和千年以后的除銹,很容易使字畫變細、殘壞、甚至局部消失,也會有因殘壞而局部變肥的情況,如逨盤。所以,讀帖時要對種種拓本現象做出正確的解讀,尋繹出器物初成的字畫狀態,以便明晰應該采用的筆勢,而不是依樣葫蘆,掉入作字、畫字、描字的陷阱。臨大盂鼎,尤宜如此。
依筆者臨此器的經驗和感悟,關鍵在于怎樣去認知作品的美感。既得,則貯之于心;能以心馭筆,則道味斯在。古人所謂“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者,誠不我欺也。概括言之,大體可如下所言。
重下筆,穩運行,慎出鋒,力含收。澀在骨,利資神;樸欲 拙,巧涉華,枯觀勁,潤生色;老扶壯,質勝文。心有物,意成象,虛生實,無藏有。字外功,君知否。
管見所及,意在面對拓本以推想筆勢,上復于本,使用筆不為表象所困,而終歸于書寫。此則為臨習大盂鼎書法尤難于他器之所在,如能做到“思過半”,則成就可期也。
(本文作者為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