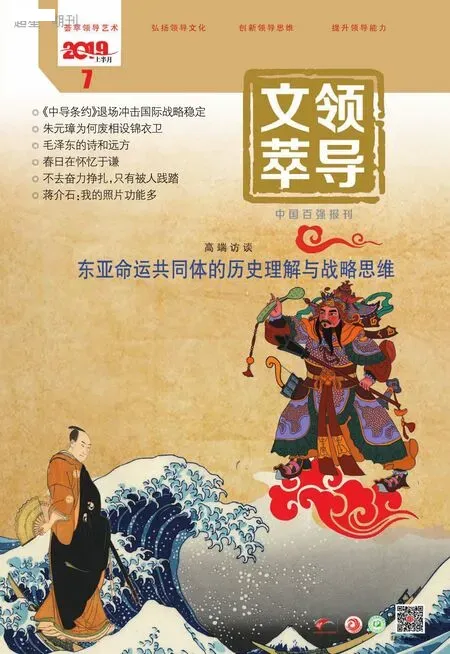朕亦一書生
卜鍵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當朝天子猝然崩逝,皇四子弘歷繼位。剛過二十四歲生日的寶親王,由每日在上書房用功的書生,一變而君臨天下,各項新政隨之頒布:驅逐宮內僧道,釋放在監皇叔,求賢求言,厘正文體……由先前的嚴苛峻急變為寬緩,贏得朝野稱頌。而他那份關于“書生”的長篇訓諭,更使天下讀書人聞之振奮。
一、“書氣二字,尤可寶貴”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乾隆帝連頒數道諭旨,其一專為疵議書生的官場積習而發,《清高宗實錄》卷五:
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于書……人不知書,則偏陂以宅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郡,則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
弘歷旁征博引,以商代賢相傅說、周成王的語錄,闡述讀書明理對于處事行政的意義,申說官員不讀書的害處,提倡州縣官以“書生”自勵,希望地方官員能知書愛民,造福一方。針對那些譏諷書生迂腐、嘲笑書呆子氣的觀念,新帝還以己身為例,痛加駁斥:
若以書生為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疏庸者為書生,以相詬病,則未知此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
實為堂皇正大之論!古往今來,世上都不乏迂拘之人,不乏陳腐之書,卻不能將之說成讀書所致,更不宜視為讀書人的通病。弘歷嚴正指出,“迂謬疏庸”之官正在于不知讀書,或不解書義,豈可歸咎于前人經典!
說到書氣,宋陳著有“便覺酒香隨笑動,共將書氣拓塵開”句,詞義甚美。后多指書呆酸腐氣,成為貶毀書生的常見俗詞,戲曲小說更加以形象化,至今不絕。乾隆帝對此斥之尤力:
至于“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沉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即為粗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末除者為病乎?
此處化用孟子學說。《孟子·公孫丑下》論浩然之氣,有“直養而無害”“配義與道”“集義所生”,皆為胸中正氣的修煉涵養之道。弘歷復加以引申,指出浩然之氣正可由書氣滋潤積聚、吸納生發而成,大哉此論!
這是乾隆帝早期發布的一份重要諭旨,興會淋漓,惜乎久被忽視。頒發此諭時弘歷剛登基一個多月,還不太熟悉朝政運作和官場規則,胸中激蕩的多屬書生意氣。他見督撫折奏中不斷出現貶低讀書人的說法,也意識到其背后那股保守愚昧力量,即痛加批駁。一番話氣象正大,理直氣壯。此諭必也出自乾隆帝之手,非一般御用文人所能撰作,亦非他們所敢論議。
二、燒鍋事件
對書生與書氣大加肯定,是因為青年弘歷頭腦簡單嗎?怕也未必。與此諭同日,乾隆帝發布的第一道諭旨是“命厘正文體,毋得避忌”,主要應是針對朝中文官,要求盡快改變浮靡趨奉與說假話套話的文風。諭旨說文運與政治相通,應“修辭立誠,言期有物”“理為布帛菽粟之理,文為布帛菽粟之文”“勿尚浮靡,勿取姿媚”,尤其要實話實說,掃除避忌之習。對于彌漫朝廷的行文和奏章通病,新天子早就看在眼里。此后不久,發生了一個爭持數年的燒鍋事件,也使之對官場書生有了更深的認知。
燒鍋,此處指釀酒的作坊。乾隆改元后畿輔連年干旱,糧食嚴重匱乏,京師卻有人囤積官米,再運往通州造酒。朝廷聞知后亟命禁止,接著便有旨查禁燒鍋。弘歷起初也有些猶豫,怕影響百姓生計,得知壟斷造酒的多為富民,“串通胥役,敢于觸禁肆行,并非貧民無力者之生業”,即下決心在北方五省永行嚴禁。
皇上自以為深思熟慮的利民之舉,未想到刑部尚書孫嘉淦上疏提出異議,提出燒鍋之禁對執業者生計有害,也無益于儲存糧食,“止宜于歉歲,而不宜于豐年”。乾隆帝有些猶豫,命王大臣會同九卿詳議,表示禁酒本為節省民食起見,若是嚴禁燒鍋不但不能有益民生,反而有害,則可以收回旨意。皇上采取寬舒謙退的姿態,可并未出現所期待的熱烈討論,六部九卿大多置身事外,緘口不言。弘歷極為失望。
乾隆三年十二月,北方的災情仍未見好轉,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方苞奏請禁止煙酒。這是他第二次提出此議,反駁孫嘉淦關于禁酒病民的說法,并由制酒擴大到種煙,認為都是造成糧荒的罪魁,應在全國嚴禁。內閣大學士奉旨集議,大多贊同方苞之議。
孫嘉淦已任直隸總督,對民情的了解更為深入,再次上疏反駁。孫嘉淦指出釀酒種煙皆百姓謀生之道,將他們作為罪人,并非“致吾君于堯舜”的長策。查禁也帶來官吏貪腐與社會動蕩,各級官衙都存有抄來之酒及變價之銀,吏役兵丁熱衷于查拿,百姓苦不堪言,被迫反抗,“弱者失業,強者犯令,十百成群,肩挑負背。鹽梟未靖,酒梟又起”。孫嘉淦坦言禁酒令并未讓百姓喜悅感激,帶來的只是混亂和災難,曰:
夫天下事為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難。從前禁酒禁曲之議,不惟大學士九卿等俱屬紙上空談,即臣言宜于歉歲,不宜于豐年,猶是書生之謬論。……饑饉之余,民無固志,失業既眾, 何事不為?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于豐年。……今大學士及方苞等所議,皆系空言不適于事。
一身浩然之氣的孫嘉淦是在為民請命,疏中的矛頭卻指向“書生”,首先指向自己。他以自我反省來批駁方苞與閣部之論,雖沒明說那里是一幫書生,然一句“空言不適于事”,也就表達無余。
這件奏疏同樣給乾隆帝帶來震動,認為“于國體甚有關系”,也使他對“書生”二字細加酌量。就在這之后,諭旨中不斷出現“伊原系書生”“拘于書生之見”“此皆書生不識事機之語”“書生拘墟之見”“書生習氣”“懦弱書生”“文怯漢人”的說法,在于證明弘歷出現了認識和觀念的改變。當初的贊譽之辭忽然間不見了。
三 、“百無一用是書生”
與弘歷對書生的復雜心態大致相合,乾隆朝的文化與學術,也呈現著錯落纏結的狀態:一方面是禁言禁書,苛細吹求,不斷制造大大小小的文字獄;一方面是學術興盛,彬彬濟濟,官修《明史》與《四庫全書》等先后行世。正因為皇上對古代典籍浸潤較深,能讀懂那些弦外之音,使書生輩無論在朝在野都變得小心謹畏。大家不約而同地先降低嗓門,再集體緘默。當緘默也可能被指為腹誹或包藏禍心,大量精美的頌圣之章便應運而生,嗡嗡營營,競為高亢。
于是,“書生”的光暈漸漸消退,不再需要那些目不識丁的滿蒙大臣(乾隆年間其實越來越少了)挑剔指責,頗多漢臣已自慚形穢。翻看那些大致雷同的謝恩折,觸目皆是“臣材同樗植、質陋蓬心”等自貶之詞,應不是出于真心,卻寫得極為真誠,演為一個基本話語模式。恃才狂傲、唇天齒地本是文人常態,所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是也,此際雖較為少見,卻也不會絕跡。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大概是“讀書無用論”的一種極端表述。百無一用之說,有點兒調侃,有點兒自省與自嘲,不宜當真,又絕非作假,應于言外求之。
揀讀清朝檔案史料,斯時也堪稱重視人才,正科恩科,大挑拔貢,加上皇帝出巡途中的召試等等,書生的出路和機遇不可謂不多,可仍有飽學之士被隔在體制之外。其間有淡泊遺世、專心著述者,有性情偏執、憤世嫉俗者,更多的則在求仕長途上左沖右突,終不得其門而入。
四 、“畢竟是書生”
這句話是周一良先生回憶錄的書名,自責、自謔與自辯皆在其中,寫照一代學人的命運沉浮,值得回思品味。作為一個分屬不同社會階層的龐雜群體,對書生的準確定義甚難,更難的是做出整體評價。
那時的弘歷頗以書生自詡,后來似乎未見說過這樣的話。但其一生都酷愛讀書,每日晨起先要讀書,還寫了許多讀史和題詠“某某書屋”的詩;他為圓明園的上書房題寫“斯文在茲”,寄寓著對皇子成為書生的期望。清廷重視宗室覺羅與滿人教育,天潢貴胄中可稱書生者甚多。
弘歷晚年身邊信用的大臣仍以書生居多,如王杰、董誥,如劉墉、紀昀、彭元瑞。
龔自珍注意到乾隆帝“朕亦一書生”之說,贊美其“炳六籍,訓萬祀”,進而將書生與俗吏對舉,批駁官員懼怕擔“書生”之名的怪現象:
天下事舍書生無所屬,真書生又寡有,一于是,而懼人之訾己而諱之耶?且如君者……嚙指而自誓不為書生,以喙自衛,嘵嘵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為也哉?
可證當龔自珍之世,“書生”已是一種官場差評,蒙其譏者,往往要力加辯駁。而龔自珍所呼喚的真書生,至今讀來仍令人感慕警勉,切切自勵。
(摘自《讀書》)